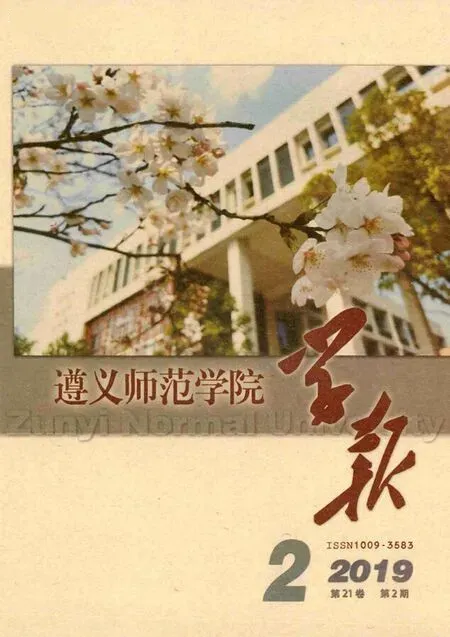評《政治文化重建視閾下的南宋初期詔獄研究》
王友富
(遵義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貴州遵義563006)
南宋立國之初,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不安,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多事之秋。宋高宗一朝,詔獄泛濫,史學家及民間公眾,歷來對此多有關注,但仍存在著不足。正如董春林博士所著《政治文化重建視閾下的南宋初期詔獄研究》[1]所云:“這些詔獄多被時人或后人視為冤案,……研究不約而同陷入倫理道德的俗套之中。”該論著從南宋政治文化層面來研究南宋詔獄,探討南宋初期詔獄發生的政治路徑和政治規則。全書雖然只有25.9萬字,卻對南宋初期政治文化重建語境下系列詔獄事件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探討,諸多論點可圈可點。
首先,這本論著著眼于政治文化重建視閾下詔獄案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而不是單純從道德層面品評政治人物,視角新穎。涵蓋價值理性與目的理性的合理性,在其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價值理性逐漸衰竭而目的理性不斷獲得制度化,這種政治社會學的思維或認識,投影到南宋初年的詔獄事件上,卻也折射出無限接受的光芒。該論著研究對象是南宋政治文化重建視閾下的詔獄,詔獄雖然是由皇帝掌握其判決權和宰相控制審核權的政治性獄案,但畢竟是刑事案件,同樣需要因循一定的法律條文,走過完整的法律程序,所以這篇論著首先對南宋初建的法制環境及詔獄實況作了簡要的陳述,目的在于讓讀者對南宋詔獄形成的法制環境有一個大概的認知,為后文論證詔獄發生的歷史誘因有一個前期了解。作者把詔獄案例細分為個案與群案,以便精微地分析案件形成的細節。個案方面,例如張邦昌案,諸多文獻記載中并未梳理清楚張邦昌詔獄案件的真實原因。該論著將張邦昌詔獄放在法制語境與政治環境中動態勾勒事件的進展情況,揭示其案件實為宋高宗政權謀取政治利益的需要,表面化的法律依據程序實為政治選擇的膚淺依據。另一個陷入詔獄的個案是與張邦昌有瓜葛的宋齊愈。作者認為宋齊愈被判腰斬重刑,同樣為了重塑南宋高宗政權的政治語境。皇權至上的封建統治,讓宋高宗容不得有半點染指皇權的行為,既要鞏固皇權又要籠絡人心:一方面,誰敢覬覦我的位置,就要下狠手懲治;另一方面,又要體現了“祖宗好生之德”的寬容之心以收買人心,一味懲治,并不是好的政治策略。宋高宗在嚴懲與籠絡之間左右搖擺,政治文化下的權術游戲就是這樣的微妙,在腰斬宋齊愈不久,高宗又對宋的家屬進行撫慰。法律條框在這個時候似乎成了政治的附庸,政治文化重建這樣的政治利益遮蔽掉了政治規則,卻勾畫出了政治交換的粗淺邏輯路徑。作者所論的群體詔獄,并不是個體的疊加,群體代表的是一種政治選擇,一種政治博弈。南宋初年金人南侵,顯然是南宋朝廷火燒眉毛的事情,表面來看南宋初年這些系列群體性詔獄,應該與宋高宗政權急欲與金人言和相關,和議才是最大的國是,這些獄案罪名遍及“動搖國是”“以搖國是”“交通罪臣”等說辭,也著實使立案不容置疑。但作者并未簡單認為這是宋高宗政權茍延殘喘換取偏安東南的主觀目的,而是對紹興和議的合理性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紹興初年和議之前宋廷所面臨的財政負擔主要來自于高額軍費支出。“東南之財,盡于養兵,民既困窮,國亦虛弱”。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七,紹興九年三月丁未條。何忠禮先生認為:“南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并不具備戰勝金國的絕對優勢,紹興和議簽訂之前,社會經濟衰竭。”[2]P372由此可見,軍費開支造成南宋政權面臨困境,可謂詔獄案件發生的一個條件。此外,作者并沒有受限于兩宋重文輕武的傳統意識,還指出南宋初年“將不可依”的實際情況。
其次,著眼政治目的,探討南宋初期詔獄語境下的政治行為,將法制與道德放之與政治利益博弈的視角下,意欲挖掘群體詔獄的時代意義。作者指出,南宋初期發生的眾多士大夫詔獄,除了案犯罪名及涉案原因的差異之外,都屬冤獄。這次詔獄案件一如中國歷史上其他詔獄冤案,案件類型沒有什么兩樣,多是文字獄、朋黨交通、口頭言說等。從其中的嚴刑罪名來看,常常歪曲正常的審訊程序,詔獄審訊程序也常常成為掩蓋冤案實質的借口,這些詔獄的發生似可歸因于法制制度不健全,但從證據及審判技術角度來看,南宋初期的詔獄事件卻也符合法律規范:一方面“告訐”合法化指向嚴刑罪名與有罪推定思想的融通;另一方面法理建設與眾證定罪等法制手段融于審刑之中。由此可見,這些詔獄中獨特的法制面相,著實突顯出超越法制的政治意圖,正如作者所言:“從大量紹興詔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恰恰并非單一的行政或刑律處罰,而是介乎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法律的公正與否已顯得微不足道,而法理精神卻隱喻其間。”[1]P105法理的解釋或建構多是緣自國是政策,這進一步將詔獄案件轉向了執政者的政治選擇上。除了詔獄案件逾越法制語境之外,詔獄的倫理關懷也無不折射出執政者的價值選擇。作者首先將詔獄案件面臨的傳統儒家倫理觀進行全面剖析,指出“功過混淆”與“忠良泯滅”實為品評詔獄案件的傳統倫理標準。但是,宋高宗政權南渡之后急欲重建政治文化時“收人心”及其重生王道觀,并不與這些詔獄踐踏儒家倫理沖突,因為他們最終的政治目的較為一致。正所謂:“道德評判在這個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下可能顯得蒼白無力,道德標準往往消解于執政者對政治利益的選擇之間。”[1]P59作者著眼于詔獄案件背后政治行為及政治選擇的研究,進一步拓展了傳統政治史研究的視野。
最后,切合政治過程論,嘗試勾勒皇權專政視閾下政治交換的路徑,提出全新的理論認識。鄧小南先生曾指出:“政治史研究,要注意鼎革、突變,更應該探求漸次過渡、承接遞進的脈絡;既要看到時代變遷的影響、制度之間的差異、行為選擇趨向的不同,也應該辨識其內在理路的傳承與融通。”[3]P4作者即是將南宋初期政治文化重建視為一個過程,而詔獄結束后執政者對政治規則的修正與重構恰恰是這一過程的尾聲。在本書第四章里,作者認為“紹興更化”與孝宗初年的政治重建,既是對過往政治行為的修正,也預示著規則性政治行為與非規則性政治行為循環往復的面相。南宋初期發生的“紹興更化”,“特指紹興末年宋高宗為整治秦檜專政而制造的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1]P182作者把“紹興更化”解讀為宋高宗的“政治轉向”,紹興末年制度更革與吏治整頓,顯然是政治規則重建的重要內容,但這一時期宋高宗政權先前的政治目的并沒有嘎然而止,新的政治生態直到宋孝宗朝北伐失利之后得以實現。金人在紹興末年再度南犯與宋孝宗意欲重建政治生態與政治理想的愿望不謀而合,此前詔獄雖然大多已經平反,但曾身陷詔獄的張浚卻又涉足新的政治糾葛之中,這種沉浮不定的政治人生最終讓步給了孝宗朝“內修以圖恢復”的政治路線。
縱觀此書,作者不是僅從法制角度剖析詔獄,而是從政治文化視閾來洞察歷史事件的深意,用意識形態來探討政治行為的邏輯路徑,視野開闊,立意新穎。此前日本學者寺地遵先生所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書,也是著眼于歷史過程,對南宋初期的諸多政治事件及走向進行了深入研究,本書則以詔獄事件為線索深度勾畫了南宋初期政治交換的大致圖景,可謂是對此前相關研究的補充與拓展。但此書亦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本書所論南宋初期的詔獄事件是否符合政治合理性?對詔獄事件所反映的政治交換理論的認識是否過于牽強?總體上肯定該書創新創見的同時,也期待作者或后來研究者對南宋初期的詔獄事件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嘉惠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