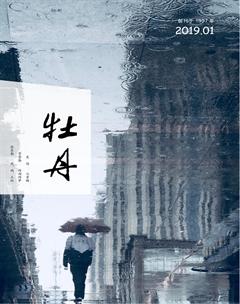談龐鐵堅(jiān)詩歌《渡口,望思想的彼岸》
李青汶 潘思羽
望思想的彼岸,可見絢麗的晚霞。/渡口空寂無人,我在岸邊徘徊。/我是一個(gè)渴望過河的渡客,/不知艄公在哪里,只知太陽何時(shí)落山。//當(dāng)落日將晚霞收進(jìn)自己的口袋,我過河又干什么呢?/如果有人擺我渡過這條其實(shí)不寬的河流(它在我們的觀念中,卻是又深又寬),/我追得上晚霞的腳步嗎?//渡船的船頭朝著彼岸,/它卻被繩索栓在河的這端。/小河兩岸已經(jīng)飄起縷縷炊煙,/誰知趕路的我還在這里望河興嘆!//
——龐鐵堅(jiān)《渡口,望思想的彼岸》
詩人龐鐵堅(jiān)將思想當(dāng)作彼岸,而自己站在渡口眺望。在思想的維度之中,詩人在這頭,彼岸是其窮盡一生想要到達(dá)的地方。在思想的宇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過是浩瀚宇宙中的沙礫,一切虔誠的思想朝拜者都是孤獨(dú)而又渺小的,而思想朝圣的路上,一切都是那么的孤寂。渴望探求思想深度到達(dá)彼岸的詩人看著寂寥的渡口,發(fā)出絕望的感嘆,他在渡口徘徊,卻又看到了絢麗的晚霞。思想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美麗,令人心神向往,卻看不到艄公,渴望渡河的渡客在渡口看著太陽日升日落。
從本詩的第一段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詩人的哀嘆,面對近在咫尺的彼岸,奈何無人渡他一程。這讓筆者想起“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的無奈。詩人在浮沉的世俗中望著縹緲的思想彼岸,迫切地想要追尋那抹晚霞。詩人在向世人宣告思想旅途的孤獨(dú)之感,為什么渡口空無一人?不妨回看現(xiàn)如今的不少詩人日日嚷著要解放心靈,在自由中浮沉,在思想中徜徉,但仍舊為塵世所困,為小贏小利折腰。他們或?yàn)榱斯γ摚驗(yàn)榱嗽娮鱾魇溃灾劣隍\的渡客寥寥無幾,作品像極了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化批量生產(chǎn)的作物,毫無生氣,那一針一線的心血蕩然無存,有的只是迎合大眾的模板。
當(dāng)近代一批批渡客渡過思想的恒河到達(dá)彼岸之時(shí),現(xiàn)如今的渡口寂寥無人,凄神寒骨。詩人便是那到達(dá)渡口的渡客,而他的孤獨(dú)來自同程的渡客都在凡塵之中歇下腳步,只有詩人苦苦地、虔誠地踏上旅程來到渡口,當(dāng)前人渡客已到達(dá)對岸,詩人明白磅礴宇宙中思想的維度有多深有多遠(yuǎn),他站在渡口彷徨、徘徊,期盼著能夠渡過河水,但渡他過河的艄公不知去向何處,只能望著對岸的太陽墜落。
在筆者看來,詩人惋惜的是浮沉世間的知識(shí)分子,他們不以提升自我而是以功名利祿為先,所以致使現(xiàn)代的大師寥寥無幾,當(dāng)前人的思想火焰高高揚(yáng)起的時(shí)候,詩人的伯樂還沒有出現(xiàn),沒有渡他過河,可是人生短暫,當(dāng)前人的思想無人加持的時(shí)候,詩人仿佛看到了太陽何時(shí)落山。在這首詩中,人們分明看到了詩人對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嘆息,思想是縹緲虛無的,晚霞卻分明耀眼,前人綻放的晚霞,他們達(dá)到的高度是今人畢生的追求。現(xiàn)在詩人卻只能孤獨(dú)寂寥地在渡口徘徊著,迷惘著。龍應(yīng)臺(tái)說修行的路總是孤獨(dú)的,因?yàn)橹腔郾厝粊碜怨陋?dú)。那晚霞被落日收進(jìn)口袋之后,露水掛滿發(fā)梢間,結(jié)滿透明的惆悵,是這一生最初的迷惘。詩人是矛盾的,他想要過岸卻也害怕過岸。
詩人在旅行與行走中思考。馬良在《坦白書》中說:“這世界沒有一件事情是虛空產(chǎn)生的。這深夜里一片寂靜,是因?yàn)槟氵€沒有聽見聲音。”詩人龐鐵堅(jiān)之所以會(huì)選擇渡河,執(zhí)意踏上思想的彼岸,是他的旅行經(jīng)歷給了他無窮的思想動(dòng)力。在每一個(gè)足跡里聆聽每一縷陽光的歌唱,細(xì)數(shù)每一朵晚霞的嘆息,撫摩落日每一片溫柔的翎羽。在詩歌里傾聽遠(yuǎn)方的聲音,捕捉遠(yuǎn)方的回響,背起詩歌和行囊,接受遠(yuǎn)方的召喚。最后,詩人的腳步停留在家鄉(xiāng)的桂林山水里,找到了最舒適的歸宿,他的心卻始終一刻不停地在追尋,直到某天止步于無人擺渡的河邊。此非真實(shí),但是無人擺渡的河與桂林真實(shí)存在的河有了虛與實(shí)的對比,此刻更傾向于虛的一面,虛又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影射到實(shí)。
詩人龐鐵堅(jiān)迷失在桂林的河邊,最舒適的歸宿仍存在一種失落感。
將人生哲學(xué)糅合進(jìn)生活里,在旅行中學(xué)會(huì)思考,然后踏上人生的旅途。正如詩人自己所說,人生其實(shí)就是一場旅行,最美的風(fēng)景在旅程中,而不是在旅程結(jié)束后的總結(jié)里。詩人在另一首詩中寫道:“街市依然平靜/似乎什么也沒有發(fā)生/事實(shí)上那荒原/真的燃燒過一縷微火”,“微火”指的便是詩人自己一次忘情的燃燒,也可能是詩人在旅行中任何一個(gè)落下的腳步,然而除了荒原,沒有人看見。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旅行卻在詩人心中播下了思考的火種。
詩歌相統(tǒng)一,亦相矛盾。同樣,詩人也是這樣一個(gè)矛盾體。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又寬又不寬的河流,其實(shí)是現(xiàn)實(shí)與內(nèi)心的抗?fàn)帲亲晕业目範(fàn)帲硐紱]有了,是否還要渡河?渡過了河,又能否再看見晚霞?于是“欲濟(jì)無舟楫,端居恥圣明”的詩人暫時(shí)只好“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孤獨(dú)還是詩人龐鐵堅(jiān)情感的主流。除了天邊的晚霞,沒有任何人陪伴,詩人用最虔誠的心來觸摸一草一木,萬物的脈搏都跳動(dòng)在詩人的胸腔里,將詩人點(diǎn)燃。其中又摻雜著孩童的活潑淘氣,落日將晚霞收進(jìn)自己的口袋,就好像貪嘴的孩子趁大人不注意時(shí)悄悄拿走了一塊糖,可是這一塊糖在詩人看來是苦澀的,因?yàn)檫@是自己旅行路上唯一的美麗伴侶,最終只好在自己暗長而沉重的身影里,踏上追逐思想的旅行。就像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詩人本身,在急躁空浮的環(huán)境中保持著不媚不俗的文風(fēng),秉持自己的獨(dú)立見解,拒絕隨風(fēng)而動(dòng)。在《峭壁上的絕望》里,“只有云朵喜歡在這里嬉戲”,云朵是詩人,因?yàn)闊o人涉足,峭壁成了白云的天堂;云朵又不是詩人,因?yàn)闊狒[是別人的,不是詩人的。哪怕發(fā)出了“如果”的感嘆和遐想,詩人是孤獨(dú)的,因?yàn)樘热糇凡簧贤硐迹c詩人相伴的依舊是漆黑的夜。于是在人生的河岸邊,詩人還寫下了《當(dāng)我迷失》,只能在暗夜的睡眠中暫緩悲傷,尋求“莊周夢蝶”的希冀。
詩人在追逐這一切又一切的時(shí)候,他發(fā)現(xiàn)自己在思想的旅途上,河面上的霧氣騰起,航向已經(jīng)清晰,渡船已經(jīng)朝向著彼岸,卻被繩索栓于渡口這頭。萬家燈火裊裊炊煙,而孤獨(dú)的詩人只是無助的渡客,站在河的這頭望河興嘆。他是孤獨(dú)的但又是堅(jiān)定的,他在思想維度的朝圣路上追趕著晚霞。當(dāng)他獨(dú)自踏上路程的時(shí)候他不會(huì)感覺孤獨(dú),但當(dāng)停下腳步站在渡口的時(shí)候他才會(huì)發(fā)現(xiàn)孤獨(dú)。全詩在望河興嘆里戛然而止,接下去詩人也許仍會(huì)堅(jiān)定地踏上那條渡船,縱使世上只有孤獨(dú)的他仍在追尋思想的彼岸,那又如何?至少在不久的未來必將會(huì)到達(dá)的。
縱觀全詩,人們可以看到詩人就似那瀟灑卻又孤獨(dú)的俠客李白一般,他灑脫自在,即便路程艱難險(xiǎn)阻,也孤身一人義無反顧。當(dāng)詩人站在寂寥無人的渡口時(shí),他孤獨(dú)、寂寞。孤獨(dú)不正是彼岸的敲門磚嗎?渡口的孤獨(dú)是詩人自身的孤獨(dú),但它更是思想維度里的一抹顏色,詩人所經(jīng)歷過的孤獨(dú)與痛苦、迷惘與無助,最終會(huì)化作絢爛的晚霞。
詩人龐鐵堅(jiān)的這首詩直白卻不顯得庸俗,他讓人看到了一個(gè)渡客身上猶如朝圣者一般的虔誠,詩人自身涉獵廣泛,內(nèi)容廣闊駁雜,他總是保持著自己的獨(dú)特見解,不跟風(fēng),不附勢,而現(xiàn)如今,一個(gè)虔誠不問功過的學(xué)者甚少,正因?yàn)槿绱嗽娙瞬艜?huì)在詩中發(fā)出孤獨(dú)的吶喊。身處體制內(nèi)的詩人看到了體制中的污濁之象,而為之膠著彷徨,孤獨(dú)地徘徊在渡口。當(dāng)小河兩岸炊煙升起的時(shí)候,也只能夠輕輕地望河興嘆一會(huì),繼而奮勇前行。詩人將一切追逐學(xué)問的最高境界化作渡客追趕思想的彼岸,站在渡口望河興嘆。這字里行間不正是對現(xiàn)實(shí)的嘆息,對人生的感悟?孤獨(dú)是詩人自身追尋學(xué)問的真實(shí)寫照,而不停的步伐是他對功名利祿的抗?fàn)帯R粫r(shí)鉆營得勢的虛名近利,都不過是過眼云煙。前人的步伐仍舊需要追尋,如果這個(gè)世界上的渡客都停下腳步,那他也會(huì)灑脫地帶上行裝,以思想的彼岸為航標(biāo),讓絢麗的晚霞做伴。縱使世間孤獨(dú)得只剩其孑然一身,我想他也定不會(huì)為了沽名釣譽(yù)而改變航向。詩的結(jié)尾那不經(jīng)意間的哀嘆,便是學(xué)者的夜半鐘聲,是詩人對世間的些許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