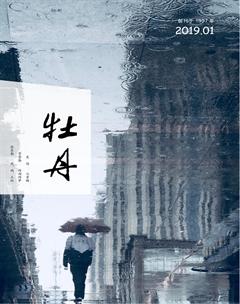從“詩家總愛西昆好”小論“西昆”與李商隱
劉紹穎
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中稱“詩家總愛西昆好”,以“西昆”一詞指代李商隱。而《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將“西昆”冠于李商隱是錯誤的,為辨析孰是孰非,本文探究“西昆”一詞的出處及此稱謂的演變歷程。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四【李義山詩注三卷附錄一卷】談及李商隱詩集注疏時,扼腕劉可、張文亮詩注本已佚,云:“故元好問《論詩》絕句有‘詩家總愛西昆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之語。”而此語下,有小字:“案:西昆體乃宋楊億等模擬商隱之詩,好問竟以商隱為西昆,殊為謬誤,僅附訂于此。”
《論詩絕句》是元好問歷評漢魏迄于宋代之詩人及詩派的作品,其十二云:“望帝春心讬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首句所引“望帝春心讬杜鵑”正是李商隱《錦瑟》中的詩句,而“錦瑟”一詞的出現也驗證了這一點,“鄭箋”是指東漢鄭玄所作《毛詩傳箋》,鄭玄以《毛傳》為主,兼采今文三家詩說,加以疏通識別,使《毛詩》日益盛行,而其他三家詩漸廢。李商隱詩詞晦旨幽,眾人讀之,茫然不知其意味所在,對此,元好問借鄭玄光大《毛傳》之事感發李商隱詩用事頗僻以致其集無人注釋發揚之憾。可以斷定元好問在這首詩中評點的詩人就是李商隱再無其他詩人或詩派,據此句中“西昆”一詞當指代李商隱。
而《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將“西昆”冠于李商隱是錯誤的,為辨析孰是孰非,應首先探究“西昆”一詞的出處。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真宗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跡》,欽若請以秘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在編修之余,楊億等人“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后合“十有五人”之作為集,“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爾”。“玉山”一詞見《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群玉之山,見其無險,四徹中繩,先生之所謂策府。”另外,王仲犖注《西昆酬唱集》解釋其命名:“按楊億等奉詔在秘閣修《歷代君王事跡》,秘閣是帝王藏書冊之府,有似西北昆侖之玉山策府,故名其唱和之集曰《西昆酬唱集》,而其后亦定名所修《歷代君臣事跡》為《冊府元龜》云。”另據翁方綱《石州詩話》:“宋初楊大年,錢惟演諸人館閣之作,曰《西昆酬唱集》,其詩效‘溫李體,故曰‘西昆。‘西昆者,宋初翰苑也,是宋初館閣效‘溫李體乃有‘西昆之目,而晚唐溫、李時,初無‘西昆之目也。”可見,“西昆”(或西昆體)特指宋初一個詩派,以楊億、錢維演、劉筠等人為代表,師法李商隱詩創作幽深諧美的詩歌,追求雕琢密麗和音律鏗鏘。
通過對“西昆”的探源,可以得知“西昆”與李商隱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淵源,既而能夠理解為何元好問獨將“西昆”一詞指代李商隱。但此說無疑是錯誤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言其“殊為謬誤”。
《石州詩話》又云:“遺山沿習此稱之誤,不知始于何時耳。”在現存的唐以后文人論詩文集中按圖索驥,最早將“西昆”指代李商隱的文獻當是宋代惠洪的《冷齋夜話》。其卷四在“西昆體”的標目下云:“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昆體。”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延續了惠洪的說法:“西昆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按照嚴羽的說法,“西昆體”以李商隱為主,溫庭筠次之,楊億、劉筠等反似西昆體后繼之人。《南宋群賢小集》中趙汝回言:“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唐之晚為昆體,本朝有江西體。”趙汝回將“昆體”的時間段限于“唐之晚”,顯然剔除了宋初楊億等人。據此可知元好問作《論詩絕句》之前,宋人論詩文集中已有將“西昆”混用不別者,故遺山或沿襲其說或受其影響,將“西昆”指代李商隱。
此后,明清兩代的論詩作品中仍然有論家持此說。明代高棅論及李商隱:“唐史本傳云:李為文章,瑰邁奇古。長于律詩,尤精詠史。與溫庭筠輩號三十六體。自稱玉溪子云。亦曰西昆體。”高棅所說“唐史”當指《新唐書》,其稱李商隱“瑰邁奇古”“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而“西昆體”一說則是高棅自加于李商隱。
明代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言“人譏西昆體為獺祭魚”,“獺祭魚”最早出現于《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獺喜排列魚于水邊,含有堆砌羅列之義,宋人吳坰《五總志》中說:“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集左右,時謂為獺祭魚。”后來,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進一步發揮:“商隱工詩,為文瑰邁奇古,辭隱事難。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每屬綴,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自此,“獺祭魚”之稱于李商隱,其戲謔之義猶如駱賓王被叫作“算博士”、溫庭筠被稱為“溫八叉”。王夫之言“人譏西昆體為獺祭魚”無疑是延續前人的稱謂轉述他人對李義山的嘲弄,句中的“西昆體”依舊誤指李商隱。
“西昆”一詞從宋代出現以來,其使用混沌之態直至清代馮班始糾此謬,在其《鈍吟雜録》中馮氏針對嚴羽《滄浪詩話》中的誤以西昆為李商隱體,云:“李義山在唐……于時無西昆之名,按此則滄浪未見《西昆集敘》也。何焯注云:‘……玉溪不掛朝籍,飛卿論于一尉,安得廁跡冊府耶?”馮班論詩講求“無字無來歷氣”,本著這種嚴肅細致的態度,馮氏始廓清原有舊說的舛誤。繼而錢曾于《讀書敏求記》中也駁斥嚴羽之說:“按西昆之名創自楊、劉諸君,及吾遠祖思公,大年序之甚明。其詩皆宗李商隱,故宋初內宴,優人有撏撦義山之謔。今云即李商隱體而兼庭筠,是統溫、李先西昆之矣。”錢氏不滿此說,排斥此等“疑誤后學,似是實非”的謬論。更有直截了當點明者,如沈德潛、胡鳴玉。沈氏稱:“宋初臺閣唱和,多宗義山,名西昆體。以義山為昆體者非是。”胡氏語:“今直以義山集為西昆詩,非是。”至四庫館臣修書,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由元好問詩句“詩家總愛西昆好”重提糾謬之說。
何以宋代以后論詩諸家頻頻將李商隱冠于以“西昆”名號,究其原因蓋自惠洪之說后論詩者不細辨是非,人云亦云。以其中嚴羽為例,嚴氏論詩執著于“妙悟”,其說“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強調“一知半解”,自然不會在意一詞指代的差別。而清代考據之學興盛,且有論詩者如馮班講究言而有證,批評空疏之詞“似是而非,惑人為最”,進而字字探究,廓清“西昆”指代李商隱的舊說。另有藏書家如錢曾,藏書校對之時辨別問題,無怪乎《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其作《讀書敏求記》“見聞既博,辨別尤精”。人們且不管歷代論詩思想分歧與門派之爭,單論此誤用之事,給后學者以啟示,做學問應扎實勤奮,持沉穩之態,多讀多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