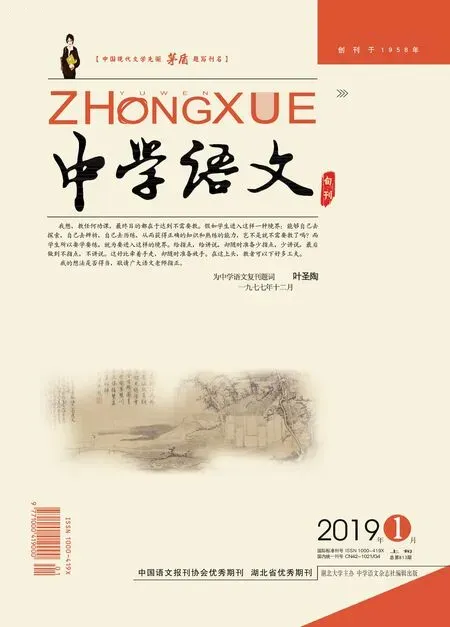意蘊與融通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
——《愚公移山》中的整體思維剖析
徐向順
[作者通聯: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
《愚公移山》出自戰國時列御寇所著的《列子·湯問》。列子,戰國前期思想家,其學本源于老子,主張清靜無為,是老、莊之外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子》字里行間表達了崇尚虛靜思想,強調人在自然天地間的積極作用。“愚公的形象本質上是道家文化的產物,道家思想構成愚公移山精神的文化底色。”①愚公移山精神蘊含博大的道家思想,大智若愚、以愚為本的智慧境界,至誠至性、天地暢達的自在性靈,逍遙生死、卓然無限的豁達性情,直面艱若、舍取豁達的堅毅行動等等,吸納了道家文化因子的養分,傳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愚公移山的精神,放置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文化歷史背景下,則具有更為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哲學意蘊,闡發出極為深刻的社會性題旨。遺憾的是,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做得很不夠,諸如《愚公移山》所構建的與現實系統有著密切關聯、心心呼應的“現實——神話”系統,“移山”神話所隱含的“天人合一”原始普遍性象征,遭到人們普遍的忽視,或為無意識的冷落;其中所蘊涵的意蘊與融通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以及整體思維中的典型思維模式,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破譯。基于此,像《愚公移山》這樣的古代經典詩文,有待我們進一步挖掘、探究。
研究中華傳統文化,不能不探究中國傳統哲學;探究中國傳統哲學,又不能不探析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傳統哲學是通向傳統文化寶藏的通道,而傳統思維方式更是解開中華文化神秘面紗的鑰匙,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是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處于文化結構的最內層,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更具有穩定形態的東西。一般說來,中國傳統哲學把宇宙理解為一個有機的系統整體,這種系統整體觀是古代哲學家認識、把握客觀世界的一種總體觀點與基本方式,體現了華夏民族自然認知理論水平所能達到的高度,并構成觀念性的理論基礎,直接或間接地規定和制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質。然而,傳統哲學的系統整體觀卻又實實在在地建立在傳統整體性思維方式基礎上,整體思維是“從整體的角度出發,著眼于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進而理解和規定對象的一種思維原則。”②把天地、人、社會看著密切貫通的一個有機整體,天地人我、人身人心等作為系統要素,統一處于這個整體系統之中且結成相互依存的聯系。“天下之物,貞乎一者也”(《易·系辭傳下》)。“圣人抱一以為天下式”(《老子》)。“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作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基礎和核心,在幾千年的文化創造、傳承、發展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當今人們解決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時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整體思維是一種有機循環的整體思維,把自然界看成一個有組織的有機系統,構成這個整體系統的又有許多小系統,每個系統又由不同部分所構成,整個宇宙自然界就是由這樣的部分所構成的系統化整體”③。放眼縱覽,自然界萬景萬物,大到宏觀宇宙,小到微觀粒子,無一不在循環不殆的整體系統中運行;世間萬事萬理,小到細事修身,大到治政邦交,無一不在終始恒常的復雜關系中制衡。同樣,一篇篇傳誦古今的詩文佳作,無一不在遵循整體構思的思維路徑,建構“頭”“中”“尾”要件齊全的詩文生命體,這三部分的基本結構又須遵循整體性思維模式,“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所謂“鳳頭、豬肚、豹尾”。《愚公移山》篇幅雖短,全篇只310字,卻結構完整,張馳有節,可以說,深諳“六字法”要領。
《愚公移山》開篇“鳳頭”精要,小巧玲瓏,短小精美。開門見“山”,交代所要移動的對象,“太行”“王屋”二山的面積“方七百里”、高度“高萬仞”及地理位置,點明故事的背景,簡潔明快,直截了當,為下文埋下伏筆。主體“豬肚”豐滿、充實、健壯、容量大,情節生姿曲折。以愚公提出移山主張為情節開端;以家人“雜然”爭議、商定解決方案,旋即挖土辟山為情節發展;以智叟的笑止、愚公的駁詰構成情節高潮。結尾“豹尾”利索,干練精要,收束有力。以天帝被愚公的誠心感動,派二神將王屋、太行二山背走,愚公移山愿望得以實現收結,照應開頭,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蘊含深意,讓百世讀者揣摩、體悟:移山之功全仗神助,雖非愚公之力,卻因愚公至誠,故而不可磨滅。其結構安排貼合,情節采用線性結構,環環緊扣——各情節按時間自然順序、事件的因果關系順序連接起來,呈線性延展,由始而終,由開端到結尾,情節一步步向前發展,矛盾沖突引人入勝,情理至臻且扣人心弦,構建一個互為依存、演繹縝密的有機整體。
《愚公移山》文筆不豐,三百余字的短文,暗設“兩世——三重因果”關系,寫來卻是細絲嚴扣,彼此關合。“兩世”:是指愚公生活的現實世界、天帝掌管的神域世界的“兩個世界”;“三重因果”:現實世界的“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之“因”,引發愚公立志“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之“果”,這是第一重因果;神域世界的“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帝感其誠”之“因”,于是才牽出“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之“果”,這是第二重因果;現實世界的愚公“畢力平險,”“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焉”之“因”,引致神域世界的介入,“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并產生“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之“果”,這是第三重因果。第三重因果是前兩重因果的交集,并在此形成終結,使看似不相干、彼此獨立的現實世界、神域世界里的因果關系得到整合,融匯到更高一級的整體系統中,形成有機關聯。一般說來,現實世界的因果聯系賦予人們實際的真切感,神域世界的因果關系卻充斥大量玄想的虛幻感,而本文在揭示諸多因果關系的局部系統,特別是構建貫通兩個世界的第三重因果關系的整體系統中,嚴格遵循因果律,做到層層相扣,充分展現一個因果相成、邏輯嚴密的系統整體。
上述論及的結構完整、因果相成,固然呈現了整體性思維的一般特征,而最能表現中國傳統的整體思維方式特征的則是 “天人合一”“陰陽思維”這兩個典型思維模式。
一、“天人合一”思維模式
華夏民族經過長時期的觀察、領悟,逐漸形成了由 “天—地—人”組成的整體諧和的宇宙觀念。“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觀念中最高、最為典型的理論形式,也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根本內容之一。
所謂 “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天地以生物為心,’‘道體流行’,具有‘生意’,自然界是一個有結構——功能的統一整體,人則‘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從而能‘為天地立心’,人既是自然界的產物,又是這一整體的具體體現。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二者具有同構性,即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④換言之,一方面,確認人由天地生成的自然物性,人的生活需服從自然法則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自然界的普遍規律與人類道德的最高原則,呈現形式相異,但本質相通。“乾,天道也,父道也,君道也”(《周易大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泛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莊子·天下》)“萬物皆一”(《莊子·德充符》)。“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呂氏春秋·有始》)。“天地萬物為一體”(王守仁《傳習錄上》)。董仲舒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把天、地、自然與人包羅在一起的思維模式,視天地萬物由某種特定的機制而相互聯結為統一的整體。
在《愚公移山》建構的系統密切、整體關聯的寓言世界里,實質上存在兩個相互滲透、互為補充的子系統——即“愚公辟山”指向的現實系統、“天帝移山”虛構的神話系統。現實系統是作者著力刻畫,使用八成五的筆墨,于“否定性”爭議中凸顯決策的周密性,于“移山”過程中彰顯行動的意志力;相比,神話系統敘事簡潔,直陳結果,用墨不豐。從表層結構看,神話系統近乎附著于現實系統的貂尾,缺乏內在的有機聯系,實際上,神話系統不僅貫通首尾、統攝全篇,而且居于現實系統之上起著支配和解釋機緣的樞紐作用。主人翁虛擬如神,具體表現為:其一,高壽體健——北山愚公“年且九十”,尚能親力親為,身先士卒,“率子孫荷擔者”,“叩石墾壤”,經受繁重的體力勞動,“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長途搬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其妻同好健在,年壽齊眉。其二,思維敏捷,愚公頭腦清醒,“謀”事句句入情貼理,懟“智叟”邏輯推論縝密,而其妻也不迷糊,尚能“獻疑”。這些現實人物遠超一般尋常人能耐,他們的身心與體智似乎與神仙異域達成一種通靈、照應,因而可感動“天帝”,派遣兩員大力神士,背走王屋、太行二山,了卻愚公的心愿。
人(社會)與天(自然)何以通靈、合一?抑或前云的“三重因果”何以貫通“兩世”——現實世界、神域世界?從神話特質看,神話作為超現實的幻想形式,與原始文化、原始思維方式相溝通,顯現集體潛意識,且能象征性地投射作者主體意識中更為深層的內蘊。原始初民面對神秘不可知的外部世界,抱有普遍的“萬物有靈論”,即自然神,如山神、水神等充滿整個世界;隨著自我意識的加強,人類開始了按照自我的樣式來想象、塑造神靈,“愚公移山”故事中,操蛇之神、山神、天帝、夸娥氏之子等諸神被賦予鮮活的存在,并被寄予人格神的特征。當神話題旨與現實意旨具有了相匯通的一面時,天帝用憐憫與幫助的方式解決移山問題,化解愚公的生存危機,便在情理之中。神話形象也是表達神秘感的最好途徑,一旦被藝術地想象并高置于神壇,便具有了與人保持某些距離或曰某種隔絕的不可知性,于是就成了神秘性的化身和偶像意義的崇拜物,至于“夸娥氏二子”極具“超自然”本領,“負二山”舉重若輕,就不足為奇了。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天’與‘人’的關系實際上具有某種不確定的模糊性質,既不像人格神的絕對主宰,也不像對自然物的征服改造……‘天人合一’,便既包含著人對自然規律的能動的適應、遵循,也意味著人對主宰、命定的被動的順從崇拜。”⑤
二、“陰陽思維”模式
“陰陽思維”之“陰陽”,是指自然變化中的兩種功能或力量,或析為事物具有的兩種屬性——對峙、統一、變化的功能。陰陽對峙,貫通于天、地、人三才——自然、社會、人身均具陰陽互相對峙的兩種勢力;陰陽統一,陽依附于陰,陰依附于陽,“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任何陽的一面或陰的一面,都不能離開另一面而單獨存在,二者處于互包、互涵、互補、互轉之中。陰陽思維將一切事物視為矛盾統一體,沒有對立面也就不可能形成統一體,沒有統一體,對立的兩方面將無法相互作用,據此應“從事物對立的兩端、兩方面、兩部分,解釋復雜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把握事物變化的規律。陰陽思維是一種抽象的理性思維。”⑥《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揭示事物內在的對立統一,賦予陰陽思維以規律性。《易傳》斷言更是明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陰陽”作為最基本的觀念,將陰陽的對峙、變化、統一作為總規律、總原則,進而解說萬事萬物的普遍聯系及其矛盾對立、相反相成。《莊子·天下》即言“易以道陰陽”。北宋張載在進一步闡釋的基礎上,提出“一物兩體”(《正蒙·參兩篇》)、陰陽和合的思想,“一”是指對立面的統一,“兩體”是指陰陽兩個對立面,“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陰陽思維是中國傳統整體思維方式的典型模式之一。
需要指出,“陰陽五行”思維模式以陰陽兩極建構宇宙生成圖式,在推演五行的基礎上闡釋社會運動規律及其終始循環的命定論特征,為人類思維作出了重要貢獻。“陰陽”“五行”的混合、統一,起始于戰國時的陰陽家;漢代對陰陽五行學說作了進一步完善,對陰陽概念及其無所不包的特性、陰陽的對立統一關系、陰陽互相調節維持整體平衡的功能等作了充分的闡說。董仲舒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第一次提出一般系統論的理論模式和一般系統的雙層結構模型。從時間序列看,列子《愚公移山》先于漢代,因而未將“陰陽五行”思維模型視為整體思維方式予以研究。
“陰陽思維”認識統一體中具有對立面,對立面又存在統一體之中,對立和統一是不可分割的。道家始祖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陰陽、雌雄、古今、生死、智愚、剛柔等等,所謂無對不成物,世事萬物皆是相反相對而存在,進而形成對立統一的“陰陽”合體。出自道家著作《列子·湯問》的《愚公移山》,其原始語境就是殷湯與夏革君臣之間的問答,探討物之始終、有無極盡、巨細修短等哲學命題,其中“巨細”“修短”“異同”等哲學概念涉及“陰陽”之辯,實屬“陰陽思維”。《愚公移山》文本中呈現:智愚、正反、異同、巨細、大小、虛實、有限無限等“陰陽思維”之情狀,其中“愚公”——“智叟”劃歸的“智愚”對立最顯著、表現也最充分,由此形成的移山“堅定派”與“阻止派”構成“正反”或“異同”的陣營。在“移山”事件上,愚公身上展示出的堅定不移、堅毅勇為,象征“正面”“正能量”;智叟言行中表達出的畏難縮進、消極對抗,象征“反面”“負能量”。除了這兩個不同壁壘構成的整體的“陰陽”對峙外,壁壘內部形成局部的“陰陽”對比,比如在“阻止派”方面,愚公妻質疑式的“獻疑”——商榷,而智叟否定性的“笑而止之”——反對;基于出發點不同、表達方式差異,性質判別相異,比如同是對待“愚公移山”事件,操蛇之神是“懼”——害怕,帝“感”而“命”——支持。
在“愚公移山”構建的“天—地—人”龐大體系中,眾“人物”分列“天”“地”“人”三才:愚公、子孫荷擔者、京城氏之子、愚公妻、智叟——“人”,操蛇之神——“地”,天帝、夸娥氏之子——“天”。先秦以來的學術成就表明,古代便編制了“天—地—人”系統的次序:在“天”——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晝為陽、夜為陰;在“地”——下為陰、上為陽,右為陰、左為陽,西為陰、東為陽;在“人”——尊為陽、卑為陰,德為陽、刑為陰,君為陽、臣為陰,據此,“超自然”神性象征的“天地”——“陽”,屈于自然威力下的“人”——“陰”;“天地”體系里,位尊權重的“帝”——“陽”,位卑的山神即操蛇之神、夸娥氏之子——“陰”。不僅表明自然、社會、人身普遍存在陰陽互相對待的兩種勢力,而且進一步論證人與天的統一。
《愚公移山》包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精華和深刻的哲學思想,折射出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厚,具有了不以時空為轉移的基本內涵,因而能夠走出歷史的塵埃,閃耀睿智的思想,卓而不群的智慧,至今仍光彩奪目、熠熠生輝。理解《愚公移山》這篇奇筆異思的先秦之作,需要重返文本產生的原始語境,尋蹤探源,領會其在現實系統中言說的表層意義,更須解剖整體系統中融入的文化信息,破譯“天人”神話、“陰陽”符號的普遍性的象征內蘊和原始意象的原型模式。否則,將無法窺視列子著述的全貌,更妄論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精神的深層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