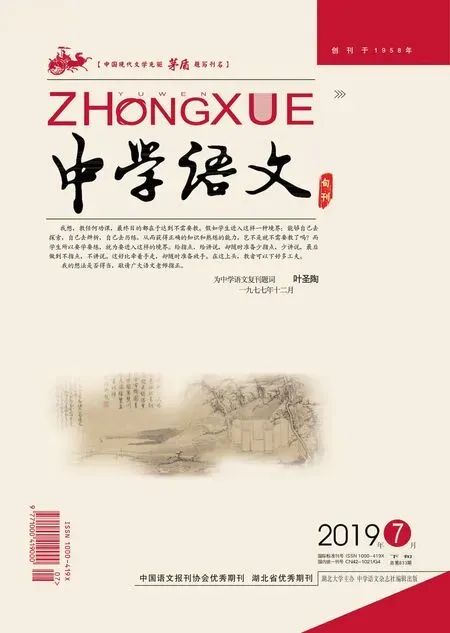核心素養導向下的“主問題”生成策略
文心全
“主問題”教學是在傳統閱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學生為提問主體,老師適時引導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模式。“主問題”是引導學生以剝筍之法對課文的重要或關鍵問題進行深入研讀,問題呈現做到清晰、高效,避免了問題的細碎、無序、無效。學生能夠以清晰的思維,層層深入,主動研討問題,達成提升語言認知、審美體驗和實踐能力的目標。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包括“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四個方面。“主問題”實施過程強調“思考”“討論”“理解”“品析”“創造”這幾個環節,這與核心素養達成的過程是一致的。因此,“主問題”的設計、實施、評價應該貼合語文核心素養來進行,以真正實現學生語文核心素養的落地。
“主問題”是閱讀教學中立意高遠的課堂教學問題,是深層次課堂活動的引爆點、牽引機和黏合劑,在教學中顯現著以一當十的力量。為此,筆者圍繞語言、思維、審美與文化素養的提升,從四個角度談談“主問題”的生成策略。
一、從質疑點深入
學起于思,思源于疑。學生的任何思維活動都是從“疑”開始,又在“疑”中得以發展。南宋哲學家陸九淵有言:“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在語文課堂上,讓學生質疑,是為了增強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文中,孔子在聽完各弟子暢談理想之后,一句喟然長嘆:“吾與點也!”孔子為何如此激動?我把這個問題拋給學生,學生很自然回到曾皙的回答上來。教材把“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翻譯為:“暮春時節,換季的春服穿上了身,約上五六個年青人,六七個少年,在沂水里洗一洗,在舞雩壇上吹吹風,然后唱著歌回家。”曾點的“穿春服”“沂水洗澡”“舞雩壇吹風”和“唱歌”近似現在的春游活動。孔子為何如此贊同這個消磨時光的“春游”?我把這個疑問作為主問題,師生課下準備,課上共同探討。根據《禮記·王制》的記載,周代有四時之祭,春祭曰礿。《春秋繁露·四祭》:“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四月就是暮春時節,春祭必須盛裝,所以曾皙的“春服”不是一般的衣服,而是祭服。“浴乎沂,風乎舞雩”,這里的“沂水”“舞雩壇”都具有祭祀的象征意義,絕不是“沂水洗洗澡”“舞雩壇吹吹風”這么簡單。《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裸,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因此,可以推斷曾皙詠唱的是禮樂之聲,具有祈求福祉,萬民安康之意。孔子一向推崇周禮,而曾皙之志正符合其心意與理想,所以孔子才發出“吾與點也”的喟然之聲。師生一起通過查閱資料,最后解決了疑點,也就很自然地完成了文本的深度解讀。質疑讓學生的思維活躍起來,通過翻閱資料,拓寬了經典文化的視野,傳承了文化、加深對儒家文化的理解。
二、從趣味點延伸
不少學生厭倦語文課堂,這不是語文資源的枯燥乏味,而是平淡無奇的問題呈現和千篇一律的教學路徑導致的。趣味課堂可使學生集中注意力,更好地調動學生探索欲望,使學生熱愛思考,愿意表達,疏通語言經脈。《祝福》一文的教學,可設計的問題很多,諸如環境描寫的分析、人物形象的品讀、主題思想的探究。這些設計不免陳舊,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探究欲望。我們可以從細處著手,在人物分析中,把祥林嫂作為核心點,設計主問題:為什么說祥林嫂是一個沒有春天的女人?學生注意力很快就會集中在“春天”這個詞語上。“春天”這個詞本身具有豐富的含義,“春天”自然會成為學生的興趣點。教師就可以帶領學生細讀文本,梳理情節,尋找答案。學生貢獻集體智慧,互相補充,得出一致結論:1.立春之日,丈夫去世;2.孟春之日,被迫再嫁;3.暮春之日,痛失愛子;4.迎春之日,一命嗚呼。這個主問題又可以延伸出許多子問題:1.祥林嫂的春天應該是怎樣的?2.作者為什么把祥林嫂的悲劇設計在春天?3.是誰讓祥林嫂沒有了春天?通過對這些子問題的解決,學生能夠深入地挖掘出文本的主題,一主多子牽動了學生對整篇小說的理解與探究,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趣味可以激發內驅力,學生會真正動起來,語言上暢所欲言,思維上多角度,最終建立起語文課堂自信力。
三、從空白點挖掘
接受美學論者英加頓指出:作者在創作文學作品過程中,為典型地反映客觀事物和追求社會效益,往往采取“文約事半”的創作手法,作品只能提供一個多層次的結構框架,其中留有許多“空白”,只有讀者在一面閱讀一面將它具體化時,作品的主題意義才逐漸表現出來。文本“空白”是創作者基于文本內涵延伸出的一種有意或者無意空間,是讀者的一種再創作。學生的思維會在填補“留白”的過程中被激活。從創作層面上來講,留白可以達到表達含蓄避免直露和擴大意蘊豐富情感的作用。留白的填補需要我們體悟、預設、分析、甚至創設,這個過程伴隨著聽、說、讀、寫、思、辯等環節,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也會隨之提升。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全詩只有四句,共34字,但蘊含了豐富的人生哲理,給讀者提供了諸多解讀的可能性。詩人自己也曾說過,《斷章》“寫一剎那的意境。 ”全詩用“橋上”“樓上”“明月”“窗子”等意象,給讀者構建了一個看似真實的意境,但全詩沒有任何的情感指向,只有空間的相對性,在“模糊”與“真實”之間構筑了詩歌的“空白”,它促使讀者在“空白”中“再創造”。因此,可以借助詩歌的“空白”設計主問題:結合自身的生活體驗,從多角度領悟詩歌內涵與哲理。通過補白,學生的語言感知潛能得以激發,審美鑒賞能力得以調動,表達與寫作能力得以提升。
四、從比較點剖析
用比較思維來教學,可以更好地調動學生探究興趣,讓學生在尋求異同的過程中,提升感知能力,拓寬思維廣度和理解深度。學生在比較探究過程中會逐漸形成多維的辯證習慣,從而不斷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能力。根據不同題材的不同作品或者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進行比較,教師設置好主問題,把主動權交給學生。學生以文本為中心,以語言為載體,深入揣摩分析作品創作諸多方式,撥云見日,尋找到其中的異同,最終以語言或文字的形式凝結成自己的觀點。比較閱讀是對語言建構與運用的精心探秘,調動了敏銳的思維,領略了文字的魅力,提升了語言審美感受力。
《登高》一文可以采用比較教學法。毛澤東《沁園春·長沙》中的“獨立寒秋”與杜甫《登高》中的“百年多病獨登臺”皆有一“獨”字,但意境與情感大相徑庭,從“獨”字入手,進行解讀,微言中可見大意。學生從主人公“獨立”形象的背景意象和身世遭遇為突破,尋蹤覓跡,剖析兩位詩人的不同情感。因此,我設計了主問題:請比較品析《沁園春·長沙》與《登高》中的“獨”字。圍繞主問題,師生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探討:其一,析意象,品“獨”境。《沁園春·長沙》塑造的抒情主體獨立寒秋,但空間背景很遼闊,詩人選取的意象皆生機勃勃。湘江遠眺,萬山紅遍,層林染透,湘江碧澈,鷹擊魚翔。雖然時值深秋,但詩人在如此背景下的“獨立”,沖淡了秋的蕭瑟與凄涼感,使得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更為高大。“獨立”二字體現了毛澤東傲然屹立的高大形象。而杜甫登高所見到的是蕭瑟的秋江景色:猿聲凄厲,天高風急,秋氣肅殺。鳥盤旋,洲冷清,木蕭蕭,盡顯秋之蕭條。杜甫在此意境下“獨登臺”,加之“百年多病”,不能不讓人愴然泣下。因此杜甫的“獨”包含了人生的悲愴與獨自承擔苦難的情懷。其二,知人世,悟“獨”情。毛詩和杜詩中的“獨”字的解讀亦可從人物與背景的角度去分析。毛澤東于1925年創作了《沁園春·長沙》這首詩。此時,作為一個心懷壯志的革命者,面對敵人窮兇極惡的追殺,依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于臨寒秋而“獨立”,充分表現出詩人的勃勃英氣、颯爽英姿以及他蔑視敵人的非凡英雄氣概和昂揚的革命斗志。《登高》是杜甫晚年流寓夔州,重陽節登高時所作,地方軍閥割據又乘機而起,相互爭斗地盤,社會一片混亂。詩人在四川失去依靠,漂泊到夔州,飽經風霜,歷經戰亂。因此,詩中流露出羈旅異鄉、舉目無親、世亂年衰、日暮途窮的悲愴情緒,令人不忍卒讀。通過比較分析這兩首詩的“獨”字,從意象與背景切入,細細剖析,詩人的情感取向便一目了然。比較閱讀法是一種全方位調動學生能力的學習方法,它強調語言的運用能力,注重多角度的思維方式,考查鑒賞和創造的綜合能力。
核心素養的達成是語文教學熱點與難點,已然成為語文教學的任務與目標,任重道遠。“主問題”教學作為語文教學的重要方法之一,應該為核心素養的達成分擔重任。只要我們尋找適合于不同文本的主問題,精巧設計,深入研討,總結反思,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應該會有不錯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