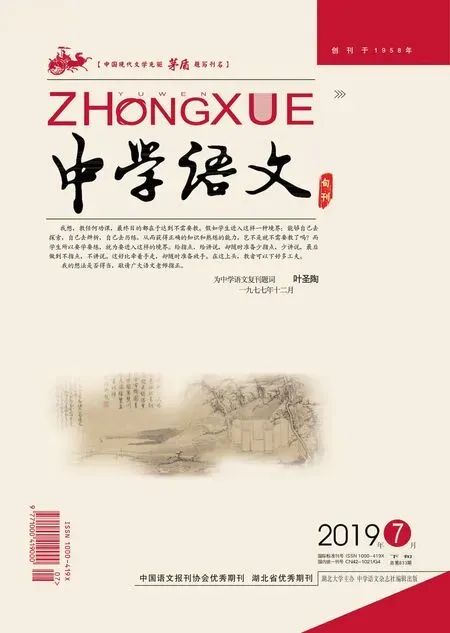淺析“打工文學”中的人文情懷
黨月玲
“打工”是廣東方言,“打工文學”是指反映“打工”這一社會群體生活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散文、劇作等各類文學體裁。廣義上講,“打工文學”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學創作,也包括一些作家創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它是時代發展和社會城市化進程的產物,“打工文學”真實地記錄了底層打工者的打工生活。
一、“打工文學”的由來
“打工文學”真實反映打工者的生存狀態和對世俗的欲望以及對底層生活的關注。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進展,催生了“打工潮”。大量農村青年為了實現自身價值,帶著對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擺脫貧困生活的強烈愿望,背井離鄉涌入城市,形成了“打工族”這一特殊群體。為了生存,他們選擇放棄祖輩流傳下來沿襲多年的謀生方式,從偏僻落后的鄉村走向陌生的城市,開啟了漂泊與打工的生涯,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勞作的間隙和空閑之余,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理想,以自己的打工生活為題材譜寫出反映底層真實生活的文學作品,作品涉及有關農民工對自身的出身、生存、生活、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困惑與思考。
生存的艱辛和現實的重壓讓打工者明白,城市于他們而言只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傳說,雖然迫切希望能夠融入城市,卻每每處于無門可入的尷尬境地。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在城市漂泊,雖不屬于鄉村,但也不屬于城市,終日生活在城市和鄉村的夾縫之中。帶著心靈的傷痛、帶著對城市生活的迫切向往、帶著被現實排斥的痛苦掙扎,在城鄉文明的沖撞下,他們提筆抒寫自己的打工生活以及被城市所排斥的邊緣生存狀態,將自己的生命體驗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打工群體中的一批文學愛好者開始走上文壇。隨著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學作品的大量問世,“打工文學”逐漸蔓延。“打工文學”的創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著與眾不同的關注點和切入點,其作品往往反映的是自身從農村走向城市的漂泊經歷,展示他們在城鄉夾縫中艱難生存和堅強生活的境遇,以及他們渴望融入自己打工的城市、得到城市認可的強烈愿望,給當代中國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打工者在承受現實嚴重錯位的同時,還要承受生存的艱辛、居住環境的擁擠嘈雜、待遇的不公、外界的隔閡、心理的迷惘以及不被城市認可的不安全感等,所有這些構成了他們肉體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讓他們倍感焦慮和壓抑。他們的作品往往關注的是自己的悲歡和生存的痛苦,寫作的視角從內心世界向外部世界折射,以寬大的胸懷對人性中的善與惡進行深度剖析。透過他們苦難生活的自身經歷,對自我心靈進行探索和解讀,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他們對打工者的世俗欲望和心路歷程加以關注,并發出關于個體生存、權利、平等的吶喊。
二、“打工文學”中人文情懷的具體表現
人文主義是以人為本的世界觀,集中體現為對人本身的關注、尊重和重視,它著眼于生命關懷、著眼于人性,注重人的存在、價值、意義,尤其是人的心靈、精神和情感。人文精神倡導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關注人的精神狀態和內在需求,人文關懷是善的終極價值體現。
1.關注農民工自我和人格意識覺醒
“打工文學”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打工文學目前多是描述打工者的辛酸,內容包羅萬象,如寫拖欠工資、身份歧視,或是打工者的遭遇等等,有些則是描寫農民工在社會經濟轉型下靈魂的斗爭,表現出人的自尊和尊嚴,但“打工文學”不能只停留在“吐苦水”的層面上,而是應該用更多的筆墨反映農民工的精神世界,如自我意識和人格意識的覺醒、道德重建、人的全面發展這些題材,從而讓“打工文學”走上更加廣闊的道路。
2.走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內心世界
打工者經過多年和城市的融合,這個過程是從簡單的傾訴向城市艱難融合的歷程轉換,打工者和城市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緊張的。“打工文學”要走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內心世界,從外向內拓展,而不僅是從外在的角度描述他們,而是要進入他們的內心,反映他們心靈的焦慮,要由外向內走。
3.關注被書寫者的精神內涵
“打工文學”應更多關注被書寫者的精神內核和精神狀態,人物的精神狀態更應是文學把握的靈魂內核。現實生活中描寫柴米油鹽的作品很多,但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打工文學應讓后人感受到被書寫者的精神狀態。否則即使物質富有了,精神沒有提升,便仍然是貧窮者。
4.更加突出人文情懷的感召
打工文學和任何題材作品一樣,都是以人為中心,關注的是個體的生命體驗和感受。優秀的文學作品離不開鮮明的人物性格,打工文學要努力塑造符合時代要求和心靈要求的形象,在積極保持時代氣息的同時,更加突出人文情懷的感召。更多的挖掘出人性的光輝、人性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