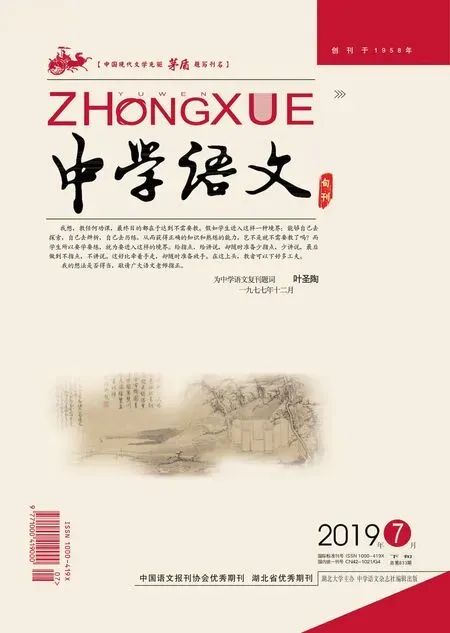主體視角觀照下的《師說》閱讀新解
菅彥玲
一、概念界定:何謂主體視角
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不再簡單強調作家的創作心理、創作手法和風格及作家對作品不斷修改所形成的文本檔案史,而是注重文本所暴露的作家被壓抑的無意識,及其對社會、權力壓抑的反抗顛覆和創造出的具有解構意義的新敘事。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雖極具現代性,但從中可看到其非常重視對言說主體的主體性研究。
主體視角即是在文本解讀中不僅要分析文本本身,還應從言說主體的視角觀照文本。對古代文學來說,我們在解讀古代文學文本時,應將研究對象作為一個有生命的、有意識,甚至有文化構建意識的主體看待,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文本。
二、主體視角觀照的必要性
以往的有些古代文學、文論研究極其重視辭章學意義上的研究。這種研究強調以事實為根據,以考據、檢索、梳理為主要方式,以清楚揭示某種術語或提法的發生演變軌跡為目的,即進行知識話語系統的構建,這是必需的,但這還不夠,容易限制我們的研究視野,容易將研究脫離古人實際,也容易將學問“無趣化”“僵死化”。
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本身具有很強的主體意識,它不同于西方唯理的邏輯的文本,正如錢穆先生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一書中的《略論中國文學》一文所言,“中國文學亦可稱為心學……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的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謂文學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學,此則為文學之最高理想與最高藝術……重生命,言性情,則無可盡言,無可詳言……則心與心相通,亦不煩多言。……而且中國文學,必求讀者返之己身,反之自心……一切文學皆自著者一己之性情出發。……中國文學實則為一種人生哲學。今必分文學哲學而為二,斯其意義與價值,唯各見其減,不見其增亦”。
錢鐘書也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一文中把中國傳統文論的一個基本特征概括為:“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易·系辭》云:‘近取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釋:我們把文章看成我們同類的活人;《文心雕龍·風骨篇》云:‘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猷形之包氣。……瘠義肥辭’;又《附會篇》云:‘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宋濂《文原·下篇》云:‘四瑕賊文之形,八冥傷文之膏髓,九蠹死文之心’;魏文帝《典論》云:‘孔融體氣高妙’;鐘嶸《詩品》云:‘陳思骨氣奇高,體被文質’——這種例子,哪里舉得盡呢?”即我們評論文學通常把風骨、氣質、氣韻、肌理這些本來是講人的術語拿來講文章,中國人對文學批評高度人化或者生命化。因此構建文史合一的文化語境與解讀上的主體視角就顯得十分重要。
在操作上我們應將研究對象作為一個有生命的主體看待,從文本資料中還原出演說的主體。我們在解讀古代文學作品時,不僅要發掘文本本身的意象、思想內容、辭章學意義上的修辭與風格等,更應探尋文本背后的言說者的主體精神,比如主體的人生旨趣、社會關懷、生存智慧等。只有這樣,才能與文本對話,與古人對話。
三、案例分析
比如,韓愈的《師說》是中學的一篇“老課文”,筆者查閱了相關教學參考資料,一般的設計思路是這樣的:
以中國自古以來的從師風尚導入新課,然后介紹作家背景,強調韓愈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柳宗元一起提出“文以載道”“文道結合”的觀點。在研習課文中,重點是翻譯文言文和理清文本的思路,體會文本的正反對比的論證方法。當然許多教師會補充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的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皆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得出結論:《師說》是針對時弊而寫,作者在文中闡述了老師的作用和標準、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和從師應持的態度,提倡能者為師,不恥下問,教學相長。
單從文本的層面這樣理解課文,沒有錯。但是作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和柳宗元一起提出 “文以載道”“文道結合”的觀點。在教學中,我們可以在疏通文意之后,設置一些問題讓學生從更深層次上去解讀作品。比如:難道僅僅將“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師道”理解成課本注釋中所注的“從師的風尚”嗎?韓愈寫作此文的真實意圖是什么呢?
課堂應用方法:
教師可引導學生再次“細讀”原文,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可發現:韓愈在文本中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即“師道”不是從師的風尚。其實韓愈說的“道”是“古道”,這從文末也可看出來:“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解決以上問題之后,我們就可引導學生更深層次地探討:本文的寫作意圖僅僅是闡述尊師的主題嗎?韓愈為什么要提倡尊師傳統呢?這和他所說的“行古道”有何聯系呢? 能不能從中發現言說主體的實際意圖以更準確地解讀文章呢?
就此,我們可根據教學實際,利用電子或紙質媒體給學生提供精當的 “支架”(比如下面學理操作中的一些資料),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性的小專題探討(當然也可用其他教學方式)。教師可讓學生或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一篇研究報告;也可以在課堂上展開交互式探討;教師也可做一個示范性專題分析等等。
以下是以上問題的學理操作示范:
要解決以上問題,我們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單純的對文學文本的理解上,就一定要從文本的言說主體角度思考問題。而要理解言說主體,必須構建言說主體當時所處的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由于本例擬說明的問題不在如何構建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在此就簡化這一程序,直呈事實了。
中唐時代,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使盛唐時代強大繁榮景象已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鎮割據、佛老蕃滋、宦官專權、民貧政亂以及吏治日壞、士風浮薄等一系列問題,整個社會表面看似穩定,實則動蕩不安。為王朝中興,一些士人開始復興儒學,韓柳更是將復興儒學思潮推向高峰。這是當時的歷史語境。
從當時的其他文本中,利用互文本融通的解讀策略,我們可知當時的文化語境。
《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
韓愈在《與孟尚書書》中說: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
在《原道》中,韓愈更是自覺地站在古代士人階層的歷史高度:“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后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可見韓愈是歷史性地以士人主體意識的角度看待師道這一問題的。他認為古文運動的目的在于“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有論者認為,韓愈弘揚儒家道統的基本著眼點,不是想在理論上有大的建樹,也不是想當孟子之后儒學的第一傳人,而是在于“適于時,救其弊”。
但從言說主體上看,韓愈所力倡的 “道”,僅僅是“適于時,救其弊”嗎?
韓愈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可見,韓愈所以極力倡導傳承“師道”,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尊師重教,其實是為了傳承先秦時代士人階層所構建的士人之道。做“傳道之師”,以自己的價值訴求重新規范現實世界的價值體系。所以他才主張“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他雖不敢像孟子那樣明言做“王者之師”,但他之所以認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就是為了以復古師道為媒介而傳承士“道”。
自然,今之君主并非圣人,自然更應有所師從了。除了這一目的之外、韓愈亦與孔孟一樣,要做整個社會,士人階層的精神導師。因為在韓愈看來,唯此才能在社會上構建一個像先秦時代一樣的士人階層的精神與價值觀念高漲的時代,一個士人階層掌握了社會主流價值話語權的時代。以極力改變中唐以來藩鎮割據、佛老蕃滋、宦官專權、民貧政亂、吏治日壞、士風浮薄的局面。
不僅如此,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云“夫子(孔子)賢于堯舜”,表明孔子的地位在堯舜之上。堯舜在孟子看來 ,只代表政統,孔子則代表道統。韓愈積極恢復師道,其實他的內心中實具一種遠古而來的 “王者之臣,其實師也”的理想地位,即認為道統高于政統,文化理想高于君主政治,身為君主之臣,心則為帝王之師,在此基礎上以“道統”制約“勢位”。
所以韓愈在《師說》中如此闡述他的師道觀念,“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他之所以如此打亂年倫秩序,絕不僅僅是強調一般意義上的能者為師,而是作為士人階層的精神代表,韓愈主張振作精神,自覺承擔起傳道的大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極力倡導重振“師道”,試圖恢復先秦時代那種私學興盛時的局面。總之,從言說者——士人主體的文化詩學角度看,我們可從《師說》中看到一個極有儒家救世意識和話語權構建意識的、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教師的“傳道之師”的主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