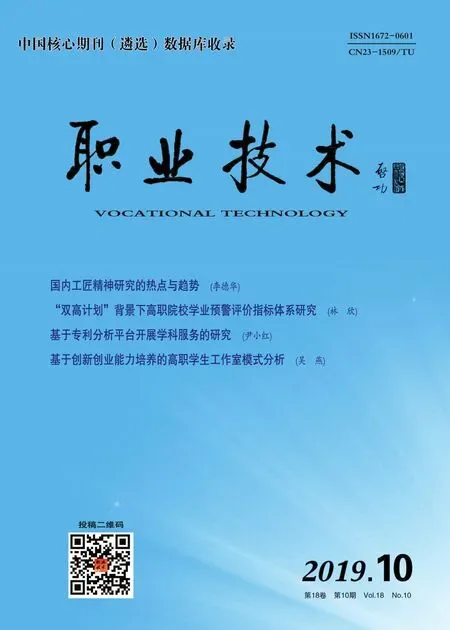論行會在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的歷史缺位與行會平臺的搭建
孫明星
(湖南師范大學, 長沙 430100)
0 引言
職業教育一度成為日本、德國促進經濟發展的秘密武器,可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性。我國越來越重視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但其發展速度和質量仍不容樂觀。比較職業教育發展強國,以德國為例,行會地位至關重要,是其職業教育成功的第二法寶。而當下我國行會在職業教育發展中存在明顯缺位現象,梳理行會在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進程中的缺位,分析其缺位原因,并進而探討搭建好行會平臺,促進職業教育發展。
1 行會在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的歷史缺位
職業教育的發展始于學徒制。中國的職業教育亦始于學徒制。中國傳統學徒制是指在職業活動中,通過師傅的傳幫帶,使藝徒獲得與從事職業相關的制作手藝或生產工藝的背景知識和實際工作經驗的一種古老的職業訓練方法[2]。中國的學徒制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官營手工業學徒制(7-14 世紀)、行會學徒制(15-19世紀)與企業培訓學徒制(20 世紀初至中葉)[3]。與歐洲行會在學徒制發展中具有的作用和價值不同,行會在我國學徒制發展的三階段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
第一階段,官府掌握并控制著手工教育。手工生產是封建社會生產力的主要形式,在封建集權的古代中國,統治集團控制手工生產活動,壟斷最為精湛的手工技藝。尤其在封建社會鼎峰的唐宋時期,官營手工業已經具備了系統而完善的學徒培訓制度。該階段,在封建經濟的束縛中、在官府強力的控制下,學徒制呈一種封閉狀態。而伴隨唐宋商品經濟萌芽而萌生的行會,也無法脫離官府的管理,它不同于歐洲的自治行會,缺乏本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這種缺失也使其沒有能力承擔學徒制的管理。歐洲則不同,學徒制與政府無太大關系,由力量強大、組織自治的行會將學徒制制度化,將其納入管轄范疇、使之成為一種重要的內部組織制度,由此手工業學徒培訓完成了“從私人性質的制度向公共性質的制度過渡”,并使之逐步完善,標志著職業教育的開端[4]。
第二階段,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帶動了行會的出現。封建社會的逐步瓦解打開手工業和學徒制的封閉圈,行會介入學徒制管理,將其作為維護行業健康發展的手段。在經濟體制不變的情況下,行會無法擺脫官府的管理。
第三階段,從清末中國創辦第一所職業學堂開始,職業教育就從零散的學徒制逐漸過渡到系統的教育體系。以黃炎培為代表而興起的近代職業教育思潮讓職業學校如雨后春筍般蓄勢而發,而行會在19世紀后所發生的變化和衰落也使其參與職業教育的能力再次衰退。在此階段后期,職業教育系統未完全吞噬學徒制,學校職業教育發展的緩慢性和殘缺性使得企業學徒制在該時期興起和發展,企業內部創立職業培訓制度,學校職業教育與企業學徒制并存,行會處于游離二者的尷尬地位。[5]近現代,職業教育納入正式的教育體系是不可逆的趨勢,歐洲也不例外,資本主義工業化沖擊著傳統行會學徒制,傳統行會學徒制培養的人才不能滿足社會的發展,學徒制培訓體系被迫改革,廠內培訓成為一種有效的解決形式,從而行會學徒制轉為在廠培訓學徒制。與此同時,國家主義職業教育制度確立,因此人才培養的重任由學校職業教育與在廠培訓學徒制共同擔負。歷經以上管理權的淡化和轉移并不意味著歐洲行會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無足輕重,相反,歐洲國家清楚認識到行會在促進職業教育發展中的不可替代性,因此進入以學校為主的現代職業教育時代仍一直保留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發展的傳統。在歐洲眾多國家中,德國行會參與并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成效是值得借鑒的,德國重視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的程度可從德國職業教育界最高法律——《聯邦職業教育法》窺見一斑。德國從法律的高度對行會的權責進行規定:行會是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組織者;行會在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中的作用;行會負責職業教育培訓的審查與監督。[6]德國職業教育領先于世界得益于健全的法律體系、雙元制教育模式等,行會在其中的貢獻也不容小覷。
縱觀中國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不同于歐洲社會,中國真正推動學徒培訓走向制度化的主導力量不是行會,而是國家,國家設置專門的機構和職位來掌管百工技巧。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經歷了從“游離于學徒培訓之外”到“介入學徒培訓”再“游離學徒培訓”的發展軌跡[7]。發展至今,中國行會在企業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已大大減弱,職業教育參與能力也漸被遺忘,而歐洲國家卻一直保留行會對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德國,行會仍在職業教育中有一席之地,并推動職業教育向前發展。而當前我國行會在職業教育中的地位微乎甚微,行會為什么在我國未能引起重視,行會是否對職業教育發展具有意義值得考究。
2 行會在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缺位的原因
行會在歐洲職業教育興起和建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后期國家政府的力量逐漸強大而削弱其主導作用,但行會依舊有其價值。相比之下,當前我國行會的缺位于職業教育的發展,結合行會參與我國職業教育的歷程及其現狀,進一步探尋其缺位原因。
行會缺位的問題須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去分析。首先談歷史原因。職業教育誕生的邏輯起點應是“技藝的自由”,所謂“技藝的自由”指兩方面:一是技藝的形成,它是人在勞動生產過程中,發揮聰明才智而形成的富有技巧性的、難以掌握的武藝、工藝等;二是指自由,它意味著技能擁有者具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對技藝的發展和傳承有選擇和決定的權利。[8]原始的職業教育在于發明、掌握某一技能的人將這一技能以某種形式自發地傳授給后人,缺乏這種自由性,職業教育即不存在。以此邏輯起點來看,在封建時期的中國,技藝者是沒有自由的,技藝者被君主壟斷而僅為其服務,限制其傳承,因此中國沒有原生職業教育。技藝者自由受限的狀況直到19世紀60年代才發生改變,洋務運動中興辦學堂被認為是中國職業教育院校的萌芽。同樣,在皇權專制的古代社會,雖然產生了行會,但基于商業和手工業服務于皇權其發展才不會受阻,行會派生于皇權之下,所以中國行會一開始就帶有官營性。除了官營性,中國行會還具有原始的宗族性。宗族是古代甚至到現在也是中國社會關系的核心維系方式,而儒家倫理是宗族的核心。古人云,“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商人地位的低下使行會中的商人一方面享受著工商業的果實,另一方面內心又鄙視工商業,仍以“仕途”為宗族榮耀。[9]土生土長的官營性和宗族性使行會發展不如歐洲那樣開放和迅猛,更內斂和封閉。因此,從歷史角度來講,我國具有官營和宗族特性的行會以及缺乏原生性的職業教育使得兩者關系不緊密,缺少歐洲國家中職業教育與行會的共生關系。
除了以上所述的歷史原因,還需要直視當下行會未能參與職業教育的現實原因。我國興辦職業教育的氛圍不濃厚、職業教育法律法規不健全,行會地位不突出、公信力不高。職業教育作為我國教育系統的一部分,受政府指導、依賴于政府的扶持,而在政府對職業教育的統管較多的情況下,行會的地位自然受沖擊,歷史經驗亦是如此。就行會本身,缺乏參與教育管理的意識,中國商界向來較少干涉教育,學校大多是國家公立性質。但近年來這種狀況逐漸得到改善,私立學校的興起對行會涉足教育、參與職業教育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觀念、社會制度不斷邁向現代化,工匠精神不斷被豐富和呼吁,行會在此背景下應愈加受重視,其官營性和宗族性在民主、法制的現代社會中也漸漸消退,理應有著良好的發展空間。對于職業教育,我國早已意識到職業教育發展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長期以大量資金、優惠政策來填補職業教育起步晚、發展慢的空缺。由此可見,現今中國社會為行會和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溫暖的氛圍。但同時面臨的現實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仍舊不溫不火,陷入多重困境。為改變以上現狀,不乏研究者討論如何推動職業教育發展,作為參與職業教育發展的主體,學校、政府和企業成為相關研究中最頻繁的關鍵詞,行會卻似乎被遺忘。批判性借鑒德國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的經驗,彌補行會缺位、促進行會參與職業教育對突破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困境是一種新思路、新辦法。
3 搭建行會平臺,促進職業教育發展
為使行會充分發揮其功能,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
3.1 依法設置行會
依法設置行會是職業教育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以行會為中介打通政府與企業的聯系,制定法律法規去引導和規范行會。如德國的《聯邦職業教育法》以及俄羅斯的《俄羅斯聯邦工商會法》,都從法律高度明確了行會的職責和地位。我國目前尚無針對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的立法,有的是一些較為零亂、分散的關于行會的規章制度,主要包括 1997 年國家經貿委《關于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會試點的方案》、1999 年《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試行) 》、《關于加強行業協會規范管理和培育發展工作的通知》,2004 年國資委《國資委行業協會工作暫行辦法》等部門規章,以及一些省市出臺的關于行業協會管理的法規。[10]立法的缺失是行會職能不明確、動機薄弱、參與度受限等問題出現的重要原因。在我國職業教育相關法律不斷趨于健全和完善的過程中也需要將行會相關法律納入其中,賦予其嚴肅性、調動其積極性。因此政府應推進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的立法工作,通過立法,明確行會的性質、職能、運作模式,使行會參與職業教育有理有據。依法設置行會,有助于我國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
3.2 政府搭建平臺
無論是行會還是職業教育我國政府都有最高的統籌和協調權力,因此行會和職業教育之間橋梁的搭建依靠政府的力量。首先,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與行會的關系。將目前一些超出政府管理職能或事務性工作轉交給行會,讓行會承擔起職能,以增強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發展的能力,這既對政府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也對職業教育的發展有利。因此有必要出臺權威性文件,以此規范政府與行會的關系,明確規定政府部門職能轉移的范圍和事項,如促使有關部門把行業統計、行業規劃、行業規范、資格認證前置審查、市場準入資格認定、許可證發放、專題調研和專項工作等工作轉移給行會。[11]在此基礎上,制定細則闡明行會參與職業教育中的權利和義務,也對企業和學校作出要求,為行會疏通阻礙,避免其缺乏號召力的尷尬局面。只有在政府的統一監管下,行會才能“揚長避短”,揚其“平衡、傳遞、溝通、服務”所長,避其“定位不明、職能不晰”所短。
其次,改變政府的經費支持方式。政府的經費支持是行會建設的重要支撐,但若要真正發揮行會的第三方作用,應保持行會原有的商業性質,變直接撥款為購買行為。行會致力于職業教育發展的一系列服務性工作將以產品的形式向政府兜售,而政府也據其成效進行購買。這樣既可以保證政府經費投入的效率、為行會提供經費保障,又不致使行會的商業化性質轉向政府依附性,保持了行會獨立性。此外,政府還可以輔助減免稅收、提供實用性資源等方式給予行會支持,增強其生存能力。
如上所述政府積極幫助行會搭建與職業教育界或是職業學校的對話平臺,共同探討職業教育發展的困境與難題,行會才能明確自己的職責、參與職業教育的管理和發展,提出意見和建議,在職業教育的前進之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3.3 實現多方聯動
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緊靠一己之力是很難實現的,企業、政府、職業學校、行會是參與職業教育的四大主體,它們分別在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進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以聯系的觀點來看四位主體,不難發現職業教育突破困境的重要法寶以及未來發展趨勢是:企、政、行、校四方的合作,四位一體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聯動機制,互相補充、互相監督。在這樣的關系網中以企業為參與主體,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同時也為企業的發展儲備人才;以政府為主導,政府在統籌兼顧中實現權力下放;以學校為中心,學校在積極改革發展中整合利用多方資源,以市場為導向突出辦學特色;而行會則作為紐帶,是政府統籌職業學校的調節劑,使其權力運用恰如其分,是企業與學校的中介,使人才的培養滿足社會的需要。行會的紐帶作用使企業、政府、學校之間的緊密聯系,搭建共同對話的渠道,整合力量,形成多方聯動、共同致力于職業教育發展。
4 結語
如何提升職業教育質量水平,促進我國職業教育健康快速發展,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結合我國行會參與職業教育發展歷程,探尋其缺位的原因和補位的意義,在基于我國國情的前提下提出搭建行會平臺,以行會促進職業教育發展是突破職業教育發展困境的一條蹊徑。在政府主導平臺搭建、完善法律法規為輔助的基礎上,發揮行會紐帶作用,形成企、政、行、校四方聯動參與職業教育必將推進職業教育實現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