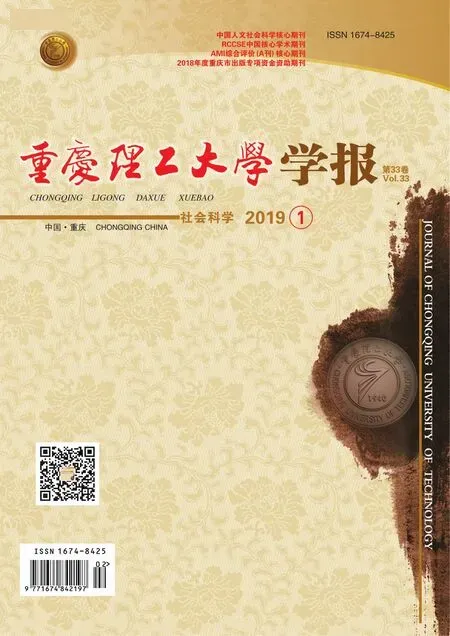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論的展開與檢驗
王東海
(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院, 重慶 401120)
刑法體系解釋是系統論思維在刑法解釋中的具體應用,是眾多的刑法解釋方法之一,在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對刑法體系解釋進行科學認知和有效運用,有利于解釋者準確理解刑法規定的含義,也有利于司法者合理處理實踐中的案件。然而,目前關于刑法體系解釋的理解和運用多將其放在“中觀”的刑法典體系這一層面,認為刑法體系解釋就是將相關的刑法規定置于刑法典這一體系之中,聯系刑法典相關條文對待解釋的刑法規定進行解釋。這一概念忽視了“微觀的條文體系”“宏觀的法秩序統一體體系”“全局的規范邏輯和社會情理價值體系”3個層次,既存在理論邏輯上的硬傷,又成為司法實踐中引起案件爭議的重要誘因。因此,需要對刑法體系解釋進行理論上的匡正,以期能夠準確指導對刑法規定含義的解讀和對司法實踐案件的處理。
一、“中觀”窠臼:當下刑法體系解釋之述評
(一)刑法體系解釋觀點梳理
在理論研究領域,對何為刑法體系解釋,不同的學者進行了不同的界定,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3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刑法體系解釋“是指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規范意旨的解釋方法”[1]。
第二種觀點認為,“在所謂的體系解釋(systematische Auslegung)中,并不是單獨地孤立觀察某個法律規范,而是要觀察這個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的關聯;這個法律規范和其他法律規范都是共同被規定在某個特定法領域中,就此而言,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體系’”[2]。
第三種觀點認為,體系解釋又可以稱為語境解釋,“是指對法律條文的解釋要依據法律條文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結合相關法條的法意進行解釋”[3]。
上述3種觀點從不同角度對刑法體系解釋的含義進行了說明,基本代表了當下理論研究中對刑法體系解釋的認知和司法實踐中對刑法體系解釋進行具體運用的現狀。
(二)當下刑法體系解釋之理性評判
刑法體系解釋是系統論思維在刑法解釋領域的應用,而系統有大小之分和層次之別,不同的系統層次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刑法體系也具有不同層次[4]。刑法體系本身的層次性決定了對刑法規定進行體系解釋也應該具有層次性。具體來說,刑法體系解釋可以分為“微觀”“中觀”“宏觀”“全局”四個層次[5]。從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說這一邏輯體系來劃分的話,前述第一種觀點可以歸為“中觀”層次,它強調刑法解釋的對象是刑法條文,在對具體的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時,需要將其置于整個刑法典當中進行考量,不能就具體條文解釋具體條文,而不顧及刑法典其他條文的相關規定。目前,關于何為刑法體系解釋的論述,多數學者持這樣的觀點。如萬國海認為,刑法體系解釋“是指根據刑法規范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把一項刑法規范或用語作為有機的組成部分放置于更大的系統內,使得刑法規范或用語的含義、意義相協調的解釋方法”[6]。肖中華認為,刑法體系解釋是指“把一項刑法條文或用語作為有機的組成部分放置于更大的系統內,使得刑法條文或用語的含義、意義相協調的解釋”[7]。
第二種觀點雖然在文字表述上不同于第一種觀點,但是其本質與第一種觀點并無二致,對刑法體系的解釋依然是一種“中觀”層次的界定,即強調所謂的體系解釋,就是將被解釋的刑法具體條文放在其所在的“特定法領域”——刑法典體系當中,觀察這個被解釋的具體條文和其所在的某個特定法領域的其他條文之間的關系,考慮到這個特定法領域之體系性。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觀點雖然出現在法理學著作中,但將其作為對刑法體系解釋的內涵界定并無不妥,因為刑法體系解釋也是法的體系解釋的一種,況且作者本人是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領域的知名教授,其對體系解釋的界定,同樣適用于關于刑法體系解釋的界定。
第三種觀點將刑法體系解釋稱為語境解釋,認為對某一法律條文進行解釋時,應當將其放在“法律體系”中,依據其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聯系相關的法條對其進行解讀。這一觀點,看似超越了前述兩種將刑法體系解釋視為一種“中觀”層面的解讀,是對目前多數觀點的一種突破甚至說是升華。但是,遺憾的是,該論者在對體系解釋進行進一步論證時指出,“體系解釋主要討論同一法律內部不同的法條之間的體系解釋問題”,進而指出,“不同位階的法律的體系解釋雖然也屬于廣義的體系解釋,但放在合憲性解釋中討論更好”[3]246。可以看出,這進一步的論證將“宏觀”的或者說“廣義”的刑法體系解釋又限定在了“中觀”層面的窠臼之中,又回到了“中觀”的刑法典體系層面,最終仍未完成理論上的突破。
前述3種關于刑法體系解釋的詮釋,之所以一直沒有更多地關注“微觀”層面、突破“中觀”層面、考量“宏觀”層面、通覽“全局”層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理論研究者給自己預設了一個“中觀”的邏輯前提和“知識前見”,進行的是一種缺乏層次性的演繹,且該種論證被已有的“合憲性解釋”所束縛,并沒有深入思考刑法體系本身的層次性特征和形式邏輯上的周延性,也沒有高度關注司法實踐中是怎樣進行、應該如何進行刑法體系解釋這一重要論題。對刑法體系解釋進行界定,應當從邏輯思維演繹和司法實踐運用兩個維度進行考慮:在邏輯思維演繹方面,應當充分運用系統論思維,分層次全方位地解剖刑法體系解釋的每一個環節要素,將其放在一個層次分明的周延的邏輯體系下進行解釋;在實踐運用方面,應當以司法實踐中解釋者怎樣以及應當如何解釋運用刑法條文為認識的起點和觀察的對象,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的概括和升華,而不是將刑法體系解釋限定在傳統的思想束縛下,先給自我限定一個范圍或者說進行一個預設,再在預定的邏輯“藩籬”之下進行討論。
顯然,上述關于刑法體系解釋的觀點,多多少少都存在局限范圍的做法。比如,認為刑法的體系解釋就是在刑法的范圍內對刑法條款進行解讀,而將刑法條款與放在整個法律體系內解釋的方法稱之為“合憲性解釋”。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時,需要將其放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加以理解,這在邏輯思維上和司法實踐中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具體論述時,卻又將該種解釋定義為“合憲性解釋”。暫且不論“合憲性解釋”的含義,單從方法論上看,就存在不顧司法實踐和理論的獨立性,而是將本來簡單明了的問題放進并不合適的預設框架內“作繭自縛”。
二、體系補全: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之提出
(一)刑法體系解釋的4個層次
對刑法進行體系解釋,需要依次考慮刑法用語和款項在條文體系中的含義、刑法條文在刑法典體系當中的含義、刑法條文與其他法律法規之間亦即刑法條文在整個法秩序統一體體系中的含義,以及成文的法律規范與社會情理價值相統一層面的含義。具體可以表述為4個層次:
第一層次——“微觀”的條文體系。對某一刑法用語或款項進行解釋,必須將其放在所在的條文這個最基礎的體系中加以理解,要考慮整個條文中其他用語和其他款項的規定,不可就詞語而解釋詞語,就款項而解釋款項。
第二層次——“中觀”的刑法典體系。對某一刑法條文進行解釋適用,必須充分考量條文與條文之間的關系、條文與章節之間的關系、總則與分則之間的關系,要將被解釋的具體刑法條文放在整個刑法典體系中進行解讀,不可斷章取義,不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第三層次——“宏觀”的法秩序統一體體系。對刑法規定進行解讀,在條文體系和刑法典體系的基礎上,應當將被解釋的刑法規定放在整個法律體系中進行衡量,注重被解釋的刑法規定與其他法律法規之間的整體協調,不能拋開法秩序的統一性和法律體系整體而解釋運用刑法規定。
第四層次——“全局”的刑法規范和社會情理價值相統一體系。對具體的刑法規定進行解釋適用,不能機械地就刑法規定解釋刑法規定,而是必須要充分考量到具體刑法規定背后的社會情理價值。即于歡案之后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所說的,要“將個案的審判置于天理、國法、人情之中綜合考量”。也就是說,對具體的刑法規定進行解釋時,要將其放在法律條文的規范邏輯和社會情理價值的有機統一體之中進行,不可機械解釋而導致損害公平正義。
因此,可以這樣界定刑法體系解釋,即刑法體系解釋是指對刑法用語和刑法條文進行解釋適用時,需要將其放在編、章、節、條、款、項當中,放在整個刑法典中,放在整個法秩序和法律體系中進行,同時也要注重法律條文背后的價值理念,進行4個層次的驗證,最終得出符合刑法用語和條文真實含義及其內含的以及法的公平正義理念的結論。
(二)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論之依據
1.規范結構之依據
刑法規范分為編、章、節、條、款、項,而其基本元素則是刑法用語,即“單字組成詞語,詞語組成句子,句子組成段落,段落組成文本”[8]。對刑法進行解釋時必須從單個用語開始,離開對單個用語含義的詮釋和界定,就不可能對刑法條文進行解讀,更遑論對刑法進行體系解釋。因此,對刑法進行體系解釋的最基本層次就是對刑法條文的用語和款項進行體系性的解讀,將具體的用語和款項置于同一個條文之中,科學闡釋其具體含義,完成“微觀”意義上的最基本的任務,使得對某一款項的解釋符合同一條文內部的協調統一。
具體的刑法條文又處在節、章、編和整個刑法典當中,對其解釋,必然要將其放在整個刑法體系當中進行,使得條文與條文之間保持協調、避免矛盾、減少對立,從而完成“中觀”意義上的體系解釋。目前,通識的觀點基本上將刑法體系解釋放在這一層次進行論證。
眾所周知,刑法只是眾多的部門法中的一種,只是鑲嵌在整個法律體系上的一個點,特別是隨著法定犯時代的到來[注]我國著名學者儲槐植教授早在2007年就提出,我國的法定犯時代已經到來。并指出,時至今日,給法定犯和自然犯做實質界定已經不可能完成,而只有從形式上給予界定,所謂法定犯,是指規定在除刑事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中的犯罪[15]。,對刑法的理解和適用離不開相關行政法規的規定,當然也需要與民法、訴訟法等部門法相協調,這就需要刑法體系解釋充分考量“宏觀”層面的法秩序的統一性問題,即刑法條文與行政法規之間,與民法、經濟法、公司法等部門法之間的體系性協調問題。
“徒法不足以自行”,單純地就法律規范解釋法律規范的方法是不科學的,特別是對于涉及人的生命、自由、財產的刑法的解釋運用,更不能只看法律規范本身的形式和邏輯,而不顧法律規范所內涵的以及社會公眾所賦予的社會情理價值。對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工具之一的法律進行解釋和運用,必須要與社會的情理價值相契合,或者說應該讀出法律規范背后的情理價值,因為“道德的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滅的人類感情為基礎的話,就別想建立起任何持久的優勢”[9]。因此,對刑法進行體系解釋,必須要將具體的法律規范與社會的情理價值相結合,使兩者協調,達到“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
2.認知規律之依據
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從初級到高級、從局部到整體、由表及里、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復雜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對文本的認識、解讀和適用,要先從單個的字開始,再到詞、句、篇、章,因為字構成詞、詞構成句、句構成篇、篇章組合成為文本,以此類推。在這一漸進的過程中,包含著普遍的認知規律和嚴密的邏輯進路,“各自有序而不可亂也”[10]。正如朱熹所言,應“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11]。當然,對文本的全面深刻理解也需要一定的生活閱歷,甚至是特定的社會背景,這是不言自明的認知規律。
對刑法進行體系解釋,就是對刑法條文進行正確科學的認知,而后將其運用到現實案件當中。這一認知過程當然需要遵循認知的規律,即要首先對刑法用語進行認知,再到語句、款項、條文、章節、刑法典整體,這一認知的邏輯思維圖示就是前文所提出的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的認知過程。然而,僅有這3個層次還不足以完成對刑法條文的科學認知和正確適用,還需要認知主體具有相當的社會閱歷并懷有正義理念,需要解釋者“運用‘事實經驗意識’和‘價值經驗意識’”[12], 讀到文字背后的社會價值,將刑法規范與社會情理價值相結合,以科學闡釋其含義,并運用到司法實踐當中。正如19世紀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所言,“沒有一種替天行道意念的人類力量,就不足以揮起行刑的刀劍”[13]。這種替天行道的意念,便是正義的理念,是社會的普世價值。因為,如果只關注刑法規范本身,而不將其與社會的情理價值相結合,將是機械地理解和運用,裁判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社會公眾的質疑和批判,也違反了刑法體系解釋的原則和要求。畢竟,“法律解釋并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只是一個枯燥乏味的形式問題,它包含著對各種基本法律價值的分析和判斷”[14]。
當下的刑法理論,由于缺乏對刑法體系解釋的分層次研究,所以關于體系解釋的邏輯關系問題也成為空白,有的只是不分層次的對刑法體系解釋運用時應當注意事項的論述。如德國學者英格博格·普珀指出,體系解釋是以不矛盾的要求、不贅言的要求、完整性的要求、體系秩序的要求4個要求作為出發點的[2]56。張明楷教授指出,體系解釋的具體要求是難以窮盡的,有避免矛盾、防止漏洞、保持協調、總則與分則的關系等要求,而要做好體系解釋,需要特別注重的是:合憲性解釋、以刑法總則規定為指導解釋刑法分則、同類解釋規則、刑法用語的相對性、對解釋結論的檢驗、以基本法條為中心、當然解釋原理的運用、對解釋結論適用后果的考察、法秩序的統一性等9個方面[16]。這些關于刑法體系解釋的各項具體要求中,看不出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內在的邏輯,而只是采取了簡單的列舉。列舉法雖然簡單明了,但是也存在難以窮盡和周延的邏輯弊端,并且邏輯上的雜亂無章往往會使解釋者有意無意地遺漏對列舉項的適用,更難以窮盡體系解釋所應遵循的所有方法。其結果便是將解釋者的思維帶入“雜亂無章”的困境,違背了人類認知事物所應遵循的漸進規律。而分層次的“微觀”→“中觀”→“宏觀”→“全局”這一漸進式認知,則是符合客觀的認知規律的應有路徑。
三、理論闡釋: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之詮釋
(一)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的內涵解析
“微觀”層次體系,即“刑法條文”體系,是指在對刑法規定的基本要素(刑法用語)和適用的基本單元(條文中的款項)進行解釋時,首先要考量的是具體的刑法用語和款項在其所在條文這個微觀系統中的含義,解釋的結論要與所在條文的其他用語和其他款項相協調,不得違背條文這個最基本的體系。因為,每個刑法條文都具有自身的體系性和整體性,而每個具體用語或者款項又處在具體的條文當中,所以對具體的用語和款項進行解釋適用,必須要在條文這個體系的規制下進行,不可就具體用語解釋具體用語、就具體款項解釋具體款項。
“微觀的條文體系”這一層次,需要理論研究者和司法實務人員高度關注的是兜底性條款。在對兜底性條款進行解釋時,必須充分考量其所在的條文體系這個微觀整體的邏輯要求和意義指向,要嚴格遵守同類解釋規則[17],使得解釋結論與明確列舉的款項在行為手段、行為類型、危險性質、危害程度等方面屬于同類,不可漫無邊際地不顧形式邏輯的制約和價值理念的規制而隨意做出解釋結論,進而違背公平正義理念。
“中觀”層次體系,即“刑法典”體系,是指對刑法用語和款項的解釋,在經過微觀條文體系考量之后,要將解釋結論再置于刑法典當中進行考量,要充分考慮此條文與彼條文的規定、條文與所在章節的整體性規定、分則與總則之間的規定等的相互關系,要保障解釋結論在整個刑法典體系之中與其他條文保持協調。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法律條文只有當它處于與它有關的所有條文的整體之中才顯出其真正的含義,或它所出現的項目會明確該條文的真正含義。有時,把它與其他條文——同一法令或同一法典的其他條款一一比較,其含義也就明確了”[18]。這也是當下刑法理論對刑法體系解釋的理解。刑法體系解釋的“中觀”層次需要考慮3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單個的條文與條文之間的關聯性、一致性問題,如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之間的關系,盜竊罪與職務侵占罪之間的關系,過失致人死亡罪和交通肇事罪之間的關系等,需要結合具體的案件事實對相關的刑法規定作出協調的解釋。二是具體的刑法規定與其所在章節的法益保護意旨、形式邏輯協調等問題。對具體的刑法規定所作的解釋,必須與章節體系保持協調一致,不得脫離甚至是違背章節對具體條文的規制。如侵犯財產罪的法益是財物,將扒竊犯罪作為行為犯處理就違背了章節對具體條文的規制,是不符合刑法體系解釋要求的。三是總則和分則的指導與依托關系問題。刑法總則離不開刑法分則,總則以分則為依托;同時,刑法總則對刑法分則具有補充、指導作用,刑法分則的運用離不開總則的指導和規制。這在理論上是不言自明的,在對刑法規定進行體系解釋時也是必須遵守的。如對犯罪主體的認定,需要受刑法總則刑事責任能力和刑事責任年齡的制約;對主觀的判斷,需要接受刑法總則故意、過失條款的指導。
“宏觀”層次體系,即“法秩序統一體”體系,是指對刑法規定進行體系解釋,在經過了微觀的條文體系和中觀的刑法典體系考量之后,需要再將被解釋的刑法規定放在法秩序統一體這個“宏觀”的體系中加以考量,使得對刑法規定的解釋適用與整個法秩序保持協調,避免出現破壞法秩序統一體體系的解釋結論。即,“‘體系’解釋要將個別的法律觀念放在整個法律秩序的框架當中,或者如薩維尼所說,在‘將所有法律制度和法律規范連接成為一個大統一體的內在關聯’當中來考察”[19]。這是因為,從邏輯演繹的角度來說,刑法具有部門法律的補充性、其他法律的保障性等特有屬性,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事訴訟法等共同組成了我國整體的法律體系,構成了整體的法秩序。刑法補充性和保障性屬性本身,決定了刑法條文與其他法律規范是相容相生的關系,因此,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適用不可能不關注其他法律,解釋結論需要與其他法律法規形成體系的協調。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說,刑法中多數罪名的判定,都需要與其他法律規定進行整體性解釋,特別是空白罪狀的適用和法定犯的認定,須臾不可脫離與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協調一致。如,對貸款詐騙罪的認定,需要借助《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貸款通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對被騙對象的貸款主體資格、借貸關系中貸款形式要件等進行具體的判定。
“全局”層次體系,即“規范邏輯與情理價值相統一”體系,是指對刑法規定進行解釋,既要充分考量具體法律條文的規范邏輯(包含條文體系、刑法典體系和法秩序統一體體系)層面的意義,也要充分考量具體法律條文所蘊含的社會情理價值,要使得解釋結論達到規范邏輯和情理價值的統一,符合規范邏輯和情理價值這一“全局”性的體系協調性要求。因為“任何規范都包含了立法者的利益評價,也就是價值判斷”,刑法規范自然不應例外,“所以,刑法解釋也就意味著在具體的案件中實現法定的價值判斷”[20]。體系解釋“不應存在規范矛盾和價值判斷矛盾”[21]。如果對刑法規定進行解釋的結論導致嚴重侵害法益的行為無罪,而輕微侵害法益的行為有罪,或者解釋結論導致重罪被判處輕刑,輕罪反而被判處重刑,這種解釋結論就是違背規范邏輯和情理價值統一體體系的;如果某種解釋違背了民眾的法感情,違背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的正義觀念,那么這種解釋就是不協調的,因而也是不正義的,是違背了刑法體系解釋要求的。只有既符合形式性的規范邏輯又符合實質性的情理價值的解釋結論,才是對刑法條文的科學解讀,據此做出的裁判才是真正的“合法的裁判”。如于歡案的一審判決,就法律規范論法律規范,忽視了法律規范所蘊涵的社會情理價值,導致判決結果受到公眾的討伐;而浙江昆山劉海龍一案的處理,則充分考量了“天理、國法、人情”,贏得了一片贊譽。
(二)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的邏輯關系展開
刑法體系解釋的4個層次,是一種循序漸進、從低到高的遞進式的邏輯關系,在運用刑法體系解釋這一解釋方法時,應當遵循“微觀”→“中觀”→“宏觀”→“全局”這一遞進式邏輯思維路線圖,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講邏輯順序地對刑法條文進行解讀和適用,因為正常的人類思維是有條理、有次序、有位階的,“混亂的思維過程無助于解決問題”[22]。四層次間的邏輯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四層次間的邏輯關系
從圖1和前面關于四層次論符合認知規律依據的論述可以看出,“微觀”“中觀”“宏觀”“全局”這4個層次之間存在著嚴密的邏輯關系。“微觀”層次是根基,是最基本的出發點,是整個體系解釋的基礎和基石所在,只有對基本法條進行正確合理的解釋才能更好地進行下一步的“中觀”層次的驗證。“中觀”層次是筋骨,是刑法體系解釋和整個刑事司法活動的中流砥柱,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承上就是刑法體系解釋必須遵循刑法條文的基本規定,堅守罪刑法定原則;啟下即應當對刑法用語、刑法條文的解釋進行指導和規范。“宏觀”層次是關鍵,其在“微觀”和“中觀”的基礎之上將刑法條文放在整個法律體系和法秩序統一體中進行考量,跳出了就刑法論刑法的視野。“全局”層次是靈魂,是在全面把控法律條文的規范邏輯的同時,重點關照法律條文所蘊涵的情理價值,強調法律條文的規范邏輯和社會的情理價值兩者的統一,既考慮罪刑法定原則視野下的“國法”,又通盤考慮法的存在所依賴的“天理”和“人情”,最終達至終極意義上的體系協調,實現法的正義理念,即我們一直強調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
刑法體系解釋的4個層次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的,因為作為一種法律規范,“它的每一個用語、條文或規定都必須考慮到整個法律體系;而整個法律體系也必須考慮到它的個別用語、條文或(及)規定”[23]。在這一有機的體系當中,4個層次間存在著由低到高、由局部到整體的遞進式的邏輯關系,但是這種遞進式的認知圖示和邏輯思維路線并不是單向制約的關系,而是雙向互動的關系,具體表現為:“在解釋刑法語義意義時,應當以字、詞入手,分析句子的結構、含義和條文之間的聯系,掌握刑法的內在精神;再以此為起點,重新審視句子,考量詞語,分析用字,經過這樣的穿梭循環,往復逡巡,達到對刑法基本語義的準確把握。”[8]232
當然,在刑法體系解釋過程中,“微觀”→“中觀”→“宏觀”→“全局”這一遞進式邏輯思維路徑是不可顛倒的,罪刑法定原則必須成為刑法不受任何挑戰和破壞的鐵則,對行為人進行刑罰處罰,必須以刑法明確規定為依據,否則,再惡劣的行為都不得成為刑法調整的對象。而“微觀”→“中觀”→“宏觀”恰恰是處在罪刑法定的層面,是在遵循客觀規律和認知邏輯的前提下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現實演繹。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將法律規范邏輯和社會情理價值相結合,來規制人們的行為,構建安全穩定的社會秩序。在運用刑法體系解釋過程中,不能先從法律的規范邏輯和社會情理價值這一層次來進行邏輯展開,一方面是因為這樣的邏輯進路違背認知規律,另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情理價值易受到“權力”和“理性缺席的民意”的“綁架”,有侵犯人權、違背罪行法定原則的危險。雖然“價值選擇從根本上講純粹是任意的,根本不能納入理性的辯護或批判的范圍”[24]這一評價有過于武斷之嫌,但是也從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價值判斷所具有的缺陷。“價值判斷對于法律文本的沖擊也必然經常影響到法律判斷的穩定”,“罪刑法定原則這樣具有普適價值的刑法鐵則,不斷經受著價值多樣性的考驗”,因此,“必須對價值判斷加以規制”[25],亦即,不能將刑法體系解釋的第四層次——“全局”放在第一層次。
四、實踐檢驗: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視角下王力軍收購玉米案的解決路徑
2016年4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臨河區法院的一紙判決,將通過收購玉米補貼家用的當地農民王力軍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期2年執行,并處罰金2萬元,沒收違法所得6 000元。判決指出,被告人王力軍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在未取得相關執照的情況下,收購當地散戶農民種植的玉米,倒賣給巴彥淖爾市糧油公司,經營金額20余萬元,獲利6 000元,其行為違反了《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觸犯了我國《刑法》第225條第(四)項規定,構成非法經營罪。該案經媒體報道后,引起廣泛關注。201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再審決定書,令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再審。2017年2月17日,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宣判,認為王力軍的行為雖然違反了《糧食流通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但沒有達到構成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撤銷原判,改判無罪。
對王力軍收購玉米案的處理,從刑法體系解釋層次論角度來看,應當對所適用的具體條款進行“微觀的條文體系”“中觀的刑法典體系”“宏觀的法秩序統一體體系”“全局的規范邏輯與情理價值體系”遞進式檢驗,以驗證解釋結論是否符合刑法體系解釋的原理。在本案中,一審判決運用了《刑法》第225條第(四)項規定,而該項的具體規定為:“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就要求在應用這一項規定時,必須首先將其放在整個法條中加以解讀適用。然而,一審判決卻無視同一法條內部的體系性結構,將僅僅違背了《糧食流通管理條例》的行為上升到刑法的角度進行懲罰。對于該案,如果從同一法條內部體系協調的角度來看,應當作為無罪處理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刑法關于非法經營罪的規定首先就是“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并明確列舉了3種具體的情形,最后才是這一兜底性的條款。一方面,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在本案中,王力軍收購玉米的行為并沒有擾亂市場秩序,相反卻在農民和糧食收購站之間搭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不但無害反而有益,因此并不屬于“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情形;另一方面,刑法用語“其他”“等”顯然與該條明示性的規定應該處于同一位階,從行為上來說應該是性質、手段、類型等方面具有同等性,從結果上來說也應當具有同等性。即,將具體的案件事實用兜底性條款來處理時,該案件事實的行為和結果必須與明示的行為和結果具有對等性。王力軍案的一審判決所引用的第(四)項,顯然在行為和結果上都與前3項以及本條的總規定不符,即該案一審的處理結果違背了上文所提出的刑法體系解釋層次論的第一層級——“微觀的條文體系”。
如果說上述分析只是理論推演的話,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的態度可以說代表了司法實務界的權威。這一權威分析認為,我國《刑法》第225條第(四)項所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是在本條所明確列舉的3類具體非法經營行為基礎上的兜底性條款,司法適用時應當特別慎重,“相關行為需有法律、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且要具備與前3項規定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嚴格避免將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當作刑事犯罪來處理”。這一司法權威觀點鮮明地指出,對本條第(四)項的適用和解釋應當運用體系解釋的原理,并進一步指出,“就本案而言,王力軍從糧農處收購玉米賣予糧庫,在糧農與糧庫之間起了橋梁紐帶作用,沒有破壞糧食流通的主渠道,沒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且不具有與《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前3項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不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26]。即一審判決違背了刑法體系解釋層次論的原理,違背了系統性解釋刑法兜底條款的要求[27]。按照刑法體系解釋四層次的解釋原理,如果第一層次就出罪的話,也就沒有必要進行下一步的論證分析和檢驗,至此,便可以認定王力軍的行為并不構成非法經營罪。即使繼續推演論證,我們也會發現,王力軍案一審判決沒有考量到社會危害性這一總則指導思想,違背了“中觀的刑法典體系”;不加區分地將行政法規運用到刑事案件當中,違背了“宏觀的法秩序統一體體系”;無視王力軍行為在當下社會的價值和公眾對王力軍行為的肯定性評價,不顧人們基本的法感情或者說“常識常理常情”,同樣也違背了“全局的規范邏輯與情理價值體系”。
五、結語
刑法體系解釋是一種重要的刑法解釋方法,需要理論界的深入挖掘和司法實務界的高度重視,需要司法人員培養科學的法律思維能力和精致的法律論證能力[28]。特別是理論研究上,要突破現有研究的藩籬,打破預設的概念、方法和思維邏輯的束縛,從法條本身的規范結構和人類的客觀認知規律出發,突破“中觀”的刑法體系解釋概念的窠臼,向下關注刑法條文本身這一“微觀”體系,向上關注整個法律體系這一“宏觀”體系和法律規范邏輯及社會情理價值這一“全局”體系,全方位、立體化地對刑法體系解釋進行思考。并且要嚴格遵循4個層次之間的邏輯思維路徑,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可違背規范結構和認知規律而隨意調整4個層次之間的邏輯關系。具體而言,刑法體系解釋要依次從“微觀”→“中觀”→“宏觀”→“全局”4個層次把握、運用、驗證和考量對刑法規定的解釋結論,使對案件的裁判符合規范邏輯和情理價值,使蘊含于法律規范背后的公平正義理念得到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