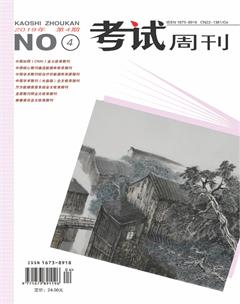迪士尼動畫中花木蘭形象探析
摘 要:美國迪士尼動畫在改編異域童話、民間傳奇時,通過添加故事情節及配角,以此補充或反襯出主角的性格特征,塑造了追尋自我價值實現的女性形象。迪士尼動畫《花木蘭》(Mulan)改編自中國古代傳奇故事,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戰功卓著、功成身退等故事情節,與中國南北朝樂府詩《木蘭詩》中的表述大體一致,但動畫片增添了花木蘭相親、愛情等情節及守護神木須龍等配角,這使得動畫電影的主題思想發生了變化。迪士尼動畫以西方的表現方式,闡釋個人英雄主義、女性意識、民主自由等美國文化精神。現以迪士尼動畫《花木蘭》為中心,與中國南北朝樂府詩《木蘭詩》相比較,探討花木蘭的精神成長歷程。
關鍵詞:迪士尼動畫;花木蘭;形象
一、 質疑自我
動畫片《花木蘭》開始部分,花木蘭被人盛裝打扮,加入相親隊伍。家人期望她嫁個好人家以光宗耀祖。但是,生性活潑熱愛自由的木蘭,顯然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要求女性的三從四德標準。木蘭相親失敗,被媒婆指責為“永遠不能為家族爭光”。花木蘭處處不合時宜,時時遭遇尷尬,她對著水中倒影,唱出心中的困惑:“我看見的女孩是誰?……何時我的倒影,能映出真正的自我。”自我懷疑與追問是女性意識覺醒的前提,體現了花木蘭潛意識中對實現自我價值的渴望。
此時,匈奴犯境,國家征兵,花木蘭年邁傷殘的父親在被征之列。《木蘭詩》中花木蘭做好出征前的準備工作,“朝辭爺娘去”,在親人的牽掛中出征。花木蘭替父從軍體現的是忠孝兩全的中國傳統文化觀,“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重男輕女、家庭榮譽、集體觀念、效忠國家等固有價值觀念都在這一長詩里得到表達,木蘭也只是為了盡孝道而參軍。”而迪士尼動畫片中,花木蘭在相親失敗,受到眾人嘲笑,傷心、迷惘、反思自己之際,恰好遇到皇帝征兵詔書,于是才穿上父親的盔甲,女扮男裝偷偷地踏上征程。國家征兵只是花木蘭實現自我價值的導火索。而自我質疑、自我價值的追尋是激起花木蘭從軍的重要現實因素,這一情節安排體現了中西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二、 尋找自我
關于戰爭,《木蘭詩》中的描述言簡意賅,“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短短幾句詩歌概括出戰爭的持久、激烈、悲壯。戰爭的勝利是花木蘭和戰士們同甘共苦、視死如歸換來的,是集體戰斗的結果。而迪士尼動畫中則更加細致地展示個體是戰爭取勝的關鍵:大軍遭遇匈奴強敵伏擊時,花木蘭機智準確地判斷軍情,發射火炮擊中高山積雪,將來勢洶洶的匈奴大軍淹沒于雪崩中,從而扭轉戰局,上演了以少勝多的傳奇戰爭場面。剛參軍時笨手笨腳的花木蘭,經過戰爭的磨煉,終于成長為機智勇敢的戰士。
然而,花木蘭在戰場上受傷治療時,暴露了她的女性身份。軍隊將會受到欺君之罪的連累,木蘭被遺棄在荒寒之地。她在絕境中自我反思:也許我參軍不是為了救我爹,我只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希望對鏡自照時,我能看到真實的自己。明確了參軍的真正意義后,花木蘭不再消沉與猶豫,當她發現單于的殘余軍隊混入京城,木蘭一路跟隨并警示京城護衛。但是,沒有人信任恢復女性身份的花木蘭。單于挾持皇帝,千鈞一發之際,花木蘭智救皇帝,救了國家,花木蘭終于以女性身份獲得君民的尊敬與認同。
《木蘭詩》中,花木蘭自始至終以男性身份參軍,戰爭結束后功成身退才恢復女兒身,“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而花木蘭也以未被識破身份而自豪:“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男尊女卑、忠孝兩全是《木蘭詩》最突出的主題。而迪士尼版花木蘭在征戰時身份就被識破,但她以女性身份自救并救了君臣,獲得了皇帝的賞識。這顯示了迪士尼公司刻意打破男女性別界限,突出女性意識的一貫努力。
三、 確認自我
較之《木蘭詩》,迪士尼動畫片增添了兩個重要配角:李翔和木須龍。前者是花木蘭所在軍隊的將軍,也是與她相愛之人;后者是花木蘭從軍時的守護神。《木蘭詩》回避了愛情描寫,更為突出地表現忠孝主題。而迪士尼動畫則增加了花木蘭和李翔在共同戰斗中產生的真摯感情。這使得故事更加充滿生活氣息與人情味,木蘭不僅僅是戰場上的勇士,也是充滿活力的感情豐富的女子。
《花木蘭》續集《花木蘭2》算得上迪士尼原創故事:正在籌備婚禮的木蘭與李翔接到皇帝密信,命令他們護送三位公主與鄰國王子結婚,以期通過和親結成同盟,對抗強大的外敵。李翔順從地接受任務,而花木蘭則面露驚訝,大膽質疑這場舍棄女子個人幸福的包辦婚姻、政治婚姻。針對和親事件,李翔的家國責任感強烈,他指責花木蘭:“責任、義務、傳統,你都不在乎。”而花木蘭說李翔是個“好戰士,勇敢、忠誠,但卻忽視自己的內心”。花木蘭漸漸覺醒的女性意識與自由思想,與李翔的忠君思想及集體主義精神之間產生分歧。李翔的角色設定,更加反襯花木蘭現代女性意識的覺醒。
而另一重要配角木須龍,對花木蘭的性格塑造具有補充作用。這一添加的角色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龍的形象與文化內涵。花家祠堂的這只身材瘦小、外形像蜥蜴的小龍,一直不被重視,為了證明自己,冒充神龍成為花木蘭出征時的守護神。木須龍角色除了推動劇情的曲折發展,增加劇情的幽默與喜劇色彩,最為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它使花木蘭的形象更具立體感,性格更加豐富多彩。與木蘭的初次見面,木須龍借助火光的映照,將自己的身形放大,龐大的身影使木蘭也大吃一驚。這一舉動暗示了木須龍內心的不自信,并渴望自己強大的愿望。這與木蘭當時的處境及追求自我價值的愿望是一致的,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
當花木蘭女性身份暴露時,木須龍哀嘆:“差一點木蘭就成英雄了,祖宗就會對我刮目相看。這下完了。”木須龍并沒有將木蘭參軍上升到忠君救國的高度,在它眼里,木蘭參軍是“為救父親的命,沒想到卻讓他顏面盡失,朋友也失去了。你得嘗試看開些”。木須龍自私、狂妄自大、虛榮心重,但它勇于自我剖析,“咱倆都是冒牌貨,花家祖宗沒有派我來。你犧牲自己救人,我卻利用你救我自己,至少你比我善良”。在它的鼓勵與引導下,木蘭更加明確了自己的內心渴望。就像木蘭所說:“沒有你,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花木蘭2》)木須龍驕傲地宣稱:“拯救中國給了我莫大的榮耀。”(《花木蘭2》)從開始相處時亂出主意的任性,到勝利在望卻功虧一簣時的懊惱,木蘭拯救中國后的驕傲等,木須龍身上的人性化表現很好地襯托出木蘭從自我懷疑,到追求自我價值的復雜心靈歷程,這使花木蘭形象更加生動可感。
四、 完善自我
其實,在跨文化傳播中重新塑造主角,是迪士尼動畫一貫的創作實踐。動畫片中常常通過添加配角,塑造體現美國現代文化的主角形象。這些主配角之間有多重關系,包括親人、主仆、敵友等關系,以此襯托主角的個性與復雜的精神世界,如木須龍與花木蘭的關系,迪士尼動畫片《冰雪奇緣》中的雪人奧洛夫、雪怪與艾莎公主的關系。《冰雪奇緣》改編自安徒生童話《白雪皇后》(The Snow Queen),但故事情節與人物形象做了大改動。童話中的冰雪皇后是一個邪惡的形象,但動畫片中的艾莎(Elsa)公主則兼具魅力與魔力,其復雜形象與動畫片中添加的配角雪人與雪怪密切相關,它們分別是愛與恐懼的化身。
童話中的白雪皇后冷漠無情,是惡的化身。而動畫片中的艾莎公主性格則復雜得多,她在童年與妹妹安娜玩耍時,曾制造出可愛的雪人奧洛夫,給姐妹兩人帶來無窮的快樂。成年后的艾莎在加冕禮時,情緒失控冰凍了王國,她逃到深山盡情釋放魔力,高唱“Let it go”:“展現自己,沖破極限……世界由我,放寬心,向前進”時,再次制造出雪人,并賦予它生命與情感。雪人是快樂、純真、善良的化身,它陪伴前來尋找艾莎的安娜公主,并告訴安娜“愛”的含義:“愛就是把某個人看得比自己重要。”雪人成為兩姐妹之間愛的紐帶。而艾莎情緒失控時創造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雪怪,代表著她內心的恐懼。這兩種力量集中在艾莎身上:對妹妹的隱忍深沉的愛,對自己無法控制的魔力的恐懼。最終,艾莎與安娜終于憑借真愛的力量,控制了魔法。較之于早期迪士尼動畫片《白雪公主》中的鳥兒及《灰姑娘》中的小老鼠等動物,雪人與雪怪形象更具人性化色彩,它們是艾莎公主內心世界的外化,使艾莎的性格更加豐富立體。艾莎內心愛與恐懼的糾纏,展示了女性追尋自我的歷程中必經的精神歷練。
迪士尼動畫在改編與原創故事中越來越注重時代審美變化,在一系列的關于冒險、愛情、親情等傳統故事的講述中,更加注重“追尋自我”“表現自我”的主題。注重親情、肩負責任又努力做回自我的艾莎公主、花木蘭等女性形象,獲得了中外觀眾的普遍認同。
參考文獻:
[1]賈冀川,何森.好萊塢電影的中國想象——近年來好萊塢電影對中國文化元素的“拿來主義”[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42-47.
作者簡介:
譚默涵,江蘇省南京市,南京金陵中學河西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