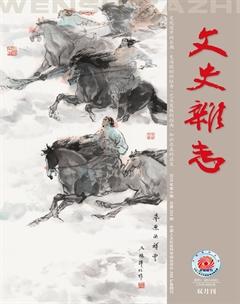試探稷下學宮的特點和性質
趙志堅 陳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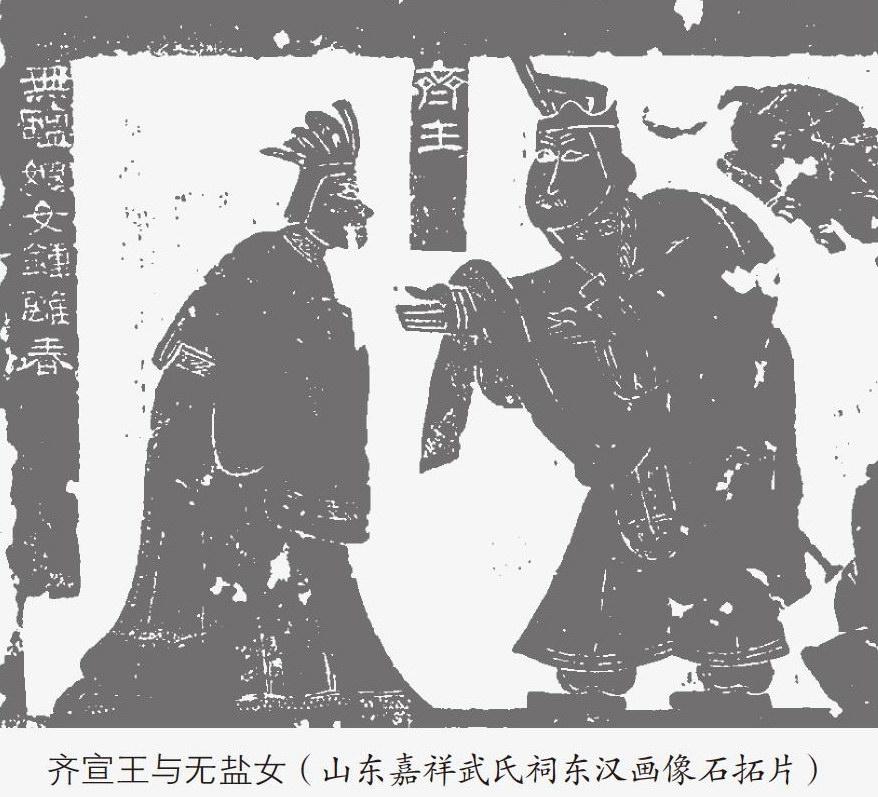

摘要:作為戰國時期學術中心與教育中心的稷下學宮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游學為主,來去自由;各家并立,平等共存;百家爭鳴,自由辯論;相互吸收,融合發展。在戰國時期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土壤中,稷下學宮集智囊機構、學術中心、教育中心于一體。稷下學宮的多重功能是有機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其政治功能是以學術活動和教育活動為基礎實現的,而其學說功能又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通過教育的實踐活動來傳播和實現的。
關鍵詞: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特點;性質
一、稷下學宮今安在?
稷下,本意為稷門之下。稷門,是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的城門之一。《史記集解》注引劉向《別錄》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明確了稷下與稷門的關系。稷門為何城門呢?《太平寰宇記》卷十八“益都”下注引《別錄》說:“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史記索引》注引《齊地記》說:“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址)往往存焉。”《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居處部三·堂》記載:“臨淄城西門外,古有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七《郡國志》也說:“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為稷下學。”由這些記載可知,稷門就是臨淄城西城門,而“講室”“講堂”就是稷下學官。稷下學官就建筑在稷門之下、系水之側。稷門是齊國都城郭城(大城)的一座著名的門道。該門道是聯系城內外的一條交通干道,依城傍水,景色宜人。稷下學宮就設在這里,是知識分子聚集的理想場所。大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淄水》中也這樣認為:“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考古發現和文物普查證明,在當年的稷門附近、系水旁邊,即今天的邵家圈村西南隅有一處規模相當可觀的戰國時期的建筑遺址。考察遺址可以看出,當年這里的建筑群規模宏大,很符合關于稷下學宮“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等文獻記載。這一帶建筑遺址就是稷下學宮所在地。
稷下學宮創建于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于齊威王時期,興盛于齊宣王時期,中衰于齊閔王時期,中興于齊襄王時期,衰亡于齊王建、秦滅齊時期。稷下學官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相始終,并隨著田齊國勢的強弱而興衰。田齊政權以稷下學官為基地,招攬天下文學游說之士數百千人,其中有淳于髡、孟軻、鄒衍、彭蒙、宋钘、慎到、田駢、兒說、王斗、環淵、接子、季真、尹文、田巴、鄒爽、荀況、魯仲連等著名學者,人稱“稷下先生”。齊國統治者為稷下先生設置了“上大夫”之號,“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勉勵他們著書立說,講習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當時的儒、墨、道(黃老)、法、名、兵、農、陰陽、小說、縱橫家等各派的著名人物,紛紛登上稷下學宮的講壇,大力宣傳和傳播本學派的思想理論,駁難其他學派的觀點,從而奏出了一曲百家爭鳴的交響樂。這樣,稷下學官成為諸子薈萃的學術園地和百家爭鳴的場所。許多著名人物,如孟子、荀子、顏斶、李斯、韓非、公孫龍等,都曾來稷下學宮游說和游學。稷下學宮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和教育中心。因此,郭沫若先生說:“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的。”
二、稷下學宮的特點
作為戰國時期學術中心與教育中心的稷下學官,既發揚光大了西周官學的辦學形式,又綜合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長處,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點。
1.游學為主,來去自由
游學是來稷下學官的學者們及弟子們的主要活動形式。徐斡《中論·亡國》記載:“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游于齊。”應劭《風俗通義·窮通》則說:“齊威、宣王之時,孫卿(荀子)有秀才,年十五來游學。”《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亦記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不論是孟軻之徒游說于齊,還是齊宣王招致的稷下先生多是文學游說之士,都說明游學是來稷下學宮的學者們及其弟子們的主要活動形式。游學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既有如荀子的個人游學,也有如孟子之徒的集體游學。
齊國統治者對于來稷下學宮的天下游士,來者不拒,去者不止,還歡迎去而復返。如孟子曾兩次進出稷下學宮,都受到齊國統治者的禮遇;荀子也曾兩進兩出稷下學宮,仍居稷下祭酒的顯位;鄒衍曾離齊去魏、趙、燕等國講過學。稷下師生來去自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國學術相互交流。
稷下先生之所以來去匆匆,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因為當時有名望的學者在各諸侯國都受到尊重和禮遇,他們都不以物質待遇為念,他們所關心的是統治者能夠采納其道、接受其諫。他們皆以言行合則留,不合則去為原則;一旦發現道不同不相為謀,就立即離去。如孟子第一次來稷下時,未受到齊威王的重視,離去時威王以“兼(好)金一百”與之,孟子不僅沒有接受,反而責備威王以貨取君子。孟子第二次來稷下時,受到齊宣王的重視,位列客卿。齊伐燕取得勝利后,齊宣王未聽從孟子的撤兵建議,結果燕人叛齊。齊宣王覺得愧對孟子。孟子覺得宣王對他雖“禮貌未衰,言弗行”,便決心再次離齊。齊宣王以“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的條件挽留孟子,孟子以不貪富貴拒絕了。
2.各家并立,平等共存
稷下學官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舉凡儒、道、墨、法、名、陰陽、縱橫、小說、兵、農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稷下舞臺上。各家學派,由于階級、階層、政治傾向、地域文化、心理結構、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理論學說。
由于齊國統治者實行開放、寬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對各家學派在政治上沒有什么限制和框框。盡管各家學派政治主張不同,思想學說各異,齊國統治者卻不以好惡而褒貶,這就保證了各家學派平等共存,自由發展。雖然齊國統治者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歷史階段,面對不同的現實問題,對諸子之學的取舍、選擇、利用有所不同和有所側重,但是這并不影響各家學者在政治上具有平等地位,也不妨礙學者們自由探討、開展爭鳴的權利。如孟子的仁政學說,在齊威王時沒有被重視;齊宣王時,起初頗受當權者的青睞,后因被人認為不切實用而束之高閣。然而,這并沒有削弱孟子在稷下學宮的地位,齊王對其仍能優禮有加。鄒衍的“五德終始”理論,“王宮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引起朝野上下的思想震動,一時間鄒衍“重于齊”,齊地出現了“陰陽五行熱”;后因其“不能行之”,當權者對其興趣大減,但仍允許其廣泛傳播。黃老之學的道法思想,在齊國統治者那里得到了持久的重視,在稷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然而黃老者并沒有獲得高于其他學者的殊榮。綜觀稷下學宮發展的歷史,儒、道、法、陰陽學派曾在不同時期取得相對優勢,但都未能長久占據絕對優勢。
總起來說,無論稷下諸子持何種學說,是否適合統治階級的現實政治需要,都能在稷下存在、發展;當權者非但不加干預,還積極創造條件,鼓勵他們各引一端,上說下教。各家學派在這種寬松的文化、社會環境中,共存并立,自由發展,共同促進了稷下學宮繁榮學術局面的形成。
3.百家爭鳴,自由辯論
稷下學宮的前期,正值齊國封建制度剛剛確立,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成熟思想理論尚未出現。齊王急切地尋求適合其政治需要的上層建筑以鞏固其統治,特別是齊威王、齊宣王和齊閔王的前期尚有一統天下的雄心,因此,他們都鼓勵稷下師生進行理論探討。各家學派在學術上一律平等,實行沒有明文規定的百家爭鳴和自由辯論的原則。各家學派力求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學說為齊王所采納,齊王則擇善而用之。各派學者雖然誰也沒有權力強迫別人放棄其學說,但都希望以自己的理論說服對方,為齊王所采納,為社會所公認。各家學派相互間展開了學術論爭,使稷下學官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
稷下學者多為能言善辯之士。淳于髡人稱“炙轂過髡”,以“滑稽多辯”著稱于世。孟子“好辯”,是當時著名的雄辯家。田駢人稱“天口駢”,鄒衍號“談天衍”,鄒爽被稱為“雕龍奭”。兒說亦是“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田巴是“齊辯士”,“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宋钘、尹文“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不下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其他如王斗、顏周、荀子、魯仲連等,也都善辯名析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稷下的“文學游說之士”沒有不善辯的。如何看待稷下學者能言善辯?孟子回答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荀子更明確地提出:“其誰能以已之譙譙,受人之掝掝者哉。”又說:“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在這里,孟子和荀子道破了百家爭鳴的機關所在一辯則興,不辯則亡。
在稷下學官,學術辯論之風盛行。淳于髡與孟軻爭論何者為“禮”,孟軻與宋钘說“義”談“利”,兒說與稷下學人辯論“白馬非馬”,田巴與稷下學士辯析“性善”論,批判宋钘的“情欲寡淺”說,攻擊嗔到、田駢的“道法”論,揭露諸子之學的理論缺陷;鄒衍批駁儒家的“中國即天下”思想,揭露詭辯家們的邏輯錯誤。稷下先生還和齊國的當權者辯。淳于髡曾兩次與齊威王辯論,與宰相鄒忌也有一次辯論,這三次辯論對齊國的政局有良好的影響。孟子經常同齊宣王辯論,有時使宣王無話可說,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上述論爭駁難,既有不同學派之間的思想論戰,又有同一學派內部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理論紛爭;既有同輩學者之間的理論探討,又有稷下先生與稷下學子之間的對話、批評;既有學者之間的學術研討,又有先生與齊王、宰相之間的論辯;既有面對面的切磋、溝通,又有書面文字上的論說、爭鳴;既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悉心求證的學術研討,又有各抒己見、據理力爭、咄咄逼人的思想交鋒。論辯中,學者們或是“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或是“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自是而非人”;或是“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這一系列的“相辯”反映了稷下學宮活躍的學術氣氛。
通過“相辯”,解決了一些列重要問題,并開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如孟子與告子關于人性之辯,揭開了古代人性研究的序幕。最典型的論辯要算是魯仲連和田巴之辯。稷下先生田巴“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徐劫的學生魯仲連年且十二,人稱“千里駒”。魯仲連認為田巴是夸夸其談,不切實際,面對齊國的危境提不出辦法來,于是登臺與田巴辯論:“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蕓,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愿先生勿復言。”這一席話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抽象的理論問題轉移到現實問題上來,從而折服了田巴。從此以后,田巴終身不談,后棄文從武,為齊將。田巴是先生,是名家;魯仲連是學生,是儒家。他們之間的辯論,既是學生和先生之辯,又是儒家與名家之辯。
歷代齊王不獨尊一家,而任諸子百家自由論爭,但各派在稷下學宮的地位常常時起時伏。一般而言,在一段時間內,哪個學派首領的學術水平高、威望大,哪個學派就居于首要地位,但也不能獨踞講壇。黃老學派人多勢眾,有名望的學者眾多(如接子、環淵、宋钘、尹文、季真、彭蒙等),他們在稷下常常處于顯要地位。從齊桓公田午到齊威王時期,淳于髡學識淵博,地位顯赫,又有弟子三千人,這時稷下學宮受他的思想影響較大。齊宣王時,孟子第二次來稷下學官,位居三卿。在七年多的時間中,孟子同宣王頻繁接觸,無所不談,僅《孟子》中就記載了十七處。孟子有徒數百人,在稷下宣揚仁政學說,抨擊楊墨,這時的稷下學宮則是儒家思想占顯要地位。齊襄王時,荀子再次來稷下,一直呆了十四年左右,“最為老師”,并“三為祭酒”,這時的稷下學宮自然是儒家思想占據顯要地位。從魯仲連與田巴之辯中可以看出,襄王末年名家曾一度占了上風,后被魯仲連壓下去而代之以儒家。魯仲連為稷下先生時,已是稷下學宮的末期了。
4.相互吸收,融合發展
激烈的學術論爭、思想交鋒,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知識,振奮了人們的精神,鍛煉、提高了人們的思維能力和認識水平。在辯論中,諸子百家之學的理論優勢充分展示出來,同時各自的理論缺陷亦逐漸暴露。如田巴名家學說的形而上學、不切實際在爭鳴駁難中暴露出來就是一典型例證。這就迫使人們以開放的心態和積極進取的精神,研究新問題,吸收新思想,更新舊觀念,克服自身的理論缺陷,在論戰中不斷修正、完善、發展自己的學說。
激烈的學術論辯加速了不同學派之間的思想滲透、融合。如孟子的性善說,保赤子之心,養浩然正氣,清心寡欲的思想,就吸收了道家的一部分思想。又如淳于髡學無所主,思想比較博雜,禮、法兼重。當然,這時的相承還不是主流,而相非才是主流。到了戰國末期,各國相繼完成了封建化的過程,全國統一的條件已成熟,出現了人心思治和學術求一的新形勢。諸子百家經過長期的爭鳴逐漸認識到,只有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才能獨樹一幟,為社會所接受。這樣,新形勢下的諸子百家的論辯不再以相非為主流的百家爭鳴的面目出現,而代之以相承為主流的融合發展的方式出現。這種轉變,既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在思想界的反映,又是學術界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論稷下的哪一學派,從其學術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其他學派的思想蹤影。各家各派注意融合其他學派的思想,形成了“融合發展”的學風。在稷下學官末期,出現了兩個綜合家的思想體系:一是因道合法,兼采儒墨之善,撮名、法、陰陽五行之要,而自成體系的黃老學派;一是以儒家為主體,集諸子各家之大成的荀子。尤其是荀子,從儒家學派出發,揚棄諸子各家之說,匯通百家之學,刻意求新創造,建立起一個龐大、完整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對百家爭鳴的批判性總結。
三、稷下學宮的性質
對于稷下學宮的性質,前人多有論及,眾說紛紛:有的認為稷下學官具有研究院性質,有的認為稷下學宮是“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有的認為稷下學官是齊國的議事、咨詢機構。其實,稷下學宮是當時特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條件下的產物,其性質是多重的,詳述如下:
1.稷下學宮是齊國的智囊機構
田齊政權創辦稷下學官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天下賢士的聰明才智,為鞏固田氏統治進而實現統一服務的,用齊王的話語說就是“有智為寡人用之”。為了用其“智”,齊王不僅給稷下先生以祿位,提供優厚的待遇,而且做到了禮賢下士,經常虛心聽取和征詢他們的各種意見;稷下先生也可以隨時進諫齊王,闡述自己的思想主張。
稷下學宮吸引的對象是戰國時代十分活躍的“士者流”,即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稷下學宮進行研討、爭辯、講學、集會等各種活動,大都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新序·雜事》記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也記載:“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都是說稷下先生的議論、著書立說與政治緊密相聯。稷下先生淳于髡曾用隱語諫齊威王,使其戒“長夜之歡”,從消沉中振作起來;他又以“微言”說鄒忌,敦促其變法革新。《戰國策·齊三策》》還記載淳于髡在“齊欲伐魏”的關鍵時刻,及時向齊王分析了形勢:“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成其后”,從而阻止了齊王的一次錯誤行動。淳于髡還直面批評齊宣王“好馬”“好味”“好色”,而獨不知“好士”,迫使齊宣王“嘿然無以應”。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僅《孟子》一書就有17處之多,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在《梁惠王》上、下兩章里,齊宣王向孟子咨詢的問題就有“齊桓、晉文之事”“齊王之囿”“交鄰國有道乎”“齊人伐燕,取與勿取”“諸侯多謀伐齊,何以待之”“賢者之樂”“明堂可毀諸”“王政可得聞與”“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等9處。而孟子主動向齊宣王進說的內容還有“四境不治,如之何”“國君進賢……可不慎與”“幼而學,壯而行,不可舍其所學而從我”等多處。此外,齊宣王向尹文請教“人君之事何如”;齊閔王與尹文論“士”;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稷下先生的思想理論,明顯地影響著田齊政權的內外政策,對齊國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另外,還有一些稷下先生奉齊王之命,肩負外交重任,出使別國。例如,鄒衍曾出使趙國;淳于髡曾“為齊使于荊”,并在“楚大發兵加齊”時受齊王之命“之趙請救”。
上述材料說明,在列國紛爭、兼并激烈的形勢下,為稷下所吸引、招徠的稷下學士,并不是醉心于學術爭鳴而逃避現實的隱者之流,而是熱衷于社會現實的風云人物。正是這些風云人物,使稷下學官成為田齊政權的智囊機構。
2.稷下學宮是百家爭鳴的學術中心
稷下學宮雖然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它不是政治的附庸,稷下先生也不同于依附于諸侯的一般政客。稷下先生們有知識,見聞廣,長于思辯。他們除了議政之外,還相互議論,著書言事。他們的議論、著述,盡管針對著目前的現實,但往往旁征博引,曲盡事理,具有很高的理論性和學術性。例如荀況,“序列著數萬言”,講“正名”,述“王制”,論“解蔽”,明“天論”,倡“惡性”,以致激烈地“非十二子”,這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發表見解,而是帶有一定的理論抽象和較多的學術成分。
稷下學官時代,思想文化領域沒有公認的圭臬和定于一尊的權威,眾多的學者積極探求現實社會的出路。由于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有異,因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案也不同。他們極力宣傳自己的學說和主張,駁難、批判其他人的學說和主張,從而形成了學術百家爭鳴的繁盛局面。大量的文字材料表明,稷下先生們經常展開學術討論,同時也舉行定期的集會。劉向《別錄》記載:“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期會,即約定時間集會。這就是說,稷下學士們在約定的時間內,聚會于稷下學官,進行學術、文化交流。
在稷下學官,不同學派的稷下學者們大都熱衷于“作書刺世”,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漢書·藝文志》記錄了一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和篇數:荀子的《孫卿子》三十三篇,環淵的《蜎(環)子》十三篇,田駢的《田子》二十五篇,接子的《捷子》二篇,鄒衍的《鄒子》四十九篇、《鄒子始終》五十六篇,鄒爽的《鄒爽子》十二篇,慎到的《慎子》四十二篇,尹文的《尹文子》一篇,宋钘的《宋子》十八篇。就思想傾向而言,班固將《孫卿子》歸為儒家,《娟(環)子》《田子》《捷子》歸為道家,《鄒子》《鄒子始終》《鄒奭子》歸為陰陽家,《慎子》歸為法家,《尹文子》歸為名家,《宋子》歸為小說家。僅就班固所見,稷下先生的著述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其思想內容是豐富而復雜的。此外,孟軻的《孟子》、魯仲連的《魯仲連子》以及《管子》的部分文章,大體上也是在稷下醞釀編寫而成的。這么一大批著作的涌現,對于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稷下先生們研究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邏輯、法學、天文、地理、醫學等學科,探討天人、心物、知行、陰陽、動靜、道氣、道法、禮法、義利、名實、王霸、法先王與法后王、人性的善惡、形神等問題。他們既研究現實的社會問題,又反思人類的歷史,還描繪未來的社會藍圖。稷下學官作為如此眾多著名學者的聚集之地和如此眾多學術著作產生的園地,成為當時中國的學術中心。
3.稷下學宮是培育人才的教育中心
稷下先生在“論國事”“干世主”“成文典”的同時,還廣收門徒,授業解惑,積極從事教育活動。在稷下學官,有各種形式的講學活動,還舉行定期的集會。通過這些教育活動和集會,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才。因此,稷下學官又具有培育人才、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性質,是一所較高層次的教育機構。
稷下學官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稷下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稷下學宮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田駢本是彭蒙的學生,成為稷下先生后又“貲養千種,徒百人”。孟子出行,“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中著名的弟子有公孫丑、萬章、公都子、陳臻等十幾人。宋钘在稷下“聚人徒,立師學,成文典”,“率其群徒,辯其談說”,可見其弟子不少,影響也很大。其他如兒說、慎到、接子、荀況等,均有眾多門徒。據《史記·田齊世家》記載,齊宣王時,整個稷下學官的師生人數多達“數百千人”。這些說明,稷下學宮是一個傳播文化知識、培養和造就人才的教育中心。
稷下學官還具有獨特的教育特點:第一,游學是其教育方式之一。學生可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老師可以自由地在稷下招生講學。可以個人來游學,如荀子;也可以如孟子一樣,數百從者—起來,有人稱其為團體游學。這些游學方式的施行,使學生們開闊了視野,增長了學識,促進了各種學說的發展和新學說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第二,理論聯系實際。齊國的統治者創辦稷下學官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一是吸引和培養人才,以便為國家選賢任能;二是利用稷下的講壇,為鞏固其統治、實現統一霸業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探討。“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都充分說明稷下的講壇是以議論、講授與政治有關的內容為主的。理論聯系實際是稷下先生教育活動的鮮明特點。第三,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稷下先生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大力開展學術研究活動,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留下了豐富的學術著作。正因為稷下學宮在教育方面所具有的諸多鮮明特點,所以才被后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
稷下學官集智囊機構、學術中心、教育中心于一體。在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土壤之中,稷下學官的多重功能是有機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其政治功能是以學術活動和教育活動為基礎實現的,而其學說功能又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通過教育的實踐活動來傳播和實現的。
稷下學宮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學校,它雖由齊國統治者創辦,但其基本細胞是私學。各家來去自由,齊王不僅不阻攔,還采取來者不拒、去者贈送路費的政策。因此,稷下學官是一個官辦之下有私學、私學之上是官學的自由聯合體。正由于此,英國的李約瑟教授稱稷下學官為“稷下書院”。他說:“在中國,書院的創始可追溯到這個很早的時期。其中最有名的是齊國首都的稷下書院。”這段話道出了稷下學官官私合辦、自由講學的性質。稷下學官可謂后世書院之淵源。同時,稷下學官還是由西周官學、春秋私學到漢代太學的過渡形態。把握住稷下學官,就找到了由西周官學到漢代太學的中間缺失環節,從而把整個官學發展史連貫起來。因此,稷下學宮既有官學性質,又具有私學性質。具有二重性的稷下學宮,實是由私學向官學過渡的形態,這是由戰國時期的特殊歷史條件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