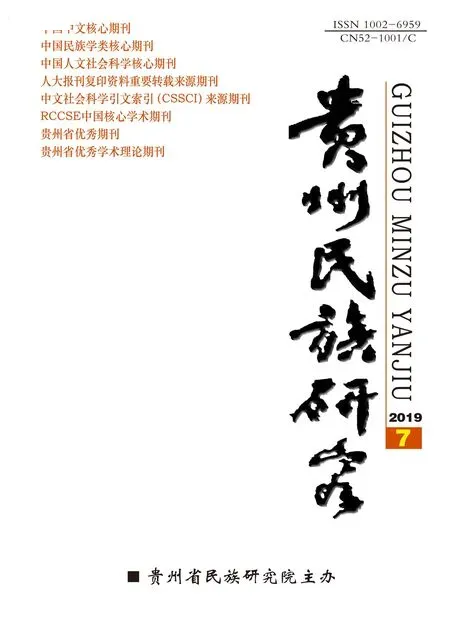苗族“吃鼓藏”儀式音聲文化闡釋
——以貴州省從江縣加勉鄉黨翁村苗族“吃鼓藏”儀式為例
譚 卉 鄧 江
(1.廈門大學 人文學院,福建·廈門 361005;貴州師范大學 音樂學院,貴州·貴陽 550001;2.貴州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貴州·貴陽 550001)
一、黨翁村苗族“吃鼓藏”儀式音聲文化生態
(一)自然地理環境
黨翁村是貴州省從江縣加勉鄉政府駐地,是典型的苗族傳統村落,地處月亮山腹地,污留河、加模河流經該村,至亞溫河再注入都柳江,村寨周圍梯田層疊。受歷史、地理等因素制約,該村經濟發展緩慢,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工作的推進以及新農村建設政策的實施,黨翁村于2004年完成了通村公路的建設,2010-2011年完成全村新村建設,產業結構主要以林業、礦產、香豬飼養、經濟作物種植(水稻、雜交玉米等)為主。
(二)社會文化概況
黨翁苗族屬苗族加勉支系,自稱“蒙”,為加鳩苗族支系近親支系之一,其姓氏主要有龍、韋、梁、王、潘、吳、李、田等,服飾為月亮山系加勉式,語言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中部方言南部土語。黨翁村苗族傳統文化積淀深厚,民族傳統節日主要有開秧節、栽秧節、新米節、苗年節、鼓藏節等。
“吃鼓藏”,又稱“吃鼓”“祭鼓”“吃牯臟”“鼓社”,是苗族以血緣、地緣為紐帶進行的大型祭祖儀式,加勉苗語稱“諾牛”“努牛”,這一表述后來被規范為“鼓藏節”。根據歷代漢文獻關于苗族“吃鼓藏”習俗的記載,通過實地調查,筆者認為歷史上沿著苗族遷徙路線分布著一個狹長的“吃鼓藏”(“吃牯臟”)文化帶,目前主要孑遺于貴州黔東南、黔南地區部分苗族村寨,在此區域內,少量的侗族、水族村寨也存在“吃牯臟”習俗。因地域、民族支系的不同,各地苗族“吃鼓藏”儀式及音聲各具特色。苗族“吃鼓藏”按舉辦周期的不同,可以分為定期和不定期兩種類型,定期鼓藏以3、5、7、9、13年為期,不定期鼓藏情況比較復雜,何時“吃鼓藏”主要根據“鼓藏”征兆,鬼師占卜(“破蛋”“看米”)結果,宗族(主要是鼓藏頭、寨老)商議來決定。按獻祭的犧牲的不同可分為牛鼓藏(即黑鼓藏,又分水牛、黃牛)、豬鼓藏(即白鼓藏)、混合型(牛鼓藏與豬鼓藏兼有)三種。以黨翁村為代表的加勉苗鄉“吃鼓藏”習俗屬不定期混合型鼓藏。龍氏祖祖輩輩都有“吃鼓藏”傳統,民國時期吃過“鼓藏”,建國后至文革前,黨翁龍氏舉辦過一屆“吃鼓藏”活動,文革期間,“吃鼓藏”活動被禁止,龍氏舉辦上屆“吃鼓藏”是在1983年。
二、黨翁村龍氏第三年“吃鼓藏”儀式音樂文化考察實錄
(一)儀式中的各種角色
黨翁龍氏“吃鼓藏”儀式參與者包括宗族所有成員及其親友。鼓藏頭(“該扭”)、祭司、寨老、鬼師是儀式組織籌備者,儀式管理人員由宗族選舉代表擔任,負責協調工作的主要是來自各級政府(主要是當地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及工作人員,儀式現場其他人員則包括街坊鄰里、游客(少量)、媒體記者、科研人員等。根據調查,黨翁地區的“該扭”通過“世襲”產生,這種身份的“承襲”不能超過3屆。“該扭”換屆需符合以下幾個條件:“祖宗來找”,出現鼓藏的征兆,鬼師“破蛋”占卜,宗族內部決議(寨老主持)。在雷山、臺江等地,“該扭”則是通過家族世襲或者由宗族內部推選德高望重、家庭和睦、懂得儀式規矩的人擔任。寨老是宗族內部的權威人物,知識淵博,德高望重,是地方精英的代表。祭師是“吃鼓藏”儀式中的執儀者,共12人,是儀式中與祖先魂靈、一切神祇交流的“使者”,通過鬼師“破蛋”,與“該扭”、寨老進行確認,儀式本身增強了其“權力化身”與“神奇符號”的身份,祭師的存在亦使“儀式”變得“超凡”與“神秘”,祭師的權力僅在祭師群體內部傳承,是一種制度性傳承。“鬼師”即巫師,因其自身可以“通靈”的特殊能力,成為儀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通過占卜來確定鼓藏頭、12位祭師,以及“吃鼓藏”舉辦的日期。
(二)黨翁苗族“吃鼓藏”儀式空間
“吃鼓藏”儀式作為黨翁苗族日常生活最核心的民俗事項,是存續于“鄉土”的特殊“景觀”,“吃鼓藏”儀式音聲實踐始終依存于儀式特定之時空。黨翁苗寨之中心由鼓藏場、鄉政府建筑群組成,“鼓藏棚”即設置于附近,龍氏宗族各戶住宅(干欄式)散布于周圍,其間穿插各種生產生活設施,諸如禾倉、牲棚、商店等,道路和河流從村寨中間通過,黨翁苗寨的寨門已被拆除,僅有守寨樹作為符號,標識出村寨的邊界,墳墓、田地、樹林則位于村寨的邊緣。根據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黨翁龍氏“吃鼓藏”儀式音聲空間可劃分為物理、社會、心理三個層面,其物理“空間”,包括家宅(陽宅)、鼓藏棚(因“吃鼓藏”臨時搭建之“祖廟”)、墳墓(陰宅)、鼓藏場、道路等。通過人的“在場”,以及儀式(含音聲)行為,這些場所被賦予社會的、文化的意義。比如“博朗”儀式中,巡游隊伍的路線為“該扭”之“家宅”——村寨道路——郊野(墳墓)——鼓藏場——鼓藏棚——“該扭”之“家宅”,形成一個“圓”的循環體,象征著時空的“流動”與生命循環往復之輪回。祭祀巡游隊伍一定要從“該扭”之“家宅”出發,這是“該扭”身份與權力的體現,家宅也被視為“祖宅”,具象地保留了人類生存方式的歷史記憶,承載著復雜的文化元素與親屬關系,象征著“祖”。龍老義(男,76歲,貴州省從江縣加勉鄉黨翁村人,為黨翁村龍氏“吃鼓藏”儀式的“神東”,從江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鼓藏節”代表性傳承人)把“鼓藏棚”比喻成“(祖)廟”,“吃鼓藏”期間,祖先魂靈即被請入并棲身于此,棚內置新制的木鼓(祖靈棲身處)、板凳,懸掛弓箭及柴火(象征苗族古代社會漁獵生活),鼓藏棚待“鼓藏”關(結束)了以后即棄置。黨翁苗族認為死者靈魂不滅,它們在墳墓中處于休息的狀態,“吃鼓藏”時,它們會出現在那里,必須通過儀式與它們進行交流,把它們請到“該扭”的“家宅”、鼓藏場、鼓藏棚,“吃鼓藏”結束又必須把它們送走,宗族所有人得以恢復日常的生活。黨翁苗寨“吃鼓藏”儀式空間是族群歷史記憶再現之場域,映射出因祖先崇拜所形成的社區心理空間、社會空間與物理空間之間的協調,是超越“日常生活結構”之“反結構”的特定文化時空,“時間”與“空間”的疊加,實乃苗族魂之所系的精神家園,“吃鼓藏”儀式音聲借此以其特有的呈現連接了過去與現在,成為區分社區局內與局外、我者與他者的文化象征符號。
(三)“吃鼓藏”儀式舉辦的原因
根據龍老義所說,從江加勉地區苗族吃鼓藏活動的舉辦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第一,必須呈現“吃鼓藏”征兆(夢見故去老人);鼓藏頭家庭成員重病不愈,就醫無效,甚至家人相繼死亡;家中水缸有蛇出現;“火塘”邊長蘑菇;婦女頭發極難梳理。第二,鬼師“破蛋”來看,一旦確定“鼓藏”來了,宗族內部由寨老出面設立籌備組,通知宗族各戶派遣代表前來商議,并請鬼師“破蛋”遴選祭司。根據龍老義所說:“在過去,‘老古代’很久沒有子孫祭奠,它們就來家找(麻煩),鬼師‘破蛋’來看,確定是‘鼓藏’來了,就必須舉辦‘鼓藏’紀念(祭祀)它們,不同意舉辦的,‘老古代’會來病他。”這是苗族“靈魂不滅”“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之具體反映。
(四)“吃鼓藏”儀式所用祭品
黨翁苗族“吃鼓藏”儀式使用的祭品分為犧牲(牛、豬、鴨、魚、竹鼠)、糧食(糯米)、飲料(酒、茶)、麻、祭器(碗、盆、鍋、竹篩、芭蕉葉、柴)。龍老義說:“過去,老古代吃糯米飯抵餓,有力氣干農活”。“糯米飯”有黏性,象征著龍氏整個宗族的團結。龍老義說:“酒的香味可以讓老古代(祖先)聞到,曉得我們喊它來喝酒,把酒灑到木鼓上面,老古代才得到喝,把酒灑(灌注)在地上,其他神啊、孤魂野鬼些才得到喝”。當地人認為奇數是吉利的,偶數則不然,祭品數量為奇數。根據龍老義、梁老幺(男,72歲,貴州省從江縣加勉鄉污扣村人,為污扣村梁、韋氏“吃鼓藏”儀式的“神東”)所說,公鴨隱喻為引領祖先魂靈上陰路,腌魚隱喻為苗族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乘舟渡于江河湖海的景象,腌魚即為“舟”。鼓藏節祭品之處理方式有“燔燒”(主要是禾晾)、“灌注”“瘞埋”“沉沒”“懸投”。
(五)黨翁龍氏“吃鼓藏”儀式過程
“吃鼓藏”周期為三年,從2013年至今,黨翁龍氏“吃鼓藏”已滿三年。根據調查,本次黨翁龍氏“吃鼓藏”儀式群包括15個分支儀式:“迎客”“醒鼓”“博朗”“伐木圍欄”“抬豬入欄”“驗豬”“驅祟(殺雞)”“驗牛”“殺牛祭祖”“殺豬祭祖”“迎朗”“敬棚”“滾豬頭”“關鼓藏棚”“送客”。
三、苗族“吃鼓藏”儀式音聲文化內涵
(一)“吃鼓藏”儀式音聲分析
苗族“吃鼓藏”儀式音聲指的是以聲音為媒介,以儀式時空為依托,以宗教信仰為目的,發生于儀式過程中有意義的音樂與聲響,其貫穿了苗族“吃鼓藏”儀式始終,是儀式不可或缺之組成部分。經調查發現,因受地域、民族語言系屬等因素的影響,沿著“苗疆走廊”分布的各地苗族“吃鼓藏”儀式音樂文化既有“共同性”,亦有其各自之“特殊性”。黨翁苗族“吃鼓藏”儀式音樂從內容與場合來看,可劃分為神圣與世俗兩種類型:一是與儀式過程中各種儀軌相應,由祭司唱(奏)給苗族祖先、亡靈、神祇、孤魂野鬼等非現實對象聽的,即為法事音樂,其按照祭祀對象的不同,可再細分為祭祖樂、祀神樂、齋醮(超度亡靈)樂。二是由除祭師外其他人員(宗族內部及其賓客)于宴飲等場合演唱(奏)的,則為禮俗音樂,可細分為禮賓樂、宴飲樂(酒歌、情歌、古歌)等。根據發音體(源)不同,又分為人聲與器聲兩種類型。
1.人聲
“吃鼓藏”儀式過程中,屬于法事音樂的聲樂體裁包括誦(鼓藏)經調、祭祀歌、其他(念誦、呼喊、哭聲、笑聲、說話等,屬音聲),屬于禮俗音樂的聲樂體裁則包括宴飲場合演唱的禮俗歌(酒歌、情歌、古歌)、其他(呼喊、說話、哭聲、笑聲等,屬“音聲”)。
(1)誦 (鼓藏)經調
誦(鼓藏)經調是是一種近似念白的唱腔,所吟誦的經文為祭師時代口耳相傳的《鼓藏經》,按內容分為三類:《祭祖辭》(《召祖辭》《贊祖辭》《祭祖辭》《祈禱辭》《送祖辭》)《祀神辭》《齋醮辭》。《祭祖辭》運用于“吃鼓藏”儀式過程中所有法事之前部(開始)或后部(結束),具有重要的結構性意義。《祀神辭》主要運用于吃鼓藏過程中“酬神”系列儀式,如“博朗”“迎朗”之《鼓藏經·祀神辭》,主要用于祭祀宇宙萬物之神,包括日神、月神、風神、雨神、樹神、動物神等,這是苗族“萬物有靈”宇宙觀的具體呈現。《齋醮辭》主要運用于吃鼓藏過程中超度亡靈系列儀式,如“敬棚”之《鼓藏經·敬棚》的內容則是超度龍氏宗族各戶為之舉行公祭的家庭成員之亡靈,又如“驅祟(殺雞)”之《鼓藏經·驅祟》,內容主要是超度孤魂野鬼。總的說來,鼓藏經具有“巫樂”之屬性,辭藻華美,講究格律,唱詞奇句、偶句之句末皆需押韻,具有“詩性”特征。從音組織上來看,采用三音列,五聲音階,使用羽商混合調式,采用三度框架,構成“羽-宮-角”核心音程關系,旋律以商音為起音,音樂以級進為主,圍繞調式骨干音進行上下環繞式波動,落音為羽音,轉調發生在結束句,從腔詞關系來看,字多腔少,從字數上看,以五言、七言為主,歌曲主要是以上下腔為基礎的原始歌謠體,具有分節歌的特點,具有口語性特點,歌曲節奏為均分律動性,后十六的節奏型比較典型,速度為56拍/ 分鐘,吟唱時,祭司根據內容進行節奏、旋律、潤腔之即興變化。
(2)祭祀歌 (鼓藏歌)
祭祀歌(鼓藏歌)是一種富于音樂性的唱腔,唱詞內容與其所做法事密切關聯,代表曲目有《祭祖歌》《頌祖德》《古老歌》等。其中,《古老歌》內容廣泛,涉及民族或家族的歷史、傳說、遷徙、生產、生活等諸多方面。根據龍老義介紹,苗族“吃鼓藏”儀式繁冗,祭師操持法事時,必須秉承“老古代”規定的“一件事一首歌”的傳統,根據龍老義所說,黨翁“吃鼓藏”儀式祭祀歌曲共計360首(其中應包含部分重復儀式之曲目),諸如“驗豬”儀式中之《唱歌給豬聽》,“修(鼓藏)棚”儀式(龍氏第1年“吃鼓藏”系列儀式之一)中之《鼓藏歌·修鼓藏棚》,“殺牛祭祖”儀式中《鼓藏歌·送牛回老家(上陰路)》等。祭祀歌常置于“吃鼓藏”儀式過程中所有法事之中部(誦(鼓藏)經調之后),祭祀歌僅一個基本曲調,專曲專用,受地域、民族系屬等因素的影響,各地所用祭祀歌曲調亦不相同。祭祀歌的唱腔源于苗語的自然調值,以及其種種自然組合,因苗語屬于單音節表意式語種,調值豐富,故其腔調富于音樂性。演唱時,腔幅隨唱詞變化而作相應之增減,速度為48拍/分鐘,句首常有“擻腔”,旋律仍以級進為主,較之誦(鼓藏)經調更顯跌宕,為上下兩匹腔之分節歌,羽商混合調式,字少腔多,更顯典雅、沉郁、抒情,演唱多使用真聲,喉音,鼻音的運用很有特色。其作為“旋律框架”之三音列,實乃蛻變于其歷史語音流變的符號,具有穩定性,成為該族群歷史文化之“基因”代碼。
(3)禮俗歌
禮俗歌,具有世俗性特點,按照內容分為酒歌、情歌、訓誡歌、迎客歌、送客歌等類別,分別適用于“吃鼓藏”儀式過程中之宴飲、迎客、送客等場合。禮俗歌的演唱主要位于“吃鼓藏”系列儀式所行法事間歇之間,置于法事音樂之后進行,曲調較為豐富。歌詞內容反映了黨翁苗族豐富多彩的禮俗文化。
(4)非音樂類人聲
非音樂類人聲包括咒語、呼(吶)喊、哭泣、歡笑等。以“抬豬入圍欄”儀式中人們的吶喊為例,筆者認為這是“吃鼓藏”儀式過程中獨具特色的無伴奏人聲多音復疊形式,娛神兼以娛人,近似于“勞動號子”,其以“喂”音節為音聲結構元素,節奏為彈性均分律動型,吶喊遒勁有力,此起彼伏,強弱對比明顯,產生出一種連續不斷,復音層疊的藝術效果,極具感染力,于協調勞動節奏的同時,生動再現了苗族先民的勞動場景,通過儀式音聲之實踐,有效喚起宗族成員關于“久遠過去”的集體記憶,增強了族群之情感及文化認同。
2.器聲
黨翁苗族“吃鼓藏”儀式中的器樂體裁主要有四種類型:獨奏樂、合奏樂、樂舞配樂、其他(儀式中各種響器之聲音,包括人之肢體碰撞、接觸所發出的聲響,比如鼓掌、跺腳等,另有鞭炮聲、伐木聲、汽車鳴笛聲、壓路機轟鳴聲等)。按其演奏場合又可分為祭祀樂與禮俗樂。“吃鼓藏”儀式使用的樂器包括木鼓、蘆笙、莽筒。
(1)木鼓
黨翁龍氏“吃鼓藏”儀式使用的是木鼓,加勉苗語稱“堆扭”,長約四尺有余,鼓身由楠木制成,鼓兩頭由牛皮蒙制而成,木鼓具有祭器、樂器的雙重屬性,分為獨奏、齊奏、合奏三種形式,木鼓樂與舞蹈結合形成木鼓舞,與雷山、臺江地區不同的是,黨翁“吃鼓藏”儀式過程中并無“木鼓舞”,其主要作為信號傳遞(召集族人)、祭器,作為樂器演奏時,相對其他地區更顯古樸、原始。
(2)蘆笙
黨翁龍氏“吃鼓藏”儀式使用傳統的6管蘆笙,由笙斗、笙管、吹管、簧片、共鳴筒組成,笙斗材質為杉木或桐木,簧片為銅片制成,分為大(低音)、中(中音)、小(高音)三種形制,按演奏形式可分為獨奏與合奏(蘆笙、莽筒、木鼓)兩種形式。蘆笙獨奏樂如“敬棚”儀式中的《鼓藏蘆笙曲·敬棚·蘆笙語》,曲調模仿“蘆笙語”(“神東”念誦咒語、鼓藏語),專曲專用,苗族認為“蘆笙語”具有可通神的“魔力”,借此與祖先溝通。“吃鼓藏”期間用于法事的蘆笙合奏樂,當地人稱為“祭祀蘆笙”,演奏者皆為男性,其樂器編制為:3支6管6音的高音蘆笙,3支6管3音的中音蘆笙,3支6管1音的低音蘆笙,與3支莽筒(小、中、大3種形制)。曲目僅有1首,即《鼓藏蘆笙曲·祭祖曲》,鼓藏節期間運用于非法事活動中的蘆笙樂,當地人稱為“寨上”(世俗)蘆笙,代表曲目有:《蘆笙曲·踩歌堂》等。蘆笙樂與舞蹈結合為蘆笙樂舞,即“跳蘆笙”。“博朗”“迎朗”儀式中的蘆笙樂舞具有祭祀性,是鼓藏蘆笙與祭祖舞蹈的結合,主要用于祀神,首先由小蘆笙吹奏引子,然后蘆笙、莽筒齊奏,蘆笙吹奏旋律部分,莽筒則作為持續低音進行。蘆笙樂為多聲音樂,調式豐富,由于與舞蹈結合緊密,蘆笙樂的節奏、節拍比較規整,小蘆笙清越脆亮,中蘆笙音色飽滿遒勁,大蘆笙音色渾厚低沉。節奏上看,“博朗”“迎朗”儀式中,踩歌堂所用的蘆笙樂舞,是“寨上”蘆笙與禮俗性舞蹈的結合,具有世俗性,是鼓藏蘆笙與祭祖舞蹈的結合,蘆笙演奏者皆為男性,女性隨樂翩然起舞,主要用以娛人,曲調歡快,使用混合節奏型,莽筒則主要作為合奏樂器使用,當地人認為,兩支莽筒“相斗”,極有趣味,而蘆笙必須與“莽筒”相配才會“好聽”。
(二)“吃鼓藏”儀式音聲文化內涵
1.“吃鼓藏”儀式音聲符號系統及結構
格爾茨認為“符號是概念的可感知的系統表述,是固定于可感知形式的經驗抽象,是思想、判斷、渴望或信仰的具體體現”。儀式是一個符號整體,作為苗族“吃鼓藏”儀式的結構要素,“吃鼓藏”儀式音聲以“音響”為媒介,通過其自身系統將象征符號與意義結合并使意義符號化。黨翁苗族“吃鼓藏”儀式音聲象征系統以儀式結構為組織原則,其主干儀式“殺牛祭祖”系由“迎客”“醒鼓”“博朗”“伐木圍欄”“抬豬入欄”“驗豬”“驅祟(殺雞)”“驗牛”“殺牛祭祖”“殺豬祭祖”“迎朗”“敬棚”“滾豬頭”“關鼓藏棚”“送鼓”“送客”等由15個不同的“分支儀式”組成,每個分支儀式群都有一個核心,每個分支儀式有著與儀式相應的固定曲體結構模式,這個模式作為一種重要的曲體結構“元編碼”,貫穿于幾乎每一個分支儀式音聲中,使得冗長繁復的儀式音聲具有嚴密的邏輯性、結構性,使得儀式音聲群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這個模式依托于儀式本身,指向儀式的核心“祭祖”,具有重要的曲體(式)學、文化學意義。
2.“吃鼓藏”儀式音聲符號的象征與隱喻
“吃鼓藏”儀式音聲蘊含豐富的“地方性知識”與“民間智慧”,具有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譬如儀式過程中吟唱的《鼓藏經》《鼓藏歌》,內容涉及族群起源、遷徙、生產、生活等各個方面的知識。根據龍老義敘述,黨翁龍氏宗族于明末清初從湖南遷徙至貴州榕江,至羊達,再至加鳩,最后到達黨翁定居,歌詞再現了苗族先民遷徙場景,而“博朗”“迎朗”儀式中,巡游以蘆笙開路,沿著“鄉村公路”走向鼓藏棚,這是對于苗族先民遷徙的隱喻,是對苗族苦難歷史的集體記憶,“道路”能指為苗族先民遷徙之路,是苗族的“心路”,是從世俗通往神圣的必由之路,是生死之間的循環往復,而鼓藏棚能指為“家園”“棲居地”。
“吃鼓藏”儀式音聲符號象征系統,反映出苗族宗教信仰以及其社會倫理道德觀。(木)鼓曾被廣泛用于苗族先民的信號傳遞、狩獵、祭祀、樂舞,軍事等方面,苗人深信其祖宗魂靈棲身于鼓,若想得祖先庇佑,鼓社須“祭鼓”,兼以歌舞樂饗祖先亡靈,祭鼓實則“祭祖”,并形成了“祭鼓”的系列程式。“鼓”即是“祖”,其秩序正是黨翁龍氏宗族成員逐漸分享共同集體記憶的方式,并由此認識世界,從而加強了族群認同,這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吃鼓藏”儀式音聲符號亦是苗族社會政治、權力的象征。“吃鼓藏”儀式音聲符號使用限定于儀式特定時空,其知識的傳承僅限于歷代宗族祭師群體內部,“神東”年逾古稀,在鼓藏節儀式過程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吟唱(坐唱、立唱與走唱)時雙目微閉,唱辭多用“鼓藏語”,吟誦曲調古樸典雅、含蓄深沉,其“言語”隱喻僅對“局內人”產生意義指向,象征著“神圣”與“古老”。
四、結語
以黨翁村為代表的加勉苗族“吃鼓藏”儀式,其過程隆重、神秘、繁復,是苗族原始宗教的“活化石”,是苗族古代社會“鼓社制”的孑遺,體現了生活在月亮山腹地苗族對祖先不變的崇敬與虔誠。在“全球化語境下社會轉型”雙重時空坐標中,中國面臨著全球化外力推動及社會內在轉型的雙向互動,“吃鼓藏”儀式作為黨翁苗族日常生活最核心的民俗事項,是鄉土社會與自然的契合,是不可替代的遺產類型。“音聲”是“吃鼓藏”儀式不可或缺的結構要素,是儀式深層意義及靈驗性體現的重要媒介,具體呈現了“音樂——行為——思想”之間的關系及動力,儀式音聲符號象征系統的生產及使用,預計其所蘊含的地方性知識,對于“非遺”語境下苗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具有理論及實踐的雙重價值。黨翁“吃鼓藏”儀式音聲實踐始終依存于儀式特定之時空,是存續于“鄉土”的活態“遺產”,是當前方興未艾的城鎮化過程中“地方性”之于“全球化”的適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