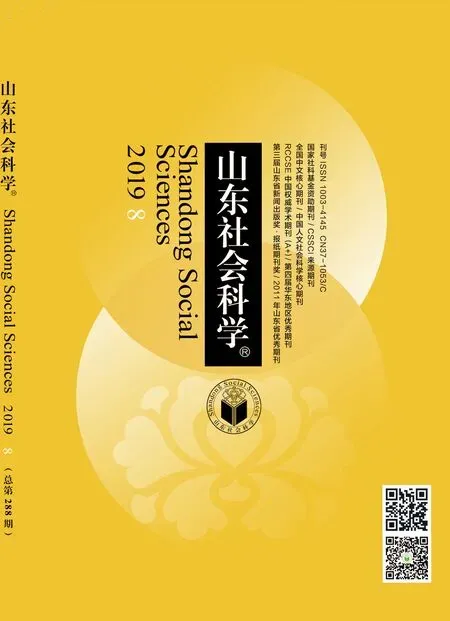從“孤立性”到“情境性”:刑罰威懾理論的認知視野轉向
李中良 畢憲順
(魯東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山東 煙臺 264025)
濫觴于貝卡里亞、邊沁的刑罰威懾理論(以下簡稱“威懾理論”)自建立以來無論是在犯罪學理論推進方面還是犯罪預防實踐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績,成為近代乃至現代刑事立法與司法模式的理論基石并一直支配著刑罰的制定、適用與執行。然而,自威懾理論提出以來,質疑聲、批判聲也一直不絕于耳,威懾理論改進勢在必行。
一、威懾理論認知視野的孤立性困境
威懾理論認為,具有“理性”能力和“自由意志”的問題青少年會先將具體的犯罪苦樂或犯罪成本、收益事實轉化成大腦可以操作的抽象符號系統,然后在大腦中對犯罪利弊表征符號予以理性權衡、算計,當運算出“犯罪之弊大于犯罪之利”的認知結果時,他們就會產生害怕、敬懼等心理狀態并在其支配下基于“自由意志”而放棄犯罪,威懾效能生成。威懾理論把威懾效能看成是封閉于大腦中的“中間加工、處理”階段認知博弈的結果,而認知結果在運算出來之前需要刑罰信息、犯罪目標信息等的輸入和表征,認知結果運算出來之后則需要支配相應的行動,威懾效能形成過程就由“刑罰信息、犯罪目標信息等的輸入、表征-犯罪利弊理性權衡、算計-犯罪利弊博弈結果輸出并支配相應行動”三個環節組接而成,這正如阿佩爾(1)Robert Apel,“Sanctions, Perceptions, and Crime: Implications for Criminal Deterrence”,in J Quant Criminol,Vol.29(2013),p.71.構建的“感知威懾基本模型”將宏觀的靜態威懾理論還原為“刑罰信息-刑罰感知-威懾效能”的微觀動態環節那般。很顯然,威懾理論對威懾效能形成機制的“看待方式”與以計算機為隱喻的第一代認知科學將認知過程看成是“信息輸入-中間加工、處理-信息輸出”的思想在本質上如出一轍。在威懾理論那里,威懾效能形成機制是問題青少年在心理層面對犯罪利弊的理性權衡、算計,這種理性博弈過程既是一種認知過程,也是一種計算過程,因此,威懾理論在闡釋威懾效能機制時無形中滲透著第一代認知科學所秉持的“認知可計算”綱領。以主客二元對立哲學觀為思想基礎建立起來的第一代認知科學把認知看作基于一定邏輯規則的符號表征-計算,這一認知觀的孤立性困境在第二代認知科學的“映照”下逐漸由“模糊”走向“澄明”。信息加工心理學的抽象性是忽視、抹殺外在情境在認知過程中的應有作用,威懾理論認知視野受此鉗制而不可避免地被動“沾染”上此番困境。基于信息加工心理學理論視角,威懾理論的核心是問題青少年在“中間加工、處理”階段對犯罪利弊的理性權衡、算計,威懾理論認知視野忽視了犯罪利弊理性博弈所必然牽涉的環境和背景知識,這直接導致了它的孤立性困境并使其在面對受外在情境影響較大的青少年犯罪類型時有心無力。
二、基于孤立性困境的威懾理論修正進路
刑罰威懾遏制犯罪的關鍵是利用刑罰產生的威懾力在問題青少年的心理或認知層面施加“犯罪之弊大于犯罪之利”的壓力,并借助這一壓力形成的害怕、敬懼心理狀態使他們放棄犯罪,所以威懾效能形成機制是一種認知形成機制,威懾效能是問題青少年在心理層面形成的一種認知結果。認知科學發展到今天,認知總是情境化的觀點已經成為學界共識,正如人工智能專家布魯克斯指出的,“認知主體處在一定的環境中,它們不涉及抽象的描述,而是處在直接影響它們行為的情境中”(2)Rodney Brooks,“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47(1991),p.139.。既然認知深植于環境之中,那么作為一種認知結果的威懾效能的形成過程就必定會受到外在情境的制約和影響。威懾理論把威懾效能形成機制看作脫離環境的、局限于大腦內部的對犯罪利弊的理性加工、計算,刑罰威懾力彰顯于問題青少年在心理層面對犯罪苦-樂或犯罪成本-收益的脫域運算結果,然而“依照這樣一種模式……對于心理操作的探求和對環境‘污染’因素的規避使得認知心理學家產生了對計算機的極大依賴……因而丟棄了社會歷史變量的考慮”(3)Isaac Prilleltensky,“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in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Vol.11(1990),pp.127-136.,因此,必須根據情境認知理論重新審視威懾效能形成機制以修正威懾理論,即實現威懾理論認知視野由“孤立性”到“情境性”的轉向。當情境認知被廣泛應用于人工智能、教學實踐、計算機支持協作學習和虛擬學習共同體建構等領域并卓有成效之時,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情境認知會協助威懾理論突圍孤立性困境。
情境認知研究發軔于詞匯教學領域,如今這一術語已成為認知科學中各種情境化研究進路的統稱。本文通過“外在情境與認知關系”這一嶄新視角來揭示情境認知的涵義,希冀以這種方式呈現出情境認知更完整、更清晰的“面貌”從而為接下來的討論鋪平道路。外在情境與認知的關系可以被歸納成條件關系、因果關系和構成關系三類。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條件關系指外在情境只是認知完整符號表征-計算過程的必要條件。在這一關系視角下,認知依然被看作基于一定邏輯規則的符號表征-計算,外在情境是認知的構成性參數或認知運算的被動、抽象數據庫,只有納入外在情境認知過程才變得完整。外在情境與認知的因果關系是指認知對外在情境具有因果性的依賴。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構成關系指外在情境是認知系統的組成部分,外在情境不僅影響認知而且構成認知。這一關系主張認知可以突破顱骨和體膚的限制而延展至環境,“在對心靈進行說明時,一定要有頭骨內外的界限,完全是多此一舉……如果拋棄心靈只在生物腦中的偏見,打破用頭骨和體膚為心靈劃界的霸權地位,就能更好地理解人類作為世界造物的真正本性了”(4)Andy Clark,David Chalmers,“The Extended Mind”,in Analysis,Vol.58(1998),pp.7-19.。這實質上是克拉克和查爾默斯提出的延展認知的核心觀點。雖然條件關系、因果關系和構成關系關于“外在情境與認知關系”的認識立場存在差異,但它們都強調外在情境對認知的重要意義,本文在有機整合三種觀點的基礎上將情境認知涵義界定如下:認知始終發生在一個特有且自然的外在情境之中,知覺到的意義和認識到的世界不可能獨立于對環境的解釋和適應,諸如感覺、知覺、記憶、想象、思維和言語等認知過程都有賴于外在情境,外在情境不僅是認知的因果性角色,而且是認知的構成性角色。
威懾理論基于情境認知理論視角實現認知視野轉向(以下簡稱“情境-威懾理論轉向”)在修正自身的同時也有效規避了認知視野的孤立性困境,“情境-威懾理論轉向”是根據情境認知理論重新審視威懾效能形成機制,改變過往將威懾效能看成是脫離環境的理性算計和權衡結果的觀點,將外在情境作為一個重要因素置于威懾效能形成過程之中,強調外在情境對威懾效能生成的制約和影響。“情境-威懾理論轉向”后的理論可以稱作“情境視野-威懾理論”,它是把外在情境作為一個重要變量納入到威懾效能生成考量之中,威懾效能是外在情境參與到對犯罪利弊理性權衡、算計之中的結果。
三、“情境視野-威懾理論”描繪出的嶄新圖景
在青少年犯罪“預防實踐困難”和“理論困境”的雙重“夾擊”下,威懾理論已經到了必須修正的地步,轉向之后的“情境視野-威懾理論”描繪出一副青少年犯罪預防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嶄新圖景。
(一)從犯罪環境到工具設計:青少年犯罪預防實踐之創見
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條件關系、因果關系和構成關系都佐證了外在情境影響和制約認知這一觀點,外在情境就必然會在威懾效能生成這一“戲碼”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研究者已經開始關切外在情境在威懾效能生成中的重要性并逐漸形成了刑罰威懾情境化研究模式,它是根據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條件關系或因果關系來探討外在情境對威懾效能生成的影響,警察對威懾效能影響的研究、克拉克提出的情境犯罪預防就是此研究模式的典型代表。由于警察對威懾效能影響、情境犯罪預防的研究者或多或少意識到了外在情境之于威懾效能生成的重要意義,因此,他們開始站在“外在情境影響認知”這一立場上來審視威懾效能形成過程,但是,他們理解、領悟“外在情境影響認知”時僅僅是基于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條件關系或因果關系,并沒有透過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構成關系去把握、領略外在情境何以制約和影響認知。這些仍然在如火如荼開展著的刑罰威懾情境化研究是對威懾理論認知視野孤立性困境的突圍,然而,當他們建基于“外在情境影響認知”的原點上修正威懾理論時,他們對“外在情境影響認知”觀點的理解、把握完全是出于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條件關系或因果關系,換言之,他們是根據“外在情境是理性權衡是否犯罪必不可少的拼圖”或“威懾效能生成因果性的依賴于外在情境”這兩個層面來修正威懾理論。他們沒有意識到外在情境對認知的影響還可以透過構成關系這一層面得以展現,也就談不上利用這層關系來重新“打量”威懾效能形成過程,也就沒有將刑罰威懾情境化研究推進至“情境-威懾理論轉向”的嶄新高度。總之,刑罰威懾情境化研究是基于外在情境與認知的條件關系或因果關系,而“情境-威懾理論轉向”除了這兩種關系之外還根據構成關系。刑罰威懾情境化研究雖然強調但并沒有徹底凸顯出外在情境之于威懾效能生成的重要性,而當“情境-威懾理論轉向”站在延展認知的構成關系立場上來把握、領略外在情境何以制約、影響威懾效能生成時,延展認知不僅可以將刑罰威懾情境化研究提升到一個嶄新高度并勾勒出“情境視野-威懾理論”的完整輪廓,而且它與刑罰威懾的“碰撞”會從犯罪環境和犯罪工具兩個方面擦出具有理論意蘊和實踐價值的青少年犯罪防范對策的火花。
1.設計犯罪環境成為刑罰威懾記憶存儲地
威懾效能是問題青少年對犯罪利弊理性權衡、算計后的認知結果,延展認知主張認知是由大腦、身體和環境互動而成的耦合巨型系統,它們都會參與到犯罪利弊博弈這一認知加工過程中,而影響問題青少年生物性的大腦、身體和外在情境就都會導致威懾效能的變動,“任何犯罪預防都必須既包括大腦又包括物理環境”(5)C Ray Jeffery,Criminology: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90,p.39.,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合理的環境設計來增強威懾效能。
青少年犯罪地點有規律可循,比如偏僻寂靜的地方容易發生盜竊、搶劫等犯罪,而賭博、吸毒等犯罪則經常發生在游戲娛樂場所和歌舞廳等地方。謝爾曼、加廷和伯格的一項開創性研究首次提供的犯罪“空間集中”程度的描述性數據顯示,只有3%的地址和十字路口發出了50%的報警電話(6)L W Sherman,P R Gartin,M E Buerger,“Hot Spots of Predatory Crime:Routine Activities and the Criminology of Place”,in Criminology,Vol.27(1989),pp.27-56.。按照延展認知的觀點,青少年犯罪頻發區域不僅是問題青少年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嵌入背景,而且是他們當下認知的構成成分,因此,可以通過設計青少年犯罪頻發地帶的環境來增強威懾效能。當然,在設計之前首先需要利用各種手段、途徑定位青少年犯罪“熱點”區域。第一,聘請警察、檢察官或法官等象征著刑罰威懾的“權威人物”在犯罪頻發地帶舉辦一系列刑法知識講座,講座內容切勿空談,要結合實際案例且通俗易懂;講座過程要能夠吸引公眾眼球,能夠聚集人氣,聲勢浩大且波及面廣。第二,在犯罪頻發地帶設置一個大型電子屏幕,播映一些與刑法知識相關的視頻。第三,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可以臨時搭建一個“仿真少年法庭”,通過模擬審判來傳播刑罰的威懾力。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宣傳、傳播刑罰威懾力的環境設計方式,但環境設計的基本原則是讓犯罪頻發地帶充滿刑罰的“味道”,并讓這股“味道”以現場式直接參與的方式蔓延至盡可能多的問題青少年的“感官”。根據延展認知的觀點,問題青少年會將一部分記憶卸載于環境中以減輕認知負荷,“大自然似乎為人腦承擔了本來只是在indoor進行的一部分工作,環境仿佛可以自然地為我們操作某些信息,從而為人腦節約了能量,減輕了記憶的負擔。我們只是在需要知道這些信息的時候才讓它們上升為意識(進行符號操作),平時則讓它們留存于現實世界中”(7)李其維:《“認知革命”與“第二代認知科學”芻議》,《心理學報》2008年第40期。,他們會把聆聽講座、觀看錄像和旁聽“審判”的記憶存儲下來,但記憶存儲的位置不在大腦而是聆聽、觀看和旁聽時的環境。當問題青少年離開犯罪頻發地帶后好像忘記了聆聽、觀看和旁聽的內容,但他們一旦又經犯罪頻發地帶并企圖發動犯罪時,儲存在此處的有關刑法知識和刑罰威懾力的記憶又會重現浮現出來,如此一來,犯罪頻發地帶儼然已經成為問題青少年刑法知識或刑罰威懾力記憶的儲存場所而不再是實施犯罪的“展現舞臺”。一個極其理想的狀態是,在所有可能發生青少年犯罪的地方都進行環境設計,并讓所有可能實施犯罪的問題青少年現場感觸,從而使他們在可能犯罪的地方都會浮現出刑法知識和刑罰威懾力的記憶以至“無地可犯”。這當然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極端理想狀態,但卻可以展現出“情境視野-威懾理論”帶給青少年犯罪預防的新創見。
2.挖掘犯罪工具提高威懾效能之屬性
延展認知主張認知過程的載體并不局限于大腦和身體,認知可以延展到世界,這里的世界不僅包括外在情境,還包括工具。“自然發生的環境事件和物理工具都是能動性的認知資源”(8)Jonathan S Spackman,Stephen C Yanchar,“Embodied Cognition, Representationalism, and Mechanism: A Review and Analysis”,i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44(2014),pp.46-79.,工具不僅是個體認知、行動的中介物,還是認知系統的構成成分并在認知過程中起著分擔認知負荷的功能。認知的外置使得工具在問題青少年認知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變得重要,既然如此,我們就能通過工具設計來增強威懾效能。按照所羅門的看法,工具可以界定為人工制品或物質構件,包括各種知識制品、互補策略和語言等。根據這一界定,與問題青少年相關的工具理應有很多,但本文僅就極具代表性的犯罪工具或作案工具作一討論。
作案工具對問題青少年具有降低威懾效能和提高威懾效能的雙重屬性,它降低威懾效能的屬性已為人所熟知,但增強威懾效能的屬性卻一直被忽視。那么,如何設計作案工具才能增強威懾效能呢?借助過往青少年犯罪案例,總結歸納出犯罪青少年經常使用的作案工具類型,然后在這些常用的作案工具上刻上能夠傳播刑法知識或刑罰威懾力的內容,比如在匕首上刻上“刑罰制裁所有用匕首犯罪的人”,以使這些常用作案工具成為刑法知識或刑罰威懾力的載體,問題青少年一旦使用這些作案工具并看到上面的內容,便會將這些作案工具耦合到他們的認知系統之中從而提高威懾效能。作案工具降低威懾效能的屬性是天然具備的,而提高威懾效能的屬性卻經后天“雕琢”而成,如果不對作案工具作任何設計,那么它只能由降低威懾效能的屬性而構成,因此,必須通過作案工具設計挖掘、顯現出它提高威懾效能的屬性并借以沖淡或抵消降低威懾效能的屬性。
(二)從凸顯到統合:青少年犯罪學理論研究之變革
1.凸顯情境認知之于青少年犯罪理論的重要性
傳統青少年犯罪學理論研究的終極目標是提出犯罪預防對策,犯罪預防對策的針對性闡發需以探明犯罪原因作前提,而犯罪原因需要在大量紛繁復雜的犯罪現象中予以追尋,它遵循這樣一條研究主線:犯罪現象-犯罪原因-犯罪對策。青少年犯罪學理論研究一般會把外在情境(尤其是社會環境)看成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會在犯罪對策部分用大量篇幅列述如何通過環境設計、干預來預防青少年犯罪,但是,這種研究范式缺少了一個重要環節:對如此干預、設計環境為什么會收到青少年犯罪預防效果作出解釋。而這一問題只有訴諸情境認知理論方能解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接下來要根據“刑罰威懾作堅實后盾”的觀點來解釋為何環境設計、干預可以收到犯罪預防之功能。事實上,有很多環境設計、干預收到犯罪預防之功能可以借助此觀點進行解釋,但有的不能依據此觀點進行解釋,比如消除犯罪目標,其之所以能夠預防犯罪是因為問題青少年施罪目標消失的緣故。此處討論的“環境設計、干預”是那些能夠借助“刑罰威懾作堅實后盾”這一觀點予以解釋的。
表面上看,通過環境設計、干預預防青少年犯罪是環境的“功勞”而與刑罰威懾毫不相干,情境犯罪預防便可以在和刑罰預防劃清關系的基礎上“自立犯罪預防門派”。但是,根據情境認知的觀點,如此設計、干預環境是通過環境“改變”使問題青少年提高對刑罰之苦的估算值、降低對犯罪之利的估算值,從而借增強威懾效能之手段達致青少年犯罪預防之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環境設計、干預要收到青少年犯罪預防之效果需以刑罰預防作堅實后盾,如果沒有刑罰威懾托底的話,那么再怎樣干預、設計環境問題青少年都不會為之所動。在“情境視野-威懾理論”指導下,青少年犯罪學理論研究不僅要繼續執著于環境設計、干預的列述以探討如何有效懾止、遏制青少年犯罪,而且還要對為何如此設計、干預作出合理性的辯護。只有訴諸情境認知這一理論工具方能達成,有鑒于此,情境認知理論必然會在青少年犯罪學理論研究中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并逐漸“鋪陳”于青少年犯罪學教材之中。
2.整合刑罰威懾情境化研究各進路
事實上,已經有部分學者借助對外在情境的關切修正威懾理論,這里面既有在保留威懾理論基本框架基礎上作簡單修補的以警察對威懾效能影響研究等為代表的溫和改良主義,也有完全推翻威懾理論另起爐灶的以情境犯罪預防等為代表的激進革命主義。但是,“運用刑罰手段預防犯罪,在犯罪體系中居于突出的地位。這不僅因為犯罪與刑罰構成了刑事法律的基本內容,而且因為在任何有犯罪現象的社會形態中,刑罰都是犯罪預防的基本手段,這種手段運用得好與壞,對于減少社會上的犯罪現象具有明顯的、直接的影響”(9)許章潤:《犯罪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頁。,這決定了威懾理論的改革之路絕非全盤否定式的革命而是基于困境的修正。警察對威懾效能影響研究、情境犯罪預防研究等如散沙一般零落地分布在各個學術角落,表面上看,它們僅有的共同點是:基于威懾理論認知視野孤立性困境而生,但當透過情境認知理論視角來審視威懾效能形成過程時,我們發現它們相匯于“外在情境制約和影響威懾效能生成”這一基本共識,它們都契合于“情境-威懾理論轉向”的基本精神。這些理論本可以由情境認知和刑罰威懾“碰撞”而生,但它們卻各自基于另外一些視角而被先行逐一提出,當它們各自為營之時,情境認知的適時興起、發展將它們整合在一起,警察對威懾效能影響研究和情境犯罪預防研究等被這樣一條理論線索串聯起來而成為整體。這就好比,因為某些不同原因產生了看上去某些不同的結果,然而這些看上去不同的結果卻有著一個共同的淵源,只是這個淵源后于結果被發現。當威懾理論研究陣地逐漸被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所把持并不斷鼓吹刑罰威懾無效致使威懾理論日漸式微之時,如果復興威懾理論的不是貝克爾的法經濟學視角而是情境認知理論視角,那么基于威懾理論認知視野孤立性困境而提出的散落各處的理論,都必將作為一個整體而呈現出來。“情境視野-威懾理論”的提出必然會將這些散落各處、各自為營的研究“遺孤”逐步統合、匯整在一個“大家庭”之中。
3.統合刑罰預防與情境預防
情境犯罪預防產生于司法預防和社會預防效果使20世紀70年代整個犯罪學界都發出“什么都無效”感嘆的背景下。在絕大多數研究者看來,情境犯罪預防是對刑罰預防的“革命”,這場“革命”實現了從理論到技術、從國家到公民等價值取向的多元嬗變。但是,在“情境視野-威懾理論”視角下,情境犯罪預防不再是與刑罰預防截然不同的犯罪預防路徑,相反,可以將前者看成是后者納入外在情境這一變量予以自身修正的必然結果。威懾理論認為威懾效能是問題青少年封閉于大腦中脫離環境的對犯罪利弊的理性權衡、比較、算計(犯罪之弊與犯罪之利)后的差值結果狀態,它忽視了外在情境在威懾效能生成中的重要性。雖然“情境視野-威懾理論”與威懾理論都把威懾效能看成是一種認知結果,但“情境視野-威懾理論”還強調外在情境對問題青少年犯罪利弊理性權衡、比較、算計的制約和影響。在“情境視野-威懾理論”那里,問題青少年身處環境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他對犯罪利弊的認知加工、計算、運算,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對外在情境的干預、設計提高他們對犯罪之弊的認知,降低他們對犯罪之利的認知,從而使問題青少年運算出“犯罪之弊大于犯罪之利”的結果狀態,而這正是情境犯罪預防的基本運思。由于對犯罪之弊的認知仍然來源于刑罰威懾,因此,就本質而言,情境犯罪預防以刑罰威懾作后盾,如果沒有刑罰預防的威懾、警戒充當防線,那么情境犯罪預防對外在情境的干預、設計就不存在任何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通過干預、設計外在情境來預防犯罪是刑罰威懾借助環境更好地釋放出它內在固有的威懾效能。總之,刑罰預防是情境犯罪預防的后盾,情境犯罪預防功能的充分發揮建基于刑罰預防威懾、警戒基礎之上;情境犯罪預防是刑罰預防意識到威懾效能大小取決于外在情境后關切外在情境的必然結果。在“情境視野-威懾理論”指導下,情境犯罪預防與刑罰預防會逐漸融合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