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風情”二則
楊建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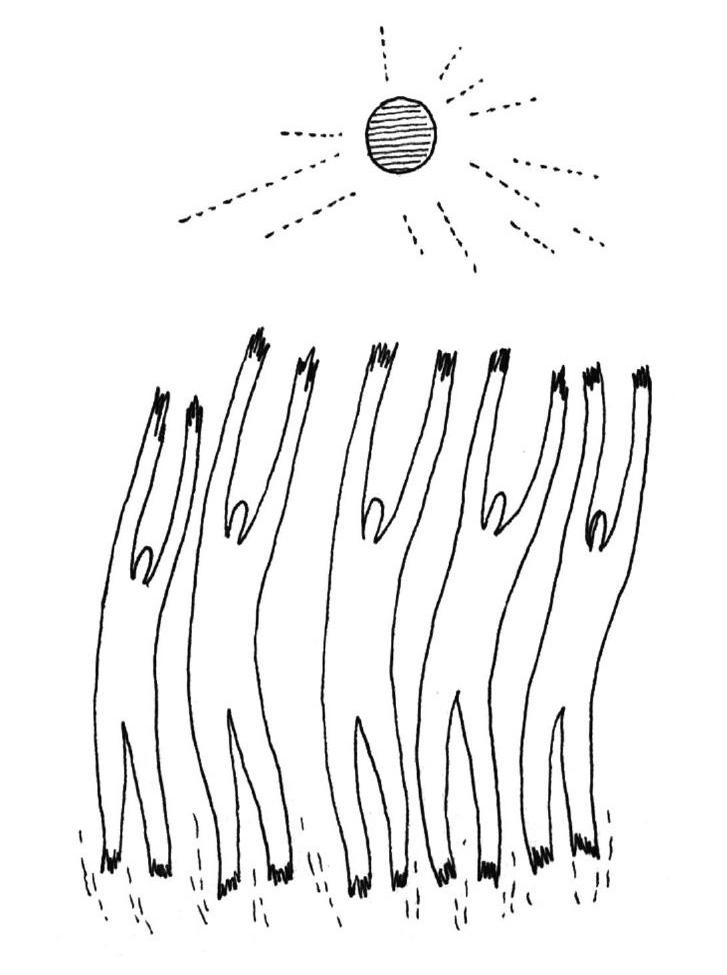
“多么美好的時代”
有關民國的風土人情,我們常見到的是些頗為煽情的贊譽文字。前兩年就有人寫道,“那是一個多么美好的時代,人和人之間的信任,人們那種自古傳承下來的、中華民族的那種忠孝禮儀都延續得非常好”。其例證就是梁思成先生抗戰前曾給全國每個縣的郵政局長匯去兩塊大洋。他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只寫郵政局長收,然后每個都寫一封信說,我們正在考察保護中國古建筑,希望你收到兩塊大洋以后,能把你們縣境內的古建筑拍照片寄回來。結果梁先生如愿以償了——所有縣的郵政局長都寄回了他們縣境的古建筑照片。(見2014年23期《讀者》)
但這樣的“美好”只是民國時期才有嗎?以梁先生那時候的名望和名頭,“親自”給一縣之中也是有頭有臉的郵局局長寫信托辦一件并不費什么大力氣的事兒,放在哪個時代,恐怕都非難事。何況還是重金相托呢(民國時期一塊大洋據說相當于今天人民幣300-500元)。
竊以為,作為“中華民國就是好來就是好”的典型,下面的例子可能更為合適:
輔仁大學有個教授叫英千里,當時還兼著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課程,其月薪最多時可到1000多大洋,約合今天的人民幣30多萬元,可謂薪水多多;聞一多先生在清華大學執教時,校方給他分配的福利新房“新南院72號”,“有臥房、客廳、餐廳、儲藏室、仆役臥室、廚房、衛生間等大大小小14間。電燈、電話、電鈴、冷熱水等設備一應俱全。房前甬道兩側有綠茵草坪。周圍是冬青矮柏圍墻,草坪中央放置一大魚缸,書房寬敞明亮,四壁鑲以上頂天花板的書櫥,窗下是書桌”,真是要多愜意就有多愜意(見2014年11月7日《報刊文摘》)。所以,民國時期對教授而言,從經濟角度上或許是“一個多么美好的時代”。
可是,民國僅是由教授組成的嗎?教授們被監視、威脅甚至暗殺怎么不一起提及?而且夸贊民國如何好的人們是不是也該關注一下其他階層的生活水平呢?據社會學知名教授陶孟和的成名作《北平生活費之分析》一書記載,北平當年的人力車夫每人每日平均只能賺到5角4分錢,除掉每天的1角4分車租費,僅剩下4角錢(見2014年9月10日《報刊文摘》)。以這樣的收入去養家糊口,又是怎樣一種生態?
由此看來,盛贊民國到無以復加的人們在研究思維上至少存在著三個“不顧及”的盲區:一是,當他們臧否一個時代或月旦一個歷史人物時,其設立標準的眼頭只是向上——上流社會,而從不向下,即從不顧及下層貧民社會的感受一一而恰恰這部分人正是當年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二是,他們考察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態時往往因其個人的某種主觀偏好而極端片面,完全不顧及全面的客觀真實,這就陷入了據說他們也很推崇的魯迅先生對當時社會吃人本質的投槍般抨擊的悖論中了;三是,其行文立論,完全不顧及歷史固有的發展邏輯:這個時代既然如此“美好”,怎么還會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眾所唾棄?這不是思辨能力的低劣,就是對歷史基本事實的不尊重。
夜半墓地里說鬼話
前些年某些精英,其“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民國情結,還影響到今天的部分商界人士,以至于其所言所行,荒謬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幾同于大白天里發囈語,夜半墓地說鬼話。日前,就從一篇文章得知,盒馬鮮生一張民國風的宣傳海報,聲稱要“穿越歷史老集市,讓物價回歸1948年”。底下還有一行小字:一夜春風,讓我們夢回民國。(2019.4.16《新京報》)
民國的1948年是個什么年月?正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之最黑暗年代。當時蔣管區經濟一片混亂,行將崩盤。百業凋敝,貨幣貶值,物價飛漲,以至于貨幣貶值到工薪人士發薪水,每個人都要靠麻袋裝、車馬運!百姓生計無著,城鄉餓殍遍地,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常態。據史料記載:“1948年3月米鋪里上等大米的標價是270萬元國幣一擔,而兩年前的3月是3.9萬元,上漲了68.2倍。一只咸蛋在市場上的價格是1萬元,豬肉是12萬元一斤,紅蘿卜是8000元一斤。相隔一月后,4月9日的上等米是340萬元一擔,豬肉是18萬元一斤。再過幾天,4月15日的上等米是400萬元一擔;4月19日升至579萬元一擔;5月5日突破603萬元一擔。升斗小民,被頻繁更換的標價牌,弄得眼花繚亂。還未踏出米鋪大門,就聽說今天的豬肉升至24萬元一斤,牛肉30萬元一斤。他們幾乎當場昏死過去。”
不曾料,那樣一個不堪回首的年代,不僅被今天一些人美化成安居樂業、精致優雅、一片祥和的烏托邦,還要我們“夢回民國”哩,真不知這些人到底想要干什么?!更值得深思的是,時至70年后的今日,還有不少的遺老遺少們對那個時代戀戀不已、懷念不已、把玩不已,且“克己復禮”美夢做得如此離譜,又說明了什么?
但話又說回來了,懷念民國,只要沒有極端行為,也是一種思想權利,還應尊重。既然這些人對民國時期如此向往,不妨按照某雜文名家的一些說法,也參照“新村運動”的做法,圈一塊足夠大的區域,仿民國時期的體制、文化、法制、報刊、學校、洋樓、郵政、商貿、集市、酒肆、餐飲、妓院……等諸多元素,廣募錢款,予以再造,令那些患有“民國癖好”的人。免去“夢回民國”的相思之苦,直接人住進這塊“民國飛地”好了。在這里可以天天坐民國茶館、喝民國咖啡、讀民國報刊、看民國電影、唱民國小曲、當民國票友、逛民國集市、坐民國黃包車……把民國雅士的癮過足。當然,也得有足夠的心理耐力,譬如說,對隨處可遇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現象和特務殺人如麻、軍閥橫行霸道都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再造民國”就得原汁原味嘛!反正中國之大,圈一塊這樣的地方也諒無問題。當然,先生們也就不必再用電腦、互聯網,也不必看電視、刷手機了,因為民國沒有這些勞什子。何況,這些“快生活”也足以敗壞民國閑靜優雅的生活情調。
但,即便有這塊地皮,也能建起這塊“民國樂園”,我疑心這“懷念民國”的美夢還是不好做。請問哪里能募招到一天僅幾個銅板收入還得掙著命去拉太太小姐、大人先生們的黃包車車夫呢?哪里能征集到那些肯為資本家拼死拼活賣苦力的包身工呢?又在哪里能找到瀕于破產仍不得不在黃土地里刨食、繳租、納糧的鄉村廣大佃農呢?沒有這些人,大人先生、小姐太太們再風情萬種典雅無比,也得餓死啊!
說來說去,懷念民國的人還是少了點。因為對絕大多人而言,他們可是沒人再愿意“夢回民國”去當“民國餓殍”的。
童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