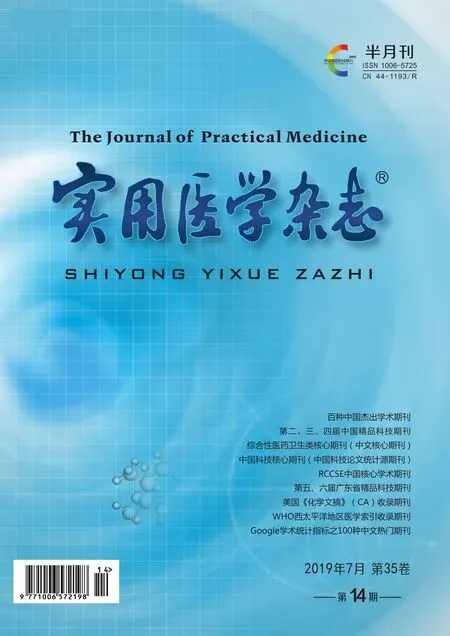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肺部疾病相關性研究進展
李文龍 李慧君 張豐泉 姜靜 張貴成 吳衛東
新鄉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河南省空氣污染健康效應與干預國際聯合實驗室(新鄉453003)
腸道菌群是人體腸道內長期存在的微生物群落,正常的腸道微生物群在宿主營養代謝、藥物代謝、維持腸道黏膜屏障結構完整性、免疫調節和抵御病原體等方面發揮著特殊功能[1-2]。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腸道菌群在疾病的炎癥、代謝和免疫調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而提出了“腸-肝”軸[3]和“腸-腦”軸等[4]概念。與此同時,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健康人的肺部被認為是無菌的,但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在分子生物學中的大量應用,越來越多的研究報道了肺組織中檢測出微生物的證據[5-6]。肺部和腸道作為與外界直接相通的空腔臟器,均存在各自的微生物群落,且有著共同的胚胎起源和黏膜免疫系統,相關研究表明肺部和腸道之間存在“腸-肺”軸的內在聯系[7-8],慢性肺疾病患者的腸道菌群特征、表觀遺傳、免疫信號傳遞和益生菌治療已經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本文主要就腸道菌群與肺部疾病的相關性進展進行綜述。
1 腸道菌群與腸肺軸
“腸-肺”軸是腸道與肺部相互聯系的橋梁,雙向調控,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1)腸道微生態的失衡影響肺部疾病的發生發展,主要表現在腸道菌群細菌豐度和多樣性的改變,以免疫系統為媒介,通過調節免疫應答、改變T 淋巴細胞亞群的活性和一些免疫細胞的募集、遷移等方面調節機體的免疫反應[9];HUANG 等[10]研究發現,Ⅱ型先天淋巴細胞(ILC2s)在炎癥信號的反應過程中可從腸道進入肺和其他器官,從而影響效應位點的免疫反應。ILC2s 參與“II 型免疫”,通常被白細胞介素-25(IL-25)和IL-33 激活,產生大量的IL-5 和IL-13,當IL-25 誘導或微生物感染作為炎癥信號時,富集于小腸的ILC2s 以1-磷酸鞘氨醇(S1P)依賴的方式打開通向淋巴管的通路。被激活的來源于小腸的ILC2s 也被稱作炎性ILC2s(iILC2s),iILC2s從淋巴管進入血管進而遷移至肺部,參與肺部的“Ⅱ型免疫”和組織修復。BRADLEY 等[11]利用自身免疫關節炎模型,發現腸道微生物群中的分節絲狀細菌(SFB)可以遠距離刺激肺部病理,通過“腸-肺”軸誘導Th17 加劇自身免疫,同時SFB 并不依賴于分子模擬或旁路激活途徑來誘導Th17。在外周組織中,SFB 選擇性擴增表達Th17 的雙T細胞受體(TCR),識別SFB表位和自身抗原,從而增強自身免疫。(2)流行病學證據表明,慢性肺部疾病患者也多伴有胃腸道疾病,某些肺部疾病的發生發展同樣會影響胃腸道疾病[12-13]。WANG 等[14]發現,呼吸道流感感染在肺損傷時會引起腸損傷,而不是直接由腸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流感感染改變了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由肺源性CCR9+CD4+T 細胞進入小腸產生的IFN-γ 介導。PR8 流感病毒株感染后,小腸TH17 細胞顯著增加,IL-17a 中和抗體可減少小腸損傷。此外,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能顯著刺激腸上皮細胞產生IL-15,進而促進原位小腸中Th17 細胞的極化。由此可見,“腸-肺”軸作為腸道與肺部聯系的關鍵性通路,在二者疾病間的相互影響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2 腸道菌群與肺部疾病
2.1 腸道菌群與哮喘哮喘是兒童最常見的慢性氣道疾病,早期的“衛生學假說”認為[15],生命早期微生物的暴露能夠刺激免疫系統發育,減少過敏性哮喘的發生。現有證據表明[16-17],在小鼠和人類的早期生活中存在一個“關鍵窗口期”,在這個窗口期中,腸道微生態失調的影響對人類免疫發育的影響最大。相關研究表明剖腹產可減少生命早期腸道菌群的多樣性,改變腸道菌群的組成[18],與此同時,剖腹產還會增加兒童患哮喘的風險[19]。ARRIETA 等[20]基于縱向研究方法比較了319 名加拿大健康嬰兒的腸道微生物群,發現有哮喘風險的嬰兒在出生后100 d 內表現出短暫的腸道微生態失調。哮喘患兒Lachnospira、Veillonella、Faecalibacterium、Rothia 等菌屬相對豐度明顯降低,這種細菌菌群的減少伴發糞便醋酸鹽水平的降低。將以上這四種細菌類群移植至無菌小鼠腸道,改善了其成年子代氣道炎癥,證明了這些細菌類群在避免哮喘發生中的重要作用。THORBURN 等[21]通過飲食干預的動物實驗發現,高纖維飲食喂養小鼠會產生特異腸道微生物群,增加短鏈脂肪酸(SCFAs)醋酸鹽的水平。高纖維或醋酸鹽喂養可通過增強調節性T 細胞數量和功能來抑制過敏性氣道疾病(AAD),在表觀遺傳方面,高纖維/醋酸鹽喂養懷孕小鼠其后代成年后不出現AAD,但抑制小鼠幼胎肺中與人類哮喘和小鼠AAD 相關的基因的表達。由此可見,腸道菌群在生命活動早期即對哮喘的發生有一定的影響,甚至影響表觀遺傳學特征。
2.2 腸道菌群與肺部感染微生物侵襲是肺部感染最常見的原因,肺部作為氣體交換的場所,與外界直接相通,不斷暴露在外環境刺激之下,當微生物的數量或類群超過了肺部免疫防御“閾值”,則引起肺部感染的發生。SCHUIJT 等[22]研究了腸道菌群在宿主防御肺炎鏈球菌感染中的作用后發現,腸道菌群在肺炎鏈球菌所致肺炎期間對宿主有保護作用,與對照組相比,清除了腸道微生物的小鼠的細菌傳播、炎癥、器官損傷和死亡率均增加。為清除腸道微生物的小鼠進行糞便移植實驗(FMT)后發現,肺炎球菌感染6 h 后,小鼠肺部細菌計數、腫瘤壞死因子-α 和IL-10 水平恢復正常。肺泡巨噬細胞全基因組圖譜顯示,在缺乏健康腸道菌群的情況下,代謝途徑上調,這種上調與細胞反應性改變有關,表現為對脂多糖和脂磷壁酸的反應性降低。與對照組相比,腸道微生物缺失小鼠肺泡巨噬細胞吞噬肺炎鏈球菌的能力降低,證實了腸道菌群是肺炎鏈球菌性肺炎的保護性因素。TSAY 等[23]發現經抗生素預處理清除腸道共生菌后,在C3H/HeN 小鼠中,大腸桿菌肺炎引起肺過氧化物酶(MPO)活性下降30%,肺泡巨噬細胞的殺菌活性和細菌計數顯著下降,而在Toll樣受體4(TLR4)缺陷的C3H/HeJ 小鼠中則無此現象。在抗生素預處理期間添加脂多糖(LPS,一種TLR4 的配體)可抵抗上述影響,減少大腸桿菌肺炎所致C3H/HeN 小鼠死亡。此外,清除腸道菌群可抑制C3H/HeN 小鼠肺內NF-κB 與DNA 結合活性,使角化細胞趨化因子(KC)、巨噬細胞炎性蛋白-2(MIP-2)、IL-1β 表達升高,加重炎癥反應。以上研究結果表明,腸道菌群可以提高對肺部感染細菌的清除能力。
2.3 腸道菌群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COPD是慢性感染和炎癥導致肺損害和功能喪失的疾病,COPD 的急性加重與肺部微生態的失衡有關,肺微生物群的豐度、組成、分類和系統發育多樣性發生變化導致炎癥反應發生[24]。“惡性循環”假說[25]認為吸煙或微生物暴露等吸入性損傷引起的肺固有防御的改變,使致病菌持續增殖。WANG等[26]發現肺部微生物組的變化可能通過介導宿主炎癥反應,參與COPD 的加重。OTTIGER 等[27]研究發現,腸道微生物依賴的三甲胺-N-氧化物(TMAO)與COPD 加重患者的長期全因病死率相關,6年后的全因病死率為55.6%。然而,截至目前,COPD 患者的胃腸道菌群特征尚不明確。有證據表明,暴露于香煙煙霧會導致人體和小鼠的腸道細菌失調。與非吸煙的克羅恩病患者相比,吸煙患者腸道微生物基因豐富度、屬和物種多樣性均有所降低,其中Collinsella、Enterorhabdus、Gordonibacter 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相對豐度較低[28]。此外,據報道,吸煙者的腸道微生物群組成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在戒煙后減少,與持續吸煙者和非吸煙者相比,非吸煙者的腸道總體微生物多樣性顯著增加,厚壁菌門和放線菌門增加,擬桿菌門和變形菌門的比例較低[29]。長期(24周以上)暴露于香煙煙霧的小鼠中結腸細菌失調,Lachnospiraceae 增加[30]。
2.4 腸道菌群與肺癌2018年全球癌癥報告[31]顯示,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居于全球首位,占癌癥死亡總人數的近五分之一。近來研究顯示,腸道菌群會影響腫瘤免疫治療[32]。VéTIZOU 等[33]報道腸道微生物群可以通過細胞毒T 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TLA-4)減弱癌癥免疫治療效果。在無菌或抗生素處理的小鼠中,anti-CTLA-4 抗體不能控制腫瘤生長,反而導致脾臟效應因子CD4+T 細胞和腫瘤浸潤淋巴細胞的活性降低。CTLA-4 阻斷使糞便中擬桿菌門和伯克氏桿菌門水平降低,梭菌門水平增加。同樣,SIVAN 等[34]的研究表明,口服雙歧桿菌可增強黑素瘤小鼠模型中抗程序化死亡配體-1(PD-L1)腫瘤應答,促進抗腫瘤免疫。另一方面,ROUTY 等[35]研究發現,腸道微生物群組成異常是導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s)耐藥的主要原因,抗生素抑制了晚期肺癌患者ICIs 的臨床療效。此項研究共納入249 例患者,其中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140 例,腎細胞癌(RCC)67例,泌尿上皮癌42 人。其中,抗生素處理組的癌癥患者無進展生存期(PFS)和總生存期(OS)較對照組明顯縮短,在考慮了腫瘤類型的情況下結果未發生改變。單變量和多變量Cox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NSCLC 和RCC 患者中,抗生素可作為ICIs抵抗的獨立預測因素。糞便樣本宏基因組分析提示,ICIs 的臨床效應與Akkermansia muciniphila 的相對豐度有相關性。動物實驗表明,將ICIs 無應答小鼠的糞便進行移植后,口服補充Akkermansia muciniphila 可以通過增加CCR9+CXCR3+CD4+T 淋巴細胞在小鼠腫瘤灶的募集,以IL-12 依賴的方式恢復對PD-1 阻斷的療效。DEROSA 等[36]的人群研究同樣發現,NSCLC 患者ICIs 的臨床活性與抗生素呈負相關。此外,KATAYAMA 等[37]回顧性研究了40 例晚期NSCLC 患者接受ICIs 治療的資料發現,糞便異常的NSCLC 患者的疾病控制率低于無糞便異常的NSCLC 患者。與無糞便異常的NSCLC患者相比,糞便異常的NSCLC 患者ICIs 治療失敗率更高。這些研究均說明腸道菌群與肺癌治療效果密切相關,使用抗生素會導致腸道微生態失衡進而降低ICIs 療效。
3 腸道菌群的作用機制
3.1 G 蛋白偶聯受體(GPCRs)激活GPCRs 是一大類膜蛋白受體,這些受體可以感知多種信號分子,與多種配體結合,激活細胞內一系列傳導通路,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研究發現,G 蛋白偶聯受體GPR41、GPR43、GPR109A 可被短鏈脂肪酸(SCFAs)激活,參與機體免疫應答[38]。SCFAs 是腸道菌群與膳食纖維的發酵產物,可以調節免疫功能,預防過敏性氣道炎癥的發生[39],這些分子通過抑制組蛋白脫乙酰酶活性發揮抗炎特性[40],還能誘導調節性T 細胞[41]、前列腺素E2 產生[42]及改變樹突狀細胞功能,在多種環境下發揮抗炎作用。MACIA 等[43]研究發現,SCFAs 可與代謝敏感受體GPR43 和GPR109A 結合,通過調節炎性小體促進膳食纖維誘導的腸道穩態。MIRKOVIC 等[44]的研究表明,SCFAs 刺激囊性纖維化(CF)患者的支氣管上皮細胞產生過量的IL-8,SCFA 受體GPR41 在CF 患者上皮細胞中過度表達,通過小干擾RNA(SiRNA)阻斷其信號通路,抑制CF 氣道細胞IL-8的產生,參與微生物介導的炎癥反應。
3.2 TLRs 介導TLRs 是一類在先天免疫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參與炎癥過程的蛋白。TLR 信號轉導通路的激活可使許多在宿主防御中起作用的基因表達,包括炎癥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抗原呈遞分子[45]。有研究[46]表明,在高脂肪飲食條件下,腸道微生物群可通過TLR 信號(主要是TLR2 和TLR4)加重炎癥和代謝。給小鼠喂食富含飽和脂肪的食物會導致體重增加、食物攝入量增加、呼吸商降低,并增加Bacteroides,Turicibacter和Bilophila的豐度。而喂食富含多不飽和脂肪的飲食,則可增加Bifidobacteriumadlercreutzia、Lactobacillus、Streptococcus、Akkermansia mucinila 的水平。同時,ROUND 等[47]證明了腸道共生菌Bacteroides fragilis可以激活TLR 通路來建立宿主-微生物共生關系,Bacteroides fragilis 的共生因子(PSA,多糖A)可通過TLR2 信號直接作用于Foxp3+調節性T 細胞,促進免疫耐受。FAGUNDES 等研究[48]也顯示,腸道微生物可通過激活TLR 依賴的途徑改變宿主對環境感染刺激的反應。
3.3 NOD 樣受體(NLRs)識別NLRs 是一種模式識別受體,類似于TLRs,屬于細胞質受體,可識別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PAMPs)和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Ps),激活的NLRs 具有炎癥小體形成、信號轉導、轉錄激活和自噬四大類功能,在先天免疫應答中發揮重要作用[49]。CLARKE 等[50]發現,清除腸道微生物群后,肺炎克雷伯菌的早期清除率受損,可以通過源自胃腸道的NLRs 配體(主要是NOD1 和NOD2 配體)識別病原體分子來增強肺泡巨噬細胞活性,挽救肺部防御。此外,NOD2 表達依賴于腸道共生菌,為無菌小鼠補充共生菌可誘導NOD2 表達增加[51],NOD2 缺失會導致促炎細胞因子生成增多,從而加重上皮細胞發育不良,這種情況可以通過使用抗生素或抗IL-6 受體中和抗體來改善[52]。
4 結論與展望
腸道菌群與肺部微生物群、腸道與肺部相互作用關系正在被揭示,面對我國嚴峻的大氣污染形勢,呼吸系統的暴露首當其沖,以COPD、哮喘為代表的慢性肺部疾病負擔日益加重,疾病防控形勢不容樂觀,已經成為我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腸道菌群研究有望為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帶來新的治療契機。然而在此之前,哮喘與腸道菌群的相關研究已經被廣泛報道,但關于COPD 與腸道菌群的相關研究卻依然欠缺,COPD 作為比哮喘更為嚴重的慢性肺部疾病,正亟待我們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