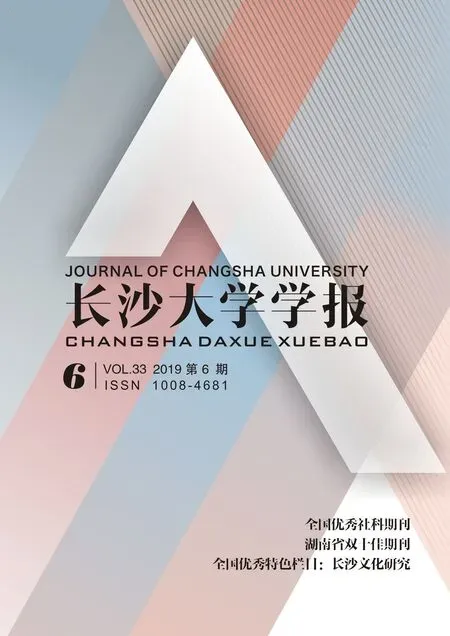新生研討課的由來、特征及教育價值
肖 雄
(長沙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022)
針對高等教育大眾化持續發展、本科教育質量有所下滑的狀況,我國政府適時地實施了本科教學工程。由于“落后的教學模式已成為影響大學教學質量的一個主要因素”[1],盡管保障和提高本科教育質量關涉到辦學條件、學科建設、師資隊伍、教學管理等諸多因素,但從教學方法或教學模式改革創新入手則被我國高等教育學界所認同。在各式各樣的教學改革實踐中,大學新生研討課的引入尤其值得關注,作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重要舉措,新生研討課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取得了普遍推行,但在我國的開展卻不盡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缺乏相關支持、保障措施和實施條件,另一方面則在于許多高校對其意義和價值認識不夠。因此,對這種教學模式的特征和價值進行探討實有必要。
一 新生研討課:在“習明納”基礎上結合新生教育傳統發展而成的教學模式
(一)基于洪堡“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理念的“習明納”
新生研討課(Freshman Seminar)由歐洲傳統的一種教學組織形式——“習明納”(Seminar)發展而來。“習明納”是seminar的音譯,原意為苗圃、發祥地、學術的溫床。早在16、17世紀,受到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思潮的影響,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學者們首創了習明納。現代意義上的“習明納”則始于19世紀的柏林大學,是踐行洪堡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獨創精神與學術自由相統一和注重協作的教育教學理念的教學模式。在洪堡看來,首先,大學是“探究的場所”,科學研究是大學的重要使命,教學應該與科研相結合,科學研究既是發展科學的手段,也是培養人才的手段;其次,大學所取得的教學、學習與研究的成果是通過個人自身并由個人自身獲得的,個人應以獨立思考和鉆研的精神參與到各種精神活動中,這種獨立性又是以自由作為保障的;再次,應以合作作為獨立性和自由的補充,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不僅僅能夠使一個人彌補自己的缺陷,也能夠使一個人成功的鼓舞其他的人。換言之,在洪堡看來,只有保證教、學、研的自由,才能充分舒展師生的個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洪堡認為,大學教育工作者既是教師,又應該是科學研究者,受教育者既是學生,也應該是研究者,師生都應獻身于科學,用比較系統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并為科學而共處。因此,教師在講授知識時,應激發學生的研究興趣,教授學生研究的方法,使學生在獨立研究中獲得啟發。大學教師的主要任務不是教,而是激發學生學習研究的興趣,并進一步指導、幫助他們從事研究,學生的主要任務也并不是學,而是教授的指導下協助教授進行科學研究,并逐漸養成獨立從事研究的能力。基于上述理念,洪堡及其同事創立了“習明納”這種“仿佛把一切可能解決的問題的辦法都提出來,僅僅使人做好準備,自己去從中找出最巧妙的解決辦法,或者最好是僅僅從對一切障礙適當的描述中,自己去發明這種解決方法”[2]P74-75的教學模式。
概而言之,“習明納”是學生在教授的指導下,就某一課題結成學習或研究小組,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與教師自由地進行學術探討,以達成教學與科研雙重目的的一種教學模式。經過不斷的演進,“習明納”形成了基本穩定的講授-研討的二元結構和程序,此程序包括教師宣布討論主題和要求—學生以個人或小組的形式開展研究—學生匯報研究成果—教師組織討論—教師總結與點評、討論—教師對學生做出評定等六個階段。
可以這樣認為,在現代大學的發展中,基于洪堡的大學理念而創立的“習明納”教學模式不僅促進了柏林大學乃至整個德國科學的繁榮,而且也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大學教學改革。“雖然不可能確定資金投入和科學成果之間的比重,但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說,德國政府從他們相當少的投入中,獲得了學術進步的可觀紅利。”[3]P66其中,“習明納”功不可沒。“‘習明納’是輪中之軸,是現代大學真正的具有生氣的中心,是激動人心和富有創造力的力量。”[3]P76-771870年,曾在柏林大學學習的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將其引入哈佛學院,從而使美國大學開始朝著高深學術研究的方向前進。
(二)在“習明納”基礎上結合新生教育傳統發展而成的新生研討課
20世紀中期,哈佛、南卡萊羅納等美國高校為了促進新生學習、提高教育質量,在借鑒、吸納“習明納”主要特點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新生教育傳統,創立了新生研討課。新生研討課有學術性新生研討課和適應性新生研討課兩種類型。學術性新生研討課發端于哈佛大學。1959年,在因應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的挑戰所掀起的教育改革運動中,哈佛大學為了提高一年級學生的學術能力,提高教育質量,開始嘗試性地為新生開設研討課。到1963年,哈佛大學正式將新生研討課納入本科生的課程體系中。之后,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伯克利大學等諸多著名高校紛紛效仿,開設了新生研討課。適應性轉變新生研討課則產生于南卡羅萊納大學。1972年,作為應對校園騷亂事件的舉措之一,南卡羅萊納大學校長托馬斯·瓊斯(Thomas Jones)在校內開設了以加強師生溝通和促進新生適應性轉變為目的的新生研討課,并產生了積極而顯著的成果,其101項目(University 101 Program)因效果顯著而發展為國家課程,得到了幾乎所有其他高校的借鑒和效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越來越多的教育機構和人士深刻地認識到,主動、有效的學習是學生成功和保持在校學生率的關鍵,遂陸續發表了《學生學習乃當務之急》《從教到學:高等教育的新范式》《強烈的期待:一種定位于國家民族的大學學習新愿景》等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報告和論文,呼吁高等教育工作者改變對高等教育方法的認識,從關注“教”轉移到關注“學”,強調應通過教學方法的變革促進學生學習,以應對在工作場所、多樣化的民主和相互聯系的世界中出現的挑戰,從而推動了新生研討課在美國大學中的深度發展。這些意見引起了美國許多研究型大學的高度重視,這些大學在采取多種措施改革本科教學的同時,紛紛開設新生研討課,以回應報告中關于“建立基于研究的學習模式、構建探究式的一年級教學、構建新生基礎、使交流技能與課程學習相結合、培養團隊精神”等要求。據博耶委員會2001年對全美123所研究型大學的調查,有85.3%的學校開設了新生研討課,其中有42%的學校新生研討課覆蓋半數以上的大學新生[4]。
為保障并提高本科教育質量,我國的清華大學于2003年為本科新生開設了新生研討課。之后,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華中農業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化工大學等一批研究型高校也跟進開設了新生研討課。
二 新生研討課的根本特征:以“學”為重心,以探究為主線,重視學生參與
新生研討課是主要由各學科的知名教授或其他專業教育工作者擔任指導教師,專門為大一本科新生而開設的小班研討課。盡管各國各高校的新生研討課各具特色,但不論適應性的還是學術性的,以“學”為重心、以探究為主線、重視學生積極參與則是新生研討課的根本特征,也是其區別于傳統教學模式的特征所在,這些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教學目的聚焦于新生學習的轉換
歸納起來,新生研討課的教學目的主要聚焦于:1.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2.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同伴關系;3.引導學生認識大學和熟悉學校環境、學習資源,掌握基礎的學習技能;養成大學生應有的學習習慣,具備自我管理能力;4.培養學生的學術品質,體驗研究的樂趣;5.指導學生初步規劃大學學習生涯和人生發展目標。可以看出,新生研討課的教學目的旨在促進新生學習,幫助新生順利實現從中學學習向大學學習的轉換。
(二)教學內容以學習技能、探究的視野和方法為主
適應性轉變新生研討課大部分主題是大學學習技能和方法,內容涉及大學學習的特點、高效的學習小組、學習能力與風格、學術成功的秘密、有效的記憶工具、建構學術自信心及抗逆能力的技巧。學術性轉變新生研討課則涉及批判性思維、分析能力以及辯論等高層次能力為導向的研討,以及專題為導向的學術研討,其內容帶有導論、引論的性質。但又并非是全面系統的知識講授,教師注重從自身專業研究的角度給予學生啟發,選擇的研討主題往往是各專業的前沿問題、社會熱點問題或是教師正在進行的研究,籍以拓廣學生的學術視野,激發學生和教師共同探究未知的興趣,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在研討中,專業性本身僅僅是手段,激發學生對學科產生興趣,對所學專業和學科有深入的了解、擴大學生的學科視野、明確今后的學習方向和掌握專業特有的學習方法才是重點所在。
(三)研討主題由教師自由確定,學生自由選擇參與
教學內容或研討主題的確定注重教師的專業自主和學生的選擇自由。特別是學術性轉變研討課的教師有著相當大的教學活動自主權,研討課的主題、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主要由任課教師自主決定,教師傾向于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或所屬研究領域的前沿問題帶入課堂,學生也可自主選擇教師和課程,使得教師的研究和教學有機結合,同時激發了學生參與和探索研究的興趣。
(四)教學方法以研討、探究、講演、辯論為主
新生研討課類似于“習明納”的講授——研討二元結構模式,摒棄了以往教師教授為主的教學方式,注重學生的自學、小組合作和研究性等教學方法,同時也提倡采用實驗、參觀、調查、實踐以及研討、論辯、口頭報告、講演等,強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力求使學生從被動學習轉換到主動學習、自律學習。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主要起著引導者、幫助者的作用,只在開始階段講授該專題的背景知識和當前研究現狀,學生則是整個教學活動的主體,學生自己發現、探索、解決問題,在此過程中體會探索的興奮和研究的樂趣;積極的參與帶來了更多正面的聯系,而更多的聯系也使學生獲得了豐富的經驗或體驗,培育了合作態度和交際能力。
(五)學習考核注重過程參與而非結果
學生的參與程度是是否有效或學習能否成功的關鍵,“學生對大學教育主體性參加過程中所獲得的深刻體驗以及這些事物所激發的全新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能促使學生更積極地投入學習活動,是一個“學習和成長的良性循環”[5]P13。新生研討課中,教師對學習的考核重視的是學生學習的過程,而不是追求標準答案。教師一般依據學生的出勤情況以及學生參與課堂討論的表現、對知識的綜合運用、思考問題的角度、方案的合理性、組織討論的效率、最終報告的表述及口頭表達能力進行綜合評價。考核方式通常不采用分數考核,而是采用等級考核;考核結果多為通過和不通過兩個級別。學生通過積極參與,經歷實踐、感悟、反省、認識概念化等一系列過程,并在這一過程中循序漸進逐漸養成獨立學習和研究的能力。
(六)教學形式為小班教學,教師多由名師或專業工作者擔任
新生研討課對每門課程的人數有嚴格的限制,如哈佛大學限制在12人以下,麻省理工學院每門新生研討課的人數為8—10人,我國清華大學新生研討課的人數則限定在10—25人之間。小班教學有利于增加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討論與交流,保證學習效果。為了使新生從一開始就能與名師共享科學探究的經歷和樂趣,培養追求科學、真理至上、嚴謹治學和反思批判的精神,新生研討課對任課教師也有特殊的要求,學術性研討課的主講教師大多由著名專家、教授擔任,在哈佛、耶魯、麻省理工等一流大學,還推崇諾貝爾獎獲得者上課。我國清華大學則由院士、國家級教學名師等知名學者開設新生研討課。適應性轉變研討課則主要由受過專業的指導者開設,教師絕大多數是專門的學生事務工作者、教育行政人員以及大學生學習指導中心等相關機構的工作人員。
三 新生研討課的教育價值:幫助新生適應大學學習,夯實基礎學養,培育自主學習能力
(一)幫助新生適應大學學習
本科教育質量的落腳點是學生的學習質量,學生能否適應大學學習則是影響學習質量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我國高校連續擴招,大學生數量劇增,學生群體的構成、需求及特性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新生對大學學習的不適應現象明顯增多。究其原因,一是與大學生在實現上大學的目標以后學習目標不明確、學習動機減弱等有關,二是與基礎教育階段被動的、應試的或訓練的學習有關。由于大學學習要求學生具有自主性、專業性、研究性,故新生大多感到不適應。新生研討課則可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幫助學生規劃大學學習和職業生涯,明確學習目標,引導學生了解和熟悉大學學習和專業的特點,實現由被動學習向自主學習方式轉變,幫助學生順利地完成從中學學習向大學學習的過渡。
(二)夯實新生基礎學養
新生研討課有助于克服現行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模式的缺陷,通過課程的實施,有效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探究能力和良好的交流能力等重要的基礎學養。自主學習能力包括積極的學習態度和獨立的學習能力,是學習成功的基礎;探究能力包括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研究和創造的基礎;良好的交流能力包括表達自己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團隊合作能力,也是學習、研究的重要基礎能力。這些基礎學養無疑可以為學生的后續學習提供堅實的支持。值得提及的是,新生研討課大都積極地為新生提供聽說讀寫鍛煉的機會,幫助學生獲得良好的交流與溝通技能,使其學會在口頭上和文字上都能有效地表達其學習或工作的成果。這也正是包括“習明納”在內的研討式教學模式備受青睞的原因之一。
(三)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在學習化社會中,教育不僅僅要為學習服務,而且要為學習者的終身學習服務。大學教育作為基礎教育通向終身學習的重要階段,不僅要讓學生學到現在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態度、能力和習慣。要達成這樣的目的,正如胡森所說,教育過程特別是教學方法就需要有大的改變,其焦點應該放在促進“學”上而不是放在如何“教”上;教學法將鼓勵孩子更多的是自己去學習,要求更多的主動性和自主學習活動;課堂的規模和小組將根據任務而變化,組織更多的討論和獨立作業;學習的個人化要求教師從說教轉變為對學生的學習需求的診斷者[6]P102。新生研討課則可以被看做是現代大學對這種倡導的積極回應,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生存等終身學習能力均可在新生研討課上得到初步的培育。
新生研討課不僅傳承了“習明納”學術自由、獨立、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現代大學理念,蘊含著民主、合作、平等等現代教育的精髓,也有助于實現從應試的、被動的學習向“探究的自主的”現代大學學習范式的轉換。在美國,新生研討課教學形式是大學在新生階段關注和促進學生個性成長的一種有效途徑,已成為大學生最好的學術經歷之一,受到高校學生的普遍認同[7]。新生研討課尤其在引領學生專業選擇、培養新生學術能力、幫助新生順利實現學習階段的過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美國提高本科教育質量的有效舉措。在日本,伴隨其本科教育改革,新生研討課也成為其第一年最重要的內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據其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07年對國立、公立、私立大學的第一年教育的調研顯示,開設新生研討課的大學占到了68.8%,其中國立大學為75.1%,私立大學為68.8%。我國大學新生研討課的嘗試也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本科教學中學化、高等教育質量有所下滑的背景下,新生研討課特有的教育價值更顯得彌足珍貴,其對于大學整體學習改革的引領、示范作用也更加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