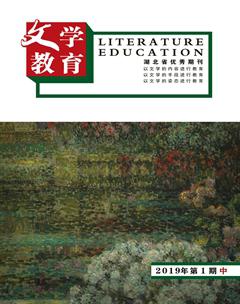建安時期詩樂慷慨悲涼的成因淺探
2019-02-17 06:19:24郭欣欣
文學教育·中旬版
2019年1期
關鍵詞:音樂
郭欣欣

內容摘要:建安時期,由于特定的政治環境,有不少的文人都寄情于音樂之中,并且統治者在與群臣交往時,音樂也成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因此詩樂關系變得更加緊密,兩者是相互影響的;除此外,當時的文人大都具有相當的音樂造詣,有相關的音樂理論和實踐,建安時期詩樂慷慨悲涼的特點也因此而產生。
關鍵詞:建安時期 音樂 詩歌 慷慨悲涼
一.音樂與詩的緊密聯系
建安文人與音樂的關系是十分緊密的,可以這樣說,在整個中國古代文學階段,每個文人與音樂的關系都是如此,音樂從影響每一個具體的文人開始,逐漸形成足夠影響一代之文學走向的地位,建安文人普遍具有很高的音樂修養,這可從筆者粗略的翻閱嚴可均先生《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逯欽立先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兩本著作后,統計出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詩文中看出,圖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這幾方面明顯的特點:
第一,建安時期文人與音樂相關的詩、賦數量還是較多的,尤其以三曹及建安七子居多,如曹操《氣出倡》:“出隨風列雨,吹我洞簫,鼓琴瑟,……酒與歌戲。”[1]《短歌行》:“我有嘉賓,鼓瑟吹笙。”[2]王粲《公宴詩》:“旨酒盈金罍,管弦發徵音,曲度清且悲,……”[3]曹丕、曹植更是有很多的詩賦與音樂相關,曹丕有《善哉行》《燕歌行》《于譙作詩》《孟津詩》《夏日詩》《清河作詩》等等,曹植有《野田黃雀行》、《怨歌行》、《孟冬篇》、《斗雞詩》等等在詩里已經直接涉及音樂,如“管弦”“撫節彈箏”“清商”“箏瑟”等,從這些詩里很清楚地看出,當時音樂是很受歡迎的,尤以清商樂為重,清商樂是一種建安時期十分流行的俗樂,文人間尤甚,這可由建安文人詩佐證,曹丕《燕歌行》中就寫到:“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瘋狂英語·新悅讀(2022年8期)2022-09-20 01:32:1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0年3期)2020-12-16 02:56:12
文苑(2020年6期)2020-06-22 08:41:40
海峽姐妹(2019年6期)2019-06-26 00:52:50
電影(2018年8期)2018-09-21 08:00:00
藝術啟蒙(2018年7期)2018-08-23 09:14:16
兒童繪本(2017年24期)2018-01-07 15:51:37
華人時刊(2017年13期)2017-11-09 05:39:13
西部大開發(2017年8期)2017-06-26 03:16:14
東方藝術·大家(2016年6期)2016-09-05 07:3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