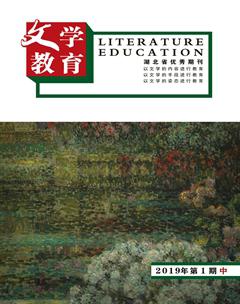意外
姚自蹊

夜很靜。盡管街道上有車,有人,但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無聲的。夏夜的涼風吹在我身上,這是我對外界的唯一感知。我很緊張。我即將去完成一件大事,生死攸關的大事。
我將自行車騎得很快。離家越來越近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一處狹窄的巷子入口,巷子里面黑黢黢的,黑的像是要把我吞沒。入口處一盞昏暗的路燈,仿佛隨時要被夜風吹滅。踩踏板的腳頓了一下。但我終究還是向這吃人般的黑暗騎去。
不要慫!我對自己說。高度的緊張令我的感官敏銳又麻木。我保持著高速而均勻的行駛。到了!我快速伸出手去,緊握住黑暗中另一只手。冰冷而光滑,像乳膠制的假手。但我知道這是一只真手,來自一具男尸。我強迫自己緊握住它,拖著尸體飛快騎行。不知騎了多久,我的直覺告訴我,該是出手的時候了。于是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將這只手甩了出去。我似乎將尸體甩過墻,甩到了巷子的另一邊。體育課上扔鉛球,我的成績一向很差。不知道為何,這時迸發出這么大的力氣。我好像還握著這只手掄了幾個圈才脫手。但由于緊張,我已經忘了我到底有沒有握著它掄幾圈。
我已經完成得很好了,我盡力了。我對自己說。雖然這樣講出來不是很好,我是個善良的人,但我承認我就是這樣想的——由于知道他不久之后會復活,我對他的尸體做這種事的罪惡感減輕了一些。
將車騎進小區時,保安看我的眼神很怪。是我表現得太明顯了嗎?我知道這方面我不夠成熟,我總將情緒寫在臉上,而不是埋在心里。我懼怕那種探尋的眼神,因為我這個人很容易被看透。
騎過小區里玩鬧的孩子們身邊時,不知是不是由于我的錯覺,我覺得孩子們的嬉鬧聲小了,他們也看著我,帶著那種不懷好意的好奇與探尋,和他們的父母一個樣。
終于到了。我停好車,轉身的瞬間看到一個人!住我家樓下的李奶奶。今天的她也和平時不一樣。平時她對我很熱情,見我就笑,大聲和我打招呼。我不喜歡她,但也不討厭。今天她仍對著我笑,滿是皺紋的臉笑嘻嘻的,我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那笑仿佛是一種大聲的宣告——看哪!這個兇手!我匆匆向她點了一下頭,算作打招呼,然后逃離般往家跑。
到了家門口,我不敢大聲敲門,喊媽媽來給我開門,盡管我很想這么做。我急急忙忙在書包里找鑰匙,不到十秒我就找到了它。我想我的心理素質還行,因為此時我背后仿佛有一大票人即將追來,嘴里喊著“兇手!兇手!”我哆哆嗦嗦開了門,進門看到媽媽的一瞬間我幾乎要哭了。幾乎,但我沒哭。因為她的表情讓我硬生生止住了想要撲上去親親抱抱并且埋在她懷里嚎啕大哭的沖動。她的表情很輕松,顯然現在她對晚飯的興趣大過我。“媽媽。”我讓自己的聲音盡量正常一些,像平時一樣喊了她一聲。“嗯,吃飯。”她說。語氣跟平時一樣,甚至還有一絲高興,大概因為晚餐有幾道她愛吃的好菜。爸爸也從房間里出來了,臉上是一貫的嚴肅淡漠。我絕望的把頭轉向借住在我家的表哥,他一臉同情的回望我兩秒,然后開始吃飯。“我不太想吃飯。”我賭氣般說。“嗯,那就想吃的時候再吃吧。”媽媽頭也不抬的繼續夾菜,在咀嚼的間隙回了我一句。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我覺得我委屈的要化掉了。為什么?為什么?他們明明知道的!知道我今晚做了什么,知道這一切來龍去脈。為什么要裝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樣子!這種毫不在意的態度,讓我憤怒,更讓我傷心。我不是他們的孩子嗎?雖然他們有過數不清的孩子,但現在,此刻,這個家里,我是他們唯一的孩子啊。雖然這種事對他們來說習以為常,但我是第一次做啊。十六年來,我像個普通的孩子一樣長大,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我努力做了普通孩子做不了的事,我是不是很棒啊,受了很多委屈啊,為什么你們都不關心我一下?
今晚所有的面孔一一在我眼前出現,那些奇怪的、似乎看穿一切的目光,保安的、小孩的、李奶奶的,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所有人,都在聚攏,不斷聚攏,烏泱泱一片。他們朝我說話,又或是在竊竊私語,我聽不清,但有一個聲音格外清晰——“兇手!這個兇手!”我知道這句話可以囊括所有我聽不清的聲音,這些聲音濃縮成一句話,就是“兇手!這個兇手!”我想大聲咆哮——“我不是!你們這些蠢貨!”但我不能,我像是被定住了一般,越縮越小。我覺得我哭了,身體從某一處開始慢慢化了。但當我能動時,我摸了摸我的臉,是干的。
我站起來,推開門,時間仿佛過了一個世紀。外面天色都亮了。我走向陽臺,打開窗戶,以面向大地的姿勢跳了下去。“砰!”一聲悶響。我的臉砸進小區花壇的泥土中。我知道我摔不死。準確來說,我是永遠不會死的,即使死了也能夠復活。
我面朝下躺在花壇里,清晨濕潤的泥土弄的我有些難受。我不會流血,所以那些沖我喊“兇手!兇手!”的人,看見我這個樣子,沒準以為我在裝死或是進行什么神經病的舉動。以昨晚我做的事為界,在這些正常人的眼中,這之前我是他們的同類,這之后我就不是了。所以他們不會將眼前的場景聯想到自殺或是以死自證清白之類的。想到這里,我有點難過。
我努力撐起身子,艱難的爬出花壇,爬到路上。我想我此時比昨晚甩出去的那個更像尸體,一個自己移動著的尸體。我爬到路中間,仰面躺下,已經無力動彈。小區的小孩子們不知何時突然出現。他們圍著我聚攏,像在看一件新奇的玩具。一個小女孩沖我笑了,天真爛漫。然后她把手伸出來,開始撓我癢癢。我很難受,想阻止她,但一點力氣都沒有,每動一下,都感到一陣鈍痛。我的力氣,我的感官,正在一點一點消失。但我能看到,從花壇到路中間,我爬過的地方,拖出了一道粗壯的血跡,我躺在自己的血泊中,被一群孩子圍觀。不知何時,天開始下雪。一片,一片,將這一切都蓋住了。
以上是從一個不死者的記憶球中提取出來的回憶,在這個十六歲的不死者的葬禮上。我們這個族群和普通人類大致相似,不同的地方是,我們永生不死。即使有什么意外使我們“死去”,只要請同族人為我們進行一項儀式,我們就會復活——就是這個十六歲的不死者在臨死前的晚上進行的儀式。這個儀式對我們來說,也相當于成人禮。一個年輕的不死者第一次為他的同族進行過這個儀式后,意味著他正式成年。
這個十六歲的不死者,不知為何,在其“自殺”之后,經過了夜晚的儀式仍無法復活。于是我們按照人類的方式舉行了一場葬禮,在場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參加葬禮。這位不死者的父母在葬禮上表現得很傷心,就像人類一樣。雖然他們有過數不清的孩子,但這是唯一一個死了的孩子。不過只要他們愿意,他們還會再有許多新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