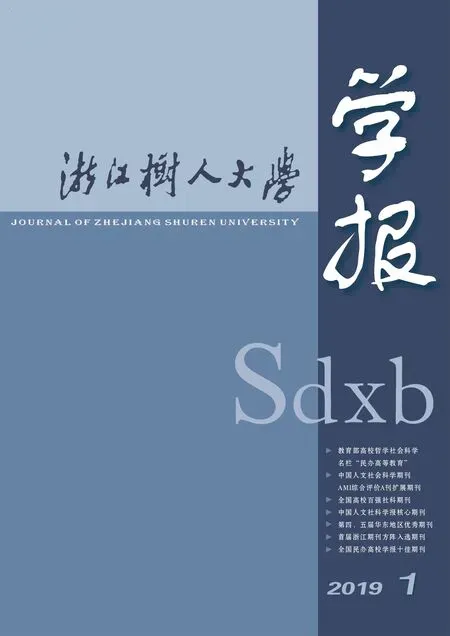從設施到場景:城市更新的文化策略
——基于Z省P市的個案研究
徐雅琴
(浙江樹人大學 人文與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5)
2013年,上海市出臺《關于營造上海城市文化氛圍的三年行動計劃(2013—2015)》,旨在推進文化地鐵、城市廣場音樂會、市民文化節、城市藝術集市和街頭藝人展演等項目,以營造開放、活躍、本色和寬松的城市文化氛圍。城市更新是城市有機體新陳代謝的過程,既是物理空間的再造,也指文化傳承、經濟增長與社會正義維持等重要議題。文化正成為我國城市更新的通行策略,在改善城市文化形象、實施“文化+”戰略、發展文化產業背后更為本質的議題是作為娛樂機器的城市①Clark T N,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Research in Urban Sociology, 2004, No.6, pp.357-378.價值觀,也即城市場景②吳軍、特里·N.克拉克:《文化動力——一種城市發展新思維》,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頁。或曰城市氣質對文化創意階層的吸引、對文化消費力的促進、對文化創造力的培育。在其他城市尚著力推行園區建設、場館修建之外,已有田子坊等諸多成功典例的上海市開始推動無形的、長期的城市文化場景建設,這對于陷入歷史文化斷裂、產業動力不足和社會排斥嚴重等困境的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場景理論作為優化城市文化政策的分析框架等值得關注。
一、城市更新文化策略成敗的啟示
畢爾巴鄂是西班牙的一座小城,古根海姆博物館的落地以及由此而來的“古根海姆效應”,使這座遭受洪災和經濟危機雙重打擊的衰退工業城市在過去的20年逐步發展成為充滿活力的文化藝術之城;2013年,曾是美國第五大城市的底特律申請破產。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興建文化復興中心、體育館等文化導向的城市更新策略以失敗告終。這兩座城市的經驗與教訓,對正在實踐文化策略的我國城市更新有何啟示?
(一)文化成為城市更新的通行策略
全球化進程推動資金、信息、技術和人力等知識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資料廣泛流通,使傳統的依賴自然資源稟賦建立差異化優勢的城市發展模式面臨挑戰。發揮著協調作用的國家經濟實體——其功能從傳統意義上來講是由民族國家擔當的——地位在不斷下降,地區和城市作為頗具競爭力的競爭實體,其自治能力與重要作用在上升[注]德波拉·史蒂文森著,李東航譯:《城市與城市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頁。。城市演變成獨立的經濟行為體及其在與知識經濟諸多生產資料博弈中的弱勢地位,加劇了城市經濟增長的難度。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化率已從1978年的17.92%、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17年的58.52%[注]國家統計局:《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 城市面貌煥然一新——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一》,2018-09-10,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10_1621837.html。,這表明我國僅用不到4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從農業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的過渡過程[注]文軍:《城市更新的社會文化基礎及其張力》,《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第30-33頁。。伴隨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作為主導產業的傳統制造業、加工業,逐漸遭遇生產成本、資源、環境和土地等壓力,城市發展面臨著產業結構轉型的困境,依托既有土地、建筑等存量資源開發的城市更新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路徑。此外,契合消費升級趨勢的文化產業正顯現出強大的經濟拉動作用,文化旅游的發展、城市形象的營銷以及由此帶來的發展活力,為尋求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的城市更新提供新的可能,文化成為城市更新的通行策略。
城市更新的文化策略有三種類型:一是通過改善城市形象及文化影響力吸引資本、技術以及人才等實現城市發展;二是通過“文化+”模式實現旅游業、制造業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三是發展文化產業。其中,尤以第三種類型最為凸顯:一方面,文化產業具有新業態、高速成長的特點,能從國際產業分工和價值鏈的高端位置,將經濟、文化、技藝和藝術有機結合,對創新型經濟的發展起到戰略引領作用;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具有城市空間響應特征,能在城市發展方式轉換、空間功能轉換、空間布局規劃以及培育創新體系等方面發揮多元和系統的作用,與城市整體的轉型升級關系密切[注]周蜀秦、李程驊:《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城市轉型的機制與戰略路徑》,《江海學刊》2013年第6期,第84-90頁。。
(二)硬件設施建設與文化策略失效
文化策略的實踐階段不同,目的指向也有差異。20世紀80年代,西歐許多國家接受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當地政府的財權受到擠壓。國家政治導向的改變和對當地政府花銷削減的壓力,使策略目標從社會發展轉變為經濟發展[注]佛朗哥·比安基尼、王列生:《重建歐洲城市:文化政策的角色》,《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8期,第117-126頁。,經濟發展成為城市更新的優先指向。作為城市更新策略的文化也是作為城市經濟發展動力的文化,指向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
那么,文化策略的效果如何?建設文化產業園區、大型場館和娛樂設施是我國城市更新文化策略的慣常做法,可作為研究材料。以文化產業園區為例:從20世紀90年代起步到2002年末只有48個園區建成,2012年為1 457個,2015年已達2 506(見圖1)[注]數據來源于智研咨詢集團《2016—2022年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園行業市場分析及發展趨勢規劃報告》。。但與“造園”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入住率不高、90%以上處于虧損狀態,更無從談及園區對城市的輻射帶動[注]張云飛、張曉歡:《試論我國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的現狀、問題與對策》,《中國市場》2013年第20期,第42-46頁。。很多大型場館也變成了“鳥巢”,凋敝冷清,沒有展示、沒有展覽、沒有表演、沒有活動,成為名副其實的鳥來筑巢和蜘蛛拉網的“巢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文化策略效果并未達成。

圖1 1990—2015年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數量變遷
文化嵌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化策略發展不當會造成諸多社會問題,致使資本外逃和人口流失等塌方式衰敗。1950年,底特律擁有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巨頭,180萬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68萬人口,僅為1950年的38%,且成為美國最貧困、失業率最高、最危險、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城市[注]馬秀蓮、吳志明:《掙扎的底特律:后工業城市復興的理論、實踐與評述》,《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第1-9頁。。其背后的邏輯在于市民參與的文化轉向,即伴隨著物質生活的普遍提高,個體變得越來越富足,市民對生活方式、價值理念與社會公正環境等非經濟性訴求越來越看重。已有實證研究表明,城市包容性、文化氛圍、公共服務以及沙龍俱樂部等社會文化因素正在替代收入等經濟因素,成為我國年輕人城市選擇的重要原因[注]吳志明、馬秀蓮:《文化轉向:大學畢業生城市流動的新邏輯》,《當代青年研究》2015年第1期,第88-93頁。。
(三)文化策略失敗的解釋及解決
古根海姆博物館對西班牙畢爾巴鄂市轉型、“倫敦眼”對倫敦城市形象和經濟價值的提升以及迪斯尼樂園對上海旅游業的帶動等案例表明,興建文化產業園區、大型文化設施是文化策略的重要內容。為什么某些城市以設施為主的文化策略會失敗?即便是建設同樣的設施,為什么會出現截然相反的結果?夾雜著封堵“開墻打洞”、驅趕“低端人群”的城市更新,來勢洶洶,使公共政策的驚心動魄性遠超資金和人力的浪費,對歷史文化的破壞、對文化創造力的傷害、對文化消費力的堵塞及以上問題的不可逆性,使城市文化發展策略及政策的制定成為需慎之又慎的議題。基于文化策略的重要性和風險性,本文擬回答如何解釋以及如何解決設施建設為主的文化策略失敗問題。
二、場景理論釋義及其運用
芝加哥大學特里·N.克拉克教授提出的場景理論運用社會學視角解讀城市文化經濟增長問題,關注作為城市更新實踐背景的場景問題,為文化策略失敗提供理論解釋。
(一) 場景理論概述
場景(Scenes)是指電影藝術的對白、場地、道具、音樂、服裝和演員等元素傳遞給觀眾的信息和感覺。芝加哥大學教授特里·N.克拉克領銜的“財政緊縮與都市更新”研究團隊將這種現象引入城市社會學研究中,形成場景理論。場景含義至少涵蓋以下5個維度:一是社區。其小巧的體量比城市或國家之類較大的空間范圍,更易捕捉到內外部的區別;二是物質結構(咖啡館、酒吧、書店、博物館和音樂會等);三是由種族、階層、性別和教育程度標簽化的個體;四是前三者和參加音樂會相類似活動的結合;五是人們在某個場景中追尋的價值觀[注]Silver D, Clark T N, A Theory of Scene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onsumption, http://scenes.uchicago.edu/drafts/scenesbook/A%20Theory%20of%20Scenes4-30-07.doc.,由合法性、本真性和戲劇性3個主維度以及15個次維度組成(見表1)[注]吳軍、夏建中、特里·N.克拉克:《場景理論與城市發展——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新理論范式》,《中國名城》2013年第12期,第8-14頁。。
(二) 文化設施策略的實踐背景
過去10年,社會科學領域關于城市發展與經濟增長有兩大中心議題:一是托克維爾和普特南等所持的“參與促進發展”;二是熊彼特、雅各布斯、佛羅里達和格萊澤等人所持的“創新驅動發展”,該議題還認為波西米亞(狂放不羈的文化或者精神)是驅動創新的核心要素。產生在歐美社會的議題一在其他地區受到質疑,市民參與對政治體系并沒有影響,甚至有可能減少對政治體系的信任和支持;而議題二中的波西米亞精神在亞洲大部分地區也比較弱甚至看不見。場景理論以上述兩項議題為基礎,加入作為實踐背景的場景因素,通過15個維度形成以下三個理論:理論一,市民參與的理論;理論二,創新與波西米亞的理論;理論三,重新解釋理論一和理論二的沖突與不一致的理論[注]特里·N.克拉克、吳軍:《一起卡拉OK VS.獨自打保齡球:西方規則轉為發展與民主驅動力的場景詮釋》,《社會學評論》2015年第6期,第44-53頁。。

表1 場景的分析框架
場景理論啟示人們關注文化策略實踐的基礎背景,這種背景由客觀的文化設施、主觀的價值觀念和作為主體的消費者三重維度組成。文化設施策略失敗的原因在于,沿用硬件思維治理文化,將市民看作單個原子,將娛樂設施和文化活動看作萬能的人工礁石,似乎照搬照建,魚群便能自動聚集,文化便能自動生長。事實上,文化設施不能脫離當地基礎背景,不會憑空產生;設施和設施之間以及設施與人的實踐活動之間并非沒有關聯而各自獨立。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富有魅力、自我表現和藝術氣息濃厚的場景特質之外的區域推行前衛的藝術節或者過度娛樂的政策似乎是陌生而危險的;相反,園藝、徒步以及社區節日等活動可能更加有效[注]Silver D A, Clark T N,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p.302-303.。
(三)場景理論的具體運用
在工業社會,城市經濟增長來源于土地、自然資源和資金等;在后工業社會,藝術館、圖書館和展覽館等文化場館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文化創意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城市競爭力體現為其吸引創意階層的能力。佛羅里達最早提出“創意階層”理論,他發現美國科技產業城市分布與同性戀人群城市分布的重合率較高。原因在于,同性戀人群偏好的城市較為開放、包容,這種城市氣質同時吸引了普遍有點怪癖的創意階層[注]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Basic Books, 2002, pp.66-80.。作為一種媒介,城市空間或曰文化設施傳播的文化價值觀對創意階層的吸引是有影響的。因此,文化策略之文化是符號意義和價值觀念,重在能否吸引創意階層。
明確城市或場景的文化價值之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對于制定城市文化政策仍不夠具體,特別是要明確哪一部分、哪一類別文化價值起到了積極作用,此時,場景理論為評估測量提供了工具:建立涵蓋劇院、影院、書店和博物館等藝術文化設施的數據庫;采用專家打分法,按照五分量表分別對某個單一設施的15個價值觀進行賦值;根據某一設施的數量及賦值計算某一區域的場景得分;根據研究目的進行相關或回歸分析,找出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以此邏輯推延,城市的設施建設和文化活動可根據以上15個維度來測算,以便了解這個地區的文化特質是否適合建設相應的文化設施,設施興建之后還需進行有針對性的補充。比如麗江古城,其主體文化是少數民族風情,在增加酒吧街、推出“艷遇麗江”的概念之后,增加了青春、激情等現代文化的特點,極大地吸引了年輕游客[注]祁述裕:《建設文化場景培育城市發展內生動力——以生活文化設施為視角》,《東岳論叢》2017年第1期,第25-34頁。。
三、案例印證:Z省P市場景優化
2017年7月至9月,筆者選取我國南部Z省縣級P市進行實地調研,深度參與《P市文化產業三年行動方案(2018—2020)》以及《P市關于進一步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試行)》的制定。隨機采訪政府工作人員14位,探尋政府部門推動城市更新的主要思路;走訪調研文化企業14家,探尋文化企業發展中的問題及對現行文化產業政策的評價等;隨機訪談市民6人,探尋市民對城市發展感受及對城市政策的評價。
(一)個案的典型之處
本文研究的問題類型是“怎么樣”和“為什么”,研究對象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件,研究者對當前正在發生的事件不能控制,適用于案例研究方法。單案例研究有檢驗廣為接受的理論、極端案例分析、縱向案例分析等五種適用范圍,本文意在研究典型案例,以加深對同類事件、事物的理解。P市城市更新的背景、問題和模式有以下兩個典型之處。
1.遭遇著中國城市更新的普遍背景。即面臨產業結構轉型和文化消費升級的雙重挑戰與機遇。P市以服裝、箱包為傳統產業,發展模式的關鍵詞是世界工廠、人口紅利、出口加工,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產品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未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和知名品牌。21世紀以來,P市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工業拉動,隨著人口紅利減弱、資源壓力凸顯以及環境約束增強,工業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傳統制造業生產經營方式尚未轉變,難以擺脫低端制造、低價競爭的路徑依賴;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偏慢,2016年P市服務業增加值占比39.5%,而全國、全省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均為51.6%,差距較大。
2011—2015年,P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1 902元、36 053元、39 659元、43 192元和46 470元,年均遞增10.7%。居民收入穩定增長推動消費不斷升級。P市地處長三角經濟圈中心地帶,北接上海、南瀕杭州,也是寧波、蘇州一小時經濟圈的中心,交通便利、環境良好等方面的優勢明顯,對于周邊中心城市文化消費的吸附能力逐漸增強,面臨新的發展機遇。
2.面臨著我國城市更新文化策略的普遍問題。即城市基礎設施較為落后,文化產業發展粗放。《Z省文化產業發展“十三五”規劃》顯示,到2020年全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將達到8%以上,文化產業將成為Z省的八大萬億產業。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通過與收入考核和政治前途掛鉤的模式,推動Z省各級政府推動文化產業發展。P市所在地級市J市實行與P市相關文化主管部門年終獎掛鉤的“文化發展指數考核”。在此考核標準下,設施建設、產業投資等文化產業發展的諸方面由產業政策的引導而快速落實,在市場需求和政策引導雙重作用之下,文化產業發展成為P市的重要課題。
目前,P市文化產業以小規模、分散化經營狀態為主,規模以上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僅占總量的4.8%,優勢明顯、特色突出、帶動作用大的龍頭企業較少。2016年印刷、童車等文化制造業增加值占P市文化產業增加值的3/4;現有的文化服務業企業集中在廣告設計、娛樂和文化旅游等低端行業,需求旺盛且增長強勁的軟件業、影視業、會展業和網絡游戲等新興文化產業發展不足。P市的兩處文化產業園區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企業入駐率不高,空殼化明顯。此外,創意人才不能扎根,高端人才缺乏,從訪談中了解到,這與當地缺乏良好的基礎設施、商業環境、生活配套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才歸屬感缺乏息息相關。當地推行的“文化禮堂”對由下而上的自發性文化建設作出嘗試。截至2017年9月,P市鎮街道共建有特級文化站3個、一級文化站6個,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室)在全覆蓋基礎上,建成60個文化禮堂,群眾性文化活動也正在展開,但目前很多活動以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人員攤派的形式展開,普通市民的參與率不高。通過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調查了解到,群眾性文化活動發展定位不明確,特色不鮮明,缺乏統籌安排。2017年上半年,新對接21家文化企業,涵蓋影視文化、軟件開發、藝術培訓和文化旅游等多個行業,且很多項目的選擇是偶然性的。
(二)P市場景風貌觀察
1.戲劇性觀察。戲劇性觀察是關于“如何展示自己”也即“城市風格”的測量。將城市擬人化,戲劇性就是個人的衣服、演講、行為、手勢、穿戴和面龐等給別人留下的印象。戲劇性可以是溫暖的、親密的、友善的,或者是正式的、挑釁性的,是城市風格特征的表現。在特里·N.克拉克團隊研究中,酒吧比較集中的街區代表著開放或叛逆,有利于吸引創意階層和文化消費人群。
P市戲劇性可描述為睦鄰的、正式的,違規性不明顯。其地標性建筑報本塔修建于明嘉靖年間,明清兩代,報本塔幾度廢興,屢坍屢建,成為P市持續時間最長、參與面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一項民間文化工程,既是有形文化地標,也是無形精神符號。主持修建的邑人陸杲在《報本塔記》中寫道:“蓋天地者,萬物之本也;大君者,萬民之本也;父母者,身之本也;師者,闡教作人之本也。統宇宙所有,莫不有本,容無以報之乎?” P市夜生活設施較不發達,68.61萬常住人口(截至2016年底)僅有4家酒吧、2家電影院以及1家購物中心。教育設施數量較多,幼兒園46所,小學17所,普通中學18所,中等職業類學校3所,各類職業技術培訓機構24個。這反映出的城市風格與“報本”精神強調的敬天法地、孝老榮親、尊師重教等傳統理念相一致。這種城市戲劇性也反映在商業領域,企業經營管理理念較為傳統,以“穩妥”為主,對于冒風險的“轉型升級”“創新突破”等嘗試不夠;正直、忠厚、與人為善是P市企業經營者普遍的品質。
2.合法性觀察。合法性觀察是關于“如何界定行為對錯”即“道德權威標準”的測量,考察的是城市場景所推崇的核心價值觀。P市場景合法性維度主要體現在傳統和功利兩個維度。
P市歷來人文興盛,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的傳播與浸潤深入人心,以“琴、棋、書、畫、印、唱、燈、舞”為城市名片,號稱“中國書法之鄉”“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文人墨客和世家大族浸潤之后遺留的是高雅藝術。P市的李叔同紀念館、陸維釗書畫院、吳一峰藝術館、民俗風情館、文化館、城市規劃館以及在建的璽印博物館等文化設施,更多指向傳統主義維度。
P市西瓜種植歷史悠久,刻瓜制燈是當地的特色民俗。“西瓜燈文化節”自1991年創辦以來,至今已有20多年歷史,是P市最大的節慶活動之一,主打特色文化和藝術活動之余,與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的滲透日漸明顯。2017年,該文化節設置“開幕式暨投資貿易洽談會”“產業轉型升級論壇咨政座談會”和“服裝設計大賽”等環節,借此推介P市的投資環境、政策優勢以及支柱產業,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取向。
3.本真性觀察。本真性觀察是關于“你真的是誰”的考量,考察城市場景是否受到外部文化影響、沾染乃至同化。本真性是社會層面的文化認同,也是產業層面的異質符號,如文化旅游建立在游客對異質文化的消費凝視之上。這種本真性糾纏在當地人對現代生活和異域文化的渴望、營造虛假“本真性”以迎合文化消費者的動機以及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影響之中,呈現出復雜性。P市特別是中心城區的本土性場景較為完好,“老味道”“原汁源味”“百年老店”等餐廳數量較多,有地方特色的書場等文化消費場所也較為常見,“尋找P市老味道”“尋找江南好匠人”“P市人講P市故事”等文化活動活躍。
這種本土場景本真性的維護與行政推動關系密切,如P市僅存的書場因房屋結構問題于2008年關門,后經地方政府出資保育,2011年重新裝修;一系列主打P市特色的文化活動也是近幾年在政府主管部門的推動下展開。這種本土場景的營造還與經濟效益關系密切,如主打作為營銷策略的“老味道”符號是餐飲店鋪的自覺和共識。行政力量驅動的城市場景本真性維護容易出現“為了本真性而本真性”的傾向,并非一種自下而上的文化生長,而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規劃,這也導致P市諸多文化活動的市民自發參與率不高。
(三)P市城市更新文化策略的優化政策
道路、樓宇以及園區猶如城市骨骼,而城市場景的涵養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血肉,關注實施文化策略的場景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原則。
1.豐富日常生活,提高城市場景本真性。“創意階層理想的生活狀態是讓生活變得真實和鮮活,比起被動觀看體育運動,他們更喜歡那些具有自主性、能夠親自參與其中的娛樂活動,他們喜歡本土的結構文化,喜歡那里由咖啡館、街頭音樂家、小畫廊和小酒館構成的種種風情”[注]理查德·佛羅里達著,司徒愛勤譯:《創意階層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頁。,“一家路邊的咖啡館,就把一條街道從臨時工人和無家可歸者手中奪了回來”[注]沙朗· 佐京著,張廷佺等譯:《城市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頁。。日常生活是使作為產業符號和認同機制的本真性歸位的內生力量。P市當前的本真性場景更多地依附于政府推動的文化自信工程,從其現有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來看,興建棋院、推進璽印篆刻博物館等大型場館,舉行與文化自信相關的諸多活動依然是重點所在,而優質電影院、精致咖啡館等生活娛樂類設施建設尚未提上日程,有參與感和生活氣息的文藝活動也并不在規劃之內。這種情況在我國城市更新、文化發展中較為常見,指向政績考核的行政力量和承載經濟效益的象征價值,容易脫離日常生活。
P市歷史上物產豐富、水網密布,相對安定,是一方樂土,當地居民有自娛自樂的傳統,因此,應提高產業發展與現代日常生活的互動性。具體而言,應注重園區建設與市民審美提升的關聯度。P市兩處文化產業園區都以孤立的樓宇形式存在,空間逼仄、開闊性不夠,與市民生活互動不足,日常實踐、生活美學可以帶給城市雕塑、文創園區以生命,而民眾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美學的感召,提升消費品位,儲藏消費動能。
2.鼓勵多元文化,涵養城市場景戲劇性。理查德·佛羅里達用波西米亞指數、人口混雜指數、種族融合指數和同性戀指數考核文化包容性,認為創意階層更傾向于居住在聯系松散、進入障礙較少的社區,而非遵從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規范的聯系緊密社區[注]Florida 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No.4, pp.743-755.。這一理論發現始終具有指導意義,“創意產業需要蓬頭垢面、放蕩不羈的波希米亞人”,這樣一種典型的波希米亞場景“寬容地接受文化人的奇談怪論、特立獨行,寬容地接納藝術家的奇思妙想和作品的奇形怪狀”[注]金元浦:《藝術創意集聚區與“波希米亞族”》,《藝術評論》2011年第4期,第31-34頁。。伊麗莎白·科瑞德重點關注了紐約夜生活中的文化經濟,認為休閑吧、酒吧、慢舞吧等非正式場合是創意碰撞和交易達成的重要場景:“大家心知肚明……許多重要的決定不是在董事會議上作出的,而是誕生在舞池里。”[注]伊麗莎白·科瑞德著,陸香等譯:《創意城市:百年紐約的時尚、藝術與音樂》,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頁。
在特里· N.克拉克提出的理想的波希米亞場景里,有3個維度得分最高的選項分別是自我表達、挑釁性以及少數群體。當前,P市場景以正統和傳統為主,某位打扮“怪異、新潮”的企業家能否出現在P市城市宣傳片引起該市外宣部門的爭議,P市以Z(某第三方機構發布的2016年度中國網絡紅人排行榜中位居前三)為代表的網絡紅人也并未出現在該市服裝產業規劃中。文化產業是城市經濟的產物,與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P市可適度引進更富現代化、適度新潮前衛的生活娛樂設施,增加城市場景的現代魅力以促進文化消費、吸引創意人才。
3.提升經濟效益,實現城市場景合法性。2011年,P市成為Z省“美麗鄉村”項目首批創建先進縣,當下該項目的資金來源有三:市政財政及其他部門向省以上競爭性爭取的專項扶持資金,市政財政安排、統籌(含融資)及整合的“美麗鄉村”建設資金,鎮街道配套資金。可見,資金來源以行政力量推動為主。P市“美麗鄉村”項目的推動對于營造優美的江南特色、改變城市風貌有一定的幫助;但是該項目的推動主要倚靠行政力量,市場邏輯弱化導致所依附的旅游產業并未發展壯大,《Z省深化美麗鄉村建設行動計劃(2016—2020)》中提出“以水為鏡、以凈為底、以美為形、以人為本”并未提到產業層面的問題。P市村民大多持圍觀而非參與的態度,導致該項目預期效果無法達成。
合法性關注市民認可,良好的政策愿景需要獲得合法性才能在實踐中達成。P市既有場景的合法性關注傳統主義,與文化自信相關的政治績效考核傳導的結果對市民認同的喚起和對產業符號的促成等愿景是好的,但實踐效果不理想,原因在于未與產業發展、經濟獲利這一合法性關聯。特里· N.克拉克框定的理性場景強調自我表現、無用藝術等的合法性,在當前的現實經驗中似乎難以達成。作為一種消費嚴重依賴文化“前見”的產業,消費者知識結構、文化素養、審美趣味直接影響著產業生態和價值導向;反過來,優質的文化產品也可涵養消費者的審美趣味,如何打破這樣的循環圈是政策的著力點,顯然,產業發展和市場邏輯是一種可能。
本文的價值有三:一是引入場景這一城市經濟學和城市社會學前沿理論,為以文化為策略實踐更新的我國城市提供一種警示、解釋和優化路徑;二是對P市這一典型個案分析的過程中,連帶出績效考核、數字崇拜等文化產業發展中的其他問題;三是本文的上位研究是空間與文化經濟,此空間可以是產業集群、城鎮、城市乃至國家,場景理論關注作為實踐背景的文化背景,為當下特色小鎮建設等提供借鑒。但因條件受限,無法采用正規的專家打分法,只能采用質性的觀察和訪談;場景理論的分析結果需要借助對比以引發進一步的討論,本文采用的個案研究無法橫向比較。以上不足之處,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