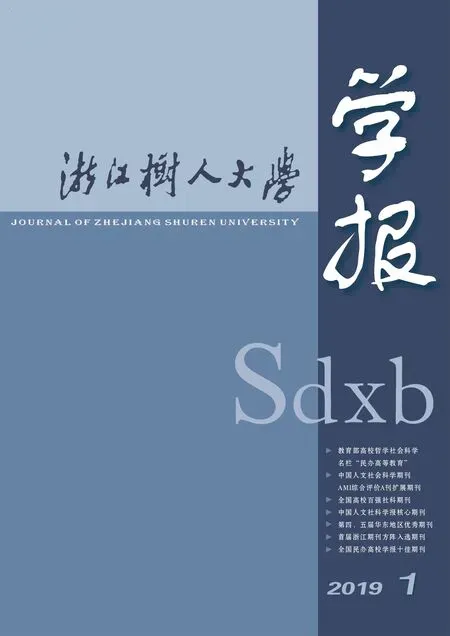教育資源流動視角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現狀、問題與策略
劉 琪
(貴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貴州 貴陽550001)
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我國正著力于完善教育對外開放布局。2016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明確了對境外辦學、中外合作辦學和共建大學聯盟三種模式發展的要求。為貫徹落實《若干意見》,同年8月,教育部牽頭制定《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特別提出實施“絲綢之路”合作辦學推進計劃。東盟經濟體量龐大,又與我國山水相鄰,一直是我國的重點合作對象。為使合作達到最佳契合點,本文以教育資源流動為視角,分析我國與東盟國家高等教育合作的現狀和問題,進而提出發展策略。
一、教育資源流動視角下高等教育跨境合作模式
教育資源是支撐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主要指各類教學元素和關乎教育的知識技能、制度理念、品牌人格、資產設施等資源,其集聚度因國家(區域)不同而有所差別。早期高等教育交流的主要內容是人員流動,帶有自發性,在“人往高處走”的自然規律下,其流向通常由高等教育欠發達國家(區域)流至發達國家(區域)。隨著國際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現代高等教育交流的內容已經由人員流動擴展至跨國辦學、共建區域性和全球性協作組織等多種模式合作,其背后的驅動力量也由公益性、營利性和政治性等構成,資源流向更具多樣性。高等教育國際化有助于擴大資源總量,特別是優質資源的增量和存量,還可為先進經驗的交流提供平臺和契機①馮用軍:《“一帶一路”倡議下馬來西亞私立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60-69頁。,因此,由教育合作產生的資源流動更多帶有政治性質的驅動力量。從教育資源流動走向研究教育合作模式,是一個獨特的視角。站在中國的角度審視高等教育資源跨境流動的走向,“走出去”的主要實踐形式是境外辦學;“引進來”的主要實踐形式是中外合作辦學;共建跨境大學聯盟則是介于“走出去”與“引進來”之間的一種中間形式[注]劉琪:《中國—東盟中等競爭力水平國家高等教育合作路徑探析——基于馬來西亞、泰國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分析》,《中國高教研究》2017年第7期,第62-67頁。,是教育資源的有效整合。
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把中外合作辦學定義為“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教育機構的活動”。目前,中外合作辦學是我國唯一需要經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審批并上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備案的一種涉外辦學模式,目的是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豐富教育供給。境外辦學旨在輸出教育資源,與中外合作辦學協作,形成資源進出雙向流動。我國《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暫行管理辦法》將境外辦學定義為“高等學校獨立或與境外具有法人資格并且為所在國家(地區)政府認可的教育機構及其他社會組織合作,在境外舉辦以境外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教育機構或者采用其他形式開展的教育教學活動”。跨境大學聯盟則指在跨境區域內,匯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教育資源進行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從而更好地服務區域社會經濟建設[注]劉琪:《北極大學:一個新型跨境大學聯盟的案例分析》,《外國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第42-54頁。。
二、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現狀及問題
我國與多數東盟國家均非高等教育強國,通過合作促使教育資源流動,有助于增強高等教育競爭力和跨境人才培養能力,還有助于促進人文交流。目前,中國—東盟高等教育三種合作模式的發展呈現中外合作辦學整體弱、境外辦學規模大和共建跨境大學(教育)聯盟發展快的特征,但這一現狀并不符合中國—東盟區域建設的需求。
(一)面向東盟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現狀及問題
中外合作辦學在涉外辦學模式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為跨境教育在我國最重要的實踐形式,當前這一模式的發展已由外延擴張轉向內涵建設。截至2017年5月,全國經審批的各類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共計2 539個,面向東盟的有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泰國合作舉辦的44個機構和項目,占總數的1.7%,其中本科及以上層次項目數僅8個(見圖1)。從項目分布狀況來看,舉辦高校主要集中在江蘇、新疆和吉林三省,占比分別為35%、18%和9%,其余項目則零星分布在9個省市(見圖2)。統計發現,面向東盟合作項目的專業主要集中在會計、管理等社會科學類別,僅有3個工程技術類項目[注]依據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信息工作平臺(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公布數據以及對數據的計算結果而得。下文中外合作辦學相關數據若無特殊標注,皆來自該網站。。

圖1 我國與東盟國家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個[注]數據來源于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

圖2 我國與東盟國家合作辦學項目地域分布情況⑤數據來源于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
我國與東盟的合作辦學呈現數量少、規模小、層次低和分布窄的特點,對比當前東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所占的經濟體量,現有的辦學規模遠不能滿足“一帶一路”建設人才支撐和人文交流的大局所需。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圈定的18個沿線重點推進省市中,與東盟接壤的云南省僅與泰國舉辦了2個項目,而唯一與東盟國家既有陸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廣西壯族自治區,至今未有面向東盟合作辦學的項目。節點城市未能發揮區位優勢、擴大與東盟教育合作的現狀,說明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對外開放布局上還有待完善。據《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顯示,我國各省市、各行業對駐外高層次管理人才和工程技術類人才均有較大需求[注]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發布的《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705/201705240923004.pdf.)整理而得。下文中我國對外投資的相關數據、事實等資料若無特殊標注,皆出自此報告。,但當前我國與東盟合作項目的既有專業主要集中于社會科學類,且人才培養層次低,說明面向東盟的中外合作辦學專業設置、培養層次與國際人才市場的需求存在對接盲點。
(二)面向東盟境外辦學的發展現狀及問題
境外辦學是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之一。截至2016年3月,我國已有35所高校在14個國家和地區舉辦了5個海外機構、98個項目[注]人民網:《境外辦學:“一帶一路”還要“走得穩”》,2016-11-29,http://edu.people.com.cn/n1/2016/1129/c1006-28904841.html。;位于亞洲區域的境外高等教育機構和項目共計83個,其中37個面向東盟國家,占44%;位于新加坡和泰國的境外辦學規模較顯著,占比分別達16%和10%(見圖3)。從辦學層次來看,碩士及以上層次項目30個,占29%;本科層次項目50個,占49%[注]林金輝:《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報告(2010—2015)》,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頁。。從專業設置來看,以人文社會科學類別為主,其中漢語言文學、中醫藥等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專業占40%以上(見圖4);5個海外機構中有3個位于東盟國家,分別是老撾蘇州大學(以下簡稱“老撾蘇大”)、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以下簡稱“廈大馬校”)、云南財經大學曼谷商學院。其中,老撾蘇大開創了我國赴海外創建高等學府的先河,廈大馬校則開創了我國在海外創建實體校園高等學府的先河。
東盟是我國境外辦學最集中的區域,我國與東盟的境外辦學呈現數量多、規模大和層次高的特征,但也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一,財務風險問題。

圖3 我國在亞洲地區境外辦學機構和項目分布情況[注]數據來源于林金輝:《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報告(2010—2015)》,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213頁。

圖4 我國高校境外辦學機構和項目開設的學科及專業分布情況⑤數據來源于林金輝:《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報告(2010—2015)》,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213頁。
作為創建老撾蘇大的親歷者,原常務副校長汪解先表示資金是該校在辦學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老撾蘇大的設立源于蘇州工業園區邀請蘇州大學參與其在老撾萬象新城開發區的規劃,此后工業園區撤回使老撾蘇大失去經濟依靠。受資金短缺影響,老撾蘇大自招生以來一直靠租賃校舍開展辦學活動,其規劃的350畝校園至今僅修建了6 000平方米。事實上,海外分校辦學經費保障不力帶來的損失已早有教訓,如新南威爾士大學新加坡分校僅維持了2個月便虧損3 800萬美元,密歇根州立大學迪拜分校已虧損數百萬美元[注]中外合作辦學教育網:《海外辦學做好吃苦準備了嗎》,2017-04-27,http://www.cfce.cn/a/news/zhxw/2017/0427/3258.html。。其二,師資問題。如何保障師資質量及其穩定性,一直是境外辦學的難點。參與創建廈大馬校的一位教師表示:一方面,廈大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保證母校與分校共同良性發展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優質師資的配額問題;另一方面,海外分校的艱苦環境和在異國他鄉生活的諸多不適應,影響了師資隊伍的穩定性。同時,熟悉國際關系、涉外法律和非通用語種的國際化管理人才的缺乏,也制約了高校境外辦學的發展。其三,專業課程設置問題。目前,我國境外辦學的專業設置集中在漢語言文學、中醫藥等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人文社科類別,既與孔子學院的定位重合,又與東盟國家經濟處于快速上升通道而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規劃存在對接盲點。另外,中國高校的一些課程并不具備國際共通性,比如不能融入當地的政治文化背景。其四,境外辦學定位問題。境外辦學的本質是輸出優質教育資源,部分高校卻將海外項目打造為國內師生暑期課程、短期培訓的基地,違反了教育資源輸出的本意。
(三)面向東盟共建大學(教育)聯盟的發展現狀及問題
截至2017年8月,中國與東盟共建的大學(教育)聯盟已有10所,其中最早的東盟—中國商學院聯盟成立于2013年,此后兩者共建的大學(教育)聯盟在名稱上皆由“東盟—中國”轉變為“中國—東盟”。名稱順序上的變化,標志著聯盟主導力量的更改。2014年以后,雙邊共建的大學(教育)聯盟皆為中國政府或高校主導創建。從各聯盟成立時間來看,中國在2016年后進入與東盟共建大學(教育)聯盟的密集期,此間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共創建了8所面向東盟的大學(教育)聯盟。從各聯盟成立地點來看,集中于廣西南寧和貴州貴陽。國家將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的永久會址分別選于廣西和貴州,以引導沿邊地區充分發揮地緣優勢,推進與周邊國家的教育合作和交流,形成因地制宜、特色發展的教育對外開放布局。從各聯盟的類型來看,涉及不同主題和多個學科,未來還會成立更多不同主題的大學(教育)聯盟,類型將更加多樣。從主旨來看,各聯盟皆是為了推進中國與東盟政府、東盟高校在聯盟主題內的交流與合作,以培養區域建設人才(見表1)。

表1 中國與東盟共建跨境大學(教育)聯盟的時間、地點及主旨[注]依據各聯盟官方網站發布資料整理而得。
我國面向東盟共建的大學(教育)聯盟集中創建于2016—2017年,目前尚處于發端期,一些問題還未顯露出來。但歷史上跨境大學聯盟在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共同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中國面向東盟共建大學(教育)聯盟中不可回避的。其一,經費問題。籌資幾乎是所有跨境大學聯盟面臨的共同難題,而面向東盟共建的大學(教育)聯盟發展歷史短、知名度小以及缺乏校友會等具備籌資功能的組織,籌資難題是其必然要面對的一道關。其二,管理運行問題。跨境大學聯盟特有的跨境組合性質,使其組織結構較常規大學松散,而松散的組織結構往往會導致制度漏洞。跨境大學聯盟的成員來自不同國家,其風俗傳統、文化理念和法律法規等的差異,會使聯盟在行政管理、溝通合作等方面留有隱患。其三,吸納成員問題。創建跨境大學聯盟的目的在于服務區域經濟建設、搭建行業交流合作平臺,這就需要聯盟成員恪守發展目標[注]劉琪:《北極大學:一個新型跨境大學聯盟的案例分析》,《外國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第42-54頁。。在聯盟創建之初,組織者為廣泛吸納成員以迅速壯大聯盟,往往會降低盟友資格審查標準,成為其后續發展的隱患。創建于2001年的知名跨境大學聯盟北極大學的Hayley Hesseln教授至今依然強調:“北極大學在吸收新成員上應審慎和克制,如果成員不能恪守共同的目標,大學聯盟將會淪落為研究者的旅行俱樂部。”[注]Hesseln H,Uarctic: Evaluating 10 Years of Collaboration,Popar Journal,2013,No.3,pp.204-226.
三、教育資源流動視角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
作為東南亞區域最大的經濟體,東盟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盡管我國面向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模式的發展各有不同,但本著加強與東盟國家教育互利合作、合理規劃,與東盟教育對外開放布局的目的,我國高等教育資源流動的路徑仍需進行差異化設計。
(一)面向東盟舉辦中外合作辦學的策略
針對我國面向東盟中外合作辦學發展薄弱的客觀現實,首要任務是擴大與高等教育較發達的國家中外合作辦學的規模。在東盟國家中,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及新加坡在2017QS世界大學排行榜中上榜高校分別為9所、8所、9所和3所;在2017QS專業領域排行榜中上榜學科數量分別為40個、18個、6個和12個[注]依據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公布的數據整理而得。。目前,我國面向東盟的合作辦學除了與新加坡有比較充分的合作外,與馬來西亞僅舉辦了11個項目,與泰國僅舉辦了2個項目,與印度尼西亞尚未有合作辦學。基于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強強合作、優勢互補”的原則,我國面向東盟舉辦中外合作辦學尚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開拓教育合作空間的問題上,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用不可替代,我國與東盟國家比鄰的省市應充分利用自身的區位優勢,積極制定地方政策,推動中外合作辦學事業的發展,以對接“一帶一路”教育行動計劃。中國—東盟區域建設需求的重點是跨國管理人才和工程技術類人才,而與東盟緊鄰的西部省市因高校師資力量、辦學水平相對較弱,在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方面能力有限,故面向東盟的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西部省市,還應鼓勵中東部高水平大學針對東盟國家行業之所需,引進歐美發達國家的優質教育資源,舉辦碩博層次的機構和項目。此外,具有高職(專科)層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審批權的地方政府,應將批復重點適當向工程技術類專業項目傾斜,以擴大國際技能型人才的培養規模。
(二)面向東盟開展境外辦學的策略
面向東盟境外辦學的蓬勃發展彰顯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實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高校的辦學水平得到了東盟國家的認可。盡管我國現行財政政策禁止公辦高校對境外辦學進行投資,但《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顯示,目前我國多數省市對外投資主體均為非公有制企業,占比超過80%,境外辦學若能精準對接駐外企業的人才需求,攜手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共赴海外聯合辦學,則能解決其運行經費的難題。如在柬埔寨最大的經濟特區西港特區入駐企業中,80%以上是中資企業,特區對掌握中柬雙語的技能型人才需求旺盛,因此,無錫商業職業學院攜手紅豆集團柬埔寨西港特區有限公司聯合共建西港培訓中心[注]董慧:《無錫商職院服務“走出去”戰略 探索公辦院校與民營企業海外辦學》,《中國青年報》2017年5月22日,第10版。,既保障了高校海外項目的辦學經費,又精準對接了海外人才市場的需求。另外,高素質、國際化的師資隊伍是境外辦學可持續發展的關鍵。2017年,中共教育部黨組印發《關于加快直屬高校高層次人才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支持高校境外辦學,并要求實施多元化、柔性人才引進機制,鼓勵高校實行高層次人才協議工資制、項目工資制等績效工資分配方式[注]李文姬:《教育部談高校發展:支持海外辦學 招聘人才需面向全球》,《法制晚報》2017年8月22日,第8版。。各高校應認真執行指導意見,將優化人才布局的措施落到實處。同時,積極探索分段培養模式在海外項目中的應用,如由青島科技大學、泰國王子宋卡大學和橡膠谷集團共建的泰中國際橡膠學院,在本科層次項目中試行“2+2”分段培養模式,計劃讓學生在泰方高校學習2年后,選拔能夠適應中方高校教學的學生赴青島科技大學完成后2年的專業學習[注]李鯤鵬:《青科大泰中國際橡膠學院今年首度招生》,《山東教育報》2017年4月9日,第02版。,以解決中方外派教師短缺的困難。在專業課程設置上,應調整中國特色顯著的人文社科類別專業在辦學中的比重,精準對接我國駐東盟企業的人才需求,既能保障生源,又能承接企業發展所需的技術創新等任務,直接為企業服務。高校要始終對境外辦學定位保持清醒的頭腦,緊緊圍繞建立長遠、完整及可持續發展的教育資源輸出這一目標進行規劃。
(三)面向東盟共建跨境大學(教育)聯盟的策略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我國面向東盟共建大學(教育)聯盟在短期內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故對其后續發展所要面臨的困境更需未雨綢繆。針對運行經費問題,聯盟雖為中方主導共建,但聯盟搭建的交流合作平臺是多方共享的,因此要盡快讓成員國家(機構)樹立起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調動其資助的積極性。聯盟也應充分發揮平臺功能,輔助高校與企業拓展海外辦學項目,從而增加自身經費來源。如當前我國已與多個國家簽訂高鐵建設合作協議,雅萬高鐵、中老鐵路都正在建設中,無論是在建項目還是項目建成后的運營管理,都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南京鐵道職業技術學院利用加入“中國—東盟軌道交通教育培訓聯盟”的契機,迅速與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老撾等國的學校取得聯系[注]中國臺州網:《多所南京高校辦學瞄準“一帶一路”》,2017-09-07,http://www.taizhou.com.cn/jiaoju/2017-09/07/content_3671852.htm。,提高了其“高鐵海外培訓中心”項目海外布局的效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秘書長加多特博士在中國—東盟職教合作聯盟成立大會上表示,合作聯盟是一個長效機制[注]中國新聞網:《中國—東盟職教合作聯盟成立》,2017-07-29,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7/07-29/8290791.shtml。。若干跨境教育聯盟的經驗表明,科學構建這一長效機制的重點在于加強合作體系的頂層設計,并持續完善運行機制。而在聯盟創建之初,堅守會員資格審查標準的底線,是構建長效機制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