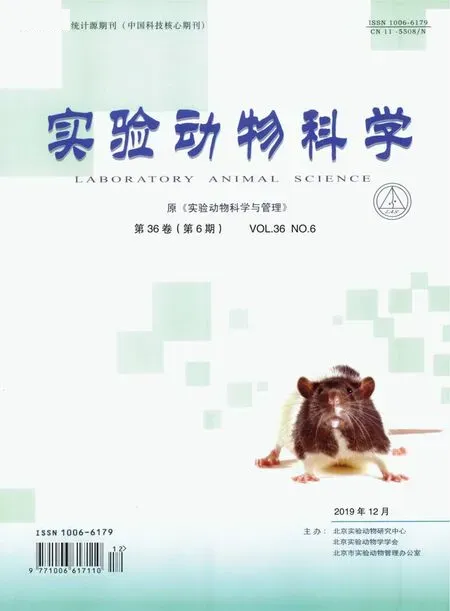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評價方法研究進展*
曲書苑 龐寶興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青島大學口腔醫學院,青島 266003)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心理障礙疾病,隨著抑郁癥發病率的逐年上升,抑郁癥發病機制和治療方法已成為研究熱點,因而建立合理有效的抑郁動物模型是進行抑郁癥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環。抑郁動物模型按造模方法可分為應激性模型、藥物誘導性模型和損傷模型,其中以應激性模型最為常用。應激抑郁動物模型包括強迫游泳實驗模型、懸尾實驗模型、習得性無助(LH)模型、慢性不可預知輕度應激(CUMS)模型等[1]。本文將圍繞表面效度,結構效度和預測效度[2]三個方面對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常用的評價方法展開綜述。
1 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
表面效度為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與人類抑郁癥現象學的相似程度。目前廣泛認為,現象學的相似度僅包括行為和/或認知方面,而不是生理和/或神經基礎[3],所以表面效度的評價常采用行為學測試的方法。研究表明各類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均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4]。
1.1 懸尾實驗(Tail suspension test, TST)
懸尾實驗既是一種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的造模方法,也是抑郁動物模型最常用的檢測方法。用膠帶固定在小鼠尾末端2 cm左右,懸掛6 min,由攝像機記錄行為,并由一名實驗人員記錄小鼠不動時間[5],其中小鼠不動時間的長短反映了其絕望程度[6]。
1.2 強迫游泳實驗(forced swimming test, FST)
同懸尾實驗一樣,強迫游泳實驗也是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的造模方法和最常用的檢測方法[7]。大鼠強迫游泳實驗分為訓練和測試兩期。在訓練期,令大鼠在一個狹窄的充滿足夠深度水的圓柱體中游泳15 min,保持溫度為(25±2)℃,不能接觸底部并保持頭部高于水面,使大鼠習慣裝置。在測試期,大鼠被迫在相同的裝置中游泳5 min,記錄大鼠游泳、攀爬和不動時間。此外,小鼠的強迫游泳試驗裝置與大鼠類似,實驗持續6 min,前2 min用于小鼠適應裝置,最后4 min進行行為記錄[8]。
1.3 曠場實驗(open field test,FT)
曠場實驗由Hall和Ballschey首先提出并使用,可用于評價各類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的自主運動行為、探究行為和緊張度,從而反映抑郁程度。曠場實驗的具體操作方法為:將底面積為213.36 cm×213.36 cm的敞箱均分為49個方形區,中央的25個方形區用圓形絲網屏障隔離,分別將食物放入中央區和邊緣區,將嚙齒類動物放入特定區域,觀察其行為[9]。周波等應用Matlab程序設計軟件結合數字圖像處理方法對曠場實驗行為學視頻進行分析,檢測嚙齒類動物于曠場總體、中央、周邊等不同部位的運動距離或時間[10]。
1.4 糖水偏好實驗(sucrose preference test, SPT)
糖水偏好實驗是慢性應激性抑郁模型最常用的評價指標。動物模型中出現蔗糖偏好下降的現象,并非由運動或感覺缺陷引起,而是快感缺失的表現,這是抑郁癥的一個核心癥狀[11]。具體操作為:第一天動物可以自由飲用兩瓶1%蔗糖水,第二天用普通蒸餾水代替一瓶蔗糖水,在第二天禁食24 h后給動物一瓶1%蔗糖水和一瓶蒸餾水(100 mL),1 h后稱重瓶子計算消耗量。蔗糖偏好的計算公式為:蔗糖偏好=蔗糖消耗量/(蔗糖消耗量+耗水量)×100%[12]。
1.5 新奇物體探索實驗(Novel object exploration test)
新奇物體探索實驗反映動物在新奇環境中的探究能力,抑郁癥動物模型在新奇事物實驗中探索行為減少屬于快感缺失的表現,多用于慢性應激性模型或LH模型的評價。新奇物體探索實驗的具體方法為:將一個2.5 cm×2.5 cm×4 cm表面具有復雜花紋的新奇物體固定于底面積為18 cm×20 cm塑料箱中心,保持光照強度為5 lx,再將小鼠放入箱中,用攝像機記錄15 min內小鼠行為,評估小鼠對新奇物體探索的時長[13]。
1.6 噴濺實驗(splash test)
噴濺實驗通過快感缺失和自我關心兩種機制測量抑郁樣行為,需要和其他行為測試合用來評價抑郁模型[14]。該實驗需要在鼠背上噴灑10%的蔗糖溶液兩次,鼠毛被溶液弄臟后會觸發以舔毛為特征的梳理行為,觀察并記錄在噴灑蔗糖溶液后5 min內梳理的頻率和時間[8]。
1.7 新奇抑制攝食實驗(novelty-suppressed feeding test, NSFT)
陌生環境會誘發動物食物攝取的延遲,屬于一種焦慮行為[15]。由于臨床上抑郁和焦慮常有共病現象,所以檢測抑郁動物模型的焦慮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模型的表面效度,但需要與其他行為學檢測方法合用。新奇抑制攝食實驗共分 2 d:第一天為適應期,給藥后 1 h,將動物放入方形敞箱適應 10 min。動物禁食不禁水48 h后,在敞箱中心放置一食丸,將動物背對食丸放入,保持每次同一位置、同一方向,觀察并記錄動物自放入籠中至首次攝取食物的時間,每次 5 min,以動物開始咬食食丸為攝食標準[16]。
2 結構效度(constructive validity)
結構效度是指抑郁動物模型與抑郁癥患者需要具有相同的病理生理學基礎和發病機制[17],因此,結構效度的評價主要依賴于實驗室檢查。在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中,慢性應激模型尤其是CUMS模型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而FST模型和TST模型的結構效度較差[18]。
2.1 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
HPA 軸功能亢進被廣泛認為是抑郁癥的發病機制之一,也是各類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最常用的檢測指標。HPA 軸活動增高是抑郁癥患者常見的神經生物學異常表現之一[19]。應激引起大腦前額皮質和海馬區域的神經細胞萎縮與凋亡,并導致HPA軸興奮,促使皮質酮為主的糖皮質激素過度釋放,糖皮質激素受體表達降低及功能失敏,不能正常進行其負反饋抑制,損傷海馬組織等,引起學習記憶功能改變[20]。地塞米松通過激活大鼠垂體的Ⅰ型腎上腺類固醇受體而抑制HPA軸功能,用于評估HPA軸的亢進水平[21]。1989年, Greenberg等應用地塞米松抑制實驗(DST)對獲得性無助模型進行評價。具體方法為:在對大鼠進行行為學測試后的第二天下午4∶00用二氧化二碳麻醉所有大鼠,經心臟穿刺取2 mL血液,皮下注射地塞米松(100 μg/g),24 h后重復采血測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對血漿皮質酮濃度進行測定和分析[22]。
2.2 單胺類神經遞質
單胺類遞質假說也被認為是抑郁癥發病機制之一。該假說認為腦內 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多巴胺(dopamine,DA)、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 等神經遞質含量不足或功能低下可導致抑郁[23]。幾十年來,對LH模型的神經化學機制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單胺類物質上,單胺類神經遞質檢測成為LH模型的主要評價方法[24],也可以用于其他慢性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的評價。具體方法為:各組大鼠末次給藥 30 min 后處死,冰上迅速剝離大腦皮層和海馬部位,稱重制備勻漿后離心,檢測5-HT、5-羥基吲哚乙酸(5-HIAA)、DA、高香草酸(HVA)、二羥基苯乙酸(DOPAC)和NE濃度[25]。
2.3 腦源性營養因子(BDNF)
抑郁癥發病機制中,神經營養因子假說得到了越來越多證據的支持,許多抗抑郁藥物通過調節腦內BDNF發揮作用[26]。在多數抑郁癥患者和抑郁動物模型中,BDNF的含量均低于正常水平,但也有些研究發現在慢性應激模型中BDNF水平沒有變化[27],因此該指標較少用于評價其結構效度。BDNF水平測定的具體方法為:動物使用氯胺酮麻醉,取海馬組織放在冰上,制備海馬組織勻漿。然后進行勻漿離心,分離上清液,用ELISA試劑測定BDNF含量[28]。
2.4 炎癥因子
炎癥和神經組織退化導致抑郁假說由Maes等提出。該假說認為抑郁癥的神經變性和神經發生減少是由炎癥、細胞介導的免疫激活及其長期后遺癥引起的[29]。應激導致中樞神經系統中促炎細胞因子的表達增加和各種炎癥相關通路的激活,在慢性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中,可以檢測到IL-1β, IL-6 and TNFα水平增加[30],在LH模型中可以檢測到IL1α, IL-1β, IL-6, TNF-α, IL-3,IL-10等水平增加[31],故該指標多用于評價這兩類模型。
2.5 氧化應激損傷
氧化應激產生的自由基造成蛋白質、核酸、膜脂質等氧化,從而導致細胞發生退變甚至死亡,被認為是抑郁癥發病機制之一[32]。通過常規生物化學方法測定動物模型大腦皮質丙二醛(MDA) 含量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和過氧化氫酶(CAT) 活力可以用于評價氧化應激水平[33],多與其他指標聯合評價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
2.6 非單胺類神經遞質
目前多項研究表明,非單胺類神經遞質在抑郁癥的發病機制中也起著重要作用。例如γ-氨基丁酸(GABA)[34]、谷氨酸[35]、肽類[36]和大麻素[37]等,有望為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的結構效度的評價提供新的生化指標。
3 預測效度(perspective validity)
預測效度主要指抑郁動物模型能夠很好地區分對抑郁的有效和無效治療。除測試動物模型對經典的三環類抗抑郁藥物、單胺氧化抑制劑之外,還應測試對電休克療法以及一些非典型的或第二代抗抑郁藥的反應[38]。一系列研究表明: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都具有較好的預測效度。其中FST、TST和習得性無助(LH)模型對急性抗抑郁治療敏感,常用于抗抑郁藥物初篩。慢性不可預知輕度應激(CUMS)模型對慢性抗抑郁治療敏感,常用于抑郁癥發病機制以及抗抑郁藥物作用機制的研究[39]。黃曉雪和張錦坤利用小鼠CUMS模型證明咖啡因對小鼠抑郁行為有改善作用,且該行為改善作用不是通過興奮大腦皮層所致,提示咖啡因具有潛在的抗抑郁性[40]。
綜上所述,由于目前應用的應激性動物模型很難同時具有較高的表面效度、結構效度和預測效度,造模時應合理選擇動物模型,并結合多種評價方法綜合評價,用以滿足實驗目的和實驗需要。目前,對抑郁癥相關的腦內生物標記物研究力度正在加強[41],為應激性抑郁動物模型的結構效度評價提供了新思路。隨著抑郁癥臨床治療和基礎研究的緊密結合發展,一方面將對抑郁癥的發病機制得到更深的認識,開發出新的抑郁藥物作用靶點;另一方面將進一步完善抑郁動物模型的評價標準,開發出較為完美的抑郁動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