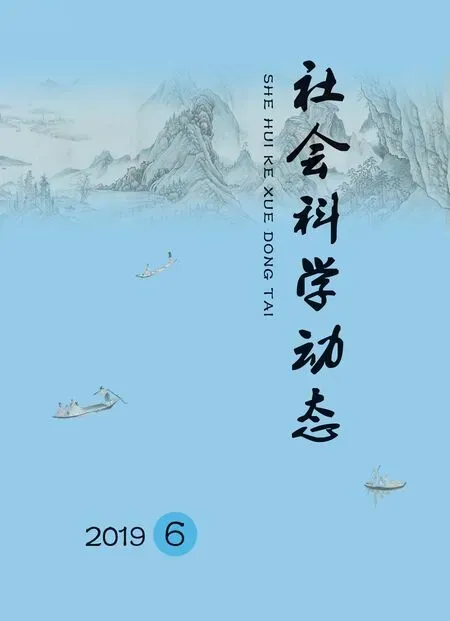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西部”影像流變
崔 軍
在中國歷史影像圖景中,西部沉默了太久,荒漠、黃土、高原、空曠、貧乏的自然景象,連帶著勤勞、善良、勇敢、愚昧的人性積淀,混雜成了光影西部的重要構成元素。西部如同中國歷史一樣久長,卻總是被歷史含糊其辭且又不容爭辯地藏在身后,隱約透露出幾分惆悵與無奈。筆者這里所要討論的中國“西部”,并不指慣常意義上的一種中國版的電影類型元素,不單是一種電影創作模式以及結構的定型,它雖然在不同發展時期有著變動不居的氣質與個性,但在這背后總有一些共通的品貌。在更大的意義層面上,是指從1980年代第五代導演開始形成的、彰顯電影文化以及人文精神內核的一種群體特征,大體包括以下幾點因素:題材及地域風貌以中國西部為展示對象;包括中國大陸導演以及港、澳、臺地區華人導演的作品;中國“西部”在精神視野、文化氣度和表現形態上具有豐厚的包容性,蘊含了開放的流動性,但在思維意識以及跨文化、跨民族的歷史修辭上尚缺乏一種差異反思、批判與自我批判、互補與融合的眼光和力量。
筆者以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西部”影像流變大致可分為這樣三個階段:1984年至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為第一階段,“西部”電影以一種迅猛的姿勢急遽躍出了歷史地平線,開始確立群體風貌,并以歷史反思為主, “西部”成為一種文化標志;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末期為第二階段,“西部”電影開始回歸傳統,“西部”成為一種政治標識;90年代末期至今為第三階段,“西部”電影一改舊日容顏,對歷史的反思逐漸演變成封閉而又獨具意境的地域傳奇。可以說,中國“西部”影像整體上依舊在沉默,但人們總能聽見它若有似無的聲源,仿佛能看見歷史的陷落與西部的沉默一齊隱入地平線,“西部”正慢慢變成了一種商業標識、文化標識與政治標識協商的場域。
一、在歷史的視野中發現西部
1984年,導演陳凱歌推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黃土地》,這部以西部黃土高原為題材的影片,不僅是陳凱歌作為導演確立自己風格的作品,同時堪稱新時期中國“西部”電影的形象基調確立之作,也是第一階段中國“西部”電影確立審美與意趣的奠基之作。此后,中國第四代、第五代導演陸續推出了系列代表作,如田壯壯的《盜馬賊》和《獵場扎撒》、張藝謀的《紅高粱》、何平的《雙旗鎮刀客》等,這些影片共同構成了新時期中國“西部”電影的一道風景線,它們以不同的姿態反思歷史、審視民族與自我,以深沉的喟嘆構建了中國 “西部”電影最初的精神特質。在這些影片中,地域上的中國西部顯示了其蒼涼、廣袤、貧荒的古舊色彩,影片在大全景與特寫的剪輯風格中推演著人與歷史、人與自然的主題。“西部”作為一種歷史的沉積和自然地貌的命名,客觀上直接參與到電影創作過程,敘事不再圍繞人與人、教化與斗爭,而是更多展現為自然、歷史、人類之間的互動與對峙。電影創作者通過對自然“西部”的仰拍鏡頭與對人物個體生命的俯拍鏡頭,共同構成了知識分子式的問訊和疑惑,這一階段的 “西部”差不多是“ 中國”的代名詞,電影鏡像世界中呈現了西部高原連綿不絕的高山與黃土,通過攝影機橫移舒緩地展開了帶有思索性的卷軸畫,展示了歷史動蕩之后人們熟悉而陌生的現實生活。這些電影如 “西部”概念一樣負載著厚重的中華歷史人文積淀,但又似乎在這片決絕的山水之間找不到出口和方向。現實的中國舞臺上早已沒有了政治的喧鬧和口號,只剩一片絢爛光彩中歷史的空洞回聲,而故事中的矛盾情節則導致了影片敘事的曖昧和結局的開放性。政治幻想在第五代導演的“ 西部”影片畫廊里成為一種關于生命與歷史的雙重隱喻,“ 西部”不僅有孕育華夏文明的深厚根基,也有著讓 “陳凱歌們”痛心不已的歷史痼疾。在歷史書寫的鏡像中,“ 西部”以清晰而富有質感的形象出現在地平線上,然而終究不過是一張自然中國的隱喻象征體,并沒有說出其自我的歷史證明與文化身份,電影創作者以遠距離的觀察來表達他們對于“ 古老中國”這一歷史意象的影像思考,他們鏡頭下的“ 西部”是借用自然西部這一悠悠蒼蒼的意象來傳遞知識分子群體對于華夏文明以及中華民族更為深廣更為凝重的觀照與洞悉。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 “西部”具有文化品格上的主體性,但這個主體性卻是帶著全景式的“ 中國假面”。
楊遠嬰在《百年六代,影像中國》中指出,造成第五代導演群體姿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國新浪潮電影給了中國第五代導演電影作者的觀念和影像寓言的啟示,他們的學院生活時期恰逢國門頓開新潮迭出的思想解放之際,新思潮新概念新藝術紛沓而至,他們縱情于激蕩80年代整個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深切體驗改造本土文化的急迫性和現實性;而在電影方面,他們如饑似渴地觀看當時頻頻舉辦的法國電影、英國電影、意大利電影、瑞典電影、日本電影、西班牙電影等各類專題電影展,將隔絕30年后的外國電影流變盡收眼底;當時的影展多側重對國際重要作者導演和藝術電影代表組的介紹,可以說第五代導演群體吸納了當時能見到的所有外國經典藝術電影的精華。因此,他們的創作借鑒絕不會僅僅囿于某一單個國家或單個導演的流派和風格,事實上是思想啟蒙造就了第五代導演的文化態度,藝術電影養育了他們的電影品味,變革精神塑造了他們的創新激情,尋根思潮啟示他們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敘事和主題。這“是當時整體文化現象的結晶,是八九十年代中國特定社會語境的產物”。①
第五代導演群體性地選擇中國 “西部”作為電影場景和故事題材的原因,筆者認為還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鄉的經歷大都發生在西部,“ 西部”意象既讓他們深刻感受到蠻荒與貧困,又讓他們因青春的揮灑而對這塊土地愛得更加深沉。此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 西部”精神品貌的缺失也有著重要關系,近現代以來,“ 西部”始終處于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邊緣,既是文化的邊緣,也是知識心理的邊緣,這使得“ 西部”在追根反思的啟蒙浪潮中處于一個精神母體的想象性的原生態位置;加上當代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中或多或少包含著些許優越感和自我感覺的“差異性”,思想上混合著與生俱來的歷史使命感,使得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向了經濟欠發展的“ 西部”——一個既能標示“差異”與“自我”的屬性,又能在與西方/他者的初次對壘中平衡失落的中心性,聚焦于這樣一個特殊的“所在”,進而獲得一種想象性的滿足。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這種文化兩難處境,另一表現就是中國 “西部”影像長廊中缺少歷史劇的畫影,不管是中國 “西部”電影的發軔期,還是90年代中期中國 “西部”電影的衰落,再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西部”電影的再度興起,總體上給人留下的只有《英雄》《臥虎藏龍》等寥寥幾部貌合神離的中國西部歷史影片。中國導演非常一致地把故事發生時間鎖定在20世紀上半葉,大多與抗日戰爭歷史有著或顯或隱的聯系,“西部”的歷史被人為地置放在一個橫切面上,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歷史上的以及當代“西部”的風土人情成為散落的塵埃。作為曾經的中國紅色政權的歷史所在地,“ 西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全部書寫成紅色符碼,仿佛把“ 自我”奉獻給了中國現代抗戰史,進而嵌在了永恒的“ 鏡像”階段,無法顯出歷史的“真身”。
二、回歸溫情的注視
隨著張藝謀神話般的藝術 “昭示”下,第五代導演開始放棄電影原質追求,紛紛改弦易轍創作“東方奇觀”,中國 “西部”電影的第一個階段結束了。諸多電影創作者不僅放棄了中國西部,甚至將“西部”完全壓縮在一個空間化的時間流程中,“西部”連帶著“ 中國”被抽象化、邊緣化了,當年的黃土、塵沙與蒼茫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悠悠而封閉的“古老中國”的寓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電影面臨著藝術與市場/商業的同臺競技的巨大挑戰,人們也走過了歷史心理的停頓與民族性的反思,加上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觀眾對于西部景觀的非戲劇性、非豐富性、非流動性表述不再容易引起共鳴,精英意識被大眾意識逐漸取代,同時又受制于主流話語的圈界,于是知識分子在大眾與主流夾擊下的不斷妥協和開始潰逃。而外國影片特別是好萊塢大片的大量涌入,不僅使中國電影面臨失去市場的威脅,同時在對文化的甄別上也出現了多元價值傾向的“共謀”現象,在本土電影與民族電影旗幟下,“張藝謀們”依舊癡迷地的變換著形象來演說 “西部”繽紛而又空洞的回響。實際上,第五代導演日漸把目光鎖定在現代城市文明與自我的蟬變,而90年代初中期崛起的第六代導演則熱衷于個性與邊緣的揮灑,其結果是,中國“ 西部”電影在這一時期面臨著尷尬的停滯,電影界先前對于“ 西部”的關注變成了一種自我成全的想象性界面。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第五代導演為代表的中國“西部”電影強調的是當下與傳統的對話,那么90年代中國“ 西部”電影在強調回歸傳統的前提下又開始了另一番博弈,在與市場、與西方/他者的對峙與磨合中,更強調不同文化的不期而遇,形成一種文化交鋒的局面。如果說第五代導演的中國“ 西部”世界是一個“ 中國”整體概念整體的時間“ 差異”扮演者,它不時與另一個變化的、有力的“ 中國”發生沖突,那么90年代的中國“ 西部”儼然又成為世界眼中“ 中國意象”的代名詞,它在“ 西部”的景觀下述說著中國/中華的宣言,與各種外來的、異質的文化交手過招。如果說第五代導演的中國“ 西部”是以“西部”為契入點來切開中國歷史心理的傷疤,是對歷史的質問與反思,那么90年代中國“ 西部”是以“ 西部”為背景回歸傳統,回歸久違的主流話語,以期作出對于歷史的現實應答。如果說第五代導演那里,“ 西部”是以一種憂思、迷惑、郁悶的情緒氛圍登場的,那么90年代中國 “西部”影片則重新披上了溫情、正義、悲壯的意識形態外衣,更多是回歸傳統的正劇,以一種溫和感人的姿態講述著國家民族的歷史神話。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導演馮小寧憑借《黃河絕戀》《紅河谷》等影片艱難地維系著中國“西部”影像,并且使中國西部重新回歸文化傳統與集體記憶。以馮小寧為代表的90年代中國 “西部”鏡像確立了重回解放初期的中國“西部”電影傳統,如《阿詩瑪》《冰山上的來客》《五朵金花》等影片所展示的,“西部”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身體會和言說”,對西部自然景觀描寫也不再是冷峻、深沉的筆觸,而是代之以詩意的、昂揚的、充滿神秘的氛圍,故事講述的更多是中國歷史上那段悲壯慘烈的抗戰年月,雖然其中不乏對當地風土人情的細致描寫,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中心/主流話語服務的,“西部”闡釋著“中國”整體的概念,把內部差異演繹成了一種歷史神話話語,而且還動人地引入了文化對話。如電影《黃河絕戀》中,黃土高原的自然風貌被拍攝得溫暖而祥和,努力還原歷史真實面貌,展示這塊土地上抗戰時期的血雨腥風,影片以一個美國人的視角開始故事的敘述,賦予其一種濃厚的人情味和抒懷氣質,對異質文化的碰撞也有著肯定、開放的結局。影片中二姑娘一口地道的普通話,對花花一家的刻畫頗具臉譜化,憨厚的爺爺、機靈的花花和操著一口陜西方言的正直勇敢的共產黨員爸爸,但他們的感想和心理沒有過多展示。總體上給觀眾的感覺是歷史政治主宰了影片的敘事,不論是花花的剛毅堅強,爸爸的勇猛果敢,抑或二姑娘的大義凜然與機智頑強,都是一般戰爭電影的形象模式與敘事策略,二姑娘與美國大兵的愛情既未深刻揭示出二姑娘作為一個人/西部的人/女性所具有的思想與感情脈絡,也沒有把這份情感作為一種過程來描摹,只是讓這份殘缺的愛情加深了故事主題意念——對戰爭殘酷性的一種揭示,對非正義行為的一種撻伐。一定程度上,影片中的 “西部”最后還是隨二姑娘一起沉入滾滾黃河水中,傳統的意識形態教化功能終歸遮蔽了 “西部”的真實面容,淪為一個在蒼山野水間亙古不變的 “真空”臨界點。
三、突變、本原與傳統的并雜
歷史行進到20世紀末和新世紀以來,中國影壇上又刮起了一陣西部風,各種體裁、各種樣式、各種風格的中國 “西部”鏡像競相登上光影殿堂,以致出現了大批以西部為題材、展現西部風貌的影片,如謝飛的《嘎達梅林》、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和《英雄》、娜仁花的 《天上草原》、章明的《巫山云雨》、李安的《臥虎藏龍》以及高群書的《西風烈》等作品,這些影片按照其表現特征及敘事模式大體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突變類型。作為一個從西部成長起來的電影人,張藝謀對西部有著由衷地偏好,從早期的《紅高粱》,到后來的《秋菊打官司》,再到《一個都不能少》 《我的父親母親》,他一直執著地譜寫著中國“西部”電影組曲。21世紀伊始,張藝謀推出《英雄》,宏大、艷麗、高科技自不必說,但這部“ 羅生們”式的影片依舊是一部涂著華彩流連于他者/西方與觀眾目光中的視覺盛宴。絢麗的西部景色一改以往暗淡蒼涼的單調色彩,顯露其美麗卻總被遮掩的一面,已經習慣了黃土、渾水、愚昧世態的電影觀眾開始被美麗如畫的另一番西部影色所吸引,“ 西部”背負已久的凝滯衰敗在這里被置換成了詩意與浪漫,也由此啟動了刻寫“西部”的另一條路徑。但在本質的文化意蘊上,《英雄》比張藝謀以往的中國 “西部”影像塑造走得更遠了,景色被突變了,對于中國/西部的文化想象卻更加癡迷,漫天遍野的落葉中幾位不知來歷的俠客幻境般拼貼著生死情仇,“ 西部”仍然是一個空洞的“能指”,換湯不換藥的敘事手法把“ 西部”推至到另一個邊緣,時間仍舊被空間牢牢地固置著,被無限期的延沓。張藝謀無意于刻畫、無意于敘事,他所鐘情的只在于展示“羅生門”的故事、“西部”的視點、迷幻的色調結構,“古老中國”再度登場,影片成為一道憂傷而唯美的彩虹,“西部”困守在載體的原地,一個如同《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古舊庭院般歷史缺失的錨地,無法言語,只能注定是一處奇觀的所在,是一瞥視覺大餐的底色和旁白。
第二類是以《天上草原》為代表的本原類型。在跨越21世紀的前后幾年中,中國銀幕上出現了多部描寫普通西部地區原住民生活的影片,以《天上草原》和《嘎達梅林》為代表,這些影片不僅把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以此為契入點深度挖掘他們的所思所想,而且在電影的視覺造型、音畫配備上走向精致、細膩、豐富,“ 西部”這個蠻荒的意象在影片中以一種充滿生機的、多姿多彩的、流動的形象出現。 “西部”不再是大民族國家神話的承載者,影片真正表達了人們在歷史現實中的抉擇和困頓,中國“西部”跳離了僵持于民族寓言和政治攝取物的苑囿,通過豐厚的人情味和立體多層次的人物形象塑造來展示“ 西部”地域本真的歷史流程,更以樸實誠摯的精神品格深深打動著觀眾的心扉。在《天上草原》中,蒙古大草原被表現得豐饒而壯美,畫面色彩的飽和度使得草原和草原上的人們以耳目一新的嶄新風貌出現在觀眾面前,阿爸、阿媽、叔叔們在這美麗的地方守護著人們的精神家園,在散文般的故事結構中以一種詩意情懷去傳達生活的美好與希望,在 “西部人”的獨特生活方式中去升華人類共通的情愫。可以說,這種本原式的中國“西部”影像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西部形象,剝離了意念化描寫,真實的“西部”浮出了水面,以其獨具魅力的影像語匯成為一道中國文化的特殊風景線。
第三類是以《高原如夢》為代表的傳統類型。“西部”作為一種地域特征,成為故事發生的背景,并以特異的自然景觀構筑了一帶奇異風光,同時為故事的發展鋪設了最初的心理期待以及懸念效果。故事講述依然是大中國民族神話和政治立意的歷史隱喻,人類在征服自然和戰勝困難的過程中,實現了國家權力的無微不至及個人人格的升華,人與國家融成一體,“ 西部”在國家和民族的懷抱中自許為證據和契約,不僅呈現出宏觀敘事的正統與強勢,同時也呈現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精神復制,“ 西部”與西部人事被鑲嵌在主導話語的陣勢中,以一種決絕、平面而又充滿力量的涂抹著故事的動人與宏偉。
一定意義上說,造成20世紀末中國“ 西部”鏡像“三方會談”(王一川語)情境有其歷史的原因:
首先,電影自身藝術規律使然。作為一種藝術承載物, “西部”這個地域形態在磁場平臺上賦予了影片是大眾話語、精英話語與主流話語的交織,任何一方占支配地位的局面不復存在,這既有大眾對于電影的客觀需要(好看/精彩),又有精英階層對于 “西部”電影表現側面的文化挖掘與提煉(本圖/民族/差異),當然也有主導話語/國家權力對于“ 西部”先驗傳達的意識形態復現(積極/正義)。
其次,“ 西部”電影人的崛起為中國“ 西部”影像的本原形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力量。憑借著先天的淵源,中國電影創作者會更加深入到“ 西部”文化歷史的內部形態和構成中去,進而發現歷史與現實眼中的“ 西部”形象,展示“ 更加真實的西部”。
再次,藝術與市場的關系決定了21世紀中國“ 西部”電影將更加精細、耐看與豐美。西部作為中國電影取材的一個重要場景,依然要在市場與藝術追求的對峙中不斷尋求突破。電影要經得起市場的考驗,必須具有精良的技術制作、深厚的文化內涵,同時在視聽造型、結構紋理以及主體意念上具有沖擊性和現代感。
此外,國家戰略層面的 “西部大開發”決策以及 “一帶一路”的實施,也是形成21世紀初期中國“西部”鏡像世界色彩紛呈、爭奇斗艷局面的重要因素。“到西部去”將成為持續不斷的社會號召,對西部的支持必然包括對西部文化事業的全域關注,這些勢必引發全社會對中國西部從經濟、地理、旅游、文化、生活等多層面的重新再認識。越來越多的電影人可能到西部采景,這不僅會為影片增添濃郁的地方氣息和視像造型的新穎性,同時也是對西部自然地理、人文歷史的大力宣傳。作為中國電影一種獨特的電影材質類屬,“西部”電影將以其流動的、色彩豐富的形象繽紛著中國和世界的銀幕,同時也以一種 “混雜”的姿態顯示其長久的生命力。
注釋:
① 楊遠嬰:《百年六代,影像中國》,《當代電影》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