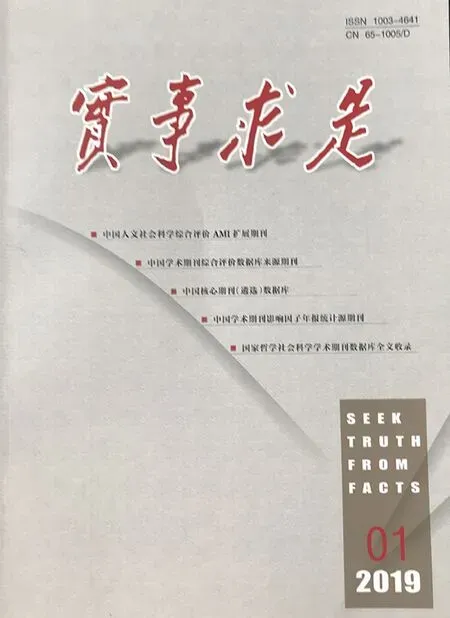論農(nóng)村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的規(guī)制*
王洪用
(安徽省淮南市中級人民法院 安徽 淮南 232000)
從法教義學(xué)出發(fā),農(nóng)村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是指依據(jù)已批準(zhǔn)的征地方案,由行政主體與集體土地所有人圍繞征地補(bǔ)償?shù)姆绞健⒎N類、價金及支付方式、違約責(zé)任等事項,所達(dá)成的權(quán)利義務(wù)性安排。應(yīng)當(dāng)講,現(xiàn)行《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一)項賦予了其行政協(xié)議①需要厘定的是,行政協(xié)議究竟指涉的是什么概念?其與以往學(xué)界討論的行政契約、行政合同是何種關(guān)系?臺灣學(xué)者一般認(rèn)為三者不能等同視之,如林明鏘主張行政契約屬于上位概念,并從主體對等性的角度出發(fā),認(rèn)為行政合同是非對等的行政契約,行政協(xié)議則是對等的行政契約(締約方必須限定為行政主體之間)。而我國大陸學(xué)者(如王名揚(yáng)、應(yīng)松年、羅豪才等)則一般認(rèn)為行政契約就是行政合同,修法前的實(shí)踐中也均采用行政合同的概念。至于對行政協(xié)議的概念厘定上,大陸學(xué)者(如余凌云、葉必豐)則與臺灣學(xué)者觀點(diǎn)無異。現(xiàn)行《行政訴訟法》摒棄了以往行政合同的用語慣例,而徑自采用了“行政協(xié)議”的字眼。但從法律文本角度粗略的判斷,當(dāng)前法典中的行政協(xié)議基本等同于以往學(xué)界所闡釋的行政合同。規(guī)范中未采取行政合同的用語,主要是基于立法實(shí)踐的妥協(xié),因?yàn)榕c行政法學(xué)界不同,長期以來我國民商法學(xué)界(如梁慧星、王利明、崔建遠(yuǎn)等)極力否認(rèn)行政合同存在之余地和必要性,認(rèn)為行政法律關(guān)系的單方性與合同對等性無法兼容。某種意義上,這種妥協(xié)式的立法用語造成了理論上的混亂,但確屬不得不然。因應(yīng)當(dāng)前立法和司法的現(xiàn)狀,為保持概念的統(tǒng)一性,本文初步堅持行政協(xié)議就是行政合同的立場。的地位,當(dāng)下的司法實(shí)踐對其該性質(zhì)也予以了肯認(rèn)。依循現(xiàn)行法律規(guī)范,相對人對行政主體履行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失當(dāng)?shù)模商崞鹦姓V訟,但對于相對人不履行協(xié)議時行政主體如何救濟(jì)卻付之闕如。②據(jù)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童衛(wèi)東主任介紹,之所以立法未明確行政協(xié)議“官告民”的問題,主要是考慮到實(shí)踐中爭議一般是由行政機(jī)關(guān)不履行或違法變更引起,在目前我國有關(guān)行政協(xié)議的統(tǒng)一法規(guī)范缺位情況下,此類問題尚有賴于實(shí)踐探索。參見童衛(wèi)東:《進(jìn)步與妥協(xié):〈行政訴訟法〉修改回顧》,載于《行政法學(xué)研究》,2015年第4期,第24頁。規(guī)范制度供給的不足,造成了理論和實(shí)踐上的齟齬。社會生活中難免發(fā)生相對人簽訂補(bǔ)償協(xié)議后,基于諸多緣由(如因其他被征收人獲得更高補(bǔ)償而產(chǎn)生相對剝奪感)拒不履行的情況。該種情勢下,行政主體應(yīng)通過何種路徑而獲得正當(dāng)救濟(jì)?
一、問題緣起: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規(guī)制路徑的理論紛爭
應(yīng)當(dāng)講,對于采取何種路徑解決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的問題,其路徑選擇不僅關(guān)涉監(jiān)督行政和維護(hù)相對人合法權(quán)益,決定著審理組織的確定和司法知識的分工,某種程度上還觸及到司法權(quán)和行政權(quán)的具體配置。梳理該問題在立法前后特別是當(dāng)前的研究現(xiàn)狀,主要存有以下觀點(diǎn):
1.民事訴訟說。依循該觀點(diǎn),當(dāng)相對人不履行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確定之義務(wù)時,目前只能按照雙軌制救濟(jì)的思路,借助于民事訴訟解決。即賦予行政主體民事訴訟資格,其可基于協(xié)議約定的內(nèi)容,向法院提起民事履約之訴。[1]
2.行政訴訟說。依循該觀點(diǎn),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之訴的主體是協(xié)議關(guān)系之主體,原告不應(yīng)局限于相對人一方。為了從根源上消除當(dāng)事人訴訟地位的差異和爭取糾紛的實(shí)質(zhì)解決,此時應(yīng)肯認(rèn)行政主體具有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如葉必豐所言:“一份合同或協(xié)議是否屬于行政合同,當(dāng)前屢屢發(fā)生爭議。但在屬于行政合同的情況下,在履行行政合同中的爭議,屬于行政訴訟而非民事訴訟的范圍”。[2]
3.變革審判組織說。依循該觀點(diǎn),其并不著墨于相對人不履行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規(guī)制行為的性質(zhì),而主張法院可變革現(xiàn)有的審判組織及審理分工,通過建構(gòu)行政與民事相混合的公私法案件審判組織,繼而對該類履約糾紛進(jìn)行解決。[3]
4.自行強(qiáng)制執(zhí)行說。依循該觀點(diǎn),其認(rèn)為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首要目的是實(shí)現(xiàn)公共利益,協(xié)議中相對人義務(wù)的本質(zhì)仍歸屬于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相對人不履行該義務(wù)與不履行單方行政決定的義務(wù),有同樣法律后果。并據(jù)此認(rèn)為此時行政主體可依職權(quán)自行強(qiáng)制執(zhí)行。[4]
5.自力救濟(jì)轉(zhuǎn)化說。依循該觀點(diǎn),在法律未賦予行政主體原告資格情況下,相對人不履行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由行政主體予以處分(制裁),若相對人對此不服的,則由其提起行政訴訟。即“行政主體如欲救濟(jì)其權(quán)利,可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通過其公權(quán)力行為而‘自力救濟(jì)’,從而把相關(guān)糾紛消解在既有的‘民告官’模式中”。[5]
6.非訴行政執(zhí)行說。依循該觀點(diǎn),相對人對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既不尋求救濟(jì)又不履行約定義務(wù)的,行政主體應(yīng)申請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而法院應(yīng)依非訴行政執(zhí)行程序?qū)徖怼M瑫r主張協(xié)議本身不能直接作為執(zhí)行名義,需將協(xié)議轉(zhuǎn)換為“催告”形式的行為,并據(jù)此提起非訴行政執(zhí)行程序①需要說明的是,梁鳳云法官在這個問題的立場上是前后不一致的,《行政訴訟法》修訂前其贊同賦予行政主體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立場,認(rèn)為“在行政合同案件中,僅僅賦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原告資格而排除行政機(jī)關(guān),不僅違反了合同的相對原則和平等原則,也不利于法院對行政合同進(jìn)行全面審查。”可參見梁鳳云:《論行政合同訴訟的基本構(gòu)造》,載于《行政法論叢》,2012年特稿,第43頁。。[6]
二、抉微甄別:對規(guī)制路徑理論觀點(diǎn)的辨析厘定
透過上述觀點(diǎn),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必要予以逐個厘清,以此管窺規(guī)制征地收補(bǔ)償協(xié)議履行中相對人違約的可欲路徑。
第一種觀點(diǎn)“民事訴訟說”的理論動因很大程度上源自《行政訴訟法》修訂前的司法實(shí)踐,以往法院行政審判庭對此類糾紛往往以屬于民事糾紛為由而拒絕受理。其理論根基是對行政協(xié)議中“行政性要素”和“契約性要素”的拆分,認(rèn)為相對人違反協(xié)議的應(yīng)歸類于契約性要素審查,故應(yīng)適用民事訴訟方式調(diào)整。目前法律雖經(jīng)修訂但該問題仍留空白,基于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故堅持以民事訴訟方式解決該類問題。但問題在于,“行政契約盡管是在公法與私法融合、交叉的邊緣滋生的產(chǎn)物,但是,在對行政契約糾紛的解決機(jī)制上絕不是合同法(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簡單拼加。”[7]民事訴訟的機(jī)能是解決平等主體間財產(chǎn)和人身關(guān)系的糾紛,但行政主體既是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當(dāng)事人,同時往往又稟賦一定的優(yōu)益權(quán),當(dāng)事人的主體地位存在差異,這從根源上否決了民事訴訟適用的正當(dāng)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中增添行政協(xié)議的初衷是維護(hù)民眾合法權(quán)益,若該類糾紛適用民事訴訟則掩蓋了當(dāng)事人地位差異的實(shí)際,損抑了訴訟權(quán)利配置的公正。更重要的是,民事訴訟的審查方式僅針對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本身,但協(xié)議效力的判定往往與作為其原因存在的土地征收行為相牽連,其涉及到公私利益的衡量與對行政行為的監(jiān)督,而民事訴訟并不具備該類司法審查的機(jī)能,制度框架下法官也沒有相應(yīng)的審查權(quán)限。另外,同樣是關(guān)于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爭議,若相對人提起時以行政訴訟的方式處理,而行政主體提起的訴訟則為民事訴訟,這顯然也背離了法治統(tǒng)一的原則。
第二種觀點(diǎn)“行政訴訟說”頗具理論市場,也很有信服力。應(yīng)當(dāng)講,無論是從監(jiān)督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行政和維護(hù)公私權(quán)益的角度,還是從協(xié)議當(dāng)事人訴訟資格對等的角度,將該類履行糾紛納入行政訴訟的制度設(shè)計中都較為適宜,也有助于我國高權(quán)行政向合作行政的良性演進(jìn)。但問題在于,目前賦予行政主體原告資格缺乏規(guī)范的有效支撐,法律文本中的行政訴訟仍是單向訴訟而非雙向訴訟。行政訴訟的原告恒定為相對人,行政主體不具備原告資格。“在法定程序中,不得改變通過立法程序形成的制定法,這是一種永恒的政治責(zé)任。”[8](P192)因而,在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時,行政主體無權(quán)提起行政訴訟。
第三種觀點(diǎn)“變革審判組織說”雖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也存在與立法相沖突的癥結(jié)。《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二款明確規(guī)定:“人民法院設(shè)行政審判庭,審理行政案件。”很顯然,在行政案件的處理上,立法上是強(qiáng)調(diào)其應(yīng)歸屬于行政審判庭,而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糾紛仍屬于行政糾紛的范疇。另外,探索組建行政與民事混合的案件審判組織需支付巨大成本,這種組織改革也非一蹴而就。尤需強(qiáng)調(diào)的是,即使建構(gòu)了相應(yīng)的審理組織,其在處理相對人違約問題時仍面臨著采用何種法律程序的問題,具體實(shí)踐中對該問題仍無法回避。“倘若人們求助于法律程序來解決爭議,那么爭議須在某一階段上最終解決,否則法律程序就毫無意義。”[9](P37)因而,該路徑也非可欲的。
第四種觀點(diǎn)“自行強(qiáng)制執(zhí)行說”根植于行政主體優(yōu)益權(quán)和確保行政效率的立場上,或許在單方行政行為時該觀點(diǎn)尚存合理性,但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畢竟是一個雙方行為,實(shí)踐中其協(xié)議內(nèi)容也往往具有一定的可妥協(xié)性(或可磋商性),因而其并不主張(實(shí)質(zhì)上反對)行政主體在相對人違約時予以自行強(qiáng)制執(zhí)行,更何況當(dāng)前征地協(xié)議中行政主體自身的強(qiáng)制執(zhí)行權(quán)也難以獲得法律的允準(zhǔn)。
進(jìn)行新疆忍冬的育苗和示范推廣,可以改善城市綠化景觀,豐富城市景觀效果,儲備園林植物資源,提高城市植物造景質(zhì)量和水平。也可服務(wù)于全省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和城鄉(xiāng)街道綠化工程,為西北地區(qū)廣闊的宜林地增添適宜的造林綠化樹種和技術(shù)支持,緩解青海干旱區(qū)造林綠化工程苗木品種單一問題,對改善西寧市及周邊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生活質(zhì)量,加速國家森林城市建設(shè)步伐具有顯著的生態(tài)效益。
第五種觀點(diǎn)“自力救濟(jì)轉(zhuǎn)化說”不失為一種可行辦法,但從立法宗旨層面看,之所以規(guī)定行政協(xié)議,其考量因素顯然是協(xié)議與行政處分(制裁)在適用上的替代性關(guān)系,如學(xué)者所言:“行政合同是現(xiàn)代行政發(fā)展過程中重要的變遷結(jié)果,甚至可以說是行政權(quán)力軟化的一種形式,對行政處分起到一個替代、補(bǔ)充的作用”[10]這也意味著排除了(至少羈束了)行政主體在相對人違約時另作行政處分的容許性,否則立法上不應(yīng)當(dāng)、行政主體也沒必要選擇協(xié)議的方式征收集體土地,直接作出單方行政處分即可。正如學(xué)界批判的那樣:“行政合同之所以經(jīng)常演變?yōu)樾姓幜P、行政強(qiáng)制這兩種行政行為的爭議,主要原因在于行政主體將合同自我規(guī)制之外的行政管理權(quán)力帶入了行政合同履行之中。”[11]特別是在我國當(dāng)前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由于缺乏系統(tǒng)的程序性規(guī)定和完備的救濟(jì)制度,行政主體濫用處分權(quán)的情形時有發(fā)生,相對人也幾乎處于“失語”的無助狀態(tài)。在協(xié)議簽訂過程中,相對人所賴以憑借的簽約經(jīng)驗(yàn)也往往是鄉(xiāng)村集市交易經(jīng)驗(yàn),明顯不足以支持其與行政主體議價。此時若再允許行政主體在協(xié)議履行中另作處分,顯然是不可取的。事實(shí)上,近些年發(fā)生的征地暴力沖突,很大成因在于行政主體在協(xié)議履行中耽溺于另行處分的運(yùn)用。
對于第六種觀點(diǎn)“非訴行政執(zhí)行程序說”,筆者認(rèn)為具有明顯的妥當(dāng)性。在行政主體不具備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時,通過現(xiàn)有的“準(zhǔn)官告民”式的非訴執(zhí)行機(jī)制,來確保協(xié)議最終得以履行,同時該方式因司法審查的介入而增益了協(xié)議履行的合法性。應(yīng)當(dāng)講,在遵從既有規(guī)范的立場上,目前該程序是規(guī)制相對人違約時的最優(yōu)路徑。但是,對于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在執(zhí)行名義上轉(zhuǎn)換為催告的觀點(diǎn),是值得商榷的。結(jié)合《行政強(qiáng)制法》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我們可知,催告行為的節(jié)點(diǎn)為具體行政行為(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形成后、申請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前,很顯然其屬于過程性的告知行為,必須依附于前面的行政行為(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征地實(shí)踐中行政主體的催告載體也均是對協(xié)議內(nèi)容的重述,其本身并不會創(chuàng)設(shè)新的權(quán)利義務(wù)。因此,催告程序僅是行政主體向法院申請強(qiáng)制執(zhí)行前應(yīng)履行的前置程序,其書面載體也僅是證明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程序性材料。換言之,不應(yīng)將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執(zhí)行力托付于催告,非訴執(zhí)行審查的是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協(xié)議自身便可作為申請強(qiáng)制執(zhí)行的名義。
三、正本清源:選擇非訴執(zhí)行程序妥當(dāng)性的證成及對責(zé)難的回應(yīng)
法諺云“法律不是嘲笑的對象”,特別是對于法官而言,針對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的規(guī)制路徑選擇上,我們所秉持的根本立場應(yīng)是置于現(xiàn)行法律制度框架內(nèi),而不是動輒以批判者的姿態(tài)“超越法律”,作無實(shí)踐價值(或有理論價值)的“制度空想”。換言之,在合法性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確保違約行為得以妥當(dāng)規(guī)制和違法行政行為得以阻卻,這是我們路徑選擇的基本準(zhǔn)則。
(一)選擇非訴執(zhí)行程序妥當(dāng)性的證成
1.當(dāng)下可采程序的限定。通過對既有理論紛爭的辯駁,可以肯定的是,在當(dāng)前制度語境中,在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時,若欲為行政主體提供救濟(jì),可行的思路歸為兩點(diǎn):或者賦予行政主體更大的權(quán)力,如另行處分或自行強(qiáng)制執(zhí)行;或者將該履約糾紛訴諸法院,以司法方式處理。蓋因法律保留原則和相對人權(quán)益保障的需要,對行政主體廣泛賦權(quán)之途徑實(shí)不可行。而民事訴訟審查方式的不完整性及行政訴訟的單向度規(guī)定,又否決了行政主體以訴訟方式救濟(jì)的可能。現(xiàn)行法律框架下,唯有選擇非訴執(zhí)行的思路最為妥當(dāng)。申請強(qiáng)制執(zhí)行是作為協(xié)議一方的行政主體,作為協(xié)議相對方的被申請人在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確定期限內(nèi)既未尋求救濟(jì),又未履行約定義務(wù)(交付土地或清除附著物等),依法可由法院管轄受理,以非訴執(zhí)行程序予以妥處。
2.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屬性。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契約形式,并不意味著其行政行為公定力和執(zhí)行力的完全喪失。從契約因素方面看,協(xié)議對雙方當(dāng)事人具有當(dāng)然約束力,相對人違約理應(yīng)擔(dān)負(fù)違約責(zé)任。從協(xié)議中的行政法律關(guān)系特征看,其又決定了行政主體可基于公共利益而行使一定的優(yōu)益權(quán)。盡管理論上對行政主體在協(xié)議中應(yīng)否享有優(yōu)益權(quán)存有爭議,①有觀點(diǎn)指出,在行政協(xié)議中不應(yīng)強(qiáng)調(diào)行政主體的優(yōu)益權(quán),補(bǔ)償協(xié)議的行政性不在于其“特權(quán)”一面,而應(yīng)在于“特別義務(wù)”一面。(龍風(fēng)釗:《房屋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性質(zhì)與救濟(jì)》,載于《行政與法》,2013年第11期,第85頁。)還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在行政合同關(guān)系中,所謂的不對等關(guān)系不是傳統(tǒng)的權(quán)利主體和義務(wù)主體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guān)系,而僅僅為權(quán)利主體之間階段性的權(quán)利義務(wù)的差別。”(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論”范疇》,載于《中國法學(xué)》,1996年第4期,第50頁。)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45號行政裁定書中則承認(rèn)了行政主體具有優(yōu)益權(quán)。但無論堅守何種觀點(diǎn)和措辭,在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中,行政主體至少可基于公益而單方訴諸于法律救濟(jì)的基本共識,是不容置喙的。但賦予其申請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的救濟(jì)資格,將行為置于司法的監(jiān)督視野下,則沒有任何理由予以否決。
(二)對預(yù)期理論責(zé)難的回應(yīng)
理論責(zé)難1:有觀點(diǎn)認(rèn)為,“按照我國現(xiàn)行法律規(guī)范,非訴行政執(zhí)行僅限于具體行政行為,并不涵蓋行政契約,征收部門無權(quán)申請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1]
該責(zé)難論點(diǎn)之所以產(chǎn)生,在制度溯源上,主要是因?yàn)橐酝覈姓▽W(xué)界對行政行為(尤其是具體行政行為)概念理解的偏失。行政協(xié)議屬于行政行為的范疇無疑,②對于行政協(xié)議是否屬于行政行為的問題,據(jù)童衛(wèi)東主任所言,以行政行為為核心概念的程序法能否容納行政合同,在立法階段曾引發(fā)爭論。最高法院曾主張將訴訟法第2條的“行政行為”以“行政爭議”取代,以此消弭該紛爭。但考慮到“行政行為”概念在整部法典中存在數(shù)十處,擇一修改有失妥當(dāng)。繼而立法機(jī)關(guān)認(rèn)為“行政機(jī)關(guān)在合同中居主導(dǎo)地位,其簽訂、履行、變更、解除行政合同的行為是行使公共權(quán)力,可以解釋為是一種行政行為。”參見童衛(wèi)東:《進(jìn)步與妥協(xié):〈行政訴訟法〉修改回顧》,載于《行政法學(xué)研究》,2015年第4期,第24頁。但其是否屬于具體行政行為?過往以姜明安為代表的學(xué)者將具體行政行為限定為單方行政行為,但目前該觀點(diǎn)已不敷需要,很大程度上也已為司法實(shí)踐所證偽。不及細(xì)言,筆者較為贊成雙方行政行為依然屬于具體行政行為的范疇。相應(yīng)地,以上述觀點(diǎn)否認(rèn)協(xié)議的可申請司法執(zhí)行性難以成立。
理論責(zé)難2:有觀點(diǎn)認(rèn)為,非訴執(zhí)行程序本質(zhì)上是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實(shí)踐中其程序失范,重在強(qiáng)制執(zhí)行,無暇顧及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履行中相對人為何違約的原因,也難以涉及行政主體在簽訂協(xié)議過程中的合法性等問題。
筆者認(rèn)為這種責(zé)難理據(jù)是不充分的,因?yàn)榉窃V行政執(zhí)行程序已經(jīng)獲得(事實(shí)上在實(shí)踐中早已獲得)我國法規(guī)范的肯認(rèn),豈能認(rèn)為是“非正式制度”?另外,不能否認(rèn)目前其在具體運(yùn)行中存有諸多不良態(tài)勢,譬如,學(xué)界時常批判的其重執(zhí)行而輕審查、重形式而輕實(shí)質(zhì)等,但這是實(shí)踐中對該程序認(rèn)識的錯位和運(yùn)用的異化,不能從根本上否定該程序。換言之,不能以程序運(yùn)行中產(chǎn)生的弊病而否定程序自身,更不能以此為由而拒絕將其作為規(guī)制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的路徑。
理論責(zé)難3:申請非訴執(zhí)行的一般是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均已確定的行政行為,而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執(zhí)行內(nèi)容還不夠確定,直接作為執(zhí)行名義法律依據(jù)方面尚顯不足。
筆者認(rèn)為,回應(yīng)該理論迷思沒必要從行為轉(zhuǎn)換的角度著手。因?yàn)閺膶?shí)踐層面看,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中的約定內(nèi)容是確定的(應(yīng)該說是嚴(yán)苛的),無論是行政主體還是相對人,也都以“內(nèi)容明確”作為簽訂協(xié)議的根本訴求,至今罕尋權(quán)利義務(wù)等不明確的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另外,如上文所言,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屬于行政行為的范疇,因而不存在執(zhí)行名義不足的問題。退一步講,協(xié)議達(dá)成的過程也是相對人意思表示被行政主體接納的過程,所形成的協(xié)議意志在法律上仍可視為行政主體的意志,據(jù)此也應(yīng)肯定其能作為執(zhí)行名義。事實(shí)上,如果認(rèn)為其不具備執(zhí)行名義的要素,則意味著對其行政行為性質(zhì)的根本性顛覆,而這顯然是不可取的。換言之,理解法律時不應(yīng)自鑄語言的柵欄和理論的桎梏,那樣成文法律就只會淪為“符號暴力”。
四、革故鼎新:非訴行政執(zhí)行程序?qū)彶榈膶?shí)質(zhì)化改造
程序是正義的“蒙眼布”,以非訴行政執(zhí)行程序作為規(guī)制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的路徑,有必要結(jié)合協(xié)議自身的特點(diǎn),對當(dāng)下非訴執(zhí)行程序運(yùn)行中的沉珂痼疾予以規(guī)整,以求得程序周延。初步構(gòu)思如下:
(一)審查程序的定位
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作為行政主體和相對人的利益安排,相對人在約定期限內(nèi)不尋求救濟(jì)又不履行的,并不意味著行政行為合法無疑,非訴執(zhí)行中對其進(jìn)行嚴(yán)格審查是無可置辯的。另外,當(dāng)前我國集體土地所有權(quán)主體虛化,簽訂協(xié)議的相對人一般法律意識均較為淡薄,實(shí)踐中,協(xié)議簽訂過程中不乏嚴(yán)重違法情形的存在。法院作為正義的最后屏障,對此類案件的非訴審查理應(yīng)更注重對實(shí)質(zhì)正義的追尋。換言之,具體審查時應(yīng)排除非訴審查標(biāo)準(zhǔn)須低于訴訟審查標(biāo)準(zhǔn)的簡單思維,不再囿于是否屬于“重大明顯違法”的簡單判斷模式,而應(yīng)對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非訴執(zhí)行增大審查強(qiáng)度,進(jìn)行必要的實(shí)質(zhì)性審查。
(二)審查體系的具體設(shè)計
1.非訴執(zhí)行程序啟動。行政主體向法院申請強(qiáng)制執(zhí)行,必須提供:強(qiáng)制執(zhí)行申請書、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及相關(guān)證據(jù)和依據(jù)、催告情況、執(zhí)行風(fēng)險評估材料、申請執(zhí)行的土地狀況以及相對人的具體情況等。
2.審查主體及審查期限。統(tǒng)一由法院行政審判庭負(fù)責(zé)審查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非訴執(zhí)行案件,具體審查時一般應(yīng)組成合議庭。法院在接到強(qiáng)制執(zhí)行申請后,應(yīng)于五日內(nèi)裁定是否受理。裁定受理的,行政審判庭應(yīng)于三十日內(nèi)對其進(jìn)行審查,并就是否準(zhǔn)予執(zhí)行作出裁定。若有特殊事由需延期的,應(yīng)報經(jīng)轄區(qū)高級法院批準(zhǔn)。對于申請執(zhí)行材料欠缺的應(yīng)限期補(bǔ)正,并于補(bǔ)正符合要求后立案受理。對無正當(dāng)理由逾期不補(bǔ)正的,裁定不予受理。
3.審查方式及內(nèi)容。針對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非訴執(zhí)行案件,應(yīng)擯棄單純的書面形式審查,建構(gòu)以聽證為載體的準(zhǔn)訴訟化審查模式。書面審查雖簡捷高效,但不利于查明協(xié)議簽訂過程中及其他相關(guān)環(huán)節(jié)的事實(shí),難以客觀辨別協(xié)議是否合法有效,不足以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quán)益。從實(shí)踐層面看,集體土地是農(nóng)村的命脈,而協(xié)議簽訂過程中相對人申辯的機(jī)會有限,雖有聽證的些許規(guī)范,但相對人實(shí)際參與的渠道匱乏,如江必新院長所言:“對于依照聽證程序作出的行政行為、一旦執(zhí)行后會給當(dāng)事人造成重大損害其難以補(bǔ)救、書面審查難以查清案件事實(shí)、涉及重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聽證,法院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聽證結(jié)果作出是否準(zhǔn)予執(zhí)行的裁定。”[12]具體而言:
首先,賦予當(dāng)事人聽證權(quán),當(dāng)事人未申請的,法院可依職權(quán)啟動。法院應(yīng)及時向當(dāng)事人送達(dá)聽證告知書,告知其聽證權(quán)利及相關(guān)注意事項,特別是對于權(quán)利意識淡薄的相對人,應(yīng)告知其在聽證中享有陳述、申辯和質(zhì)證的權(quán)利。聽證由負(fù)責(zé)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非訴執(zhí)行案件審查的行政合議庭主持,確保組織的統(tǒng)一性,并依循程序公開原則。聽證地點(diǎn)一般應(yīng)設(shè)在行政審判法庭,同時,為緩解相對人的對立情緒及方便查明事實(shí),必要時可設(shè)在涉案的田間地頭。
其次,遵從繁簡適當(dāng)原則,初步可按照“當(dāng)事人身份核實(shí)——告知回避事項——舉證質(zhì)證——申辯陳述”的架構(gòu)進(jìn)行。在舉證責(zé)任分配上,由行政主體圍繞簽訂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目的是為實(shí)現(xiàn)公共利益、自身擁有締約權(quán)限、符合締約法定程序、已給予相對人正當(dāng)補(bǔ)償以及相對人的違約事實(shí)等進(jìn)行舉證,相對人可對此發(fā)表辯駁意見。若相對人認(rèn)為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違法無效的,或基于其他事由主張法院不應(yīng)準(zhǔn)予強(qiáng)制執(zhí)行的,其可提出相關(guān)反證。
再次,適用有限聽證調(diào)解機(jī)制。針對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無論是從其包含的契約屬性還是從節(jié)約司法資源的角度考慮,聽證中引入調(diào)解機(jī)制都是可行的。當(dāng)然,鑒于協(xié)議的行政色彩,調(diào)解必須在自愿性的基礎(chǔ)上,嚴(yán)格遵循合法性原則,對于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效力以及關(guān)涉公共利益的事項不得調(diào)解。應(yīng)該說,“行政糾紛作為發(fā)生在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人民內(nèi)部矛盾,通過協(xié)商和解方式化解符合當(dāng)前司法國情,也有利于彰顯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優(yōu)越性。”[13]
最后,形成規(guī)范的聽證筆錄,肯認(rèn)聽證筆錄的效力,確立案卷排他原則,執(zhí)行裁定書必須依循聽證筆錄而制作。需要注意的是,若相對人拒絕參加或中途退出聽證,視為其放棄聽證權(quán)利,聽證活動繼續(xù)進(jìn)行。若行政主體拒絕參加或中途退出的,則視為撤回強(qiáng)制申請。
4.審查結(jié)果。聽證后由合議庭評議,若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合法有效,符合法定執(zhí)行條件的,裁定準(zhǔn)予執(zhí)行,并于五日內(nèi)將裁定送達(dá)至行政主體和相對人。若協(xié)議存有如下情形,法院應(yīng)裁定不準(zhǔn)予執(zhí)行:簽訂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主體明顯不合法;明顯缺乏事實(shí)根據(jù)和法律、法規(guī)依據(jù);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和方式顯失公平,嚴(yán)重侵害相對人合法權(quán)益;簽訂協(xié)議明顯違背實(shí)現(xiàn)公益目標(biāo),對公益存有損害之虞;嚴(yán)重違背法定程序或正當(dāng)程序;協(xié)議簽訂中行政主體超越或?yàn)E用職權(quán);以及法律及司法解釋等規(guī)定不宜強(qiáng)制的其他情形。法院裁定不準(zhǔn)予執(zhí)行的應(yīng)說明理由,并于五日內(nèi)送達(dá)至申請機(jī)關(guān)。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法院對非訴執(zhí)行案件的裁定范圍僅包括不予受理、準(zhǔn)予執(zhí)行和不準(zhǔn)予執(zhí)行三種,而對于行政主體基于各種原因而要求撤回強(qiáng)制執(zhí)行申請的應(yīng)如何處理?筆者認(rèn)為,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行政性決定了其關(guān)涉公共利益,作為申請人的行政主體的意思自治應(yīng)受到羈束,且此時司法程序已經(jīng)啟動,因此法院對其撤回申請的行為也應(yīng)予以審查。若審查后其撤回并不侵害公益及觸犯法律的,可書面裁定準(zhǔn)予撤回,適用裁定形式的依據(jù)是最高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三條第十五項兜底性規(guī)定:“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項”。
5.執(zhí)行主體。司法應(yīng)保持必要的謙抑,故法院裁定準(zhǔn)予執(zhí)行的,應(yīng)交由行政機(jī)關(guān)具體組織實(shí)施。但不宜交付于簽訂協(xié)議的主體,法院可通過協(xié)商方式確定具體實(shí)施部門。針對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強(qiáng)制執(zhí)行,堅持裁執(zhí)分離,將司法審查權(quán)和執(zhí)行實(shí)施權(quán)分別賦予法院與行政機(jī)關(guān),是目前最為妥當(dāng)?shù)姆绞健@碛稍谟冢?/p>
其一,依循《行政強(qiáng)制法》第五十三條,其規(guī)定是“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從語義角度分析,該條款賦予了行政主體提出申請的權(quán)利,但并未主張須為法院負(fù)責(zé)具體實(shí)施,這意味著法院既可自己實(shí)施也可探索其他模式。從《行政強(qiáng)制法》制定過程看,正式文本刪除了草案中由法院實(shí)施的條文,可知立法機(jī)關(guān)有意為“法院審查裁定+行政機(jī)關(guān)組織實(shí)施”的制度探索留下空間。①喬曉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qiáng)制法(草案)〉審議結(jié)果的報告》,載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公報》,2011年第5期,第486頁。
其二,集體土地征收類糾紛往往為重大執(zhí)行案件,動輒需調(diào)動百余人力量,法院顯然難以應(yīng)對。更主要的是,若由法院負(fù)責(zé)具體實(shí)施,一旦演變?yōu)猷l(xiāng)村極端對抗事件,將對司法公信造成難以彌補(bǔ)的創(chuàng)傷。長期以來,學(xué)界也時常指責(zé)法院的實(shí)施行為僭越了司法權(quán)的界限。當(dāng)然,雖然將具體執(zhí)行實(shí)施權(quán)交由行政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但為防范不可期的執(zhí)行風(fēng)險,法院可利用執(zhí)行建議等方式給行政機(jī)關(guān)提出風(fēng)險防控意見,并告知其不得逾越執(zhí)行裁定所確定的范圍。
6.救濟(jì)方式。對裁定不予受理或不準(zhǔn)予執(zhí)行有異議的,行政主體可通過向上一級法院申請復(fù)議的方式救濟(jì)。
結(jié)語
法律正義得不到及時伸張,讓渡法律的自然暴力就會回歸。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相對人違約若不予理性規(guī)制,鄉(xiāng)土農(nóng)村的“田地悲劇”則難以避免。現(xiàn)行法律是“活著的圣諭”,目前我們理應(yīng)將非訴執(zhí)行程序作為規(guī)制的路徑依賴,探究程序修辭及其背后的張力,重申司法的機(jī)制填補(bǔ)功用,從而在規(guī)則失范的地方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