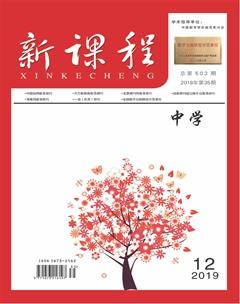例談詩(shī)文教學(xué)中的“君子人格”
鄧荷蓉
摘 要:中學(xué)語(yǔ)文詩(shī)文教學(xué)中,應(yīng)“言”“文”并重,“君子人格”是一個(gè)重要的教學(xué)內(nèi)容。
關(guān)鍵詞:中學(xué)語(yǔ)文;詩(shī)文教學(xué);君子人格
“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落實(shí)到人文教育上,就是給人建立一種精神底子”。我們的精神底子在哪里?孔子說(shuō):“圣人,吾不得而見(jiàn)之矣,得見(jiàn)君子者斯可矣。”言及學(xué)習(xí)要達(dá)到的標(biāo)準(zhǔn)是“君子”,自孔子后,我國(guó)古代志士仁人均視“君子”為人生追求最高境界,如果能于古詩(shī)文教學(xué)中提煉“君子人格”內(nèi)容,對(duì)初中生滲透人格教育,則可利于生命成長(zhǎng),且傳承了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
教材里提到“君子”,注釋一言以概之:品德高尚的人。其實(shí)籠統(tǒng)了,在孔子的思想里,“君子人格”內(nèi)涵豐富,古仁人的“君子人格”演繹方式多樣。
有直言“君子”,如: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只是不惱怒,遇事能泰然處之就是君子了嗎?顯然不是,這句話的前提是“學(xué)”,即學(xué)問(wèn)已經(jīng)做得很好了,但別人不知道我,我還能不惱不怨,這是多寬的胸襟多大的氣度,古往今來(lái)能有幾人做到?《愛(ài)蓮說(shuō)》里直寫君子:蓮,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頤認(rèn)為君子當(dāng)如蓮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如蓮一樣正直、虛心、高潔。
《陋室銘》劉禹錫引用孔子的話暗示“君子人格”,“孔子云:何陋之有?”《論語(yǔ)》原文是這樣的: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去九夷這樣的蠻荒之地“當(dāng)時(shí)想另外開(kāi)辟一個(gè)天地,保留中國(guó)文化”,意思是君子不管身處何地,都有自處之道,如果處于陋地,君子當(dāng)教化之。再看劉禹錫的自得,略有遺憾:君子境界還不夠高,還有“往來(lái)無(wú)白丁”的交游之限。不過(guò),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無(wú)法實(shí)現(xiàn)理想抱負(fù),孔子也生歸隱之心,所謂“窮則獨(dú)善其身”,因此劉的只與“鴻儒”交游,醉心于“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的情趣享受又有無(wú)奈之處。
看來(lái),“君子”標(biāo)準(zhǔn)其實(shí)很高,難怪孔子自己也感慨道:“君子道者三,我無(wú)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不憂不懼”是“內(nèi)省不疚”,便是反省自己的時(shí)候,內(nèi)心很坦然,覺(jué)得沒(méi)有什么愧疚的,所謂“君子坦蕩蕩”,“不惑”呢,是智慧通達(dá)到?jīng)]有迷惑之處。如此說(shuō)來(lái)真是讓人沮喪,原來(lái)“君子人格”竟是一個(gè)永遠(yuǎn)也無(wú)法到達(dá)的境地!但不必灰心,孔子提出了一個(gè)無(wú)限接近君子的通道,那就是“學(xué)習(xí)”,《論語(yǔ)·學(xué)而》第一句話就是:“學(xué)而時(shí)習(xí)之”,“學(xué)習(xí)”二字就由此而來(lái),學(xué)習(xí)經(jīng)荀子已將之發(fā)展成為區(qū)別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標(biāo)志。
說(shuō)到學(xué)習(xí)與成才關(guān)系就得提到明初宋濂的《送東陽(yáng)馬生序》。這個(gè)老先生很有意思,同鄉(xiāng)晚輩馬君則拜訪他,交談一番,他看到馬生“言和而色夷”,再讀其信“辭甚暢達(dá)”,聽(tīng)到同輩人的評(píng)價(jià)“流輩甚稱其賢”,綜合評(píng)價(jià)得出馬生是“善學(xué)”者,就寫了這篇贈(zèng)序勉勵(lì)馬生要刻苦學(xué)習(xí)。在這篇序里,宋濂寫了自己年輕時(shí)一心向?qū)W,再羅列了太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好條件,然后得出一個(gè)結(jié)論:其業(yè)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zhì)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guò)哉?明確表示:要想業(yè)精德成,就得專心向?qū)W。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wú)益,不如學(xué)也。孔子從自己的體驗(yàn)出發(fā),談到只自己去思考是沒(méi)有效果的,不如去學(xué)。只有學(xué)而思,思而學(xué)才會(huì)有所得。大儒宋濂年輕時(shí)的以求知為樂(lè),求學(xué)時(shí)謙恭有禮,正是“君子人格”的寫照。
蘇軾,這個(gè)瀟灑的曠世奇才,其一生演繹著“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則獨(dú)善其身”的儒家經(jīng)義。一貶再貶,職位越低,地方越偏,但他從未被打倒,反成就了他文學(xué)上的輝煌。許多人都認(rèn)為蘇軾之所以如此達(dá)觀是受道家和佛家的影響,對(duì)此兩教蘇軾確有研究,說(shuō)其超然有道釋影響沒(méi)有錯(cuò)。但只將儒家文化視作其入世利器就有失偏頗了,上文說(shuō)過(guò)“仁者不憂”,蘇軾說(shuō)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無(wú)論身處何境,心中總懷有天下念著蒼生,是可謂“仁者”,以“仁”為處世核心,他自能面對(duì)苦難而“不憂”了。“學(xué)而優(yōu)則仕”確是儒家主張,但并不是孔子提的,而是孔子的學(xué)生子夏依據(jù)自己對(duì)孔子思想的理解提出的,“出仕從政,是孔子積極主張的。但他認(rèn)為出仕從政是有條件的,當(dāng)條件不具備時(shí),他就很不以‘仕為然,甚至激烈反對(duì)”。如果單純將儒文化狹隘為“出仕”文化的話,就真是呆化了孔圣人。孔子的“君子”奉行“中行之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就是要求人們的一舉一動(dòng),都能因時(shí)制宜,做得無(wú)過(guò)也無(wú)不及,要根據(jù)客觀的具體情況行事,既有原則,又有靈活性,不拘泥成規(guī),而又有原則”,孔子的“君子人格”絕非刻板迂腐之道,而是圓融的靈活的中庸之道。自幼研讀儒家經(jīng)典的蘇軾豈有不諳其中真意?也許可以說(shuō),蘇軾借助釋道兩家思想,沖破兩漢“獨(dú)尊儒術(shù)”強(qiáng)化儒家入世思想的桎梏,還“君子人格”以孔子時(shí)代的真面貌,留給世人一個(gè)最飄逸的君子背影。
還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lè)而樂(lè)”的范仲淹;與民同樂(lè)的歐陽(yáng)修;舍生取義的文天祥……詩(shī)文的教學(xué),“言”“文”需并重,“君子人格”可為一個(gè)重要的教學(xué)內(nèi)容。
參考文獻(xiàn):
[1]錢理群,曹明海.語(yǔ)文教育文化過(guò)程研究[M].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2]南懷瑾.論語(yǔ)別裁[M].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9.
[3]中國(guó)孔子基金會(huì).中國(guó)儒家教育思想(下)[M].青島出版社,2000.
[4]中國(guó)孔子基金會(huì).中國(guó)儒家教育思想(上)[M].青島出版社,2000.
編輯 杜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