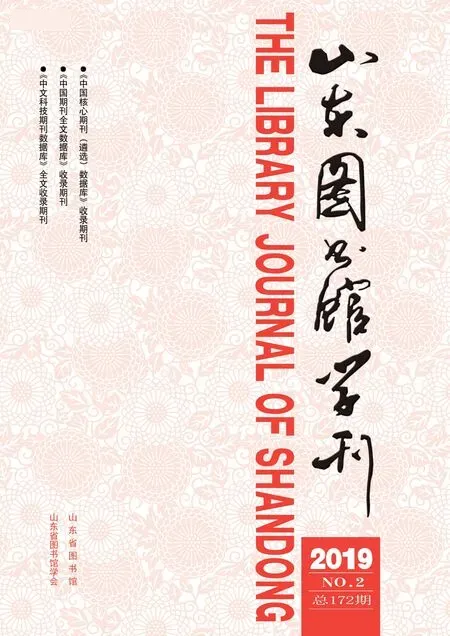縮微技術在我國近代圖書館中的應用
吳稌年
(江南大學圖書館,江蘇無錫 214122)
用銀版生產出的縮微照片是從1839年正式誕生的,“1839年,曼徹斯特光學儀器商和攝影師J.B.瑟(John Benjamin Dancer)用銀版生產出第一批縮微照片”[1]這時的縮微照片還不能商用。1852年,和丹瑟一起試驗濕膠棉處理技術中找到了生產縮微照片的適用方法的阿切爾(James Scoh Archer)將這一方法公布于眾后,丹瑟于1853年在無紋感光乳劑上成功生產出第一批縮微照片,他把這些照片印到玻璃片上出售。是年,《雅典娜雜志》(Athenaeum)登載了一條建議,首次提出縮微出版物的想法。不久,戴格朗(D.Dagron)采用丹瑟技術發展了縮微攝影術,并獲得專利權。
1 縮微技術發展概要
縮微技術首先在軍事上得到應用。第八版《不列顛百科全書》(1853-1860)的第14卷中有“顯微鏡”條目,大衛.布魯斯特爵士在撰寫此條目中提出了可能把秘密情報隱藏在一個墨水點或者句號里,這一在當時具有科幻色彩的想法,很快就在1871年普法戰爭中得到運用。以后這一技術在銀行、圖書館界等許多領域逐步得到應用。
“縮微出版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853年英國霍斯契爾寫給他表弟的信中”[2],但是,直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萊卡相機得到了發展,才開始出現了現代文獻翻拍機的縮微文獻加工平臺的出現。當時,柯達公司裝配了一臺萊卡柯達1-1型(Recorack 1-1)輪轉式縮微攝影機。1927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洛克菲勒的資助下,大規模地開展了縮微復制珍本收集計劃,簡稱“A工程”,“結果從英國博物館及其它地方獲得300多萬份縮微復制品”[3]。1930年,美國柯達公司附屬機構瑞柯達公司與紐約公共圖書館合作,共同發行了一戰期間共5年的紐約時報的縮微版,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縮微出版發行物,當時共出售給了15家圖書館。“1933年紐約《先鋒論壇報》將該社100年來發行的報紙全部制成縮微膠片,并編制了檢索系統”[4]。1936年,美國圖書館學會的帕特森(E.Patterson)首次發表了一篇有關英國圖書館界縮微照相術方面的論文,亦標志著開始對縮微技術的理論探討的階段已經開始。1938年,哈佛大學開始對美國以外的報紙進行縮微工作。是年,帕爾(E.Power)創立了大學縮微膠卷公司,擬用商業文化路徑翻拍善本等珍貴圖書,以利廣大學者使用。此時,在國際上成立了首個國際性的縮微攝影組織——國際縮微攝影大會(IMC),后于1983年改名為國際信息管理大會,縮寫不變。1939年,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首開縮微復制課程[5]。我國于1957年開設這一課程。是年,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開始在“檔案保護技術學”中講授縮微攝影技術,后成為專業課。
由于縮微技術特色鮮明,人們根據其特征和文獻資料工作的發展狀況,不斷開展技術上的突破和理論上的研究工作,并不斷進行未來預測。1944年,由F.里德(F.Rider)發表的“學者與研究圖書館的未來”一文進一步引起了人們對縮微卡片的關注,“他的想法是要把整個圖書館貯存在目錄框里”[6],這就是以后“手提箱”式圖書館的早期預測,“美國人海布林,于1962年在美國縮微協會的一次會議中,首次提出‘復制型圖書館’的概念”[7]。這一概念的提出,很快成為圖書館界的熱點,復制型圖書館,成為電子圖書館中的一種形式,在20世紀70年代后得到快速發展。
2 我國近代圖書館對縮微技術的應用
我國近代圖書館時期,開始了用攝影技術拍攝文獻的工作。這一工作,至少可追溯到1935年。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對這一工作的開展,并非始于國內,而是始于國外圖書館,主要是由“交換館員”展開這一工作的。我國的“交換館員”工作始于1930年,最早起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該館“原藏中國書籍頗富,近更努力搜羅以期完備。本年特與本館約定由本館推薦館員一人前往為之整理,服務期間以二年為期限,滿另由本館推薦他人”[8]。于是,北圖推薦嚴文郁先生于是年9月6日經由神戶前往美國。1934年,王重民先生成為法國國立圖書館交換館員,“本館前與法國國立圖書館交換館員,曾于廿三年秋間派王重民君赴法在該館寫本部實習”[9]。王先生的主要任務是“編被伯希和劫去而藏于館的敦煌卷子”[10],包括訪求明清間西洋天主教士的華文著述、太平天國史料、古刻舊鈔的經史子集等罕傳本。根據目前筆者所查到的相關資料顯示,至少在1935年時,王重民先生就開始大量攝影相關資料。1935年8月,王先生前往柏林達12天,所見古籍較多,“在柏林時,承徐樂教授(Prof.Dr.W.Simon)、葛瑪麗小姐(Dr.Annemarie Von Gabain)之引導參觀,并予以閱書與攝影上之特別便利”[11]。
在國內正式縮微文獻技術的過程,始于193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我國北平圖書館的一項合作項目。當時,美國擬以縮微攝影技術與設備的合作,獲取更多的善本圖書等重要文獻。根據美方提議,擬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北平圖書館各設一套縮微攝影設備,以拍攝圖書資料,由中方向美方提供善本書的縮微膠片,從而促進了我國圖書館對現代設備的重視。是年,北圖就擬進行現代圖書館用品展覽會,所展內容分為6部分:書庫設備、家俱、日常用品、裝訂用品、最近影印機器、盲人圖書館種種設備等[12]。圖書館界的學術刊物《圖書館學季刊》,刊載了“顯微傳影片的改進”(撮要)一文,從而將相關縮微技術問題傳播到我國學術界。是文針對當時國際上使用的顯微膠片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的設想與方法,作者的目的是要通過改進使縮微膠卷(片)在閱讀過程中不易損壞,“底片仍可完好無損的歸還,可以讓其他讀者繼續借閱[13]。其時,“縮微圖書館”“手提式圖書館”之概念也被引入我國,“一位律師可以把他整個的書籍收藏放置在一個小箱子里。一座小市鎮或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學校能購買能容納一個最大圖書館的全部收藏”[14]。當時的縮微技術已有能力將印刷文獻的體積縮小兩千倍,縮像設備的價格也已大大降低,一個全套縮小攝影器的最低價格為50美元,一些家庭用的縮微設備,其價格之低令人瞠目:“最近市場上有一種為家庭應用的,只需美金一元五角即可購一具小型的French Bakelite model。美國海軍大將菲斯克所改造的一種只需美金五元”[15]。可說,這一階段是我國圖書館界重點關注縮微技術的發展現狀與趨勢的階段,為我國應用縮微技術打下了基礎。
我國圖書館界自己縮攝圖書最早大致在1940年秋季,原擬由我國提供善本,由美國提供縮微設備之協定,在抗戰初期仍然在進行之中。1938年,美國提供的設備運抵我國。因當時北平已被日寇占領,這些設備無法在北平圖書館安裝,因此暫時安裝在當時看來比較安全的北平協和醫院,《圖書季刊》上如此記載:“北平圖書館近承美國捐贈此項攝影機一具,因利用北平協和醫院發電廠設備之使得,該機即暫時裝置院中”[16],在此期間,利用這套設備拍攝了一部分醫學方面的善本書。“該館自廿九年秋間,始擬將所藏全部中文醫書縮攝一全份,……現聞已攝竣六千三百余冊,未攝者尚有四百五十余冊”[17]。
在抗日戰爭中,中美圖書館界合作對北圖善本的縮攝工作,無論是在我國還是在國際縮微文獻史上,都可謂是一大重要事件。抗戰爆發,為使我國珍貴古籍免遭日軍的摧殘和掠奪,北圖把300箱善本書運往上海,寄存于法租界亞爾培路科學社圖書館,后又轉到呂班路震旦博物院。后因形勢突變,乃決定將這批書臨時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保存。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有三(王重民先生)不得不用三周的時間,將三百箱書一一打開,選其最優者,又裝成一百箱,所選書共二千七百二十余種”[18]。“33年(1944)美國國會圖書館商得我國同意,將全部圖書攝成顯微影卷。后該館將3套贈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圖書館”[19]。
1942年,時任美國對華關系處的官員費正清先生與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商議約定:“由美國駐華大使館學術資料服務處為中方輸送西方科技文化書籍縮微品,中方則為美國圖書館收集中國科技出版品”[20]。為此,中國方面成立了國際學術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用于接收分配縮微膠卷,顧毓琇、任鴻雋分任正、副主席,袁同禮任執行秘書,1943年2月起,委員會印行《圖書影片指南》(英文本),供學術界參考[21]。據費正清回憶,通過國際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曾把美國2000多種各式書刊的縮微膠卷,連同膠卷目錄,及縮微膠卷閱讀器70臺,分發給了20個閱讀中心。[22]當時該委員會在重慶、成都、昆明、桂林均設立了圖書影片閱覽室,分別是:沙坪壩國立中大,成都金大和華大,昆明西南聯大,桂林廣西大學,并委托這些主要學術機關負責保管此項影片及一切設備,主持閱覽及利用事項。
當時圖書影片成都區分館暫設金陵大學文學院,由劉國鈞先生負責保管,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委員由劉國鈞、周克英、蔡路得、趙華琛、孫明經、謝文炳等人組成。委員會擬定出各種保管和閱覽規則,并指定華西大學用一房間作閱覽之用,在華西大學閱覽室開放前,先在金大文學院提供一室供閱覽之用[23]。1944年,通過國際學術資料供應委員會贈送,華西協和大學獲得圖書影片250卷,“又該館最近由美駐華大使館秘書包懋勛帶來圖書影片三百余種,放映機兩架,將與成都文化團體共同使用云”[24]。1943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受國際文化學術資料供應委員會委托,管理昆明縮微圖書的借閱事宜。為開展好該工作,該館設立了圖書影片股,在校內另設四間圖書影片閱覽室,并開展對外閱讀活動[25]。
國立西北圖書館在籌備成立過程中,圖書影片在文獻的搜集和利用過程中起了較大的作用。1943年3月,教育部聘請了以劉國鈞為籌辦處主任的籌委會,在籌備過程中,圖書影片被列為先向學界開放之列。當時在總結籌備委員會工作時即有如是描述:“開放圖書影片,由國際文化學術資料委員會供給材料,頗受當地學術界之歡迎”[26]。1944年7月7日,該館正式開放。在此期間,“重慶國際學術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于1943年8月起委托該館辦理圖書微卷展覽事宜,先后領到微卷54種及放大閱覽器2架”[27]。國立北平圖書館在這一時期也“先后收到中美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所贈放映機兩架,放映鏡三只及英美期刊影片一千六百四十九卷均已運平,現正趕制庋藏木盤,編打目錄以備閱覽”[28]。抗戰勝利后的3年中,我國縮微技術的應用發展緩慢,1948年,北平圖書館購入美國柯達公司出產的一臺35毫米縮微攝影機和一臺DEPUE型拷貝機及2臺閱讀器,“這批設備直到1949年解放后開箱安裝,并為當時的文物局試拍了小報”[29]。
3 對縮微技術應用的宣傳工作
在我國近代圖書館時期,成規模的攝像技術在圖書館中的應用,開始于在國外工作的“交換館員”,很快,我國圖書館界引入了縮微設備,并通過與美國圖書館界的合作,開展善本書的縮微工作。在整個近代圖書館時期,我國圖書館界主要是從縮微技術的文獻縮微操作層面的掌握入手,開展對文獻的縮微拍攝與閱讀管理工作,并沒有對縮微技術的核心技術的研究及設備制造、規則的制定等方面開展工作,因此,僅解決了縮微技術中如何縮微文獻的操作與管理問題。
在圖書館界最早介紹縮微技術的刊物,是《圖書館學季刊》,在1936,1937年,分別用撮要的形式,介紹了國外相關論著,從而引起我國圖書館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重視。1938年,由《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刊載了相關“明日圖書館”內容的信息,展望了未來現代圖書館應該是:良好的圖書館建筑,管理科學、便捷,采用空調、音響設備,燈具光線柔和,運用無線電技術,具有有聲影片等[30],從而拓展了人們的視野。至40年代中期,隨著縮微技術的不斷發展,為人們展現出了縮微圖書館的光明前景,此時顯微印刷術已在國際上開始運用,這一新技術的發展,很快被介紹到了國內。1944年署名為“青人”者就翻譯了Marvin Lowenthal著的“明日之圖書館”一文,發表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認為“布尼發明顯微印刷術是印刷界中一革命創舉,因為顯微印刷能印在普通紙上,因之能大量生產及廉價供應的現在還是第一次”[31],并樂觀地預測,如果運用顯微印刷技術,紐約公共圖書館400萬冊圖書經過縮印后,可安放在一間二十五英寸闊三十英寸的房間內,如此,每處偏僻的鄉鎮亦可擁有豐富的圖書館了。這些都是通過翻譯途徑引入我國的。在國外最先撰文宣傳中國圖書館的發展趨勢之一者,是留美學者蕭彩瑜博士。1943年10月,蕭博士所著“戰后中國圖書館復興計劃意見書”一文在美國紐約華美協進社社報八卷十一、十二期上發表,這一文章又于翌年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刊載。文中積極宣傳縮微圖書的功能與作用,認為近10年來縮微圖書在美國圖書館得到重視,并大力發展,縮微圖書已在美國圖書館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一發展值得我國借鑒,縮微文獻的特征為節省空間,容易攜帶,利于傳播,復制價格低廉等,因而對圖書館效用的發揮有著很大的影響,并認為他所提出的我國戰后圖書館的復興計劃有3項工作組成:絕版書籍之攝制影片,新近出版刊物之搜集,圖書影片試驗室之設立[32]。
對諸如敦煌古籍等縮微圖書的整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王重民先生,至少在1947年時,已將視野超越了縮微圖書本身,而將其目光發至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對影像資料的搜集上。1947年6月,王先生在故宮博物院演講,他就大量介紹了美國在這方面的發展情況。他認為,通常人們將紙質文獻認為是檔案,這種記錄在影片上、唱片上、膠卷上的記錄,當然應該是檔案,“美國正在籌備一個影片唱片圖書館,在那個圖書館未正式成立以前,已有檔案館和國會圖書館來努力經營這項采集”[33]。為了打破圖書館、檔案館等存在的傳統偏見,王先生又于1948年在當時北平廣播電臺播講了“美國的電影圖書館”,大力宣傳“電影也是圖書”的新思想,他首先提出了問題:“電影是圖書么?若不是圖書,為什么收藏影片的地方可以叫做圖書館呢?”[34]他通過對圖書的發展史的簡說,認為有聲有影像的電影正是圖書的一個大的進步,但是還很少有人想到從圖書到電影是圖書上的一大進步這一問題,由此號召人們,尤其是辦圖書館的人,必須要轉變觀念,去研究、選擇、整理、保存這種流行廣、對讀者影響大的影片圖書。可說此時的王重民先生,已將已往傳統上對圖書的認識過渡到了現代“文獻“概念上的認識層面了,成為我國學界由圖書向文獻概念認識轉型的開始,這種思想觀念上的轉變,亦是對縮微技術在我國更好地應用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