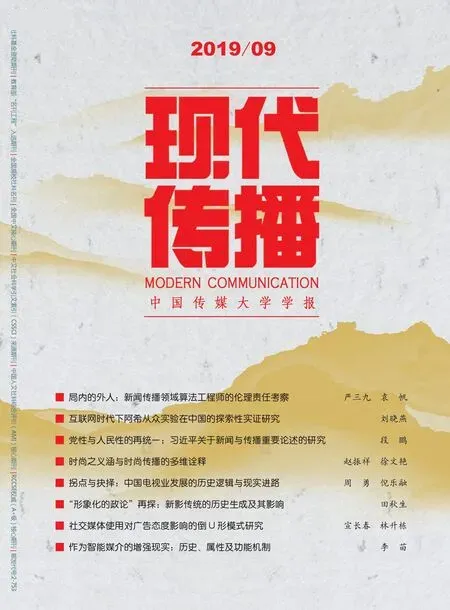意象表征·情感聯結·具身參與:論數字時代的媒體建筑光影傳播*
■ 王 蕾
坐落在城市中林林總總的建筑可以說是城市總體形象的立體展現。隨著古典建筑、現代主義建筑和后現代主義建筑風潮的更迭以及數字信息技術的持續革新,一種輝映建筑思潮和科技進步的媒體化建筑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城市的舞臺之上。何為“媒體建筑”?對于“媒體建筑”(Media Architecture)的理解需要從“建筑表皮”(Building Interface)入手①。建筑表皮,即建筑與城市、建筑與人溝通的主要界面②,借助新型技術,它日益演化為一種新的信息可視化的媒介。狹義上,建筑表皮與數字媒體影像相結合的新建筑形式即可被稱之為“媒體建筑”;廣義上,媒體建筑意指綜合數字科技、公共藝術和信息傳播等領域價值精粹,使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產生交集,以整個城市為舞臺背景建構出的媒介化景觀設施。建筑本身通過聲、光、電等技術融合為城市的肌理,與周圍環境和環境中的受眾互動,可以說,媒體建筑帶給人們視覺審美體驗,重塑著整座城市的精神面貌,而城市中生活的個體也用自身的信息接收和互動體驗促進媒體圖像符號的進步和革新。對于媒體建筑的研究理解,需要建筑學、傳播學、社會學、材料學、公共藝術、政府公共管理、智能交互等多科門類協同進行。
一、問題的提出
媒體建筑的存在和發展并非在朝夕之間,回顧媒體建筑潮流興起的歷史,在世界知名建筑大師——伊東豐雄(Toyo Ito)、赫爾佐格/德穆隆(Herzog & de Meuron)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很好的風格體現。伊東豐雄在1986年設計的“風中之塔”將真實的環境,如風、噪音等元素轉換為信息傾注在建筑表皮上,筑體上的燈光會隨著風速和噪聲的大小不斷變幻、虛實交替。由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的位于德國慕尼黑的安聯大球場,在夜晚,白色充氣膜做的建筑表皮可以根據場內比賽球隊的變化釋放出不同顏色的光芒③。 中國首座媒體建筑是2006年建于北京中關村的“第三極創意天地”,設計者是著名設計大師馮·康格,建筑屏幕影像可以根據北四環車流造成的震動音場強弱起舞。我國媒體建筑已經發展了十年有余,已經成為近些年的焦點話題,“燈光秀”“光影秀”層出不窮,“上元之夜”更是引發各地關注,光媒介藝術性地“點亮”夜空之時,也引起了各界對于建筑的光影實踐是否起到有益有效傳播的討論。誠然,建筑早已超脫了辦公和居住的物理空間屬性,逐漸成為信息的傳播者以及公共空間的數字藝術締造者,建筑和傳播的關系可以借由不斷發展更迭的數字媒體技術來承載,以多元藝術化的手法在城市公共空間中呈現,使公共情境營造和社會互動交往成為可能。與此同時,怎樣將LED、激光、投影、AR、MR、大數據等不斷更迭的技術有效地疊加整合起來為藝術設計和文化傳播服務,也是需要實時跟進且深入打磨的課題。媒體建筑作為一種數字公共藝術實踐,不僅需要結合國家社會價值理念和本土地域性文化,也要恰當迎合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其燈光烘托渲染的傳播理念和視像效果是值得深入挖掘分析的,這也是本文探討研究的意義所在。
建筑的功能轉型是與城市形象的塑造、城市文化的傳播相鋪相成、相互作用的。城市向“智慧”“智能”“信息”“全球化”等方向邁進的征途中,作為城市骨絡經脈的瓦宇樓閣也在人文、技術和政策等等因素的催動下發生著改變。那么,媒體建筑作為一種公共空間的數字藝術實踐,是怎樣促進城市空間信息的傳播流動以及新形式社會交往的締結的呢?這種物理和虛擬空間交結而成的空間敘事“變革”,在城市文化傳播、情感聯結、空間消費、沉浸體驗等方面起到哪些實踐性的作用,又是怎樣建構貼合未來都市發展的人文生態環境呢?本文圍繞現代城市中建筑媒體化的藝術光影傳播現象,深入思考城市-建筑-媒體-人之間的交互關系,為理解新媒體時代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實體城市與想象城市、傳播技術革命和城市發展革新的關系,以及媒體建筑在這些關系互動中的作用提供理論肌理和現實意義的參考。
二、意象的表征:建筑營造的媒介地理空間
20世紀,隨著城市化、技術化和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空間意識開始復蘇,而傳播與建筑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都與空間轉向有密切的聯系④。空間的搭建伴著科學信息技術的革新,早已從物理空間擴展至虛擬空間,從實體空間場域延伸至人體的感知體驗;建筑表皮的媒體化所營造光影傳播映像猶如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意象蒙太奇”,不僅是對文化唯物主義的展示,而且還通過可感知的存在展開⑤,點滴觸碰城市“漫游者”(Flaneur)的身體和靈魂,促進實體空間、人、虛擬空間的融合和交織,形成地理媒介時代的賽博城市。媒體建筑在“全球化的技術空間”和“后現代的地理環境”中的意象表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超越夜空“照明”的公共藝術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信息”,媒體建筑使靜態的建筑本身成為城市公共空間信息傳播的生產者和社會不同個體之間的連接者,換言之,建筑即是媒體。建筑媒體化并不局限于簡單地在建筑外立面上投射光影視效,而是將數字信息網絡和建筑場景內外與更廣闊的城市物理與文化空間緊密融合起來,形成能反映城市總體精神風貌和文化價值觀的形象視覺傳播集合體。在全球化、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和視訊技術不斷飛躍發展的時代,時間和空間的阻礙已然不再凝結,人們對于視覺圖像信息的獲取越來越便捷和多元,對于圖像符號文本的藝術審美也越來越精細苛刻。光電能量對于城市形象的促進不再止步于“亮化”“美化”工程,而是通過物理空間和數字技術的融合輝映去搭建城市文化傳播的眩目舞臺和動態場所,媒體建筑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超越光影視像“照明”基礎功能的時代任務。
在城市化進程飛速前進的今天,“光”仿若組成城市物理和人文空間的紋理經絡,在建筑表皮上打造五彩斑斕的動態光影視效,對于改造區域空間的固有形象、打造城市對外宣傳名片以及構建嶄新的文化傳播氣息都是一種比較便利和實際的低成本運營手段,也是公共藝術在移動互聯時代最直接的符號輸出。公共藝術(Public Art),字面理解即是公眾的藝術、大眾的藝術⑥。“公共性”是公共藝術的本質體現,“交互參與”“創意營造”“文化審美”是時代和技術趨勢賦予公共藝術的嶄新要求;表征是對物質意義系統的創造,是認同感的來源⑦,表征體系的易讀性能有效推動大眾的文化認同感,而建筑表皮的光影符號傳播能快捷地抓取時代前沿時訊,以3D立體、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或全息投影的形式增強受眾的信息可獲得性,拓寬參與渠道的同時也強化了信息傳播的沉浸體驗。因此,如果說城市空間是藝術陳設的大眾博物館,那么媒體建筑即是展館中展陳的瑰麗寶藏,而實現“照明”逆襲的全新光理念會讓瑰寶閃耀得更加亮麗奪目。
2.可連接、可溝通的地理媒介空間
空間本質上有雙重特性,它不僅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也是社會關系的生產者⑧。如果從建筑和傳播的關系而言,建筑作為都市的標志和基柱,其表皮媒體化展現宛若在公共場域搭建了供城市人溝通交流的平臺,以此克服現代性空間組織和加速的社會網絡中的“異化”“隔離”“孤寂”現象,同時也迎合了現代都市人“技術具身”的觀感習慣和行為特征,使流動的空間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具備了公共性。這種公共性或“公共空間”并不僅僅是實體地理空間⑨,從本質上說,它往往是一種虛擬的領域,既滿足都市人情感的聯結和共鳴需求,也從某種意義上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以及公共參與性。亦如德布雷所說的“媒介圈”概念⑩,描述展現了技術、媒介、人和社會的一種新型關系,技術與社會文化關系已不是誰決定誰的問題,而表現成一種相互嵌入和互相咬合的關系。也就是說,傳播技術總是經由人類感官的接合,才會與社會和文化產生關聯。媒介傳播與實體建筑的關系變革輝映了“媒介圈”所營造的知覺體驗場景和氛圍,使技術的變幻展現與人類的感知相關聯,真實做到了“媒介是人的延伸”,促進發展新形態的社會關系網絡,延展和活化城市的公共場域,促進城市文明的涅槃和創新。
《文明中的城市》中提到:“技術革新不會帶來城市的整體消亡,而是地圖的綜合和重塑”。實體空間中的場景或節點,不僅為城市居民提供了公共空間交往的平臺,而且編織起人們對于地方的集體記憶,營造出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和技術演變趨勢的地理媒介空間。斯考特·麥奎爾(Scott McQuire)將移動網絡時代的媒介概括為“地理媒介”(Geomedia),其特征可以概括為:融合(convergence)、無處不在(ubiquity)、位置意識(location-awareness)以及實時反饋(feedback)。地理媒介突顯出社會信息的高效流通和技術的廣泛連接,而從廣義上對“連接型的城市”(connective city)的詮釋,除了肯定技術進步和社交自由之外,還會強調文化意義的建構與分享,也就是說,城市空間是一個關系性的空間,而溝通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技術聯結。移動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個體的身體“缺席”和“繭房”效應,自我被程序算法所構成的網絡矩陣所控制和收編,而建筑與媒介的聯姻,擴展了城市公共空間的虛擬邊界,使物理場所有了“情境化”的展示元素,吸引具有不同身份特征的移動“節點”進行公共實踐,在培養社會交往技能的同時也創造出身體“集體在場”的傳播場域,建筑所投射的光影視像不斷挑動著記憶神經,大眾的參與溝通也進一步深化了對于空間的集體想象。
三、情感的聯結:人性化的城市情境空間景觀
《城市》一書中提及:“城市實際是根植于其居民的習慣與風俗之中的,這意味著它在具有一種物理機制的同時,還保有一種道德機體。” 如果說城市起源于人類群體對自然資源和生存邊界的需求,就好像兩河流域的物質富庶孕育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一樣,那么城市的發展壯大也與其中居民的人文關懷和情感依托密不可分。媒體建筑作為都市化景觀的保存和再造,不僅是建筑自身新型物理形式的體現,更是完成其最為根本的使命——通過場所營造塑造和促進人與人的交流,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也就是說,建筑在整個城市空間的創新創意營造是與人類情感息息相關的。
1.人性化的都市景觀
揚·蓋爾在其著作《人性化的城市》中將“人性化景觀”定義為城市中利于人們行走、坐下、傾聽、交談、觀看的場景;威廉·懷特用長達3年的城市公共空間實地觀察項目來論述城市應該是人的居住地,而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經濟機器,交通節點或巨大的建筑展示臺。城市空間不僅是囊括人們衣食住行等功能性需求的基礎設施,它應該是動態更新發展且與人們的感覺、活動器官緊密相連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契合了曼紐爾·卡斯特“流動的空間”理論。如果說電子通訊和快速交通極大促進了空間的感知體驗和記憶喚醒,那么建筑的意義也早已從滿足基本功能需求延展至“生命的感動”,而媒體建筑亦是智慧城市(Smart City)環境下的社交信息互動創造的一種獨特的平臺和裝置,不僅不斷擴展和打磨空間的立體環境,而且還以符合城市主流文化建構的方式打造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交流渠道。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被速度邏輯掌控的現代世界中,速度給現代人帶來效率、愉悅和解放的同時,也帶來了時間的焦慮和意義的喪失。媒體建筑是符合社會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發展潮流趨勢的,一方面,公共大屏或大廈投影所展示的時空圖像很好地契合了現代人快速高效且略帶“碎片化”的觀視習慣,傳達有效信息的同時也激發了都市人的思慮和想象。正如梅洛·龐蒂從知覺現象學角度提出空間的問題是與真實的人相關的問題,拋開人的存在,也就無法認清空間的多樣性、流動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就像本雅明的“拱廊街”觀察調研一般,現代都市空間景觀很大程度受到關系秩序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媒體建筑的存在既可以起到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的社會建構作用,也能夠有效地連接和調適動態的都市“游移觀察者”和靜態的物理設施之間的關系,在文化的展示和解讀,文本的編碼和解碼以及比特符碼的傳導與對抗中,達到城市建筑和信息傳播的交叉融合。還能對不同“場景”空間視效的傳播效能進行分析比較,在信息傳播引領和受眾接收需求之間尋求適當平衡,實現文化空間中情緒和情感的迸發和凝結,促進城市人在全球化空間或共時性世界中的身心體驗。
2.情境化的視覺審美
當代社會的文化形態是多元動態發展前進的,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地球村”人對多元資訊的精神需求催生了媒體建筑在城市空間中的萌生。技術的迭代革新和科技的高速發展讓我們已經置身于傳播4.0甚至5G時代,“場景”“沉浸”“交互”“體驗”已然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詞。情境,在廣義上是指對獲取知識信息產生影響的各種情況,包括觀眾的內外部情況;而狹義的情景是根據主題所構造出來的生動環境,讓觀眾能有“身臨其境”的體驗,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主題內容中去。知識是個體在與環境的交互過程中建構的,是客觀事實在人腦中反映加工的產物。新時代的空間文明離不開場景再造和情境體驗,而媒體建筑則是實現“身入其境”“意境融徹”的有效方式。因此,正如美國城市研究專家凱文·林奇強調“城市形象”應是城市的一種“公眾意象”一般,想要有效地激發受眾的知覺體驗和情感共鳴,建筑媒體化的情境或場景設計是有必要的,只有與所在空間結構發生關系的建筑物才能給觀映者提供好的視覺美感。特別對于地標性建筑物而言,具有一種可想象性(imageability),它建構了城市或社區的特征、形象和身份。夜晚的城市是一種知覺環境,如何創意性地整合運用文化經濟理念和媒體科技手段在大多居民娛樂休憩時空中增添一抹亮色,喚醒人們對于融合了權威標志性特征和歷史文化情懷的“地標”建筑物的集體性記憶想象,是很有社會文化意義的時代性命題。
此外,城市建筑的情境化設計應是符合社會宏觀的生態文明觀念的,建筑可持續發展的哲學基礎即為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相對于工業文明而言的,工業文明著重于經濟累積和技術發展,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而生態文明旨在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發展經濟的同時更著重維護建立良好的生態環境。現有城市建筑普遍存在著怎樣更好地維護老建筑和發展新建筑的問題。古建筑本身蘊含著歷史的豐富遺跡、民族的瑰麗文化以及社會前進的文化內涵。城市老建筑的翻新是不應違背歷史和人文精神的,也不必將其視為與現代生活沖突的矛盾集合體。另外,有些現代公共建筑設計普遍存在明顯的自由化現象,體現在某些現代化建筑過度張揚個性且與日常生活邏輯脫軌。面對此類城市外觀構建的問題,建筑媒體化的意義在于成本較低地解決了建筑外觀翻新和地標形象特色營造的現實問題。無論是對建筑的拆解和修繕,還是大興土木地疊瓦堆樓,均會對周遭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象造成影響和損傷。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城市景觀和形象的構建已經在基礎上形成格局和風貌,只需配合時代潮流的演進在基底上進行略微的調整和改動,而媒體建筑的職能在現如今的大都市環境中可以說是應時應勢而為的。尤其對于歷史建筑而言,藉由新媒體藝術來表現建筑的美以及其歷史價值地位,還可以通過建筑表皮媒體營造的交互參與特性來引導啟發更多的觀眾去了解和保護建筑,塑造人文和諧生態的文明社會景觀。
四、具身的參與:場域空間消費的沉浸體驗
在城市空間中,依托媒體建筑可以給受眾打造新的感知體驗。也就是說,技術通過重塑人類的感知體驗實現對于人的影響,個人的身體已經與信息終端深度結合,當城市建筑逐漸呈現出“人性化”的轉變,人類個體也已然成為與數字技術深度耦合的“后人類”。唐·伊德將其數字時代呈現出的技術與身體融合的趨勢稱之為技術的具身化趨勢,他將海德格爾“人—技術”關系的現象學出發,過渡到“對技術的文化嵌入性的詮釋學”。后人類時代,新型的建筑-傳播關系給個體的具身參與提供了場景化的平臺,極大程度契合了受眾在移動互聯洪流中“復眼”觀看的視覺習性,實現以人為主體的傳播消費空間“景觀”,也帶來了身體的回歸。
1.視覺影像的具身參與
建筑是為塑造可容納身體的空間而存在的,空間與身體可以說互為“夾具”,是建筑最為本質的問題。“參與性”應該是媒體建筑區別與其它建筑表皮風格的重要特點。參與式建筑是近年來媒體建筑不斷演進過程中的主要的設計創新趨勢。用戶或受眾是參與式建筑聚焦的核心力量。受眾的反饋和意愿搭建起與靜態城市建筑之間的動態溝通互動的橋梁,而受眾本身也成為建筑藝術景觀中的重要元素。2001年柏林的“Blinkenlights”項目,一座八層的建筑外塑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互動電腦顯示屏,用手機就可以在建筑上玩電子游戲。而響譽全球的紐約時代廣場上名曰“享受15秒的名氣”(enjoy your 15 seconds fame)的媒體建筑,行人可以把自己照片傳到建筑媒體裝置上,待激活后照片影像就會從最頂上的屏幕依次落下,全程一共15秒。這種使城市靜物光影炫動的視覺效果極大程度上增添了整個城市的溫情,使被移動訊息環繞日益原子化的個體有了情感交互的契機,使社交互動中的“觀眾”積極轉換成“參與者、設計者”,給城市公共空間和文化精神嵌入了生機和活力。
蘇聯學者巴赫金認為視覺形象具有全民性和廣泛參與性。在城市空間中很好詮釋展示參與交互理念,又可為城市形象增添奪目光彩,這是媒體建筑最好的職能體現。丹麥奧胡斯(Aarhus)音樂廳門前曾舉行了為期兩個月的“交互性媒體表皮”(Interactive Media Fa?ade)的社會實驗,在音樂廳入口處設置三條照明區且分別鋪設色彩鮮明的地毯,當觀眾踏上毯子之時,照明區的影像裝置可以快速捕捉人們的各種身形姿態,并形成身軀光影投射在音樂廳的外立面上,達到人與建筑實時交互溝通的效果,也成為當地著名的文化景觀。“參與者”(Enteractive)是美國洛杉磯市的一棟公寓的建筑立面上安裝的人與建筑互動的裝置,人們可以在平鋪于地面上的LED發光裝置上行走,電腦計算和記憶人們的運動軌跡并可以完整地展示出來。互動性是滿足人類生存本能的自然屬性,在數字媒體時代萌生的媒體建筑增強了人與技術、人與人之間的情境化交互體驗,創新的觀映理念和技術的迭代發展使人的身體變成了信源裝置,在實體空間和虛擬世界中暢游翱翔,這種交互變革有效滿足了在“讀圖時代”生活的居民對于外界視像信息的渴求和期盼。
2.空間消費的沉浸體驗
傳播媒介的無孔不入和商業的繁茂興盛也使得消費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城市夜經濟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如何發掘、塑造城市和文化場所的夜形象,是使人流停駐、產生消費的關鍵因素,媒體建筑也許能成為具備物質和精神消費性質的空間景觀。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認為“景象即商品”,也就是說,當代社會的生產和消費都和景象密切相關,商品消費已經逐漸脫離了物質性消費本身,而日益轉為附著象征符號的城市景象或景觀的消費。列斐伏爾在其《空間的生產》一書中指出,空間是帶有消費主義特征的,而文化敘事和視覺藝術成為構筑城市消費空間的有效手段。建筑不再僅僅是辦公和居住的空間,它還是信息的傳播主體,是一種新的空間交流模式和空間消費模式,空間成為商品本身,消費聚焦從使用價值過渡到象征價值或符號價值,空間和地方成為階級分層和趣味分隔的屬性,也潛在地助推著差異化的消費體驗。
鮑德里亞曾言,消費并不完全等同于個體對物質使用價值的享用和滿足,反而對社會價值體系的肯定和符碼系統的構建有深層次的推動作用。城市空間是一個由各種環境和社會因素匯集交錯的動態發展的開放場域,而城市建筑的媒體化演變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推動空間場域的多維度整合和融合,以此不斷契合城市形象的內外傳播和城市居民的文化精神消費需求,開拓出愛德華·索亞(Edward W·Soja)所說的真實-想象混合的“第三空間”。空間消費主要是文化性的消費,而具備消費屬性的文化形成“可參觀的文化經濟”。在社會關系網絡愈來愈慮擬化和網絡化之時,媒體建筑或媒體立面使空間切實成為共時社會實踐(time-sharing social practices)的物質基礎,讓都市空間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不斷契合超工業化(hyper-industrialization)時代所具備的生產和消費邏輯。也就是說,媒體建筑有很大潛能搭建符合人性化需求的消費空間場所,個體消費可幻化為在沉浸化情境中的自然行為釋放,而多種類似的行為體驗進而集結成對城市文化符碼系統有助益作用的力量。
五、結語
媒介和建筑是相互作用、相鋪相成的,二者之間的交互聯系合力為城市文化的烘托和城市形象的構建服務。“交互參與”“創意營造”“文化審美”“生態文明”“智慧智能”是時代賦予城市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發展的主題和任務。城市發展是一項持久累積的系統性工程,媒體建筑的興建和修葺應綜合政策、媒介、人文歷史以及民眾心理等諸多城市發展元素,應有效地平衡權力和資本等多方力量,對建筑光污染、審美同質化、數字空間權力等問題謹慎對待。城市形象不僅是城市各種象征性符號堆積起來的外在景觀,同時也是團聚四方民眾和諧平穩發展和生活的內在精神需求。
城市未來發展方向越來越智能化,智慧城市是當代信息技術(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智能傳感器等)的一場聲色俱全的盛宴。建筑是城市文化特征和習俗價值觀的外在體現。媒體建筑亦是智慧城市環境下的社交信息互動創造一種獨特的平臺和裝置。借助智慧城市這一平臺,媒體建筑可以鍛造成信息文化的先行者、智慧生活的代言人以及數字交互技術的試驗田,利用現有的空間實物搭建傳導城市先進理念和價值觀的傳播聚合陣地,有效地實現人與空間、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共融共通。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技術革新不斷加速的現今社會,媒體生態和建筑景觀的相互交融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自然趨勢,唯有思想觀念上的不斷進步才能提高新技術手段在城市建設上的有效助益,唯有不斷打磨藝術設計和信息傳播理念才能讓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兼容并蓄地向前發展。
注釋:
① 張健:《作為城市新興景觀的媒體建筑解析》,《學術》,2013年第10期。
② 許昊浩:《媒體與建筑——互聯網時代傳播媒介下的城市空間》,《住區》,2017年第5期。
③ 宋泉昊、殷青、夏楠:《淺談數字化背景下媒體建筑的文化語義表達》,《數字建構文化——2015年全國建筑院系建筑數字技術教學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第185-189頁。
④ 孫瑋:《移動網絡時代的城市新時空——傳播學視野中的傳播與建筑》,《時代建筑》,2019年第2期。
⑤ [德]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劉北成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5頁。
⑦ [英] 斯圖亞特·霍爾:《表征》,徐亮、陸新華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63頁。
⑧ [美] 馬克·戈特迪納:《城市空間的社會生產》,任暉譯,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頁。
⑨ [英] 加里·布里奇:《城市概論》,索菲·沃森 編,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頁。
⑩ 孫瑋:《融媒體生產——感官重組與知覺再造》,《新聞記者》,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