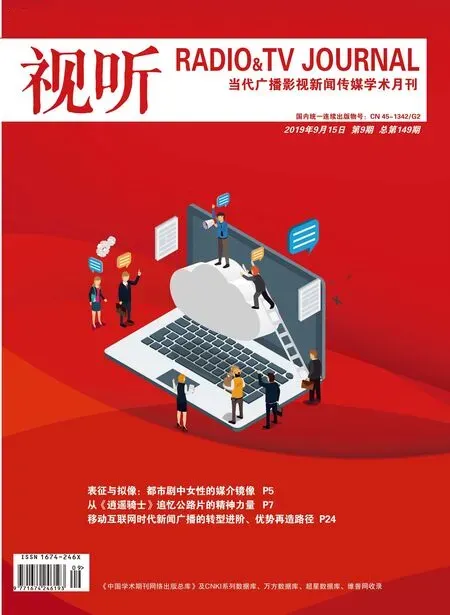燦如春華,皎若秋月:攝影師侯詠電影中的畫(huà)面美學(xué)藝術(shù)
□ 李軼天 袁 維
中國(guó)第五代攝影師侯詠十分堅(jiān)持“攝影為劇情服務(wù)”。盡管現(xiàn)代電影的元素、風(fēng)格越來(lái)越多元化,但正如侯詠所說(shuō),一個(gè)成熟的攝影師學(xué)會(huì)“放棄美”比“追求美”更見(jiàn)功底。在電影攝影方面,他的影像觀感無(wú)論何時(shí)都是無(wú)比穩(wěn)定的,哪怕他喜歡高速運(yùn)鏡,但仍然能夠最大程度地使畫(huà)面穩(wěn)定且真實(shí),沒(méi)有突兀感。他的鏡頭運(yùn)動(dòng)講究和諧順滑,注重光影色調(diào)和構(gòu)圖藝術(shù),給受眾營(yíng)造一個(gè)較為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去感受影片本身,每一個(gè)鏡頭都有依據(jù),或來(lái)源于古典繪畫(huà)藝術(shù),或來(lái)源于生活實(shí)景造型。
一、鮮明的攝影造型元素
電影的風(fēng)格會(huì)和形式相互調(diào)換,而形式或者說(shuō)風(fēng)格又會(huì)與影片的情感、內(nèi)容以及意義等元素相關(guān)聯(lián)。侯詠在與田壯壯導(dǎo)演合作的幾部電影里形成了一種風(fēng)格,這種風(fēng)格又跟張藝謀電影的風(fēng)格完全不同,樸實(shí)和張揚(yáng)的風(fēng)格在含蓄的侯詠手中呈現(xiàn)出獨(dú)具特色的影像符號(hào),這些符號(hào)以鮮明的造型元素存在于影片之中。
在侯詠與田壯壯合作的《獵場(chǎng)札撒》中,為了達(dá)到在攝影上讓畫(huà)內(nèi)空間具有縱深感這一追求,拍攝時(shí),對(duì)表演者的出畫(huà)和入畫(huà)不做指揮,使銀幕當(dāng)中所表現(xiàn)的空間就是整個(gè)世界,并不過(guò)分地去強(qiáng)調(diào)畫(huà)面以外的空間。而張藝謀則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畫(huà)面以外的空間,所以人的調(diào)度基本是縱深的調(diào)度,而非人物的平面調(diào)動(dòng)。這充分表現(xiàn)出侯詠?zhàn)鳛閿z影師的“服務(wù)精神”,即攝影要為影片的內(nèi)容服務(wù),永遠(yuǎn)不要脫開(kāi)內(nèi)容去表現(xiàn)自己。他對(duì)自己的一貫要求是要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能夠很好地為演員服務(wù),為導(dǎo)演服務(wù),為演員的表演添磚加瓦,對(duì)演員的表演提供幫助,并且在某些沒(méi)有演員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手中的鏡頭去繼續(xù)演員的表演,這是攝影師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會(huì)根據(jù)每個(gè)導(dǎo)演的風(fēng)格和劇本內(nèi)容本身去“量身打造”一個(gè)鮮明的畫(huà)面造型形式,而不是在每個(gè)影片當(dāng)中留下自己的“印記”。給影片本身打造鮮明的風(fēng)格,就是侯詠的風(fēng)格。
(一)畫(huà)面內(nèi)空間景深的拓展
在電影創(chuàng)作里,對(duì)外景的選擇與再創(chuàng)作、設(shè)計(jì)與搭設(shè)布景,都要為接下來(lái)的鏡頭畫(huà)面提供縱深感做準(zhǔn)備,攝影師運(yùn)用不同的光位、光比、光效以及其他的處理方式,在光線造型之下,可以構(gòu)成具有縱深感的視覺(jué)影像,而分別運(yùn)用不同焦距的鏡頭,在不同的F 值和與被攝物體的距離下進(jìn)行拍攝,可以在畫(huà)面里呈現(xiàn)出豐富的景深效果。
侯詠本人特別注意營(yíng)造整個(gè)縱深的甚至攝影機(jī)后的空間,而杜絕畫(huà)面兩邊的空間。侯詠在攝影上除了善于運(yùn)用冷暖色調(diào)來(lái)區(qū)別主次,營(yíng)造縱深感,還喜歡運(yùn)用線條的變化來(lái)營(yíng)造畫(huà)面的深度,再者,運(yùn)用前后物體的大小來(lái)添加畫(huà)面的層次感,盡可能地充實(shí)畫(huà)面內(nèi)部而又要做到不讓主體被淹沒(méi)。盡管在畫(huà)面內(nèi)去制造令人舒適的空間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侯詠顯然得心應(yīng)手,畢竟他的影像風(fēng)格一向比較含蓄。
(二)橫向空間煙霧的運(yùn)用
電影《盜馬賊》的開(kāi)篇就有許多運(yùn)用地平線的橫向構(gòu)圖,給人一種穩(wěn)定的平衡感,人物騎在馬背上向前縱向移動(dòng),馬蹄在跑動(dòng)中形成飛揚(yáng)的塵土,又給畫(huà)面帶來(lái)一種橫向的張力。縱向移動(dòng)的主體搭配橫向拉伸的地平線,共同組成一種視覺(jué)的動(dòng)態(tài)張弛。運(yùn)用煙霧來(lái)增加畫(huà)面表現(xiàn)力與鏡頭的朦朧感是侯詠的一大特色,在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中也有大量的使用案例。比如,父親第一次來(lái)到村里與母親相遇,父親的來(lái)臨使用大場(chǎng)景,添加煙霧效果,在母親的視角看來(lái),這正是父親從紅塵中走入她心房的瞬間,帶著朦朧與神秘。后來(lái)母親在屋內(nèi)為父親準(zhǔn)備食物時(shí),一束斜射的硬光打入室內(nèi),超過(guò)灶臺(tái)范圍的煙霧明顯是另外加入的,為了塑造母親為了愛(ài)人在背后忙碌的身影,也為畫(huà)面增加了煙火氣息,使唯美之中滲透出紀(jì)實(shí)的美感。
(三)縱向空間的主體突出
以侯詠與謝晉導(dǎo)演合作的電影《鴉片戰(zhàn)爭(zhēng)》為例,其中輪廓光的使用是十分具有探討價(jià)值的。輪廓光也稱為逆光,即從攝像機(jī)的正對(duì)方向投射過(guò)來(lái),光源、被攝物體與攝像機(jī)在水平線上約為180 度。光線的投射又分為硬光和軟光,硬光是強(qiáng)烈的直射光,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光線硬朗,可以在被攝物體上形成較強(qiáng)的受光面,明暗對(duì)比強(qiáng)烈,在被當(dāng)作逆光使用而不添加輔光的情況下會(huì)形成剪影的效果。剪影有全剪影和半剪影之分,其實(shí)也就是在實(shí)際布光中是否添加輔光的區(qū)別,在特寫(xiě)人物主體時(shí)也會(huì)呈現(xiàn)出有無(wú)面部細(xì)節(jié)的區(qū)別。全剪影的情況下往往可以給人物塑造一種神秘感,主光以逆光的方式投射到主體上形成一個(gè)鮮明的“勾邊”效果,這也是好萊塢商業(yè)片中較為多見(jiàn)的布光方式。電影《鴉片戰(zhàn)爭(zhēng)》中運(yùn)用的則是半剪影,即在硬光從主體背后投射的同時(shí)在正面加入了軟光作為輔光,給人物制造出輪廓光的同時(shí)又可以一定程度上將面部細(xì)節(jié)呈現(xiàn)出來(lái),在影視劇當(dāng)中這樣的布光方式常常被用來(lái)表達(dá)人物具有較大的壓力,此外,半剪影也使畫(huà)面更加具有層次感,給畫(huà)面構(gòu)圖增加了縱深感。
想要把輪廓光運(yùn)用得當(dāng),尤其是想要得到半剪影的效果,就要看對(duì)光比的掌控是否到位,在輪廓光凸顯“勾邊”功能的時(shí)候,還得照顧到被攝主體的暗部細(xì)節(jié),此時(shí)最重要的是硬光和軟光(即主光和輔光)的精準(zhǔn)分配,尤其是在相對(duì)的輪廓光下,對(duì)副光的照明程度把控要求非常高,也極其不易。為了將演員面部神情表演細(xì)膩地展現(xiàn)出來(lái),攝影師和導(dǎo)演一般會(huì)用到特寫(xiě)、近景等小景別,以達(dá)到利用演員的面部表演更好地傳遞情緒的效果。若是被攝主體需要用到肢體語(yǔ)言去表情達(dá)意,那么畫(huà)面所需要呈現(xiàn)的景別會(huì)較大,例如使用中景或是全景。另外,半剪影的用光比加深,更加接近甚至是達(dá)到了全剪影的效果,被攝主體的肢體感因?yàn)檩喞獾膮⑴c顯得更強(qiáng)烈,令演員的肢體表演更具靈魂與戲劇性。
二、濃重的繪畫(huà)表現(xiàn)形式
(一)攝影構(gòu)圖中光效的運(yùn)用
為了增強(qiáng)畫(huà)面的穩(wěn)定性,攝影中也常常應(yīng)用到“三角形具有穩(wěn)定性”這一幾何原理。在電影《孫中山》中,侯詠就是通過(guò)三角形構(gòu)圖法來(lái)對(duì)畫(huà)面進(jìn)行創(chuàng)作。三點(diǎn)布光法是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的發(fā)展期間經(jīng)常運(yùn)用到的布光模式,是一種更趨于傳統(tǒng)的布光方式。以電影《孫中山》中的一個(gè)鏡頭為例,在孫中山與眾人一起商討改革思想的初期,整個(gè)畫(huà)面中的人很多,鏡頭中首先出現(xiàn)的是一只點(diǎn)蠟燭的手,緊接著被點(diǎn)燃的燭臺(tái)成為了整個(gè)畫(huà)面的主光源,而后燭臺(tái)光既作為主光源又作為一部分前景,將人物照亮,兩個(gè)人物用背影與燭臺(tái)同一平行線構(gòu)成前景的另一部分,他們都處于逆光之中,以兩個(gè)黑色三角形的形式充當(dāng)前景。室內(nèi)右側(cè)角落里壁爐的火光作為輔光出現(xiàn),位于人物左側(cè)的另外一盞燭臺(tái)發(fā)揮了修飾光的作用,照亮了環(huán)境,但又很克制,畫(huà)面的明暗部分有著明顯區(qū)分。無(wú)論是人物的分布還是光源的安排,都符合“三角形原理”。通常在環(huán)境比較復(fù)雜的情況下,光源很集中,三角形光源把主體內(nèi)容凸顯了出來(lái),其他部分都在暗部,比如孫中山看報(bào)時(shí),光源只能照在文字內(nèi)容上,手部是沒(méi)有光源的,再比如孫中山和友人同睡,對(duì)國(guó)家的命運(yùn)憂心忡忡時(shí),用光也十分克制,僅僅給了孫中山一個(gè)三點(diǎn)光,其他人在畫(huà)面中幾乎是看不到的。其實(shí)侯詠常會(huì)運(yùn)用這樣的布光方式。而繪畫(huà)大師倫勃朗在其美術(shù)作品中也善于用點(diǎn)光源來(lái)照亮主體物,這種光效也被稱作“倫勃朗光效”。侯詠將這種繪畫(huà)技巧運(yùn)用到電影的布光中去,有光區(qū)域僅僅是畫(huà)面內(nèi)容主體,暗部將繁雜、瑣碎的多余部分隱藏了起來(lái),在構(gòu)圖時(shí)利用“倒三角”或“九宮格”構(gòu)圖法,給人的視覺(jué)上帶來(lái)一種平衡穩(wěn)定的感覺(jué),畫(huà)面和諧、大氣。光效與構(gòu)圖配合得當(dāng),才能把電影藝術(shù)還原成光影的藝術(shù)。
(二)光線在構(gòu)圖中參與敘事
“以光線參與敘事和表意”是斯托拉羅攝影藝術(shù)中的一個(gè)基本理念。侯詠在他的攝影中沿用了這個(gè)理念。在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中,有許多回憶性的段落,這些段落大多都是為了敘事表意服務(wù)的,片段的構(gòu)建將光影和色彩融合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比如在拍攝母親織“紅”時(shí),先是身披金色陽(yáng)光的母親坐在織布機(jī)前忙碌,再是母親在紅色布段上運(yùn)動(dòng)的手,通透的光影和濃郁的色彩運(yùn)用,使受眾情不自禁地對(duì)人物的面容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期待。接著畫(huà)面用“紅”線作為前景拍攝一臉認(rèn)真的母親,金色的光影從人物背后投射,形成了輪廓光,在浪漫的勾邊下,年輕時(shí)的母親仿佛在發(fā)光。朦朧溫暖的色調(diào)給電影故事的創(chuàng)作營(yíng)造了浪漫的寫(xiě)意空間①。侯詠把握住且運(yùn)用光線將其完美地在構(gòu)圖中呈現(xiàn)了出來(lái),找到了人物主觀心理的寫(xiě)照,現(xiàn)實(shí)的凄涼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shí),所以影調(diào)是黑白的,但是那些時(shí)光深處的溫暖和情意是美好而難忘的,與其說(shuō)是“人物在發(fā)光”,倒不如說(shuō)是“回憶會(huì)發(fā)光”。這種光線的構(gòu)架穿梭在現(xiàn)實(shí)和回憶之中,清晰地區(qū)分開(kāi)了兩者,既參與了影片敘事,又為人物的抒情表意服務(wù)。
(三)冷調(diào)與暖調(diào)的應(yīng)景運(yùn)用
在電影《我的父親母親》里,侯詠使用了大量的暖調(diào)來(lái)展現(xiàn)那種唯美的詩(shī)意感。電影《藍(lán)風(fēng)箏》里則更多的是運(yùn)用了冷調(diào),雖然從開(kāi)篇溫暖的冬日陽(yáng)光起用到了暖調(diào),夜晚的場(chǎng)景、家庭里溫馨的點(diǎn)滴在壁燈和臺(tái)燈的陪襯下,畫(huà)面呈現(xiàn)暖紅色調(diào),直到一家人在溫情脈脈的氛圍中展開(kāi)跌宕起伏的命運(yùn),影片才開(kāi)始使用冷調(diào),伴隨著人物命運(yùn)的急劇惡化,畫(huà)面的調(diào)性由暖轉(zhuǎn)冷,加之構(gòu)圖從寬闊變?yōu)榫执伲庹諒?qiáng)度由柔變強(qiáng)形成巨大反差,侯詠的紀(jì)實(shí)風(fēng)格在里面彰顯得淋漓盡致。影片中出現(xiàn)的場(chǎng)景隨著色調(diào)的變化而變化,從原先的四合院變成了陰沉的灰色辦公大樓、工廠廠房、監(jiān)獄,一家人圍桌吃飯的場(chǎng)景從之前整體的暖紅色調(diào)變?yōu)榱烁呱珳冂C燈打出的冷調(diào),仿佛是清冷的月光,淡淡地注視著這飽受磨難的家庭。但是侯詠并不把自己限制在“紅色表現(xiàn)熱烈,藍(lán)色表現(xiàn)陰暗”之類的初級(jí)色彩運(yùn)用法則之中。在拍攝《盜馬賊》時(shí),侯詠想要突出暖紅色調(diào),想要表現(xiàn)寺院的紅,寺院里的一切人物動(dòng)作都要浸泡在一片暖調(diào)之中,為此,他在拍攝藏民生活場(chǎng)景時(shí)也故意使用冷色調(diào),以此來(lái)反襯出宗教寺廟的暖,增添神圣感。而在拍攝千燈那場(chǎng)戲時(shí),侯詠帶領(lǐng)團(tuán)隊(duì)把照明調(diào)壓器與光圈相結(jié)合,使光從昏暗到明亮有較為明顯的層次感。佛殿由黑到紅,然后千燈齊亮,燭光交相輝映,羅爾布置于一片佛光之中,這種冷調(diào)與暗調(diào)的交叉使用讓畫(huà)面充滿了莊嚴(yán)與神圣的感覺(jué)。
三、鏡頭運(yùn)動(dòng)的節(jié)奏調(diào)整
(一)穩(wěn)定畫(huà)面以求客觀性
在電影《一個(gè)都不能少》和《秋菊打官司》的拍攝中,為了追求寫(xiě)實(shí)的感覺(jué),攝影機(jī)基本處于固定的位置,甚至沒(méi)有使用任何軌道運(yùn)動(dòng)或是搖臂運(yùn)動(dòng)。拍攝《幸福時(shí)光》的時(shí)候亦是這樣,影片中使用了非常多的長(zhǎng)鏡頭,且位置固定靜止,把客觀記錄做到了極致,符合侯詠所遵循的“不讓觀眾發(fā)現(xiàn)攝影機(jī)和攝影師的存在”的原則。他充滿觀察力的穩(wěn)定畫(huà)面恰好也加深了影片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影片內(nèi)容和形式與侯詠穩(wěn)定的畫(huà)面相得益彰,做到了互不干涉又互相推進(jìn)。
(二)極富動(dòng)感的高速運(yùn)動(dòng)
關(guān)于“不讓觀眾發(fā)現(xiàn)攝影機(jī)和攝像師的存在”這一理論,到了后期就得到了升華。侯詠認(rèn)為攝影創(chuàng)作的關(guān)鍵是體現(xiàn)并且讓觀眾感受到這個(gè)環(huán)境,鏡頭的運(yùn)動(dòng)可以將平面的造型變成有立體感的視點(diǎn)運(yùn)動(dòng),能夠增強(qiáng)環(huán)境的縱深感,平面的機(jī)位移動(dòng)也能使平面發(fā)生改變。往往有時(shí)攝影機(jī)固定靜止才會(huì)讓人感覺(jué)到它的存在。與其把自己限制在里面被人發(fā)現(xiàn)攝影機(jī)的存在,倒不如拋開(kāi)雜念,隨心所欲地讓攝影機(jī)運(yùn)動(dòng)起來(lái),那樣還能夠產(chǎn)生環(huán)境感。但是基于這個(gè)“隱藏?cái)z影機(jī)”的基礎(chǔ),鏡頭在運(yùn)動(dòng)的過(guò)程中就會(huì)有更多需要講究的地方,包括它的效果完成度、視覺(jué)舒適度、故事情節(jié)展現(xiàn)度等,都是要跟隨移動(dòng)一起帶入思考的。有一些影片中的移動(dòng)鏡頭里,攝影機(jī)運(yùn)動(dòng)的速度和方向與人物運(yùn)動(dòng)的速度和方向完全一致,這時(shí)候攝影機(jī)的運(yùn)動(dòng)就被人物運(yùn)動(dòng)給“吃”掉了。這是一個(gè)相互抵消的過(guò)程,其結(jié)果實(shí)際上等于不動(dòng)。侯詠認(rèn)為人物的運(yùn)動(dòng)與攝影機(jī)的運(yùn)動(dòng)之間有一種對(duì)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在拍攝中如果攝影機(jī)運(yùn)動(dòng)的節(jié)奏、方向、速度、幅度掌握得好,更加有助于表現(xiàn)出情緒。
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中,侯詠添加滑軌和搖臂,使攝影機(jī)處于較為緩慢的運(yùn)動(dòng)之中,多次運(yùn)用低機(jī)位和長(zhǎng)鏡頭配合移動(dòng)將禁煙、戰(zhàn)爭(zhēng)等宏大的場(chǎng)面展現(xiàn)出來(lái),鏡頭在大場(chǎng)面中的運(yùn)動(dòng)創(chuàng)造出一種暢快的穿梭感,使電影富有節(jié)奏和情趣。
在《我的父親母親》中,軌道運(yùn)動(dòng)一路跟隨著母親的奔跑拍攝,搖臂升降運(yùn)動(dòng)展現(xiàn)出了開(kāi)闊的農(nóng)村全貌,加持斯坦尼康,模擬人物的視角來(lái)展開(kāi)船形波浪運(yùn)動(dòng)②。在鏡頭克服重重困難跟隨影片人物和內(nèi)容高速且流暢的運(yùn)動(dòng)過(guò)程中,受眾的精神世界已經(jīng)與視聽(tīng)呈現(xiàn)完美地融合成了一體,根本就無(wú)暇顧及攝影機(jī)以及在攝影機(jī)背后露出滿意笑容的侯詠了。
(三)動(dòng)靜結(jié)合的節(jié)奏把握
鏡頭的靜止與運(yùn)動(dòng)并不是以單一的形式存在于一部影片中的,作為一個(gè)成熟的攝影師,侯詠通常對(duì)攝像機(jī)的動(dòng)與靜實(shí)現(xiàn)靈活的穿插,而精準(zhǔn)地把握節(jié)奏和時(shí)機(jī)是最為困難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環(huán)。如若節(jié)奏不對(duì),影響畫(huà)面基調(diào)不說(shuō),還會(huì)對(duì)整個(gè)影片的敘事功能造成很大的影響。比如在《盜馬賊》中,侯詠使用的固定鏡頭非常之多,尤其是拍攝內(nèi)場(chǎng),攝影機(jī)連最基本的推拉搖移都沒(méi)有,但是在渲染宗教情緒的時(shí)候則用上了軌道車。在喇嘛們念驅(qū)瘟咒時(shí),鏡頭慢慢移動(dòng),將金碧輝煌的寺廟和專注念經(jīng)的僧人面部神情緩緩展現(xiàn),給人一種莊嚴(yán)肅穆的感覺(jué)③。攝影機(jī)在應(yīng)對(duì)宗教場(chǎng)面時(shí)毫不吝嗇地移動(dòng),在點(diǎn)千燈的幾場(chǎng)戲中還使用了升降車。當(dāng)羅爾布進(jìn)入大殿朝拜佛像,進(jìn)入一種非常虔誠(chéng)的狀態(tài)時(shí),他臉上漸漸亮起來(lái),他睜眼看時(shí)已是千燈齊亮的場(chǎng)面,此時(shí)攝影機(jī)在升降車上慢慢運(yùn)動(dòng),它縱橫搖移、上升,加入照明營(yíng)造出的明暗對(duì)比,于是在拍攝出的畫(huà)面里呈現(xiàn)出了一種迷離虛幻的神秘氛圍④。
注釋:
①高磊.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之?dāng)⑹嘛L(fēng)格解讀[J].電影評(píng)介,2012(18).
②高志丹,王雨栽.紀(jì)實(shí)之真與戲劇之魂——侯詠電影攝影風(fēng)格探究[J].當(dāng)代電影,2016(01):146-150.
③④田壯壯《盜馬賊》闖入戛納經(jīng)典:非凡價(jià)值終將被歷史證明[EB/OL].http://m.sohu.com/a/311612326_100056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