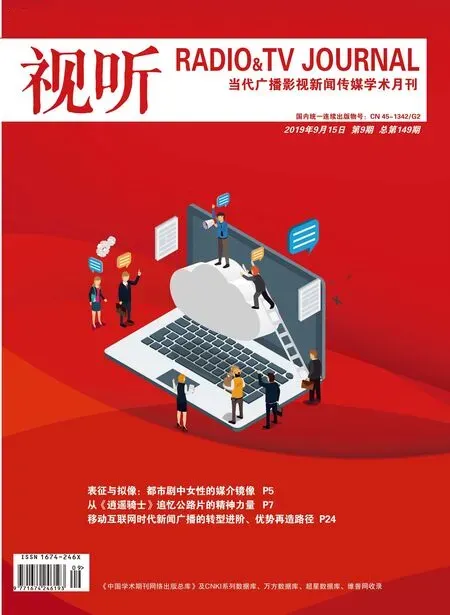媒體融合背景下的兩會內容傳播創新
——基于兩會報道中熱門Vlog 的分析
□ 王友聰 楊紅旗
Vlog 即視頻博客(Video Blog),是一種以記錄用戶日常生活為主且視頻內容極具個性化和人格化屬性的視頻形式。2019年兩會期間,人民視頻、人民網移動中心推進的攜手全國黨媒信息公開平臺,聯動新浪微博、Bilibili 等平臺面向全國征集與兩會相關的Vlog 短視頻,在這一活動中,全國800 多家媒體利用Vlog 這一新興的傳播形式參與到兩會報道的傳播矩陣。
一、Vlog傳播特點
(一)第一人視角賦予的人格化
人格化是文藝創作中常用的一種手法,在Vlog 創作中,主要是創作者在進行視頻內容創作時,通過真實記錄,將自己的生活個性彰顯出來,賦予創作內容以自己的個性。在視頻中,拍攝者往往通過第一視角進行拍攝,同時通過大量與觀眾的直接對話或問答等形式來呈現內容敘事,而非通過情節等來完成敘事。后期一般也會配有簡單的文字,但在Vlog 中經常性的轉場成為內容特性。不斷變化的場景,通過畫面內容及拍攝者的敘事來交代背景,拍攝設備大部分是手機等較為輕便易攜的設備,力求用簡單的畫面來交代復雜的信息。
(二)虛擬的身體在場感
Vlog 是視頻創作者對自己現實經歷事件的記錄,其視頻內容的敘事僅僅通過轉場、配樂、后期的剪輯來實現。其非虛構性是不同于以“表演”為核心的短視頻短劇的根本屬性。Vlog 通過第一視角,利用手機等簡單的設備,去除濾鏡等技術干擾后,極大程度地還原了真實的情境,為觀看者營造了一種身體的在場感。這種虛擬的身體在場感極大地提高了觀看者對視頻內容的認同程度。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觀看者追求一種沉浸感,在觀看視頻時,拍攝者繪聲繪色的講解,真實的場景再現,為觀看者營造了一種身體在場的錯覺,這種錯覺滿足了觀看者的窺視欲望,同時增加了視頻內容的吸引力度,給觀看者一種虛擬的身體在場感。
(三)“去故事化”敘事
Vlog 因其基于生活的真實記錄,視頻內容也變得極為豐富。不同于“抖音”等短視頻的創作較多地局限于時長,Vlog 時長大多在5 分鐘左右,所展現的視頻信息更豐富,細節更生動。同時,因為千人千面,每個人的生活與別人的生活都是不同的,因而,這大大地減少了短視頻同質化的內容局限,雖然目前國內Vlog 還處在初期的發展階段,入局的創作者較少,嘗試使用的用戶對視頻的創作比較多地跟風頭部創作者,但相對于短視頻,其豐富性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四)去表演化的審美轉向
歐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認為:“個體的表達(因為聯通他給人造成印象的能力)看來包括兩種根本不同的符號活動:他給予(gives)的表達和他流露(gives off)出來的表達。”①根據這一觀點,在“抖音”等短視頻中,較多的視頻內容都是視頻創作者給予(gives)受眾的表達;相反,在Vlog 視頻中拍攝者在給予受眾某種印象的過程中更多地是在流露(gives off)自己。Vlog 強調的是記錄真實,可以說是受眾從審丑到審美的轉向。不同于抖音等短視頻較多地以獵奇或者編造短劇的形式呈現其內容進而輸出價值觀,贏得受眾認同,Vlog 更多的是吸引不同文化圈層的受眾,打造屬于自己的圈層文化,其去表演化背后所展現的真實生活狀態成為吸引受眾的主要原因。
二、兩會報道中的熱門微博Vlog分析
(一)視頻時長適中,信息傳遞相對完整
對熱門微博進行挑選,剔除無效和重復樣本,共收集120 條有效樣本,樣本內容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是視頻時長,時長在1 分鐘以內的視頻共有20 條,占比17%;時長在1 分鐘到5 分鐘的共計90 條,占75%;時長在5 分鐘以上的共計10 條,其中有一條時長超過10 分鐘,占8%。從視頻時長可以看出,兩會報道的熱門微博Vlog 視頻中,1—5 分鐘的視頻時長占主導,這一時長能將信息較為完整地進行傳遞,又能兼顧受眾觀看體驗。其次是播放量,播放量超過100 萬次的共計14 條,有106 條播放量在幾萬到幾十萬不等。視頻播放量與該微博賬號粉絲擁有量呈正相關。人民網微博賬號擁有6000 多萬粉絲,因而,其相關視頻播放量多在二三十萬左右。最后是發布賬號中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占比統計,在熱門前50 條視頻中,微博賬號認證為傳統媒體官方微博賬號的共計25 條,占據了傳播的主要陣地。作為傳統媒體的新媒體賬號,在結合新的傳播形態進行信息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根據以上數據可分析得出,兩會報道中的Vlog 在內容的呈現上相較于短視頻而言更加完整和豐富。其次,其傳播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同一媒體視頻中,與Vlog 視頻線相比,兩會其他報道視頻有更多的播放量與互動量。最后是因其具有的媒體公信力及采訪權等原因,傳統主流媒體在傳播過程中更具有優勢。
(二)內容以小見大,豐富兩會報道傳播矩陣
Vlog 這一視頻形式以其趣味性,在吸引受眾關注、提高報道傳播力方面有極大的作用。在這次兩會報道中,傳播矩陣的構建主要以人民網為主,在微博上通過以#兩會夜歸人#這一話題,引發受眾參與討論。各媒體圍繞兩會主題,從記者視角出發,以不同于傳統宣傳報道中的微觀視角,以不那么正式和嚴肅的風格對兩會進行報道。表1對兩會中推出兩會Vlog 視頻的代表性媒體進行了羅列。

表1 推出兩會Vlog 的部分代表性媒體
可以看出,兩會報道較多地從記者的第一人視角,對兩會中的所見所聞進行記錄。其中既包括兩會報道中的臺前幕后,記者的日常、兩會現場,也不乏對相關議題的記錄。正如前文分析所見,第一人稱視角下的視頻內容被賦予了更多的形象標簽,具有更高的無可復制性。因此,即使是對同一主題內容進行的報道,不同的內容傳播者最終呈現的內容都具有極強的人格化屬性。同時,對兩會代表的記錄更是以受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力求實現傳播的有效性。環球網拍攝的Vlog《憑實力圈粉的王毅國委,處處彰顯大國風范》中,記者以線性時間對所見所聞所感進行的記錄,為觀眾營造了一種身臨現場的感受,為觀看者提供事實信息的同時也塑造了國家領導人的普通人形象,為受眾提供了一種接近性。兩會中的Vlog 視頻較多是以這樣的模式對重要議題進行傳播,雖不是正式的新聞報道的形式,但在傳遞事實信息、豐富信息內容、塑造領導人形象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兩會報道中Vlog的傳播創新
(一)價值取向創新:體驗與事實并重
傳統的兩會報道,主要以視頻新聞、文字新聞的形式構成傳播報道內容。其報道立足于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對事件中涉及的新聞要素進行羅列與呈現。與之不同的是,兩會報道中的Vlog 在遵循真實性的同時兼顧了受眾體驗,實現了從傳統新聞報道中以事實為導向到體驗與事實并重的傳播局面。Vlog 對所發生的事件同樣進行了真實的記錄,在尊重事實真實性的同時以幽默輕松的語言配以花字、音樂等要素,提高了內容的趣味性,使用戶體驗得到提升。
李普曼曾在其著作《輿論》中說過:“那些距離較遠的事物若要進入我們注意力的中心,就必須被轉化為有可能獲得我們認同的圖像信息,否則便只能在我們的注意力范圍內轉瞬即逝。”②相比以往對兩會的傳統報道,兩會中的Vlog 更能夠獲得受眾認同,在受眾認知范圍內得到更多的關注,在提高媒體傳播力方面有更大的效果。傳統兩會報道僅僅限于文字或視頻對兩會提出議題、政府工作報告,以新聞消息、新聞評論、通訊等傳統新聞報道體裁進行報道。受眾對這樣的報道形式形成了免疫,即使對兩會中的議題感興趣,但一看到這些乏味的文字和視頻,其興趣頓失。近兩年不斷嘗試的以VR、短視頻等為載體的兩會新聞報道,在吸引受眾關注、提升受眾興趣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Vlog 則是主流媒體緊跟時代潮流,轉變報道方式,使用新的傳播方式的有效嘗試,在“貼近人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等方面有一定的優勢。
(二)報道視角創新:宏觀向微觀的轉化
在報道視角上,Vlog 視頻的切入點通常較小,更多是從個人感受等角度進行報道,而非注重大而全。從宏觀到微觀視角的轉換,能夠減少視頻新聞制作過程中的不可抗因素,對畫面內容、技術條件的要求沒有電視新聞要求那么高,在進行后期的制作和傳播過程中也更容易。傳統的兩會報道框架主要通過對宏觀政策的報道為主,但在Vlog視頻中,更多的是以受眾的角度出發,對受眾感興趣的內容進行報道,同時結合微博的傳播特性,以輕松活潑的風格進行報道,很好地實現了內容的有效傳播。這次兩會報道中,中國日報社策劃的Vlog《小姐姐兩會初體驗》,以記者初次參加兩會報道,為了使自己看起來不像是第一次參加兩會,對編輯進行采訪,吸取經驗;同時,在兩會報道現場,對外國記者進行采訪提問,對相關議題進行詢問,因其活潑鮮明吸引了大量關注。在視頻中同樣涉及采訪,卻以一種更為有趣的方式進行了呈現,場景從報社到兩會現場進行了切換,帶受眾領略了兩會報道的臺前幕后,為兩會新聞“飛入尋常百姓家”打好了基礎。
(三)傳播形式創新:信息傳播效率提高
與傳統視頻新聞相比,Vlog 因其具有的隨意性、個人化等特點對設備和制作的要求更低,大大壓縮了制作時間,提高了信息傳播效率。傳統的電視新聞為了保證視頻質量,往往需要在進行拍攝時保證畫面的穩定及鏡頭語言的有效性,在進行后期加工時,往往需要配上解說詞、制作標準化的視頻新聞標題等。Vlog 則不需要專門的解說詞及字幕等內容,視頻內容中主要通過記者與觀看者的對話完成信息的傳遞,不需要專門的解說詞或旁白。在拍攝畫面上,Vlog 不需要依據視頻新聞的報道框架進行拍攝。記者只需要根據自己的特定主題進行記錄。Vlog 更加注重用戶互動及用戶體驗,更加注重內容的有趣性而非專業程度,利用手機等工具對視頻進行拍攝,隨后可借助手機軟件等對視頻進行簡單的處理,即可完成上傳、發布。這一過程大大縮短了信息的處理時間,對于盡量快速地占據信息傳播的高地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Vlog 具有的這一非正式性特點,豐富了兩會宣傳報道形式的多樣性。兩會報道與這一新傳播形式結盟,能夠從更廣的范圍上覆蓋傳播的受眾,使更多的年輕人及不那么關注時政新聞的受眾參與到這一傳播過程中。
注釋:
①[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馮鋼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
②[美]沃爾特·李普曼.輿論[M].常江,肖寒 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