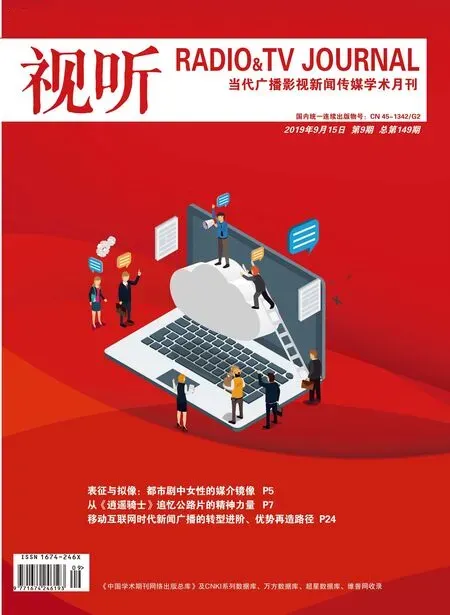淺析詩意化敘事電影
——以《小城之春》為例
□ 楊晨玉
《小城之春》拍攝于1948年,當時正是內戰如火如荼之際,這樣一部詩情畫意的作品因與暗潮奔涌的時代背景格格不入而遭到詬病,上海公映后不久,很快就被人遺忘了。20世紀70年代末,人們發現費穆的《小城之春》將中國傳統美學和電影語言進行了完美嫁接,開創了具有東方神韻的銀幕詩學和中國詩化電影的先河。本文對《小城之春》的詩意化電影風格及美學特征進行研究,探究這部于中國電影史和中國電影藝術都有著極其重大意義的作品。
一、“與其說它是一部電影,不如說它是一首詩”
費穆是最具中國傳統人文氣質的電影大師。他的影片風格低回婉轉、沉郁細膩,思想內容和電影表現手法具有現代性,在那個時代難能可貴。《小城之春》關注人本身和人道精神。下面從影片的主題、敘事結構和鏡頭語言來探討其詩意化特征。
(一)《小城之春》詩意的主題
影片詩意的主題體現在費穆站在一個人文關懷的角度去塑造人物,無關事情對與錯,充分肯定了人的精神、情感以及人性需求的正當性。影片中只出現了5 個人物:妻子、丈夫、朋友、妹妹、仆人,這樣的環境表現看似不真實,但卻體現了一種獨特的造型風格,從而更突出、更集中、更清晰地體現了感情世界的人物關系。影片反映出了細膩真摯的心理情感,同時又擁有精妙獨特的視聽覺風格,通過運用女主人公的獨白揭示了人物隱秘的內心感情,以及情感世界與現實關系的矛盾,最終達到一種詩意化的藝術追求。
(二)《小城之春》詩意的敘事
首先是敘事人稱方面的獨創性技巧。費穆有意賦予第一人稱敘述以全知視角,創造性地采用聲畫對位的方式,讓玉紋在敘述中采用“第一人稱”獨白的形式貫穿全片,賦予了其第三人稱的全知功能。這樣導演便通過周玉紋全知式的獨白顛覆了現實時空,而進入了詩情時空,從而在敘事手法上創造出了更為靈活的表達方式。
其次,從《小城之春》詩意的空間上來看,影片營造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單純化的空間環境。故事發生在一個不知名的江南小城,主要拍攝地點僅兩個,一處是小城的頹墻四周,一處是禮言的家,破敗的城墻隔斷了與世界的聯系。這樣就達到了一種分離的效果,使得觀眾與之保持一種間離的欣賞狀態,打破了熒幕上所呈現的一種真實的幻覺,從而使詩情的述說成為了可能。
最后是故事結構的封閉性。故事的開始和結束分別是章志忱的到來和離開,就像一顆石子投向了死水一樣波瀾不驚的湖面,仿佛這個地方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從來沒有這個人來過,章志忱在戴家這十余天發生的一切就是一個完整而又封閉的片斷,給人一種“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的憂哀詩意的調調。
(三)《小城之春》詩意的鏡語
影片中有大量富有內涵和詩意的長鏡頭,才構成了影片獨特的視角,通過簡單的鏡頭來表現復雜的情感。比如其中一個長鏡頭是老黃到花園的廢墟上找少爺禮言。老黃在左面的洞口看見了禮言,繼而走到右邊的洞口與禮言對話,鏡頭由左橫搖向右。本以為鏡頭會隨老黃的對話讓禮言從右洞口入畫,但攝影機卻巧妙地從左洞口慢慢推進,隨著鏡頭透過墻洞慢慢深入推向禮言。老黃再從右入畫,此段的鏡頭運用可謂是別出心裁。影片中還有一場長達1分40 秒的長鏡頭,這場戲拍攝得十分巧妙。在這一段長鏡頭中,鏡頭沒有切換,一共左右橫搖了6 次。畫面內容是志忱來到禮言的家里,戴秀給他唱歌,玉紋給禮言喂藥。玉紋是場面調度的中心點,右側是戴秀和志忱,左邊后面的床上坐著禮言,前景是在為禮言弄藥的玉紋。戴秀唱歌吸引志忱注意,志忱幾乎一直看著玉紋,玉紋在照看禮言的同時也會看一眼志忱。這六次橫搖,禮言、玉紋與志忱三人始終都沒有在同一個畫框里出現過,總有一個人在畫外,從而暗示出此時他們三人的微妙關系。
影片中很少有鏡頭的切換,大部分都是淡入淡出的疊畫,這樣就為片中微妙的人物關系添加了神秘的色彩。獨白的貫穿和淡出淡入的運用,為影片提供了一種全知式的視角和重復式的描述方式,巧妙地表達出當時情境下人物的心理,另外語言的節奏也控制得很巧妙,細膩婉轉地將情節慢慢展現出來。同時多數景別較緊,一個鏡頭整個都是全景的很少,角度絕大多數平視稍仰,體現出了費穆的人文關懷和對人物的關切。在他的引導下,我們得以進入那個封閉的時間與空間,去體驗那份紛繁復雜的情緒與淡淡的詩意。
二、《小城之春》的美學風格特征
從構圖內部分析。首先是空白背景的使用,人物和空白的背景。這些與中國傳統繪畫中對空白的使用相對應。依據虛實結合、計白當黑的傳統,空白體現出“道”的底蘊,萬物非孤立而是同在道中生化運行著的,體現出中國人的宇宙觀。其次,在人與周圍環境的關系處理方面,還運用了園林美學的處理方式。一方面,人生活在固定的框架之內,比如構圖中以窗、回廊、亭柱等為畫框;另一方面,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框架中吐納景物,營造出了一種“天地為廬”“萬物皆備于我”的整體豐盈的自足世界。最后是對有關門的鏡頭的處理,白墻、冰裂紋的窗格、人物以及婆娑樹影,豐富嚴整。正是上述獨特的處理方式展現了費穆將中國傳統美學文化同西方美學一些思想完美地結合。
影片中有大量穩定周正的固定鏡頭和以人物行動為運動支點的固定搖鏡頭,均能體現出其獨特的美學風格。一行四人出去泛舟游玩,他們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泛著舟,隨性地唱著歌謠,快樂地前行著,靜靜的湖面,美麗恬靜的山水,導演運用了極佳的構圖比例將那份詩意展現得淋漓盡致。以人物運動為運動支點,突出了行云流水的美感,如女主人公拿著菜籃子走在破舊的城墻上打發著無聊的時光時的構圖,充滿了一種淡淡的憂思,讓人迷戀沉醉。這種靜態和平面長鏡頭美學,仿若脫胎于舞臺話劇藝術,但費穆卻圓渾地結合光暗對比、獨白等純粹的電影手法化為自己的美學風格。
三、《小城之春》的評價及影響
在影片的內涵方面,費穆一貫追求儒家的理想道德境界。影片中沒有談時政,卻通過三個人的三角戀愛情,發出了家國感懷,也抒發出當時知識分子的苦悶心境,實在是極具時代意味,整體氤氳出意境之美。
《小城之春》是在國家大亂的時代背景下頑強誕生出的美麗詩篇,不但是中國電影美學上的經典,更是世界電影的杰作之一,實在值得所有中國電影工作者不斷重復觀看和體會鉆研。當今電影市場存在泛娛樂化和商業化的現狀,文藝電影在這個浮躁的電影氛圍中夾縫生存。費穆詩意化的敘事風格,這種傾向于普泛的人性主題和含蓄隱秀的藝術風格更令人覺得彌足珍貴。從當下中國電影創作的實際出發,正視對電影本體的認識,劇本應走在資本之先,實現藝術價值和商業價值(即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的真正的統一,增強當代國產電影的號召力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