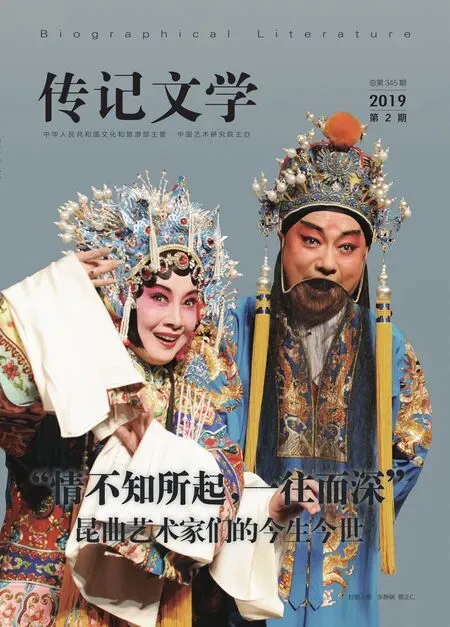默默堅守 含蓄耕耘
—— 一代昆“丑”姚繼蓀
韓郁濤
中國藝術研究院

昆曲被稱為百戲之母,她從明代中期一直走到了今天,是我國目前流傳的戲曲劇種當中最古老的劇種。而她的傳承之路,是頗為曲折的。在清中期,隨著地方花部的崛起,作為雅樂官腔的昆曲在題材與表現力上不及花部,逐漸在花雅之爭中敗下陣來,走向了衰落。到了清末民國之際,隨著京劇的一枝獨秀,昆曲更加難以為繼,已經到了面臨絕境的地步。1921年,在昆曲的故里蘇州,昆曲傳習所的成立,是昆曲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件事。它的出現,不僅使當時已經瀕于式微幾成絕響的昆曲被保存了下來,免遭消亡的厄運,而且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昆曲傳承人——“傳”字輩演員。他們成為了昆曲藝術最為重要的傳承者,幾乎是當時昆曲最后的火種。昆曲這一古老的劇種,之所以在今天再次煥發藝術的青春,與這些“傳”字輩演員有著莫大的關聯。他們將畢生所學幾近可能傳給了下一輩,希望昆曲在他們身上得以延續。他們培養的早期的“繼”字輩的學生,秉承了先師遺志,將昆曲藝術帶到大江南北,并走出了國門,水磨之聲享譽海外。此外,他們在全國各地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使昆曲在今天呈興盛之勢。毋庸置疑,昆曲皇后張繼青是“繼”字輩中最為耀眼的一顆明珠,她的藝術成就早已蜚聲海內外。而那些在昆曲舞臺上,默默耕耘、堅守自己腳下那片土地的演員,同樣值得我們尊敬。正是他們的付出,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演員,他們不該被遺忘。本文的主人公便是江蘇省昆劇院的第一代丑腳演員——“繼”字輩的姚繼蓀老師。
姚繼蓀,原名姚欣蓀,1938年出生,蘇州人,國家一級演員。1955年學藝,攻丑、付,師承華傳浩、徐凌云、徐子權、王傳淞,也受到戲劇家周貽白、舞蹈家吳曉邦、昆劇大師俞振飛等名家指導。1960年調到位于南京的江蘇省蘇昆劇團,“文革”后,此團改成江蘇省昆劇院。代表劇目有《艷云亭·癡訴·點香》《蝴蝶夢·說親·回話》《義俠記·打虎·游街·誘叔·別兄·捉奸·服毒·顯魂》《水滸記· 活捉》《漁家樂·相梁·刺梁》《繡襦記·教歌》《望湖亭·照鏡》,等等。2016年病逝于南京。
初入劇團
1953年10月,常年在浙江和蘇南地區演出的上海市民鋒實驗蘇劇團落葉歸根,于蘇州落戶,改成蘇州市民鋒實驗蘇劇團,并陸續開始招收學習蘇劇的學員,張繼青便是最早被召入學習蘇劇的學員之一。1955年,年少家貧的姚繼蓀為了討生活,初中畢業后便去報名了蘇州戲曲訓練班。訓練班包含評彈、滬劇、蘇劇3個劇種。少時的他對蘇劇幾乎一無所知,對從小耳濡目染的評彈卻是十分熟悉,所以,他最早報名的是評彈,但并沒有被錄取,而是連同當時的9名學員,一起被劃分到了民鋒蘇劇團學習蘇劇,初學小生,后改小花臉。1956年,隨著昆劇《十五貫》晉京演出后在全國取得了轟動效應,江蘇省領導認為在昆劇的發源地江蘇,應當有一個專業的昆劇團。為了加強傳承與保護江蘇地區的昆劇,江蘇省政府決定將蘇州市民鋒實驗蘇劇團改為江蘇省蘇昆劇團,駐地仍在蘇州,交由蘇州文化局代管,體制為自負盈虧的集體所有制。昆劇是蘇州戲曲工作的重點,奈何以當時的條件,無法成立專業的昆劇團。而蘇劇與昆劇又存在淵源,將昆劇的傳承與保護納入到蘇劇團中,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當時的蘇劇在江、浙、滬的觀眾群中,還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更為雅致的昆劇在當時的受眾面很少,鮮有問津,是很難獨立生存的。故而劇團確立了經濟上“以蘇養昆”、藝術上“以昆養蘇”的辦團方針,兩個劇種,一個劇團,和諧共生。而姚繼蓀那批學員與之前的學員一起,組成了第一批蘇昆劇團的學生,從事昆、蘇劇的學習,并以“繼”字輩起名,意為繼承昆劇事業。“繼”字輩也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蘇州市培養的第一代昆、蘇劇接班人,是昆、蘇劇兼習兼演的學員。
為了重視對昆劇的傳承,顧篤璜、吳曉邦、俞錫侯、曾長生、汪長全、徐凌云等名家悉數到蘇昆劇團進行教習,顧篤璜更是擔起了劇團的領導與總導演的重任。他因材施教,針對不同的學生,采取的教學方法不盡相同,為人更是平易近人,與這些“繼”字輩學生同吃同住,并為他們排了新編昆劇《貍貓換太子》,在蘇州一經上演,反響強烈。舞蹈家吳曉邦主要負責學員們的形體動作與發聲方法。直到晚年,姚繼蓀都很感念吳曉邦老師當年教他演戲時的呼吸方法。資深曲家俞錫侯則負責學員們的拍曲,對用氣、字腔、度曲都有嚴格的要求,每支曲子每天拍下來,不少于20遍。姚繼蓀的開蒙戲《望湖亭·照鏡》是和昆曲名家徐凌云學的,并得到了武生泰斗“蓋叫天”的高度贊揚,認為姚繼蓀外形雖丑,卻依舊像個少爺,符合人物定位。這出戲也被姚繼蓀傳給了學生,成為了今天江蘇省昆劇院經久不衰的劇目。有了扎實的基本功后,劇團領導便請各地的昆劇名家來蘇州為這些學員教戲與踏戲。俞振飛、朱傳茗、華傳浩等昆曲名家與“傳”字輩老師們都曾到蘇州為“繼”字輩學員教戲,有些更是一到暑期,還沒顧得上休息,便馬不停蹄地從上海戲校趕來,為這些學生上課。這些“繼”字輩學員被社會各界傾注了較多的心血與關愛,所以他們成長得異常迅速。每每談到這些為他們上課的藝術大家時,姚繼蓀感嘆不已,認為自己能夠在藝術道路上得到了諸多名師的指導是無比幸運的。
早期從事昆、蘇劇的學習,是要自負學習和生活費用的。一段時間后,可以在舞臺上跑龍套時,才會有伙食費。故而那時的學員都非常努力,很快就可以跑龍套,甚至獨當一面,隨團下鄉演出了。那時候的生活是無比艱辛的,劇團經常要跑碼頭,破屋漏廟里居住是家常便飯,經常是外面下大雪,房內下小雪。即使是這樣的條件,以張繼青領銜的年輕一代學員們在演出時依舊是一絲不茍,非常地賣力。那時候,他們陣容齊整,充滿了青春活力,所到之處,都十分受歡迎。外出演出時,白天他們要負責給劇團扛箱子,晚上在船上玩一宿,早上睡一會兒便去裝臺了。據姚繼蓀回憶,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們平均每年要演出200多場,經常在不同的城市間來回穿梭,日子基本都是在舞臺與旅途中度過的。那時的生活雖然辛苦,但卻讓姚繼蓀無比懷念,他經常給家人講述自己那些年演出時的情景。1960年5月,為了進一步擴大昆劇的影響力,江蘇省政府決定將蘇昆劇團一分為二,調部分“繼”字輩演員赴南京組建江蘇省蘇昆劇團南京團,也就是后來的江蘇省昆劇院。所調的13名優秀的演員之中,便有姚繼蓀,他們也成為了后來的南京劇團的骨干。
學藝名師
提及姚繼蓀,人們總會想到他的《艷云亭·癡訴·點香》《活捉》《義俠記》。這些都是他的代表劇目,很多甚至是獨有劇目。尤其是《艷云亭·癡訴·點香》中的諸葛暗與《義俠記》中的武大郎,成為他在昆曲舞臺上塑造的最為光彩奪目的角色。這兩出戲,也是當今江蘇省昆劇院丑腳行當代代相傳的經典劇目。這兩出戲是姚繼蓀師從當時“傳”字輩著名的小花臉演員華傳浩學來的。
由于“繼”字輩學戲,缺乏整體的師資力量,南京劇團領導采取了“請進來”與“派出去”的學戲方法。一方面利用老師們的閑暇時間,邀請各地老師來南京劇團集中教戲,另一方面將學員派往各地找老師學戲。此外,團領導會為每個學員指定特定的學習老師與所學劇目,以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老師的拿手戲與精華之處學到手,減少學習中的盲目性。姚繼蓀被指派的就是上海戲校的華傳浩老師,他通過向華老師學習,提升了在昆劇丑腳上的藝術修養。
姚繼蓀在上海戲校向華老師學藝期間,喜歡學一些冷門的戲。很多人不學的傳統戲,他都主動向華老師提出學習,因此他學了華老師身上很多的獨門戲。《艷云亭·癡訴·點香》本是一出在舞臺上絕跡的傳統折子戲,而華傳浩憑借個人舞臺經驗,自行設計動作、身段,將其恢復出來。因為它是一出瞎子戲,當時在上海戲校的科班學生都沒有學,而外來的姚繼蓀卻學走了這出戲,陰差陽錯,這出戲后來成了江蘇省昆劇院丑腳戲的代表作與獨有劇目,各地劇團紛紛派演員來向蘇昆學習這出戲。
《艷云亭·癡訴·點香》之后,“武十回”的學習經歷同樣令姚繼蓀終身難忘。姚繼蓀、張繼青、姚繼焜被南京劇團派往上海戲校學戲期間,向“傳”字輩老師學習了整本10出的《義俠記》,也稱“武十回”。小花臉行當的姚繼蓀一人就要學《打虎》《游街》《誘叔》《別兄》《捉奸》《服毒》《顯魂》7出,課業內容非常多。而華傳浩老師在教學時是異常嚴苛的,即使在拍曲時都要求學生蹲腿學唱曲子,以加強丑腳腰腿基本功鍛煉。在進行形體動作時,不僅要講究一招一式的姿態美,還需要體驗人物的個性化特征。姚繼蓀在學《游街》時,武大郎的角色不僅要走蜘蛛步,還要在肚子上裝一個圓的淘米籮,同時不影響打飛腿,是非常考驗功力的一折戲。之后,姚繼蓀在尊重老師教授的傳統基礎之上,對大籮肚進行了改良,用鐵絲做了一個類似馬甲式的肚子,既美觀又便利,還不影響打飛腿。在學《戲叔》《別兄》時,姚繼蓀被華老師要求腋下夾兩個布團練習,在舞臺上飲酒與做動作,甚至打飛腿時,布團不能從腋下掉出,以便形象地表現出武大郎的矮。由于常年累月地辛苦練功,姚繼蓀很早的時候便髕骨軟化了,“武十回”這樣的戲不能再演出了,也沒有完整地傳承下去,這是他最大的遺憾。1982年,姚繼蓀將《游街》一折,通過講戲的方式教授給張寄蝶,而張寄蝶更是憑此戲一炮打紅,獲得了第三屆中國戲劇梅花獎。

《艷云亭》,姚繼蓀(左)飾諸葛暗(王建民攝 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供圖)
《活捉三郎》是現在昆曲舞臺上常演的一出劇目,全國各大昆劇院都有自己的版本。但真正從“傳”字輩老師那里學來這出戲的,只有姚繼蓀一人。受限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在戲改之后,很多戲就不允許演出了。《活捉》就是一出被禁的戲,在上海戲校的華傳浩是被禁止向學校里的學生們傳授這出戲的。而南京劇團的領導則會給予本團學員寬松的學習環境,只要是戲好,都可以學習。姚繼蓀心心念念想要學這出戲,認為這是一出難得的好戲。所以,南京劇團領導出面為他們師徒搭橋,說服了華老師,讓姚繼蓀心愿得償。華老師在傳授這出戲時,當時還是上海戲校學生的劉異龍、成志雄是需要回避的。故而多年后,劉異龍在恢復《活捉》時,都要找姚繼蓀來請教與指導。這是一出二花臉的戲,講究冷奸,變臉時都非常隱蔽,但同時要保持刀筆的書生味兒,在花旦閻惜嬌上場后,需要和她保持高度的眼神交流。一方面要表現張文遠的情難自已,被情所勾,另一方面,要表現他二花臉陰冷的特質,情熱而人冷,是一出非常考驗功力的戲。演得過頭,會庸俗化;情感不熱烈,又表現不出他被情所迷的特征,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姚繼蓀從華老師那里學成后,又向王傳淞老師求教。作為二花臉出身的王傳淞老師,《活捉》也是他的看家戲。與華老師不同,王老師的《活捉》更具鄉土氣息,沒有華老師過多繁雜的身段,整體更接地氣。姚繼蓀從王老師身上汲取了這些優點,融合到自己的表演之中。此外,他還尤為佩服王老師《墻頭馬上》中老家院的塑造,樸實無華而又倍感親切。他認為王老師在塑造這類人物上,十分過人,值得積累與學習。正是由于他的轉益多師與厚積薄發,之后與張繼青合作《蝴蝶夢·說親·回話》時,把諸多老師的優點融會貫通,將本是配角的老家院演成了他的代表劇目之一,贏得了觀眾的高度贊揚與認可。

《蝴蝶夢》,姚繼蓀(右)飾倉頭(王建民攝 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供圖)
蹉跎歲月
1965年以后,昆劇陷入停滯狀態長達13年之久。這對于正處于成長期的姚繼蓀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南京成立的蘇昆劇團被迫撤銷,改建成江蘇省京劇二團,演職員大部分被下放、轉業。小花臉行當多以演反面角色居多,“文革”到來后,小花臉行當的演員更是沒有地位。姚繼蓀由于懂些文筆,就被派去圖書館與博物館寫材料。想要繼續練功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時間,基本都被整理與書寫各種材料占據了,身上的功夫也就逐漸荒廢了。此外,改建的江蘇省京劇二團在當時要求蘇、昆劇演員改唱歌劇與現代戲。所以,姚繼蓀還唱過一段時間歌劇與現代戲。他演唱過歌劇《警鐘長鳴》與《黃海前哨》,演過《紅燈記》中的劉副官。姚繼蓀早年是蘇劇與昆劇演員出身,蘇州方言比較明顯,而歌劇與京劇對普通話要求較高,所以他后來連現代戲也無法唱下去了,只能坐在臺下觀摩演出,回去準備文字材料,直至1972年7月,蘇州恢復建立了僅有20余人的蘇劇小組。同年10月,中共江蘇省委決定,將駐南京的江蘇省蘇昆劇團(當時已改為江蘇省京劇二團)全體人員下放蘇州,與蘇劇小組合并,恢復江蘇省蘇昆劇團建制。姚繼蓀下放到蘇州后,有了繼續演戲的機會,一方面要演《收租院》《向陽花》這樣的活報劇與歌劇,另一方面還可以演《喜搬家》《新店員》這樣反映當時生活的蘇劇。在下放期間,姚繼蓀還導演了一部名為《雪山風云》的昆劇,反響非常強烈。
即使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姚繼蓀也沒有放棄對昆劇事業的追求。有時白天寫完材料后,晚上回去就會練習與回想當年華老師教他的戲。此時的他不僅把表演昆劇當做一種娛樂與享受,來調劑生活的苦悶,同時對昆劇的鉆研也絲毫沒有懈怠,甚至是更為精益。《艷云亭·癡訴·點香》是他藝術生涯中的杰作,關于角色諸葛暗的人物分析就是在這個階段領悟到的。演瞎子戲,姚繼蓀體會到的是諸葛暗的無所求,可以自得其樂。諸葛暗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卻因為眼盲而缺乏能力,安心做一個平平淡淡的好人。讓觀眾對他充滿同情,這個人物就塑造成功了。《義俠記》中武大郎是一個懦弱的人,他沒有力量去反抗。面對潘金蓮喂藥時,他是有遲疑與不安的,但是對潘金蓮更多的愛使他打消了對她的懷疑。所以,要演好武大郎首先要從眼神開始,不能過于有神與兇狠,這些都是武丑的特征,要表現出的是一種懦弱與無奈。此外,演員身上的功夫更要過硬,因為是演矮人,所以胳膊不能伸出,要始終夾著完成程式動作。基本功過硬的同時,又不能賣弄。每場戲技法的使用與搭配是固定的,不同的戲碼亦有不同的表現。但萬不能在一場戲中堆砌技法,炫技博彩,這是昆劇所不允許的,也是周傳瑛老師之前對他的教導與叮囑。那段特殊的歲月里,基本無昆劇演出的狀態,反而讓姚繼蓀更加沉靜,去回想與思考當年名師們的叮囑,去感悟那些折子戲中角色人物的心境與特征,為他的表演積淀了內涵。這種體悟與積累,他日后也毫無保留地教給了學生們,幫助他們在藝術生涯上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成就。

《義俠記·打虎》,姚繼蓀飾酒保
1977年11月,隨著“文革”的結束,江蘇省蘇昆劇團中原駐南京的人員仍調回南京,成立江蘇省昆劇院。此時,姚繼蓀又從蘇州回到了南京,而江蘇省昆劇院也成為了當時全江蘇省唯一一家專業性昆劇院團。姚繼蓀回到南京之后,百感交集,滿心歡喜地準備投入日后的昆劇表演事業中。然而,由于受“文革”迫害與早期刻苦練功的影響,他的身形已經開始走樣,膝蓋髕骨發生了嚴重的軟化,大夫對他的建議是放棄唱戲。天生執拗的姚繼蓀并沒有接受大夫的意見,而是繼續在昆劇舞臺上展現著自己的風采,傳承著老師的衣缽。常演劇目有《十五貫》《墻頭馬上》,只是像《義俠記》《活捉》這樣難度較高的戲碼,他不得不含淚舍棄,尤其是經兩位“傳”字輩名師教授與指點的《活捉》,學成后的他本就沒有演出幾場,一直處于被禁狀態。如今,昆劇事業迎來了春天,但很多事情他卻無能為力了,無法將一些戲完整傳承下去,這使他痛心疾首。“文革”后的日子里,姚繼蓀一方面在舞臺上繼續演出,時或為張繼青這樣的名角配配戲;另一方面,也在江蘇省昆劇院指導演員與培養學生,將他從“傳”字輩老師那里學來的東西傳承下去。
傳道受業
“文革”結束后,周傳瑛老師每次到南京,就會和姚繼蓀嘮叨:“繼蓀啊,你學戲比較扎實,因為你是有知識積累地在學戲,開始知道這是好東西,為什么好,你愿意研究。我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不行了,你叫我動都動不了,對不對?你要在舞臺上拿出東西,拿出好的來。我們藝人在,戲還在,藝人走了沒傳下去,這個戲就沒有了。”這些話語深深觸動著人到中年的姚繼蓀,由于病痛的折磨,他在舞臺上已經放棄了很多劇目,演出的時間與機會也越來越少了。如果自己不能把華傳浩老師傳授的劇目傳承下去的話,就會像周傳瑛老師所說的那樣,人走了,戲也被帶走了。為了不讓一些昆劇劇目存在隱性失傳的危險,80年代后期的姚繼蓀逐漸淡出了舞臺,開始從事昆劇教學與傳承工作。
他在江蘇省昆劇院最早帶了5個學生,其中李鴻良、計韶清、袁偉如今已是省昆的知名丑腳演員了,尤其是李鴻良,獲得了中國戲劇梅花獎,現今是江蘇省昆劇院院長,盛名在外。李鴻良的拿手戲《孽海記·下山》就是姚繼蓀傳授的。計韶清的《望湖亭·照鏡》《艷云亭·癡訴·點香》這些常演與代表劇目,亦是得益于姚繼蓀的傾囊相授;此外,姚繼蓀還為他排演了《牡丹亭·上路》。當張寄蝶遇到藝術的瓶頸期時,姚繼蓀主動建議他練矮子步,將華傳浩老師傳授的武大郎的表演技巧毫無保留地教給了他,使其憑此戲一鳴驚人,被人稱為“活武大”,成為其昆劇藝術生涯中塑造的最為耀眼的角色。劉異龍想要恢復《活捉》一折,特意從上海前來請教時,他慷慨相助,為他和梁谷音版的《活捉》貢獻了一份力量。
之后,他的傳承教學工作已經不拘泥于江蘇省昆劇院,而是游走于各地,他經常會和張繼青去江蘇省蘇州昆劇院輔導教學。“文革”結束后,原蘇州駐地的江蘇省蘇昆劇團正式更名為江蘇省蘇劇團,仍采取蘇、昆劇邊學邊演的方針。這種蘇、昆共存的模式一直持續到了2001年,昆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之一”,作為昆劇發源地的蘇州市黨政領導和廣大民眾,對昆劇的“保護、繼承、創新、發展”寄以更大的關注和支持,劇團被正式更名為江蘇省蘇州昆劇院,成為專業的昆劇院團。因為十年動亂,江蘇省蘇州昆劇院底子已較為薄弱,所會的昆劇劇目十分有限,即使是蜚聲國際的青春版《牡丹亭》,亦是得益于張繼青與汪世瑜兩位外聘老師的指導。蘇州是哺育姚繼蓀藝術生命的地方,故而姚繼蓀認為來蘇州昆劇院教戲責無旁貸,甚至不計報酬。當時的蘇州昆劇院條件還是比較艱苦的,姚繼蓀腸胃又不好,無法去大食堂吃飯,需要自費飲食,教戲結束后,囊中所剩無幾。這些物質上的利益,他都絲毫不在意,唯一牽掛的是孩子們可以認真學習,把老師教的戲傳承下去。

《風箏誤》,姚繼蓀飾奶娘
他鼓勵自己的學生要厚積薄發,善于積累,不要浮躁,塑造人物要跟人物貼近,要平實自然。一定要有扎實的基本功,遵循傳統與昆劇本來的樣子,不可以隨便亂改。周傳瑛老師曾教導他說:“我們昆曲好像一套紅木家具,說我要改,把紅木家具去掉,裝個不銹鋼的行不行?不行,它只能拿個布擦擦干凈,或者抹點油上去,行了,這是昆曲。”他也以此來告誡學生。作為丑腳演員,更要注意戒躁,不要光想著去討好觀眾。好的丑腳表演是有內涵的,需要讓觀眾品讀出戲的味道。所以,他對后來舞臺上亂改程式、嘩眾取寵的行為非常痛心疾首。他對昆劇未來的前景也是有一絲憂慮的,不希望老師的東西在他這里消亡或是變了味兒。他經常叮囑學生:有了扎實的基本功與老師的指導,以程式為依托,才可能去嘗試昆劇舞臺上創造性的表演,否則就會失去昆劇的韻味。
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演戲是姚繼蓀奉守一生的準則。昆劇舞臺上,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色。即使長期從事舞臺的綠葉,他也依舊在自己的領域兢兢業業,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經典的形象,獲得了觀眾的認可。阿甲先生曾高度評價過姚繼蓀的表演,認為他是一位講究舞臺含蓄的昆丑。走下舞臺,他又是一位默默耕耘的園丁,為昆劇的傳承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踐行著一位“繼”字輩傳承人的責任與義務。姚繼蓀老師已經離開我們快3年了,他對后輩的殷殷期盼,對昆劇事業的熱忱之心,至今令我們為之動容與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