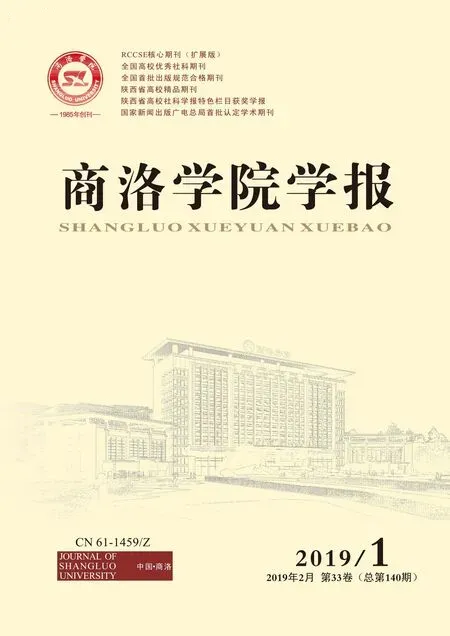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梁四公記》對“商山四皓”之典的重構
金曉琳
(云南大學文學院,云南昆明 650000)
《梁四公記》是初唐時期六朝志怪小說向唐傳奇發展過程中的典型作品,今只存《梁四公》《五色石》《震澤洞》三節。《梁四公》以闖、杰、、仉督四公為線索,內容涉及豐富的異域博物及奇珍異寶,將獨立的故事單元串聯為一個故事內核展開敘述;《五色石》和《震澤洞》則通過山人獻石、龍女獻龍珠的事件,展現了杰公善識寶物之能。關于《梁四公記》的記載,最先見于唐人顧況《戴氏〈廣異記〉序》“國朝燕公(張說)《梁四公傳》”[1]。《新唐書·藝文志》雜傳類著錄盧詵《四公記》一卷,注云“一作梁載言”[2]。《宋史·藝文志》作“梁載言梁四公記一卷”[3]。可見,《梁四公記》的作者在史籍目錄中存在不同的記載,目前仍無法確考。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關于唐代小說史研究的著作開始對《梁四公記》給予關注。李宗為在《傳奇產生前的唐人小說》中認為《梁四公記》非張說所著,其內容荒誕,文字也較蕪雜,不像是當時被稱為“燕許大手筆”的名相張說所為,并根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引證的內容,認為是唐高宗時臨淄方士田通所撰,盛唐后的方士附會為張說,以此來抬高身價[4];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對《梁四公記》的著錄、作者、佚文及內容情節做了介紹,認為顧況較梁載言、張說時代較近,且以顧說為準[5];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進一步對《梁四公記》的著者問題進行考辨,認為顧況《戴氏〈廣異記〉序》的記載確實無疑,而托名田通、梁載言是張說故弄玄虛,是張說得田通舊文加以潤色而成的[6]145-150;侯忠義《隋唐五代小說史》對《梁四公記》的內容、故事情節、藝術描寫、作者等相關問題做了概述,認為《梁四公記》在內容上繼承《博物志》的傳統,藝術上采用短篇連綴成長篇的形式,為傳奇的發展積累了創作經驗[7]。李鵬飛認為《梁四公記》反映了初盛唐時代軍事政治形勢的演變以及作者張說個人的思想情感與人生經歷,通過對素材的溯源、分析作者具體的創作手法,將其視為熔鑄史實與傳說、現實與幻想于一爐的典型的小說文本,體現了唐代前期作家有意為小說的意識[8]。上述關于《梁四公記》的研究,集中于對作者的考證和傳奇的內容、情節等方面,而對其文化內涵及意義的探析卻較少涉及。本文將結合《史記》文本中關于“商山四皓”的記載,對比分析《梁四公記》中梁四公與商山四皓的繼承、延展關系,進而探討《梁四公記》傳奇在故事內核、人物形象、小說創作觀念等方面對“商山四皓”之典的重構。
一、《梁四公記》四公與“商山四皓”形象之變
“商山四皓”的記載最早見于《史記·留侯世家》:
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9]2044-2045
《留侯世家》中關于東園公等四人的記載是“商山四皓”典故的原始出處。《史記》中關于“商山四皓”,僅有其年長,因在位者輕蔑、怠慢賢士而逃匿山中不為漢臣的簡單記載,至于其形象則是“年皆八十有余,須眉皓白,衣冠甚偉”[9]2045。司馬貞在索引中則進一步交代了四公的具體姓名:“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9]2045《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求聘四皓”條據顏師古注云:“四皓須眉皓白,故謂之四皓。”[10]697顏師古注的依據是《留侯世家》中“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須眉皓白,衣冠甚偉”的形象細節描寫。由此可知,“商山四皓”之形貌特征從始至終即是如此。
現存的《梁四公記》佚文主要見于《太平廣記》卷八十一《梁四公》(三千多字),卷四百一十八《五色石》(二百三十四字)、《震澤洞》(一千三百多字)。后二篇下皆注“出《梁四公記》”。宋代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趙彥衛《云麓漫鈔》、龐元英《文昌雜錄》三部文獻中也記載了一段內容大致相近的異文,應為《梁四公記》的開篇。
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趙彥衛《云麓漫鈔》記載了梁代大通中四公來朝,武帝問及三教九流和前朝舊事,四公皆對答如流之事,突出了全朝竟無識梁四公者,惟昭明太子蕭統識之,四公便欣然依附蕭統的情節,其中又有關于四公年齡、面貌的描寫,如《六朝事跡編類儀賢堂》:“大通中有四人來,年七十余,鶉衣躡履,行丐經年,無人知者。帝召入儀賢堂……帝問三教九流及《漢書》事……舉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而禮重之,四人喜揖昭明如舊交,時目之為四公子。”[11]《云麓漫鈔卷六》中又有一段近似于《六朝事跡類編》中對梁四公的描寫,其四人在大通中年入梁,“貌可七十,鶉衣躡履,入丹陽郡建康里,行乞經年,無人知……帝問三教九流及漢朝舊事,了如目前。問其姓名,一人曰姓名闖,一人曰姓名杰,一人曰姓名,一人曰姓仉名督。合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之。四人喜,揖昭明如舊交,目為四公子。”[12]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六》亦記載:“梁四公子:一人姓名闖,孫原人。一人姓名杰,天齊人。一人姓名,浩人。一人曰姓仉名督,無阮人。昭明太子曰:‘ 出揚雄蜀記,闖出公羊傳;出世本,字亦作簡,出三齊記,杰出竹書紀年;出索緯隴西人物志,出世本及廣雅;仉出太乙符, 出史記。孫原,僰山名。浩 ,洮湟之間二水名。五阮,雁門也。’”[13]它補充說明了四公姓氏、人氏及出處。
李劍國認為:“以上除四公姓名皆不見《廣記》引文中,亦是此記佚文。”[6]148此三段佚文中對四公年齡、面貌均有相似的記載,其中《梁四公記》中關于四公“年七十余”“知三教九流之事而無人知者”“惟昭明太子禮而遇之”等情節又與“商山四皓”在《史記》中的記載極為相似。《梁四公記》中,梁朝宮廷諸王、儒士中唯一得到正面描繪的是昭明太子蕭統,前引兩段佚文中關于四公“合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之”“四人喜,揖昭明為舊交”的情節使人聯想到《史記留侯世家》中“太子為書,卑辭候禮,迎此四人”“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等語,則四公與四皓在人主的選擇上,同歸附于對自己禮遇有加的太子。四公與四皓同樣年長而博聞強識,不僅在形象與智謀上相同,且同時都作為整體出現。而在《梁四公記》中,則著重突出了四公各自所長,并對其所長進行了詳細的刻畫。其中,梁四公“行乞經年”的人生際遇也與商山四皓不同,四皓作為高賢隱逸之人,其形象素來高潔,而四公卻頗顯落寂。
二、《梁四公記》對“商山四皓”江山之助的延展
《梁四公記》通過梁武帝時期的四位異人,將各個具有獨立性的故事串聯起來,所述四公之事,內容完整,情節頗為曲折。“商山四皓”高尚賢能、智謀出眾的佐王之才則在《梁四公記》中得到了細致的敘述。梁四公都是博才識廣的能人,闖能夠卜筮識物,知曉禮儀并且能預知后事,杰能辨明異域方物,仉督則擅長應對禮賓問答、精通儒道及梵語釋說。《梁四公記》傳奇中描寫的四公各有所長,人物性格各異,均是作者有意識地對人物進行的塑造,從而將獨立單一的故事串聯成一個博才多識的整體,而在博聞強識的整體形象中又見其個性分明。前引《留侯世家》中關于四皓的記載,未詳其人其事,只敘述了四皓歸附太子劉盈,得到了劉邦對太子的信任,認為他根基穩固、深得人臣民心,最終放棄了易儲之念。但在《梁四公記》中,四公不再是串聯在一起的形象整體,而是各有側重,闖明卜筮、知禮儀、杰識博物、仉督擅應對。在現存佚文中,唯杰公之事最為稱奇,情節最為完整,物類也最為豐富,傳奇中所涉及的異域方物、珍奇異獸、珍珠寶玉皆光怪陸離、神異非常,具有志怪小說廣征博物之質。
三、從梁四公與“商山四皓”之不同反觀小說作者創作觀念
班固《漢書·張良傳》沿襲了《史記·留侯世家》的記載,但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中對“商山四皓”作出了道德評價:“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10]3058將四人與鄭子真、嚴君平并列,成為抑制貪婪之風、勸勉良好風俗的典范。《法言·重黎》云:“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 ’”[14]揚雄將四皓列入“為人所不能”的“賢”之列。在后世的援引中,四皓皆以其賢稱名于世。如《后漢書·鄭玄傳》記載靈帝末年,黨錮之禁解除后,鄭玄拒絕接受何進、袁隗的征辟,而深得國相孔融敬重。孔融列舉漢世被冠以“公”之稱謂的有名之士:“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仆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15]可見,四皓亦并列在“公者仁德之正號”內。《晉書·殷仲堪傳》記載桓玄持“隱以保生”之論以質疑四皓羽翼太子之事,殷仲堪則認為“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16]。四皓本于仁義之道出山,以賓客之禮對待漢惠帝,問答不涉及是非之論,漢惠帝的太子之位因而得以鞏固。四皓為發揚仁義之道而出山,是保有國家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古今圣賢共同珍惜的,與踏入仕途做臣子的人相比,有著本質的區別。可見,歷代史籍逐漸以“賢能”“仁德”等表征四皓之事,并將其固化為特定的稱謂。后代也不乏對四皓事跡真實性的質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商山四皓”的形象被不斷建構和符號化,四皓也成為賢德高隱的表征和典范,備受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的推崇。
《梁四公記》中的四公形象不僅在發揮江山之助的作用方面比商山四皓更為具體,且善卜筮、熟識異域方物,已非典型的儒者形象,且傳奇文本中除了昭明太子之外,對諸王儒士均無正面、積極的描寫。四公在人生價值的選擇上,用其稟賦之異能積極輔佐統治者。如文中藩國向梁朝進貢,滿朝王公儒士竟無一人識之,唯有杰公能辨其物,令在座之人嘆服;被譽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的北魏使者崔敏與督公談論三教之理,督公所學無所不窺,辯才敏捷,崔敏為督公所沮,后竟病死。傳奇中以杰公之事最詳、博物之質最明。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對扶桑、拂林、炎洲、漆海等地各處風土物產了然于胸,梁朝君臣將信將疑,“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為誑妄”。扶桑使者至梁,杰公“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識別“赍火浣布三端”原料差異,道出胡商之玻黎鏡乃色界天王之寶,異域方物與杰公之言一一印證。《五色石》中又記載杰公能識上界化生龍之石,告帝命人琢之為甌,以盛御膳,其食香美殊常;《震澤洞》中,又述杰公能夠預知龍宮藏寶機密,制作制龍石遣人至龍宮取寶,辨別珠寶特性。
可見,四公不以商山四皓“道濟天下之溺”的儒家理想為念,相反,他們對異域方物、卜筮神異之事頗為關注,也不以朝廷“拊掌笑謔,以為誑妄”[17]的輕視態度為意,反以掌握特異之才而獨拔于士人之上,自處于世。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認為《梁四公記》“雖然偶然涉及儒釋道三教,但主導思想已然是道教思想,卜筮釋卦、陳述方外遐域所貢奇珍異寶的特性,或派人到龍宮取回珠寶,基本上是道教文化的特性”[18]。誠然,在《梁四公記》中,四公并非以儒士著稱于世,反而擅占卜、熟知異域博物,四公的形象更接近于方術之士,而非儒士。就此反觀《梁四公記》的撰者問題,李宗為在《唐人傳奇》中對《梁四公記》的作者問題進行考辨,他根據陳振孫的論述,結合篇中關于占卜釋老、輕視朝中儒生的內容,進而判斷此書是高宗時期臨淄的方士田通所撰,盛唐后又為方士附會張說以此抬高身價,但因顧況距張說年代相近,所記較為可信,姑且署名張說撰[4]。結合四公特擅博物、精通神異的特征來看,此論有其合理性,就現存文獻記載來看,顧況的《戴氏〈廣異記〉序》亦有其真實性。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中進一步對《梁四公記》的著者問題進行考辨,根據《戴氏〈廣異記〉序》,李劍國認為確為張說撰無疑,至于題“田通、梁載言云云,疑乃張說故弄狡獪,正猶李公佐之撰《古岳瀆經》然;若張言不誣,則系張說得田通舊文而重加潤色以行世。俗人不察,見卷末有梁載言,遂定為梁作。”[6]146李劍國之論調和二說,尤為允當,不妨將《梁四公記》視為張說得田通舊文而重加潤色以行世之作,反映了博物尚奇的創作觀念。
《梁四公記》投射在梁代的現實之上,其中涉及的人物及事件都與此時相關。如傳奇中言及的盤盤國、丹丹國、扶昌國、高昌國遣使獻方物等事件,在《梁書·諸夷列傳》中皆有記載。盤盤國“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19]789;丹丹國“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19]794;高昌國“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氍毹”[19]811。這也體現了傳奇或以梁武之盛托喻初唐之興,反映了傳奇作者以史為參照、力圖神異、崇尚博物的創作觀念。
四、結語
《梁四公記》以“商山四皓”為原型,旁征博引、志異尚奇,豐富了傳奇中人物與情節的完整性。雖然傳奇中關于人物形象的描寫仍然較為簡略,但仍可看出,梁四公在商山四皓這一典型形象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梁四公輔君之助的作用,凸顯了梁四公的博聞強識。“商山四皓”作為圣賢之人,實踐其“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儒家政治理想。梁四公與商山四皓同為世之高賢,商山四皓是典型的致君堯舜的儒者形象,而梁四公卻是在南朝方士盛行的現實基礎上進一步豐富的游方之士的形象。不同于兼濟天下的儒者,四公的形象與作用更傾向于精通術數的方士,寄托著一種美好的政治理想,也體現出唐代志人傳奇博物志奇、有意為之的創作觀念。作者對商山四皓形象與特性的重構,體現了作者的創作觀念并非以獨尊儒術、強調教化為主,而是以熟識異方、博物志異為尚的創作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