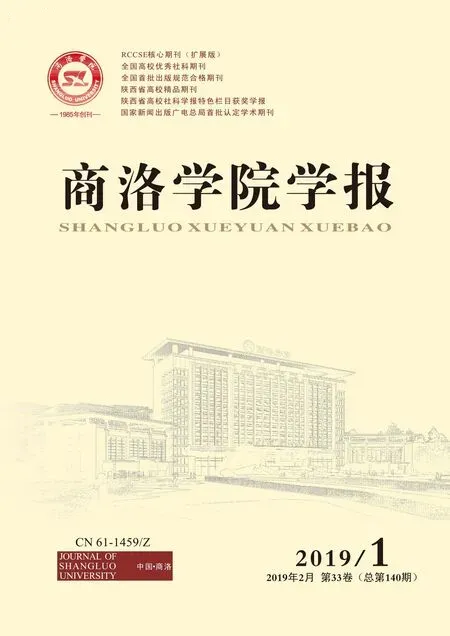徐大椿《洄溪道情》研究
武明慧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西安 710119)
道情,是道教徒在宣傳教義和募齋化緣時所演唱的一種含有特殊意義的道歌,言辭淺白、通俗易懂,后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用漁鼓和簡板伴奏,集抒情、敘事為一體的民間說唱。道情最遲在南宋時期形成,至元代發展大盛。清代道情發展受到時調小曲挑戰,生命力下降。鄭振鐸[1]認為,清代道情衰微,當時有三位作家扭轉了這個局面,激起了道情的復興。這三位便是“復活了這個體裁”的鄭燮、徐大椿和金農。
當前學界對徐大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醫學成就方面,徐氏的文學成就尚未引起關注,研究成果寥寥。僅有的幾篇針對《洄溪道情》的研究論文,主要探討的是其思想內容。陳泳超[2]重點論述了徐大椿以道情為詩文的追求及對以生活感慨入詩的表現;車振華[3]則認為《洄溪道情》不僅擴大了道情的題材,更是以儒家警世教化思想為主,半為警世之談,半寫閑游之樂;鐘微等[4]認為《洄溪道情》中除古來多見的醒世游閑之作外,還增添諷諫時事、悼亡親友、恭賀贈送、游覽書畫等大量內容,實為半儒半道之作。此外,黃瑩[5]從戲劇戲曲的角度,對徐大椿的曲學生涯、曲論思路和制曲追求進行了整體觀照。本文旨在分析《洄溪道情》在曲調、題材和內容方面對以往道情的繼承與發展,在比較中明確其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的價值和地位。
一、徐大椿與《洄溪道情》的創制
文學創作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道情發展亦如此。如果說元朝的統治為道情發展提供了寬松的創作環境,那么清朝則恰好相反。為清除異類,清朝統治者極力干預曲詞的創作和演唱,從作曲到唱曲,甚至對民眾聽曲也嚴查力堵,這直接造成了清初散曲的式微。至清中葉,道情發展情況稍有好轉,徐大椿、鄭燮、金農三人交相輝映,為道情發展史上一道鮮活亮麗的風景線。
(一)《洄溪道情》與徐大椿的家學淵源
徐大椿,字靈胎,初名大椿,后更名為大業,自號洄溪,江蘇吳江松陵鎮人。徐大椿是一位醫文俱通的大家。他性情通敏、喜善豪辯,天文地理、周樂古音、星經地志等無一不通,曾考取秀才入太學,后常往來于吳淞、震澤等地,行醫濟世。徐大椿最為人稱道的是他一身無人可比的醫術,《清史稿》中就載有其多部醫稿。作為醫者,徐大椿主要以醫學典籍聞名四里;作為曲學家,主要以《樂府傳聲》著稱于世。《洄溪道情》是他唯一遺留的文學作品,體現了其精妙的曲學才情。
《洄溪道情》最早的版本為乾隆十三年(1748)豐草亭原刻本,附于《樂府傳聲》之后,此版本的內容不甚完整,只有現今流傳的前14首,多為警世之談與閑游之樂。道光四年(1824),大椿孫徐培重刻乃祖《樂府傳聲》《洄溪道情》,在內容上多出了慶吊贈別類作品。任中敏《曲諧》所錄《洄溪道情》,共有“自序”一篇并道情39首。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和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皆言《洄溪道情》共38首,但未列細目,詳情不得而知。
按徐大椿所言,《洄溪道情》所作“半為警世之談,半寫閑游之樂”。前者指第1首至第9首,即《勸孝歌》《勸葬親》《勸爭產》《讀書樂》《戒酒歌》《戒賭博》《時光嘆》《時文嘆》《行醫嘆》;后者指第10首至第14首,即《邱園樂》《隱居樂》《泛舟樂》《游山樂》《田家樂》5首。這14首為道情本格,不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均與道情一脈相承。從第15首起,全為題畫酬贈、祭吊、壽文之類,大大擴展了道情的內容范圍,真正體現了徐氏道情的文學史意義。
徐大椿出生于書香望族。曾祖父為好學之士,學識廣博,見聞豐富。祖父徐釚是清初著名的詞人和詞論家,徐大椿最早接觸曲學即來自于祖父的影響。徐釚一生交游半天下,以文字交結四方之士,與朱彝尊、潘耒、尤侗等人關系親厚,因而徐大椿在年少時就結識了許多文壇大家。通過學習交流,大椿對曲學樂音有了自己的獨特見識,并開始創作道情。正是由于對聲樂的熟悉,徐大椿對古樂的遺失深表遺憾,決意推本求源,作道情以恢復古樂。
如果說祖父對徐大椿創作的影響在于曲體和聲腔方面的話,那么母親對他的影響則重點體現在創作內容上。徐母丁氏天資聰穎,學識豐富,文采斐然,文化素養甚高。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徐大椿對周樂唐詩非常了解,對人情世故有著獨到的見識,對母親也應當有著極大的恭敬與尊重,所以他的娛親詩中有眾多古詩名篇,并闡明了自己創作的直接原因——娛母。
我曾為娛我哀,譜得周樂唐詩入管弦。先慈年高目瞽,無以為歡。因將《關雎》《鹿鳴》等篇及唐人名句,按宮定譜,令童吹唱,以娛晚境。[6]7
與普通勞動婦女不同,徐母博學多才,平日除操持家中事務以外,還常幫助親朋四鄰解決日常瑣事,勸勉教誨他人。徐母常借詞曲誨人、醒悟人心,不論是非爭執還是家庭紛爭,都能合理處置,其詞曲動人,以至有人流淚深悔。這種以詞誨人的方式,近似道情說道勸世的意味。此外,徐母還常以韻語入詞,詞句中滿含其深沉熾熱的情感,更以變調入譜,這種勸說方式對徐大椿道情的創新意識有著直接的影響。
(二)《洄溪道情》的創作觀念
1.展現世情
《洄溪道情》多寫警世之談與閑游之樂,加以慶吊贈別類作品。徐大椿因家庭環境受儒家文化影響頗深,始終堅持儒家濟世救人的原則,不僅在行醫時身體力行,而且在文化精神上也毫不退縮,雖不走功名入仕之路,但濟世之心未泯。有感于當時的社會風氣,大椿鄙薄時文,常沉浸在經學之中,多以儒家的道德教育和處世之道入詩,淺處立說,用俚俗的語言表現世情。
儒家強調五倫,重視道德教養,徐大椿也在作品中勸勉世人重視孝親。整部作品以《勸孝歌》開篇,告誡世人要關愛、侍奉父母,以孝為先。儒家倫理體系中“悌”緊隨“孝”后,兄弟間相處應和睦友好,所以作品繼以《勸爭產》,強調兄弟間應和睦友好,雖是道德說教,卻不流于空洞:“爭天地,終日喧。錦江山,不要錢;人生何苦把家園戀。”[6]2這并非枯燥乏味的倫理解說,而是以人情度之,不顯得刻板。此外,許多人一生汲汲名利,終日企盼入仕做官,期望通過科舉考試飛黃騰達,做人上人。八股取士發展到清代,弊端日益暴露,嚴重禁錮了文人才情,眾多文人起而攻之。徐大椿更是在道情中揭露了這一現實,嘆惋時文對文人身心的毒害。雖然他的《時文嘆》流傳不廣,但用語淺顯生動,常被當時文人借用:“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似泥。”[6]4面對這種情形,徐大椿表示,對每個個體而言,人生不過百年,倏忽一瞬,要戒賭、戒酒,升華自身;人生應當盡力追求快樂,拋卻煩惱、算計,萬勿留戀身外之物。
徐大椿關注社會現實和人生百態,作品全力表現世情,上至儒家倫理,下至隱居閑游,涵蓋世間百事,包羅萬象,為道情的發展帶來了新的風貌。
2.自比狂生
文章是個人性情的最好觀照。“狂”是徐大椿作品中頻繁出現的一個字,他也用這個字來概括自己的個性。徐大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人,其祖父徐釚“少穎悟絕人”,非常人可比,而徐大椿雖不似祖父般天性聰穎,卻性情狂放、豪宕不拘,其特立獨行的任情狂傲之氣與祖父一脈相承。
在行醫中,徐大椿膽識過人,讓許多醫家束手無策的疑難雜癥他都敢于開具藥方,并對自己的藥方充滿自信。遇到懷疑處方、不敢喝藥的病人,徐大椿以強逼迫,并提前聲明,若有差池,傷則贍養一生,死則甘愿抵命,近乎狂醫。如果不是對自己的醫術有著極大的把握,沒人敢說出這種話來。高明的醫術為徐大椿提供了狂傲的資本,醫術上的“狂”又被他帶到文學之中:
君賦性端凝,篤誠謹懿,我天生頑魯,狂放粗豪。(《祭顧碧筠》)[6]17
況我半世相隨,一朝永訣,落落狂生。(《吊何小山先生》)[6]15
又怕人笑我狂縱,只得向靈前默誦,灑淚滿西風。(《祭潘文虎先生》)[6]14
這種“落落狂生”的性格伴隨了徐大椿的一生。其實,縱觀徐大椿作品及生平瑣事,他很少有極放縱的行為,“事親孝,與人忠”,見義必為,很是厚道,親朋好友也甚少有人說他狂放,在知音面前更是謙遜有禮。作品中徐大椿不止一次自我貶低,他將自己比“樸魯寒儒”“樗材散棄”,在《哭沈果堂先生》中更稱自己為“野馬”,因此我們可以猜測,徐大椿之所以用“狂生”這個詞來評價自己,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嘲。他想濟世安身,但現實卻不給他這個機會,自己孤身一人,無力改變,所以他探研易理,信奉道教,樂在其中,樂于放任自己的這一個性。
徐大椿把自身這種狂傲的性格全面細致地融入了作品中,他是頑者狂生,又是不得意的失落者,在寫作道情時,唯心而作,任心盡興。
二、《洄溪道情》對傳統道情的繼承與創新
道情有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然而一旦進入世俗視野,它卻會開辟出一片更加廣闊的天地。文人們汲取道家清虛無為的思想,不斷地進行道情創作,表達自己的出世情懷。明清時期,道教世俗化進程日益加劇,寫作道情的文人也逐漸增多,道情慢慢脫離道教思想的藩籬,越來越向世俗的思想情趣傾斜。
(一)《洄溪道情》對傳統道情思想的繼承
1.避世思想
自古以來,文人士大夫始終面臨艱難的仕與隱的選擇問題——是通過科舉居廟堂之高?還是退居山林處江湖之遠?古往今來,企圖科舉入仕、功成名就者有之,渴望隱逸山林、幽居閑適者亦有之。受傳統道教和中國隱逸文化的影響,絕大多數文人在自身創作時都對避世思想有所推崇。
散曲文學“其精神構成的軸心是避世思想和玩世哲學”,“而前者則又是后者的前提和內核”[7]。與散曲類似,道情也多以隱居閑適等為主題,有著濃厚的避世觀念,不論是道情還是散曲,避世一直都是其表現的重要主題。
大椿的祖父徐釚生值明清易代,他和多數前朝遺老一樣拒絕與新王朝合作。后來康熙帝為安撫和網羅各地文人學子,召試鴻博,徐釚無奈入征,但最終辭官隱退。徐父養浩同樣選擇隱居,終生不仕。這種避世家風深深地影響了徐大椿,他出身于這樣一個隱士門第,不愿上京應試求官也是極自然的事,因此他不滿科舉制度,厭棄時文,渴望歸居田園,觀江山滄海、駕輕舟遠帆。他在《洄溪道情》本格后五首中有著強烈的表達,在其中構造了一個無憂無慮、無榮無辱、瀟灑放達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有“朝來不怕晨雞喚,直睡到紅日三竿”(《邱園樂》)[6]7的瀟灑之人,也有“東西往來無拘系,琴書寶玩憑緣寄”(《泛舟樂》)[6]21的泛舟隱者,更有“到山中,便是仙,萬樹松風,百道飛泉”(《游山樂》)[6]6;在這個世界里,每個人不但可以“繩床鋪草,土壁涂泥……筍皮為帽,荷葉裁衣”(《隱居樂》)[6]15,亦可以“買碎魚一碗,挑野菜幾般,暖出三壺白酒,吃到夜靜更闌”(《邱園樂》)[6]7。在這里,徐大椿向往的是禪宗世界里所呈現出的幽靜,悠然自得,不需考慮俗塵雜事,逍遙適性,那里沒有神仙皇帝,沒有宮苑亭臺,不必爭名奪利,不必勾心斗角。與傳統佛道勸誡說理不同,在徐大椿的筆下,這種自給自足、淡泊寡欲的日子才是人人應當艷羨的生活。這種思想融入大椿心境,讓他自然以老莊哲學為核心,融和儒釋思想,進而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特質。
“清風吹我塵心斷。不知今夕是何年。遙望著牧豎樵夫洗足清泉。與他言,竟不曉得唐宋明元。”(《游山樂》)[6]6此作風格與《桃花源記》相似。其《田家樂》又與陶淵明的農家之樂相仿,風格迥似《歸去來兮辭》:
一頃良田,十畝桑園。兩只耕牛,一對農船。柳杏桃梅,籬間岸間。雞犬豬羊,欄邊樹邊。看了蠶收起絲綿,穿得來花樣鮮,渾身軟。過了黃梅把青苗插遍,到得那稻花香日,又正是明月團圓。收成好,滿場米谷,柴草接連天。手擁著爐,背負著暄,抱女呼男,擦背挨肩。宰一只雞肥,捉幾個魚鮮,白米飯如霜似雪,吃得來喜地歡天。完糧日到城中買一面逢逢社鼓,只等賀新年。[6]6
篇首幾個量詞的使用簡單直觀,自然超塵,淳美平淡散逸在字里行間。田家土地平坦,房屋整齊,良田桑園美景如畫,村落里雞犬相聞,人們養蠶插秧耕種勞作,閑情靜怡。被桃柳環繞的農家小院更令人如癡如醉,一絲愜意的美妙不由從心底升起,月隱陽來,又一次叩開美好之門,尋到了樹叢里素凈的一枝花,看見了白云飄曳的一份閑,抱香而舞,擁靜而眠。這里的每個人都成了有著清夢而無憂的人,穿行在其間,這種生活仿佛可以超越人間所有黑暗和苦難。
《洄溪道情》里反映的避世思想承繼了傳統文學中的離塵絕俗,構建了自身避世的精神內核,把嘆世隱居與樂道慕仙融為一體,作品雖有發展,但依舊延續了傳統道情的避世思想。
2.警世思想
古人常借寫作抒發內心情懷,唯心發聲,嬉笑怒罵等不平之音皆在文章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諷刺的手法多被用于感時傷世之作,一旦宣泄,常使人醍醐灌頂。古人的罵世手段高超絕倫,又頗為講究藝術表現,所以他們的警世之文往往如敲醒靈魂的黃鐘大呂,振聾發聵。
《洄溪道情》中有不少警世之作,具體表現的是以儒家傳統觀念為核心的道德教育和處世之道。任中敏認為此類道情“非等閑俚唱可比,自足另成一派[8]29。”
徐大椿在《洄溪道情·序》中直接指出警世之談是他創作道情的宗旨之一,他把“警世之談”納入題材范圍,始終用現實的眼光觀察世界,立意也多針砭時弊,《時文嘆》為其典型代表。明清時期痛斥八股時文和科舉取士弊端的作品很多,但都重在說理,較為雅馴,徐大椿的作品則以淺顯通俗、明白曉暢的語言開頭,全是嘲罵,尖酸刻薄,嚴厲地抨擊了科舉取士的社會現實,整首作品完全表達了作者胸中不可抑制的憤世嫉俗之情:“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似泥,國家本為求賢計,誰知變了欺人技。看了半部講章,記了三十擬題,狀元塞在荷包里。”[6]4由于對經世致用思想的偏愛,徐大椿鄙棄這種模式化、規范化的時文,運用正反對比的手法,揭露了才不如銀的社會現實,語言明白曉暢。這篇作品也因此受到很多文人的喜歡,此后多部詩人作品集中均有收錄。
除不滿朝廷科舉外,徐大椿還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市井民間,百姓的言行舉止、醫者農人的一舉一動都成為了他批評指正的對象。如《勸孝歌》:“你想身從何來?即使捐生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作者用“欠債還錢”比喻行孝,這種說法相較于儒家宣揚的“五倫”而言不可謂“不孝”,但卻正是這種直指實情的敢想敢說,讓他的作品充滿浩然之氣,給人當頭棒喝。
警世之作一般都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徐大椿更是將其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警世道情諧謔辛辣,反諷嘲弄,篇篇氣脈相通,一氣呵成。《戒酒歌》張口便罵:“造酒的是魔君,把米麥高粱,爛做了這樣醃羶醞!”更在其中快言快語地明確指明:“敬親朋必灌死方為快,爭意氣便醉殺也無論。”對喝酒、敬酒、灌酒等行為語帶嘲弄,譏誚直諷,鞭辟入里。更有《行醫嘆》對世人學醫應當保持本心進行警示勸諫:
嘆無聊,便學醫。唉!人命關天,此事難知。救人心,作不得謀生計。不讀方書半卷,只記藥味幾枚。無論臌膈風勞,傷寒瘧痢,一般的望聞問切,說是談非。要入世投機,只打聽近日行醫。相得是何方何味,試一試偶爾得效,倒覺稀奇。試得不靈,更弄得無主意。若還死了,只說道藥不錯,病難醫。絕多少單男獨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折多少少壯夫妻。不但分毫無罪,還要藥本酬儀。問你居心何忍!王法雖不及,天理實難欺!若果有救世真心,還望你讀書明理。做不來,寧可改業營生,免得陰誅冥擊![6]18
3.勸世思想
明清鼎革之際,社會動蕩不安,人心混亂,禮教松弛,很多有志于匡正風俗的文士開始大量寫作道情,宣揚勸善思想,明白曉暢,娓娓道來。清代范祖述在《杭俗遺風》中記載當時杭州的情形:“道情以漁鼓簡板為用,所唱多勸世文。大家小戶多不興,惟街書有之。”[9]雖然此處說的是杭州地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情在民間傳播的特點和內容。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影響,中國社會自古重視倫理教育,“孝”在家庭倫理中更是居于首要地位。徐大椿創作道情時勸“孝”必不可少,他在開篇《勸孝歌》中就大力宣揚孝道倫理:
五倫中,孝最先。兩個爹娘,又是殘年。便百順千依,也容易周旋,為甚不好好地隨他愿!譬如你詐人的財物,到來生也要做豬變犬。你想身從何來?即使捐生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哪里有動不動將他變面!你道他做事糊涂,說話欹偏,要曉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個嬰年,定然是顛顛倒倒,倒倒顛顛。想當初你也將哭作笑,將笑作哭,做爹娘的為甚不把你輕拋輕賤?也只為愛極生憐,到今朝換你個千埋百怨。想到其間,便鐵石肝腸,怕你不心回意轉![6]4
在這里,徐大椿仿佛是一位鄰家老者,用簡單明了的語言苦口婆心地對世人進行勸說。他指出,孝道的基本內涵是“親親”,就是對父母養、順、敬。作品以“孝”開始,從人的性情講開,嬰童顛顛倒倒、將哭作笑,青年人從嬰年度過,而老人的性情又回到嬰年,全文以佛家輪回思想警世,敦促大眾以孝親為先,淺處立說,勸勉世人。
徐大椿認為“孝”不止體現在子輩對父輩的敬愛侍奉,還表現在能夠讓逝去的親人入土為安,其《勸葬親》云:“勸世人只須得省衣節食,早早的送你爹娘入土,這就是造福之門。”葬親類作品難以表現,一般少有人作,大椿卻毫無顧忌,大力勸勉世人不能聽信風水先生一派胡言,不僅要“孝”生者,更要“孝”逝者,惟有此行為之人方能受到社會尊重,才不失為君子。
此外,徐大椿的勸世思想還體現在其更強調自我的人生升華方面,要戒賭、戒酒、戒爭產。他認為人生不長久,賭博嗜酒、煩惱算計都是對人生的荒廢,錦繡乾坤就在自然之間,美與藝術就蘊藏在日常之中,人生不是一味的行樂。《時光嘆》就勸人珍視光陰,少些算計:“勸世人且快活幾時饒人一步,不要等那鐘鳴漏盡懊悔凄惶。”[6]8
勸世道情的創作主要源于“勸善”觀念,明清時期的勸善運動把它推向高潮。明清時代的文人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變動,陸續思考保持社會穩定的問題,以扶世教、救頹俗為己任,他們的創作繼承了勸世思想,并貫穿其中,成為清代道情創作的一個重要思想。
(二)《洄溪道情》對傳統道情的創新
徐大椿用道情代替傳統詩文,把它作為自己的專用體裁,勸世警俗、酬贈知音,從俗通雅。正是在這種致用的雅俗之間,道情曲體迎來新變,題材得到極大發展,為文人創作道情提供了成熟的范式,具有深刻的典范意義。
1.成曲調之一家
道情一般由曲調和詞兩部分構成,可做表演彈唱,然發展至清代曲音大多失傳,往往有詞無聲。在清代道情的諸多創作者中,徐大椿創作的道情最具特色,他不僅關注道情辭的發展,更致力于探本窮流,恢復道情曲音。《道情序》直接表現了徐氏重視曲調的觀念:
以聲布辭,以詞發聲,悉一心之神理,遙接古人已墜之緒。若古人果如此,則此音自我續之;若古人不如此,則此音自我創之。無論其續與創,要之,律呂順,宮商協,絲竹和,可以適志,可以動人,即成曲調之一家。[10]521由此可知徐大椿以“遙接古人已墜之緒”為己任,寫作道情時本著承繼古音、協調宮商的態度,無拘無束地試驗著創作出一種自由的新詩體。
徐大椿受家世影響,曲學素養很高,對道情之曲始終有著濃厚的興趣。正是由于對聲樂的熟悉,徐大椿對“聲”有著獨特的認識,把它看作曲體之至高至妙者,并認為古人之音多有失傳,而道情曲已完全斷絕。他感慨于古樂的遺失,因而推本求源,改造北曲仙呂入雙調并推廣其音,采用道情古調表現曲情,這也成為他創作《洄溪道情》的曲論基礎。
明清時期,文人士大夫對傳統小道并不重視,僅有南曲比較盛行,徐大椿卻把北曲作為樂道典范,極力推崇。徐大椿認為,宮調從古人分宮立調開始就有了固定的模式,即使失傳,但只要依循舊例,按照已有的規律稍加變通,就可以重新恢復。宮調是從古至今音樂藝術發展因素中變化較少的一類,不同的宮調有不同的風格,黃鐘調唱情時富貴纏綿,南呂調唱情則感嘆悲傷。《洄溪道情》以仙呂宮和雙調入詞,根據《中原音韻》和《太和正音譜·詞林須知》可知,仙呂宮清新綿邈,雙調健捷激裊。現在雖然無法確定徐大椿具體使用的是哪些曲牌,但就文字部分看,作品多道情本色語,通俗質樸,明白曉暢,兩種宮調里蘊含的曲情明顯對應《洄溪道情》里的內容。
除此之外,對于曲的創作,徐大椿也做出了相應發展,反復要求能夠感動人心,強調自身對道情的創作非知音不作。其《壽沈井南》云:
自余廣道情之體,一切詩文,悉以道情代之。然構此頗不易,必情境音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故非知音不作。[6]10
傳統作者作曲時均按詞譜曲,但大椿卻另辟蹊徑,因曲填詞。他認為對道情內容的強調是其次的,而道情之音最為絕妙,詞起輔助作用,只是為了讓大眾深入理解曲所傳達的意蘊才需要填詞。因而《洄溪道情》的序言中幾乎沒有“詞”的出現。大椿強調曲音的重要,完全是為了推動道情的發展。道情以漁鼓、簡板固定節奏,北曲襯字較多,演奏時為完美承接只設置了底板,不似南曲曲牌有固定的格式,可使道情曲調自由變化,達到“聲境一開,愈轉而愈不窮”[10]521的效果。
遺憾的是,徐大椿在聲樂上的創新改造雖然展現了其獨樹一幟的曲學才華,但《洄溪道情》中他最為得意的曲調卻僅僅剩下不可歌的文字,而他對古樂的恢復也一定程度上將道情禁錮在了文人的案頭,這或許也是他的道情并未在民間得到得到發展的原因。
2.顯微曲折,無所不暢
徐大椿的道情不僅在聲腔音律方面做出了創新,而且對文本的內容與形式都有一定的發展。《洄溪道情》中除去“警示之談”和“閑游之樂”,其余幾乎所有題材都用道情來寫。題畫、酬贈、憑吊、祭文、壽文等用詩文來寫難度不大,只要做到整飭嚴密、端莊謹肅就可以了,但若用道情就需要寫出其絕塵脫俗的“道氣”。因而在傳統文學中并沒有人選擇用道情來寫作此類作品。徐大椿自己曾在《吊何小山先生》中說:“凡哀死祭吊之作,自《離騷》、四言而外,一切詩詞歌曲,無體不全,而獨無道情。”[6]15他對自己能夠拓寬道情題材應當也是感到頗為自豪的。
徐大椿結合儒家仁義與道家無為,以道教的教理教義及理想境界入詩,洋洋灑灑,竭力表現道家的逍遙灑脫,表達了自身對現實社會的憤懣以及對理想世界的向往,具有獨特浪漫的中國古典美學思想傾向。
相對道情本格的作品,大椿道情中的慶吊、贈別、題畫、壽文、祭文作品可以說是徐大椿在內容上的創新。與莊子一樣,大椿對親人離世表現得十分曠達,在三子燝亡故后他不像世人那樣悲痛嚎哭,而是只惋惜自己失去了一位青年道友:“恨只恨,又失了一個青年道友,教誰人伴我度殘生?”(《哭亡三子燝》)[6]15或許是因為清代統治者對文學創作控制嚴密,稍有不慎就會得罪,造成許多作者在創作中不敢面對現實,所以才用題畫酬贈等形式,如此可信馬由韁,比較自由,以致這種“借題發揮”在當時形成一種風尚。這些題畫、祭文等作品用道情難以表達,向來少有人作,但徐大椿卻巧妙地為其注入了一絲“道氣”:
只愿得天公憐我,放我在閑田地,享用些閑滋味,直閑到東溟水淺,西山石爛,南極星移。 (《六十自壽》)[6]11
莫笑我逍遙閑散,也只為百歲光陰有限。你不要鋤熟了亡經佚史,拋荒了越水吳山。 (《贈曹慈山》)[6]8
道情本格作品中表現的說教勸世意味明顯,但慶吊、贈別類作品所表現的“道氣”也不遑多讓,蘊含著深厚的中國古典美學思想。大椿認為,道情的“道氣”除了音詞情境之外,更要加入自身性情,以及與親朋好友相識相知的情感,所以在作品中常會看到多具有道家色彩的人物:有最愛清幽、鶴發朱顏的席士俊;有溫文爾雅、敬友謙恭的丁三母舅;有年已七十,仍赤子情腸的老友更有逍遙散仙……這些人簡單純真、品格高潔,身心不為外物所累,追求逍遙灑脫,似欲乘長風的道者。徐大椿周圍不僅有心憂天下的白衣方又將,不畏權貴、一心為民的顧碧筠,讀書不為功名的何寓庸,博古通今、學富五車的沈果堂;還有以古樂唐詩侑酒的陳圣泉,禮樂宗師禽味經,品望清隆的蔣迪甫,皓首窮經的曹慈山,崇經復古的韓云開,善于品鑒的何小山……這些本應為記人記事的文章,大椿卻把他們全入于道情,或作書畫題贈,或作壽文、祭文。這類作品在大椿《洄溪道情》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按創作時間來看,徐大椿1743年在寫作道情本格時,已經創作《題翁霽堂三十三山堂圖》和《壽韓開云先生九十》,足見其在道情創作之始就產生了創新意識。
3.句式自由不受限
除在內容方面有所創新外,徐大椿在道情曲的形式上也作出了一定創新。《洄溪道情》曲多者五十余句,少者只有十余句,短有三字,長有十余字,平仄運用也無太大講究。徐大椿主張不論是何種體裁,每首曲子的創作都應擁有自身特有的結構句法,這種結構句法是不能隨意改變的,只有在不改變曲牌的前提下,作品字句多寡方可依時而變,自由不受限。
《洄溪道情》中道情本格的十四首形式上固定整齊、簡明清晰,大多作品以三、三句式起調,無有特殊;慶吊贈別類作品與道情本格略有不同,多以四字或五字起調,其中有十六篇以四字起,七篇以五字起,而有八篇以四、四、四、四起句。這種藝術風格明顯承繼古人所作,與《詩經》頗具相似之處。如《祭顧碧筠》“同林四鳥,飲啄相招。三鳥云逝,哀鳴嗷嗷”[6]17,不但借用了典故,還運用了“興”的藝術手法,以同林四鳥為喻,將自己、顧碧筠與何家兄弟比為離別之人,四鳥本形影不離,然意外失去同伴,鳥兒低飛哀鳴,輾轉徘徊,情感強烈而執著,四人之間的深情厚誼躍然紙上。此外,作品還多處運用典故,如“所其無逸,稼穡艱難”(《題山莊耕讀圖》)出自《尚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提籃采藥非他意,只為無糧代采薇”(《題何師之采藥圖》)典出《詩經·采薇》。
大椿的道情基本如此:雖為單支小曲,篇幅較小令稍長,文辭質樸,淺顯明暢,多諭人以理,廣泛流傳于小家庭院和茶樓酒肆之中。
徐大椿利用自身不可多得的曲學才情在道情創作中擴大了道情題材,“完全擺脫詞曲的形式和規律,在試驗著一種新詩體。”[11]題畫酬贈類道情作品在元、明兩代罕見,清代以徐大椿為代表發展空前繁榮,文辭顯微曲折、無所不暢、通俗真切,聲韻流蕩生動,毫無故作典雅之弊。任中敏在《散曲概論》中說:“今世但知鄭板橋有其詞,而不知徐靈胎實定其制。”[8]345趙義山更是認為道情“可惜靈胎謚后,再無人繼其絕響。”[12]
三、結語
道情發展至清代由徐大椿發揚光大,地位幾乎可與詩詞爭席。作為一名曲學家,徐大椿幼年時期便受到祖父和母親的極大影響,深厚的家學淵源為他提供了思想基礎,使他的整個創作活動得以不斷展開,并完成了重要著作——《洄溪道情》。在道情創作中,徐大椿堅持展現市井風俗、人情天性,他情深氣盛,敢想敢言,常常自比狂生,同時繼承了以往文人創作道情的避世、警世和勸世思想,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創新。他擺脫了傳統道情詞曲的限制,對道情曲體探本窮流,在擴大傳統道情題材的同時,也為其形式發展帶來了新變。徐大椿常懷宗經法古之心,卻非處處創新求異,與板橋、金農諸人一起復活道情體裁,引領了清代道情的發展。從對后世的影響看,《洄溪道情》在道情史上的作用是開拓性的,它向人們展示了一部曲情獨特而又成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