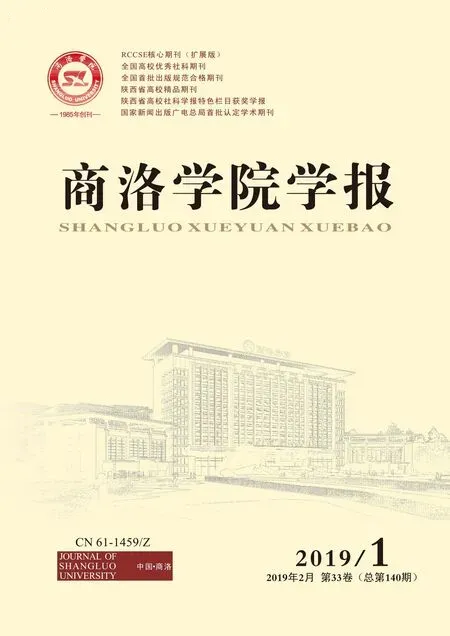論莫言小說(shuō)的“匪性”書(shū)寫
張衡
(華南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廣東廣州 510006)
在當(dāng)代文壇,莫言以獨(dú)特的眼光和奇絕的藝術(shù)手法講述著“高密東北鄉(xiāng)”土地上的風(fēng)云變幻,其小說(shuō)呈現(xiàn)的蓬勃不羈的“生命力”歷來(lái)頗為評(píng)論家所稱道。李陀在《讀〈紅高粱〉筆記》中指出,“《紅高粱》的內(nèi)核在于‘人格美’,文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一種生命活力的象征”[1]。陳墨將其界定成一種文化特色:“這是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的儒道墨佛或三綱五常的典籍文化的生命的歷史文化,是一種活的文化、活的中華民族史。是一種充滿悲劇而又生機(jī)勃勃的文化、充滿血腥也充滿愛(ài)的文化。”[2]楊守森將其抽象為是一種“宇宙精神”,認(rèn)為這是“人類由宇宙萬(wàn)物體悟到的一種超驗(yàn)力量與規(guī)則”,進(jìn)而喚醒人們的生命自由意志,張揚(yáng)生命活力,探尋生命價(jià)值[3]。由此可見(jiàn),無(wú)比旺盛的“生命力”構(gòu)成了莫言小說(shuō)的獨(dú)特姿態(tài),透過(guò)“生命力”,作家表現(xiàn)出卓爾不群的“匪性”氣質(zhì)——原始的野性與不羈雜糅,生命的躁動(dòng)與昂揚(yáng)皆具,打破了1949年以來(lái)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模式化、單一化的沉悶狀態(tài)。這既是“匪性”因子的外在呈現(xiàn),也是其作品生生不息,煥發(fā)迷人魅力的根源所在。本文以“匪性書(shū)寫”的視角切入莫言的小說(shuō),重思何為“匪性”?“匪性”因子如何在作品中得以噴發(fā)?不僅嘗試對(duì)小說(shuō)呈現(xiàn)的“匪性生命力”提出自己的見(jiàn)解,并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莫言作品,在具體分析“匪性”在其小說(shuō)中的表現(xiàn)、特質(zhì)及成因之后,重點(diǎn)歸納“匪性”的特質(zhì)下莫言小說(shuō)呈現(xiàn)出的當(dāng)代意義和批判意識(shí),探討其作品對(duì)文學(xué)、對(duì)社會(huì)的重要意義。
一、由“匪”至“匪性”書(shū)寫
來(lái)源于民間文化的“匪性”力量,是莫言小說(shuō)主人公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作品野性魅力之所在。張清華認(rèn)為“在余占鰲身上,‘匪性’成為其人性和生命力的基本特征與必然表達(dá)。”[4]83“近年來(lái)出現(xiàn)的一些作品,往往以某些土匪或類似土匪的人物行為為描寫內(nèi)容,寫他們的一些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這類作品總稱為“匪行小說(shuō)”[4]83。同時(shí)指出:“‘匪行小說(shuō)’在新時(shí)期的產(chǎn)生基本上可以說(shuō)是從莫言1986年的《紅高粱家族》開(kāi)始的……所負(fù)載的文化意識(shí)、審美趣味具有特殊的意義與價(jià)值”[4]83。
作為中國(guó)社會(huì)文化中特殊群體的“匪”,一直是人們津津樂(lè)道的話題。“匪”在古漢語(yǔ)中與“非”字相通,現(xiàn)代漢語(yǔ)中指“破壞正常社會(huì)秩序、擾亂民生的行為”。在歷史資料中查找發(fā)現(xiàn),清代中期開(kāi)始正式將社會(huì)底層犯上作亂的民眾以“匪”相稱。近代以來(lái),軍閥混戰(zhàn),社會(huì)動(dòng)蕩,殘酷的征兵、苛稅政策加之自然災(zāi)害的盛行,使得破產(chǎn)農(nóng)民的數(shù)量與日俱增,無(wú)恒產(chǎn)亦無(wú)恒心,“匪”這一群體數(shù)量越發(fā)龐大。毛澤東在《中國(guó)社會(huì)各階級(jí)的分析》中將“匪”劃歸在游民及無(wú)產(chǎn)者一類,認(rèn)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5]8,“這一批人很能勇敢?jiàn)^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dǎo)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5]9聞一多《關(guān)于儒·道·土匪》借用韋爾斯的論斷:“大部分中國(guó)人的靈魂里,斗爭(zhēng)著一個(gè)儒家、一個(gè)道家、一個(gè)土匪”,指出:“但匪畢竟是中國(guó)文化的病”[6]。正如羅維在《百年文學(xué)之“匪”色想象》中所述:“匪文化是一種民間文化中的隱性文化,它讓幾千年的鄉(xiāng)村民間總是能在惡劣的生存境遇下毫不費(fèi)力地延續(xù)起這種為匪的古老方式。”[7]
“匪性”是民間氣質(zhì)的呈現(xiàn)。中國(guó)文學(xué)傳統(tǒng)中,與之相近的“盜”“俠”形象層出不窮,而“匪”的形象駁雜、難以一概而論。盡管同屬“流民”的身份類型,“匪”與“盜”截然不同。從字形來(lái)看“盜”是會(huì)意字,甲骨文指看到人家的器皿就會(huì)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本義是指盜竊、偷東西,多指用不正當(dāng)?shù)氖侄螤I(yíng)私或謀取。因此,“盜”身上更多是偷竊營(yíng)私的性質(zhì),而以江湖義氣為核心凝聚的匪眾呈現(xiàn)出軍事化、武力化的特征,并在團(tuán)體內(nèi)部形成自發(fā)自覺(jué)的“集團(tuán)規(guī)則”,殺人如麻但也嫉惡如仇,在民間故事的口耳相傳中更富傳奇色彩。也就是說(shuō),盡管二者都源于平民百姓,但“盜”是平民利益的侵害者與損毀者,“竊鉤者誅”正是官方和民間對(duì)其不能容忍的厲切懲罰;而“匪”盡管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但以“義”為核心的規(guī)則秩序,往往在危難關(guān)頭更同情平民利益,有較強(qiáng)的正義感和傳奇性。從仗義江湖的層面而言,“匪”更趨于“俠”。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mèng)》中考證,“俠”概念最早見(jiàn)于戰(zhàn)國(guó)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其形象最早見(jiàn)于先秦史家小說(shuō),到了《史記·游俠列傳》,“俠”的形象逐漸清晰鮮明。對(duì)其定性,采用梁羽生的話來(lái)說(shuō):“‘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dá)成‘俠’的手段。”[8]文人筆下“俠”的形象大多代表正義和智慧,武俠小說(shuō)盛行,使得“俠”浸潤(rùn)著神秘、浪漫氣息,成為通俗文學(xué)中經(jīng)久不衰的一大魅力群體。就文學(xué)形象而言,“俠”往往高于“匪”,因此,“俠”的身上更多浸淫了理想主義色彩,文人書(shū)生們將無(wú)力涉足的風(fēng)雨江湖交付給“俠”一展拳腳,將自身難以企及的理想與浪漫愛(ài)情一并寄托“俠”身上,這正是瞿秋白指稱現(xiàn)代文人為“高等游民”[9]的原因所在。同樣不甘困于主流秩序之“籠”,在與官方關(guān)系的選擇中,“俠”的立場(chǎng)縈繞著舉棋不定的曖昧色彩,時(shí)而對(duì)峙,時(shí)而依附,時(shí)而隱居山野,時(shí)而煊赫江湖,時(shí)而入朝為官,時(shí)而落草為寇……體現(xiàn)“俠”對(duì)于主流秩序既想掙脫、又不愿太掙脫的道德立場(chǎng),背后是文人猶疑不決、去留不定的矛盾心態(tài)。
文人將期待的輕狂不羈寄托俠客身上,農(nóng)民的堅(jiān)韌樸實(shí)、叛逆恣肆、義氣與團(tuán)結(jié),在被壓抑的年代里總要借力噴發(fā)。獨(dú)行為俠,聚眾為匪,所以匪更能代表民間的氣質(zhì)。莫言筆下的“匪性”書(shū)寫自八十年代“橫空出世”以來(lái),便以先鋒的姿態(tài)和自由獨(dú)立的精神自覺(jué)步入了“文學(xué)窄門”:首先是摒棄了傳統(tǒng)文學(xué)中對(duì)于土匪形象“丑惡化”的渲染,把土匪的個(gè)性氣質(zhì)寫得更回歸本土、貼近大地;其次,他將“土匪們”狂浪不羈、自由自在的蓬勃野性淋漓盡致地?fù)]灑開(kāi)來(lái),形象立體飽滿,充滿生命力;最重要的是“新一代”的“匪性”人物鮮明生動(dòng)、完全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俠”劃開(kāi)界限,充滿激進(jìn)昂揚(yáng)的現(xiàn)代主義精神。這一類的“匪”繼承了“盜”的叛逆勇猛、“俠”的義氣浪漫,又很好地回避了“盜”的陰暗面、“俠”的妥協(xié)性。他們敢作敢當(dāng)、無(wú)憂無(wú)懼,背后是桀驁不馴的個(gè)性、鮮明獨(dú)立的立場(chǎng),體現(xiàn)出直面現(xiàn)實(shí)、勇于對(duì)抗的勇氣。“匪”自身浸淫的民間氣息,加之神秘的傳奇色彩,因此其順利進(jìn)入文學(xué)作品是對(duì)一定歷史條件下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反應(yīng),也是民間文化對(duì)文學(xué)作品潛移默化的影響。關(guān)于“匪性文學(xué)”的界定,當(dāng)代作家尤鳳偉觀點(diǎn)獨(dú)到:“匪性文學(xué)的外延可以放開(kāi)些,除了落草為寇的正宗土匪外,還有在心情上與之極為靠近的鄉(xiāng)村浪人、無(wú)業(yè)游民、三教九流等,從廣義上都可以一起。也就是說(shuō)匪文學(xué)可以是表現(xiàn)具有匪性意識(shí)的人物的文學(xué)統(tǒng)稱。”[10]因此“匪性”是人性深處來(lái)源于鄉(xiāng)土大地的一種無(wú)拘無(wú)束、汪洋恣肆的生命狀態(tài),“匪性主人公”以“江湖道義”和“人性欲望”為核心,游走于社會(huì)邊緣,敢作敢當(dāng)、敢愛(ài)敢恨,囊括了不為主流秩序所容的兇殺暴力和放肆性愛(ài),既彰顯出悖逆的姿態(tài),又洋溢著獨(dú)立的野性氣質(zhì),象征著當(dāng)代文學(xué)中“人性”的振作與覺(jué)醒。
二、“食色交織”的“匪性”特質(zhì)
民間生機(jī)勃勃的姿態(tài),是自然野性力量的輻射,也給了作家更多的展示空間。“匪性”作為一種氣質(zhì),透過(guò)小說(shuō)中的生命意識(shí)體現(xiàn)出來(lái)。一如作家所言:“高密東北鄉(xiāng)無(wú)疑是世界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ài)的地方。”[11]2蒼茫大地,誰(shuí)主沉浮?廣袤無(wú)垠的北方大地,是莫言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根基所在,更是小說(shuō)中“匪性”特質(zhì)的來(lái)源。莫言本人不止一次強(qiáng)調(diào):“沒(méi)有永恒和寓意的小說(shuō)是清湯寡水”[12],因此小說(shuō)中的“匪性”特質(zhì)即通過(guò)反復(fù)呈現(xiàn)又歷久彌新的對(duì)于食、色兩大意象的書(shū)寫進(jìn)行演繹。
首先是作者以自述的手法和大量心理描寫,將特殊的饑餓年代里人們對(duì)食物的迫切渴求暴露無(wú)遺。《四十一炮》中的羅小通,做夢(mèng)都幻想著大快朵頤,只因沒(méi)吃上肉委屈到淚流滿面;《豐乳肥臀》里,母親在公社磨坊偷偷吞下豆子、回家后瘋狂“催吐”,借此為嗷嗷待哺的孩子們送來(lái)糧食;醫(yī)學(xué)院校花喬其莎為一口饅頭匍匐在地瘋狂吞食,不顧身后農(nóng)場(chǎng)廚師對(duì)她的霸占欺凌。縱觀莫言小說(shuō),眾多人物一生都在努力與“饑餓”斗爭(zhēng)。天災(zāi)、戰(zhàn)亂、苛稅……足以在紛亂流離的年代摧垮無(wú)數(shù)家庭,于是有了吃草、吃煤、吃鐵、吃母親吐出來(lái)的食物這殘酷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食物的渴求使人們蠻橫如匪,對(duì)饑荒的恐懼使得農(nóng)民走投無(wú)路、揭竿而起。
其次是頗具“匪性”特色的性描寫。這是莫言作品頗為評(píng)論家詬病的原因所在。孔子云:“食色,性也。”莫言肆無(wú)忌憚地將主人公的個(gè)性借酣暢淋漓的性愛(ài)揮灑出來(lái):《紅高粱家族》中,“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大膽野合,儒家的倫理道德被拋擲九霄云外。正如王德威所言:“我們聽(tīng)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dòng)地火,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xiǎn),于是浩然展開(kāi);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wú)不令人嘆為觀止。過(guò)去與未來(lái),欲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shuō)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fēng)景。”[13]小說(shuō)再現(xiàn)了鄉(xiāng)村世界的亂倫、野合、私奔、偷情,甚至以“白晝宣淫”的方式向禁欲的人倫道德宣戰(zhàn),借此展現(xiàn)出人性中不羈欲望的張揚(yáng),對(duì)于愛(ài)與性的大膽追求使得他們勇敢掙脫綱常禮教的藩籬,因不為人所齒所以更加堅(jiān)定地逆流而上、與世俗秩序劃清界限,性愛(ài)無(wú)疑是促成反叛的重要推力。
對(duì)于食與色的狂熱可看作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反映,莫言大肆?xí)鴮戰(zhàn)囸I,使得處于“缺位”狀態(tài)的主人公為滿足基本的生理愿望為之一搏,飽含對(duì)生的迫切渴求和更好生存的強(qiáng)烈希冀。值得玩味的是,小說(shuō)主人公一旦擺脫生理上的饑餓、饑渴狀態(tài),便開(kāi)始標(biāo)榜自己的身份、地位,成功之時(shí)沉溺于物質(zhì)享受。《豐乳肥臀》中大肆鋪張的幾場(chǎng)宴會(huì),無(wú)不是“酒池肉林”的“饕餮盛宴”。司馬庫(kù)與二姐的婚宴是奢華鋪張,一掃饑荒盛行的陰暗晦澀,食物種類不計(jì)其數(shù)、色香味的奇妙融合滿足了賓客們的食欲與想象力,這種豐盛照應(yīng)了小說(shuō)開(kāi)頭七姐妹隆冬捕魚(yú)的艱辛。從青黃不接到華庭盛宴,作家借助日常飲食控訴了日軍侵華戰(zhàn)爭(zhēng)帶給中國(guó)鄉(xiāng)土大地的創(chuàng)傷。上官金童出獄后社會(huì)日新月異,在獨(dú)乳老金、司馬糧那里,上官金童飄飄不知所然。芳香四溢、目不暇接的食物超出他畢生的想象,女人們主動(dòng)獻(xiàn)身更使他不知所措。至此,作家關(guān)于“食”“色”的想象與書(shū)寫在小說(shuō)中達(dá)到頂峰。貪婪享受過(guò)后,只留有靈魂深處的巨大空虛。從“不足”到“有余”再到“過(guò)剩”,是物質(zhì)層面的提升和滿足,同時(shí)也是由“人性”向“匪性”過(guò)渡的泛濫和頹傾。如果說(shuō)最初階段“食”與“色”的高度匱乏還飽含著對(duì)于和諧生命狀態(tài)以及物質(zhì)精神文明的迫切渴求,那么到了食物與情色的“泛濫成災(zāi)”之時(shí),精神文明的影子蕩然無(wú)存,垂涎三尺、滿嘴流油的丑態(tài)吞沒(méi)一切,過(guò)度的貪婪和饕餮使得“匪”脫離“人性”墮入“魔性”,看似流光溢彩的“食”“色”書(shū)寫恰恰鎖住了這點(diǎn),贊頌生命力,批駁劣根性。
食色的交織激發(fā)了他們內(nèi)心的力量與野性,在如此風(fēng)土人情的浸潤(rùn)下,蒼茫大地上一群群野性勃勃的“匪徒”得以涌現(xiàn)。
三、野性勃勃的“匪性人物”
卡西爾認(rèn)為:“理解人類的生命力乃是歷史知識(shí)的一般主題和最終目的”[14]。生命力所蘊(yùn)含的多種氣質(zhì)是吸引我們思考探索的方向所在。莫言在充滿傳奇色彩的書(shū)寫中,始終沒(méi)有離開(kāi)對(duì)野性勃勃“農(nóng)民式匪徒”人物的發(fā)掘,悖逆與義氣并存的復(fù)雜性格,質(zhì)樸與浪漫交織的“匪徒”氣質(zhì),旨在喚醒潛藏的叛逆精神與神秘力量。
1.英雄或浪子
中國(guó)小說(shuō)傳統(tǒng)自古就有英雄主義情結(jié)。“一時(shí)人物風(fēng)塵外,千古英雄草莽間”,諸多散發(fā)著濃濃“匪氣”的好漢形象長(zhǎng)于隴畝、扎根民間,是莫言作品格外吸引人心的原因之一。1986年《紅高粱》發(fā)表,“我爺爺余占鰲”的“橫空出世”引起文壇注目。對(duì)于男性生命力的挖掘與贊嘆,是新時(shí)期文學(xué)的初步探索嘗試,由此帶動(dòng)八九十年代土匪題材小說(shuō)書(shū)寫熱潮。盡管暴露人物缺點(diǎn)總是不留余力、“噴發(fā)式”的熱情書(shū)寫總是挾裹著夸大、渲染的嫌疑,但作為忠于故鄉(xiāng)這片熱土的“說(shuō)書(shū)人”,莫言始終懷抱著贊嘆和敬仰描繪野性勃勃的“匪首”。《紅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鰲十六歲殺死與母親通奸的和尚,為了愛(ài)情又先后殺死單扁郎父子和土匪頭子“花脖子”,而后滿懷家仇國(guó)恨率民間武裝伏擊日寇,在硝煙滾滾橫尸遍野的“高密東北鄉(xiāng)”當(dāng)上了“第一司令”。同樣勇敢的羅漢大爺,面對(duì)日寇活剝?nèi)似さ耐纯嗾勰ィ鎏扉L(zhǎng)嘯、怒罵不止。《豐乳肥臀》中叛逆狡猾、頑強(qiáng)反抗的司馬庫(kù),機(jī)智隱忍、流亡北海道深林十八年的鳥(niǎo)兒韓,《檀香刑》中遭遇極刑仍放聲高歌的孫丙,都是這類形象的代表。他們身上延續(xù)了《水滸傳》中英雄好漢生死無(wú)畏、血?dú)夥絼偟臑⒚摗M瑫r(shí),在災(zāi)難危機(jī)面前,忍辱負(fù)重、愛(ài)憎分明,面對(duì)外敵所展現(xiàn)的錚錚鐵骨和壯志豪情,反照中華民族不卑不亢的頑強(qiáng)抗?fàn)幘瘢诟吡坏乩镉蒙境纱髮懙摹叭恕弊帧?/p>
《高粱殯》中,莫言不吐不快地寫道:“復(fù)仇、反復(fù)仇、反反復(fù)仇,這條無(wú)窮循環(huán)的殘酷規(guī)律,把一個(gè)個(gè)善良懦弱的百姓變成了心黑手毒、藝高膽大的土匪……高密東北鄉(xiāng)的土匪種子綿綿不絕,官府制造土匪,貧困制造土匪,通奸情殺制造土匪,土匪制造土匪。”[11]259因此,“匪”——才是他力避重復(fù)、變幻多端的小說(shuō)作品中始終不變的主人公,他們正義凜然的氣質(zhì)引領(lǐng)著“高密東北鄉(xiāng)”的精神向度。與此同時(shí),另一類平凡卻不平庸小人物的“匪性”氣質(zhì)也貫穿小說(shuō)字里行間:《生死疲勞》中地主西門鬧不屈不撓,輾轉(zhuǎn)流離,歷盡六道輪回、生死疲勞,在滄桑巨變中,成為時(shí)代的見(jiàn)證者與倔強(qiáng)呼喊者;獨(dú)居村頭矮屋,夜晚奮力犁田的“單干戶”藍(lán)臉,用行動(dòng)堅(jiān)守理想;《天堂蒜薹之歌》中失明的民間藝人張扣,即使被打掉牙齒、口吐鮮血也堅(jiān)持用嘶啞的嗓音痛斥荒唐與不公,為命如草芥的農(nóng)民們?nèi)找垢杩蕖H绻f(shuō)以“我爺爺”、司馬庫(kù)為代表的第一類英雄是萬(wàn)眾敬仰、一呼百應(yīng)的,那么第二類洋溢著“匪性”氣質(zhì)、名不見(jiàn)經(jīng)傳的農(nóng)民則是蟄伏大地、無(wú)處不在的“地之子”,同樣用熱血和力量撐起叛逆與理想,倔強(qiáng)不服輸?shù)摹胺诵浴睔赓|(zhì)散落在每寸土地,生生不息。
英雄并非完美無(wú)缺。“高密東北鄉(xiāng)”的英雄,無(wú)一不是放蕩不羈、離經(jīng)叛道的浪子,無(wú)家或被迫離家,與原生家庭劃開(kāi)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英雄或浪子,均是“無(wú)父”狀態(tài)下的產(chǎn)物,“無(wú)父”就代表沒(méi)有倫理上的被縛,不囿于忠孝“枷鎖”,一往無(wú)前、無(wú)所畏懼。因?yàn)椤盁o(wú)父”,所以更加“無(wú)法無(wú)天”,沖破一切、重建一切的欲望極富沖擊力,呈現(xiàn)出打破一切的勇氣和占山為王的“匪氣”,加之行走江湖的義氣,小說(shuō)巧妙利用這種手段對(duì)舊秩序及父權(quán)神話進(jìn)行抗衡。高密東北鄉(xiāng)農(nóng)民們的“匪氣”與“野性”是源于泥土、扎根大地的,他們的“悖逆”之志著眼于現(xiàn)實(shí)生活,同時(shí)也依附著“大地之子”的民間道義和家國(guó)情懷。
在沒(méi)有英雄的年代,人們呼喚英雄。于是,在沈從文奮筆疾書(shū)湘西蠻性生命力的半世紀(jì)后,莫言又在孔武有力、義薄云天的山東好漢身上,寄托了心中的野性與力量。盡管“匪性”氣質(zhì)難免摻雜著魯莽暴力抑或登徒浪子的成分,但在秩序瓦解、世道紛亂的年代,他們用錚錚鐵骨奏響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莊重與偉岸。
2.圣母或蕩婦
在莫言小說(shuō)中,“土匪”形象不局限于男性,女性人物或多或少也存留著不顧一切、敢愛(ài)敢恨的精神。不同于以往作家書(shū)寫歷史時(shí)對(duì)女性人物的忽視,也不著力于對(duì)女性形象的一味謳歌,“圣母或蕩婦”這一錯(cuò)綜交織的女性形象,是莫言小說(shuō)的一大亮點(diǎn)。
莫言尊重女性,他毫不掩飾地講述民間女性的大膽與倔強(qiáng),尤為可貴的是,絲毫不吝于描繪女性的聲音,借來(lái)自內(nèi)心深處的聲音宣泄女性的叛逆與欲望。《檀香刑》中的“狗肉西施”孫眉娘嫵媚多情,她口中“貓腔戲”的“喵嗚喵嗚”聲不絕于耳,借百轉(zhuǎn)千回的民間戲曲傳達(dá)著對(duì)知縣錢丁的愛(ài)與欲;《民間音樂(lè)》中小酒店老板花茉莉的聲音落落大方,她熱愛(ài)生命中的美,沉浸音樂(lè)的撫慰,為追求愛(ài)情拋家舍業(yè),追隨民間音樂(lè)家小瞎子而去;《豐乳肥臀》中姐姐們的聲音是嘈雜的,她們?yōu)閻?ài)情紛紛“背叛”母親,在戰(zhàn)爭(zhēng)的年代她們隨愛(ài)人四處征戰(zhàn),與姐妹們分屬不同政治陣營(yíng),相聚不易又以爭(zhēng)吵居多,嘈雜堅(jiān)定的聲音既是對(duì)舊家族的反叛、對(duì)愛(ài)情的追逐,同時(shí)也是自由自在生命力的體現(xiàn)。相較而言,《豐乳肥臀》中的母親上官魯氏是溫柔低沉的,話雖不多,但在沉默的年代蘊(yùn)含著母愛(ài)力量,然而“母性”的光輝遮蓋不了人性中卑劣原始的方面。特殊年代里母親的沉默在危難關(guān)頭變成叫囂,化為保護(hù)子女的堅(jiān)定力量:為應(yīng)付苛刻的婆婆,她借種、偷情,控訴生育在那個(gè)年代帶給女性的不幸;用胃做“口袋”為嗷嗷待哺的孩子們從公社偷運(yùn)糧食;為保護(hù)幼女,鼓足勇氣打死神志失常的婆婆;為保護(hù)長(zhǎng)女,將孫啞巴之死的罪過(guò)嫁禍給過(guò)路的新兵……《紅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戴鳳蓮是集美艷與匪性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代表,她用堅(jiān)定的聲音勇敢地向傳統(tǒng)“父權(quán)”提出挑戰(zhàn):認(rèn)知縣作父、又促成余占鰲殺父;她在高粱地里熱烈追求愛(ài)情,也在日軍的炮火下用生命控訴:“天,什么叫貞潔?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惡?你一直沒(méi)有告訴過(guò)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ài)幸福,我愛(ài)力量,我愛(ài)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jìn)你的十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幾眼這個(gè)世界,我的天呢……”[11]56這控訴是她人生信條的寫照,借助女性的自我發(fā)聲,作家將女性內(nèi)心對(duì)于情愛(ài)及自由的大膽追求一覽無(wú)余呈現(xiàn),同時(shí)也毫不掩飾她們的私欲和粗鄙。
莫言筆下的女性人物沒(méi)有符合傳統(tǒng)綱常倫理的賢妻良母,一方面母親繁衍哺育代代生命,圣潔端莊、無(wú)私博愛(ài),另一方面,她們騎馬射槍、為匪殺人、偷情借種,沖出世俗禮教的藩籬,在愛(ài)情的長(zhǎng)河中釋放個(gè)體的欲望與豪情。他們也曾為了生存,卑賤如螻蟻,小心翼翼延續(xù)傷痕累累的家族血脈;也曾揭竿而起,在家國(guó)淪陷、大地悲歌之時(shí),仰天長(zhǎng)嘯,向死而生。這樣的女性,既是“圣母”又是“蕩婦”,表面似大江大河澎湃洶涌,內(nèi)心深處滿含千回百轉(zhuǎn)、潤(rùn)物無(wú)聲的涓涓細(xì)流。莫言通過(guò)對(duì)女性人物的塑造,表達(dá)了對(duì)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母神”——女媧的迫切呼喚。莫言筆下的女性集美麗與旺盛的生殖力于一體,融力量與堅(jiān)韌的毅力于一身。莫言源于傳統(tǒng)而又不囿于“傳統(tǒng)窠臼”的女性人物書(shū)寫,更為溫柔有力。
3.精靈或孽障
“高密東北鄉(xiāng)”的孩子個(gè)個(gè)是天生的“土匪種”,在時(shí)代的動(dòng)亂、秩序的瓦解、饑餓的肆虐、被成人世界拋棄的寂寞童年中肆意成長(zhǎng)。他們無(wú)一不是亂倫與縱欲的產(chǎn)物,骨子里摻雜著上一代糾纏不清的孽緣,他們機(jī)靈狡詐,倔強(qiáng)又義氣,稚嫩而大膽,引人矚目的是他們旺盛無(wú)比的野心與性欲:《紅耳朵》里雙耳碩大的王十千對(duì)英才小學(xué)的姚老師情有獨(dú)鐘,《四十一炮》里羅小通醉心于氣質(zhì)神秘的女人,《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對(duì)姐姐一樣的菊子暗戀不已……青澀的少年們?nèi)杖蔗溽唷笆场薄吧苯豢椀幕孟耄缘挚谷怏w與精神的饑渴。那個(gè)年代孩子們的世界中是沒(méi)有青春期的,他們極度缺乏成長(zhǎng)的營(yíng)養(yǎng)卻又被生活逼迫著撐起傾頹的家庭、過(guò)早成熟,未曾似花般綻放便如閏土一樣漸漸枯萎,因此,內(nèi)心壓抑的那份青澀的蓬勃顯得彌足珍貴。莫言筆下這群“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孩子們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yàn)樗麄兩砩系摹胺藲狻贝砹饲啻旱拿葎?dòng)與憧憬:使不完的力氣、用不盡的想象力、講不完的奇聞異事,且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對(duì)食、色、權(quán)利、榮耀的渴求,爆發(fā)出對(duì)父輩、家族、舊勢(shì)力的反叛,而歷史的斷壁殘?jiān)阋灾闻涯媾c野心,他們?cè)凇胺诵浴奔P(yáng)的青春里,呈現(xiàn)別樣的生命力。
然而,相對(duì)于父輩們的英雄浪子形象,子孫一代身上潛藏的匪氣,已經(jīng)摻雜了扭曲的因子。如果說(shuō)他們?cè)谕觌A段是天真洋溢的精靈,那么成年后則更多地成了利欲昏心、懦弱無(wú)能的孽障。莫言的巧妙之處在于緊緊抓住了他們半是精靈半是孽障的特點(diǎn),呈現(xiàn)青春張揚(yáng)的“匪氣”,這是“種的退化”之前“匪性”洋溢的又一高峰,也是時(shí)代留給我們的沉默與思考。莫言曾談及創(chuàng)作《紅高粱》的動(dòng)機(jī):“人對(duì)現(xiàn)實(shí)不滿時(shí)便懷念過(guò)去,人對(duì)自己不滿時(shí)便崇拜祖先。”[15]祖先們的所作所為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孝子孫相形見(jiàn)絀,在進(jìn)步的同時(shí),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11]2因此,對(duì)于“精靈或孽障”形象的一再書(shū)寫,反映出作家內(nèi)心的焦慮以及時(shí)代的癥候。
蒼茫大地上隨處生根、“春風(fēng)吹又生”的“土匪”們落地生根、肆意生長(zhǎng),“英雄或浪子”“圣母或蕩婦”“精靈或孽障”交織纏繞,與洋溢著野性生命力的風(fēng)土人情共同構(gòu)成復(fù)雜堅(jiān)韌的生命體系。“土匪”已不再是具體的人物,而是“農(nóng)民或匪徒”混雜互滲的特殊合體,逐步走向象征化、符號(hào)化,可以說(shuō),匪,已經(jīng)成為莫言的心理圖示,成為追溯原始生命力與野性叛逆力量的符碼。
四、“匪性”氣質(zhì)的溯源與發(fā)揚(yáng)
文藝?yán)碚摷业ぜ{在《藝術(shù)哲學(xué)》中說(shuō)過(guò):“自然界有它的氣候。氣候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植物的出現(xiàn);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氣候,它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藝術(shù)的出現(xiàn)。”[16]“匪性”意識(shí)于莫言作品中的表現(xiàn)也是一定環(huán)境影響下的產(chǎn)物。莫言自己坦言:“故鄉(xiāng)留給我的印象,是我小說(shuō)的魂魄,故鄉(xiāng)的土地與河流、莊稼與樹(shù)木、飛禽與走獸、神話與傳說(shuō)、妖魔與鬼怪、恩人與仇人,都是我小說(shuō)中的內(nèi)容。”[17]一個(gè)地方的地氣,必然滋養(yǎng)一個(gè)地方的文學(xué),地理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滲透在作家的生命中,對(duì)一個(gè)作家的成長(zhǎng)及創(chuàng)作的影響極為顯著。山東作為莫言的故鄉(xiāng),影響了作者的習(xí)慣、性格及創(chuàng)作。
山東文化是齊文化與魯文化的融匯與統(tǒng)一。齊地是莫言的出生地,給了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源源不斷的民間素材。一方面,齊文化的神秘浪漫是莫言奇幻想象力的來(lái)源。蒲松齡故鄉(xiāng)距莫言村莊僅三百里,自幼受民間神話傳說(shuō)故事的耳濡目染,使得莫言對(duì)于蒲松齡的作品有著地域上的血脈聯(lián)系和情感親近。他在短篇小說(shuō)《學(xué)習(xí)蒲松齡》中就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形式明確表達(dá)了自覺(jué)接續(xù)以蒲松齡為代表的中國(guó)小說(shuō)傳統(tǒng)的立場(chǎng)。《聊齋》中的狐鬼花妖、魔幻傳奇給了他講故事的靈感,因此不斷變換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汪洋恣肆、滔滔不絕。很多作品看似記錄歷史、摹寫現(xiàn)實(shí),卻也在歷史畫布上盡情涂抹:借助《豐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通靈”,《檀香刑》中趙小甲那根可以識(shí)別眾人“動(dòng)物原型”的“虎須”,《透明的紅蘿卜》中黑孩燃燒紅蘿卜時(shí)眼前產(chǎn)生的“幻象”,以魔幻諷現(xiàn)實(shí)、以幻喻真,神秘狡黠地洞察周圍的一切。海登·懷特對(duì)新歷史主義曾經(jīng)做過(guò)這樣的表述:“尤其表現(xiàn)出對(duì)歷史記載中的零散插曲、逸聞逸事、偶然事件、異乎尋常的外來(lái)事物、卑微甚至簡(jiǎn)直是不可思議的情形等許多方面的特別興趣。歷史的這些內(nèi)容在‘創(chuàng)造性’的意義上可以被視為‘詩(shī)學(xué)的’……”[18]因此,深受蒲松齡影響的莫言,靈活巧妙地運(yùn)用著民間傳奇、神話故事,將奇幻因子揉入家國(guó)歷史中。另一方面,齊文化開(kāi)放大氣、兼收并蓄的特質(zhì),促使作家不斷學(xué)習(xí),推陳出新。莫言是很愿嘗新的作家,已出版的十一部長(zhǎng)篇在形式上絲毫沒(méi)有重復(fù)的成分,他不愿循規(guī)蹈矩地將自身禁錮于一點(diǎn)一面,每當(dāng)讀者驚訝于他奇幻的藝術(shù)手法和恢詭多變的想象力時(shí),他總能再度出新。
齊魯文化中,魯?shù)匚幕瘹赓|(zhì)滲入莫言作品中的并非孔孟之道、儒家正典,恰恰是揭竿而起、義薄云天的民間傳統(tǒng)。“自古山東出響馬”,歷史上山東是匪患猖獗的地區(qū),魯西地區(qū)自幼習(xí)武的傳統(tǒng),加之吏治腐敗、災(zāi)害多發(fā)的現(xiàn)實(shí),是促成匪類聚眾的主要因素。唐末山東曹州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黃巢留下“沖天香氣透長(zhǎng)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壯烈;歷史上著名的“水泊梁山”聚義,使得“水滸”好漢的豪氣廣為流傳。血性男兒的江湖義氣家喻戶曉,而他們身上的傳奇色彩使得“匪徒”有了理想的“模仿榜樣”。近代以來(lái),面對(duì)西方殖民力量的侵入,爆發(fā)了“巨野教案”和“義和拳”運(yùn)動(dòng),山東地區(qū)捍衛(wèi)傳統(tǒng)、抵抗外來(lái)文化的意識(shí)格外強(qiáng)烈。據(jù)相關(guān)資料統(tǒng)計(jì),1918年,山東30多個(gè)州縣共有土匪三萬(wàn)名[19];1923年,山東匪首孫美瑤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民國(guó)第一案——“臨城劫車案”;到1930年,山東境內(nèi)土匪已超過(guò)二十萬(wàn)人,時(shí)人不禁驚呼“魯省已成匪世界”[20]!除了土匪的數(shù)量之多、聲勢(shì)之浩大,波及范圍之廣,更為突出的是聚義精神,農(nóng)民處于社會(huì)底層,又多為無(wú)產(chǎn)者,在世道流離的年代飽受天災(zāi)人禍之苦,反倒是“匪”這一團(tuán)體的包容與團(tuán)結(jié),給了走投無(wú)路的農(nóng)民開(kāi)辟“上山”的道路,江湖兒女的傳統(tǒng)道義、世俗生活中最為簡(jiǎn)單的善惡觀將他們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
地域文化給作家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厚的土壤,也使得作家思考得更深更遠(yuǎn),不斷致力于“人性”的突出與彰顯。
首先,“匪徒”們奉行的傳統(tǒng)道義是英雄主義與家國(guó)精神的緊密結(jié)合,而不僅僅只停留在聚眾起義、集體享樂(lè)的傳統(tǒng)“匪徒作風(fēng)”的淺顯層面,他們的血性和偉岸在國(guó)難當(dāng)頭、家園淪陷之時(shí)顯得尤為悲壯。羅漢大爺遭受的“剝皮”酷刑,孫丙被施加的“檀香刑”,無(wú)疑是莫言作品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部分,下達(dá)命令的是外國(guó)列強(qiáng),施刑的是同村鄰人亦或兒女親家,圍觀的是一眾鄉(xiāng)親父老……這樣的情景設(shè)置,將國(guó)人與列強(qiáng)的矛盾激化到了極點(diǎn),在非人的酷刑中充滿著對(duì)人性、對(duì)情感的巨大考驗(yàn),別有一番寓意。秩序混亂的年代,人性淪喪,反倒是叛逆野性的“匪氣”支撐起來(lái)的農(nóng)民們堅(jiān)韌不屈、負(fù)隅頑抗,不顧一切地?fù)纹鹨粋€(gè)個(gè)傾頹的小家族。剝皮、凌遲、剜心、檀香刑……人性被殘暴與肆虐逼迫到極點(diǎn),“匪性”在這其中愈加茁壯勃發(fā)。其次“匪徒”們呈現(xiàn)出的赤裸裸的個(gè)體欲望、叛逆不服輸?shù)男愿瘢际峭⑸Φ捏w現(xiàn)。既然為匪,既然可以大膽地游走于社會(huì)秩序的邊緣,在混亂的年代,個(gè)人的欲望在“匪性”光芒的觀照下被放大到了極點(diǎn)。“匪性”來(lái)源于被壓迫到極端的“人性”,在壓抑中的爆發(fā)是個(gè)體欲望的突出呈現(xiàn),莫言毫不避諱地展示出這一點(diǎn),同時(shí)揭開(kāi)了歷史動(dòng)人色彩背后的神秘面紗。正如王岳川所述:“新歷史小說(shuō)不再是重視民族性的、革命性的、戰(zhàn)爭(zhēng)式的大體裁和大寓言,而是回歸到個(gè)體的家族史、村史和血緣的族史,使‘民族寓言’還原縮小歸約為‘家族的寓言’使其從宏觀走向微觀,從顯性的政治學(xué)走向潛在的存在論。”[21]262“新歷史小說(shuō)在人物塑造上強(qiáng)調(diào)人物的邊緣性,土匪、地主、娼妓、姬妾以及一切凡夫俗子,皆在正面描寫之列。”[21]264
由此可見(jiàn),齊文化中的浪漫與開(kāi)放構(gòu)成了莫言無(wú)拘無(wú)束、自在噴發(fā)的文學(xué)生命力,而魯?shù)氐木哿x傳統(tǒng)、豪爽民風(fēng)則為小說(shuō)主人公的塑造提供了土壤。黃河下游的齊魯文化,綿延悠長(zhǎng),其中的“匪性”因子作為中國(guó)民間文化的縮影,是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生動(dòng)寫照。民間的力量在半是農(nóng)民半是“匪徒”的“大地之子”身上得以呈現(xiàn),從本土層面折射出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歷史發(fā)展的創(chuàng)傷與艱難。
五、“狂歡”或“悲歌”:英雄末路與“匪性”淡出
在沒(méi)有英雄的年代,人們渴望和呼喚著英雄。在《檀香刑》之后的作品,莫言則或多或少顯露出主人公“匪氣”沖淡的特性,如《蛙》中雷厲風(fēng)行、藝高膽大的姑姑,隨著年齡的增長(zhǎng),越來(lái)越趨向于女性的柔和。莫言小說(shuō)中,“匪性”人物的逝去,或悲戚或壯烈,或平淡或凄慘,那個(gè)氣沖云霄、“匪氣”蓬勃的年代業(yè)已不在,年輕一代沉迷于商業(yè)化的大潮中茫然無(wú)措。一類目光短淺、沉迷于金錢、利益的誘惑,如《紅高粱家族》《食草家族》《豐乳肥臀》《生死疲勞》中的孫子一代;另一類懦弱而又狡黠,干著以寫作為行當(dāng)?shù)臓I(yíng)生,講述著沒(méi)完沒(méi)了的故事,“油嘴滑舌”地穿梭于各場(chǎng)合之間,如《生死疲勞》《酒國(guó)》中的“作家莫言”,《蛙》中的“作家蝌蚪”等。莫言熱衷描述歷史,借一個(gè)小家庭或是村莊的時(shí)代變遷映射出中國(guó)社會(huì)歷史的滄桑巨變,相較于遠(yuǎn)去的英雄祖先們,孫一代的當(dāng)代人“匪氣”散盡、骨氣全無(wú)。字里行間,當(dāng)代人的癡迷與狂癲、冷酷與暴虐有著同余華《兄弟》中的人物相似的精神面貌,正如余華所言:“一個(gè)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jīng)歷這樣兩個(gè)天壤之別的時(shí)代,一個(gè)中國(guó)人只需四十年就經(jīng)歷了。”[22]
八十年代提供的自由氛圍使得作家們噴薄的情感亟待宣泄,因此八十年代的文學(xué)一度走向超乎想象的繁盛。與此同時(shí),商業(yè)化、城市化的進(jìn)程加快,日新月異的變化使得鄉(xiāng)村變得面目全非,故土不在、家園荒蕪,在城鄉(xiāng)間徘徊的作家面對(duì)自己故鄉(xiāng)是飽含淚水、滿目憂愁的,故園失落使得他們有感于自己與生俱來(lái)的對(duì)大自然、黃土地的親近,對(duì)于原始生命力的呼喚就顯得極為迫切與重要。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匪性”書(shū)寫,與其說(shuō)是一種潮流、一種文學(xué)界的流行趨勢(shì),倒不如說(shuō)是作家們的一種“集體無(wú)意識(shí)”,一種返回人類童年、尋找原始祖先血脈的沖動(dòng)。這樣集體的“返祖”和“尋覓”,也正是當(dāng)時(shí)所盛行的“尋根文學(xué)”的內(nèi)在因素。城市精神生活的空白與虛無(wú)更加反襯出鄉(xiāng)村的野性與純粹,祖先的英武和血性更加映射出當(dāng)代人的疲軟與虛弱,作家們?cè)谖镉麢M流、風(fēng)雨如晦的年代里奔走呼號(hào),呼喚祖輩們的陽(yáng)剛與野性、叛逆與生命力,渴望振奮那個(gè)時(shí)代的文心與人心。
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心便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良心。法國(guó)有羅曼·羅蘭,俄國(guó)有托爾斯泰,而縱觀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壇,能真正低下頭來(lái)、貼近土地貼近人民、保持赤子之心在時(shí)代洪流中屹立成中流砥柱的作家,寥寥無(wú)幾。不敢說(shuō),作家莫言代表著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良心,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宛如明鏡,照得這個(gè)時(shí)代的人面紅耳赤、羞愧難當(dāng)。如果說(shuō)莫言小說(shuō)中第一類人物是狡猾的小說(shuō)家對(duì)于當(dāng)代人的批判,那么第二類人便是謙遜的作家對(duì)于自身的諷刺與反省。一個(gè)不會(huì)觀照自身的作家是永遠(yuǎn)邁不出自己的圈子,也是無(wú)法前進(jìn)的,而莫言在暴露當(dāng)代人利欲熏心的同時(shí),也不乏批判文人的軟弱與諂媚,更多地是對(duì)于創(chuàng)作以及自我內(nèi)心的審視。2012年,莫言在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頒獎(jiǎng)禮致辭時(shí)曾提到:“一個(gè)人在日常生活中應(yīng)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dú)斷專行。”誠(chéng)如他個(gè)人所言,近四十年的書(shū)寫中,莫言始終保持著這樣倔強(qiáng)與尖銳的寫作立場(chǎng),孑然而立、“匪氣”十足。盡管莫言作品中的人物有著“匪性”氣質(zhì)逐漸淡出的柔軟傾向,但作家本人的“匪性”氣質(zhì)仍是有增無(wú)減的,他仍然有著刺貪刺虐的鋒芒、變幻無(wú)常卻又滔滔不絕的故事、以及對(duì)于“高密東北鄉(xiāng)”土匪一般霸凌而又噴薄的愛(ài)與熱情。所以,作家本人才是“高密東北鄉(xiāng)”這個(gè)文學(xué)理想國(guó)中最具野心、最狂妄而又關(guān)心著民生疾苦、為其奔走歌哭的“匪首”。悖逆與野性最終指向的生命力,也是作家本人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作活力,是如何在當(dāng)代更好地觀照歷史、審視祖先、反觀自身。
六、結(jié)語(yǔ)
莫言不斷地審視著自我的內(nèi)心,堅(jiān)守著獨(dú)立倔強(qiáng)的文學(xué)姿態(tài),他在《檀香刑》的序里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大撤退”的主張,在時(shí)代的洪流面前,他抗拒著短、平、快的盛行,轉(zhuǎn)而向民間習(xí)得寶貴的資源,“大踏步地撤退”,堅(jiān)守著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陣地,記錄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以及人們心靈的流變。他筆下靈活多變的民間話語(yǔ)是一種邊緣性話語(yǔ),他所深深贊頌的民間文化也是邊緣性文化,而在作品中揮之不去的狂歡詩(shī)學(xué)同樣是一種邊緣詩(shī)學(xué)。崇高與渺小的對(duì)立與消解,英雄好漢們昂揚(yáng)的高尚氣質(zhì)與鄉(xiāng)野村民卑微的地位矛盾與統(tǒng)一,以及民間文化中生生不息的“野性”生命力,在莫言這個(gè)“民間音樂(lè)家”手中,得以交融互滲,構(gòu)成一曲曲大地之子的“狂歡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