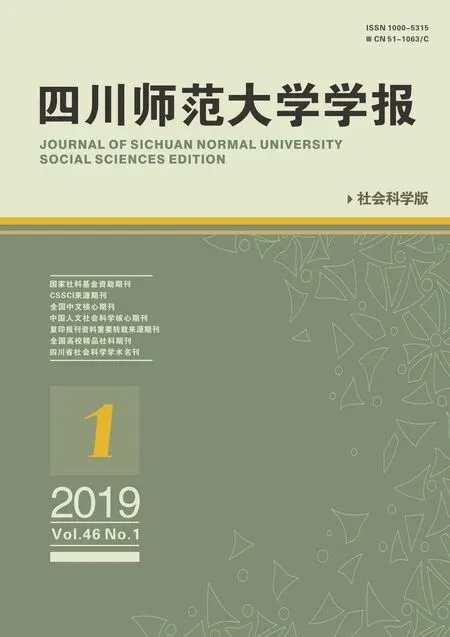他者倫理學及其對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
——從解釋學困境談起
(東華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昌 330013)
馬克思認為,哲學家試圖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關鍵是如何改造世界。同樣,傳統倫理學試圖從不同前提探索倫理原則,可問題是如何讓個人產生倫理責任。倫理首先是一種“感”而非“知”,或者說是一種由“感”而來的“知”。因此,倫理學首先是與人的全部生活相關的實踐。然而,傳統倫理學受形而上學理論態度的束縛,遺忘其實踐性,以原則的抽象性架空倫理關系和責任的實際性。
20世紀,西方出現了“實踐哲學的復興”,由此產生了現象學、存在論和解釋學等思潮。伽達默爾解釋學作為現象學和存在論的繼承與發展,體現了一種實踐倫理學。然而,它是否克服了倫理學所面臨的理論化困境?實際上,這一困境直到列維納斯的他者倫理學的提出才出現新的解決契機。作為第一哲學的他者倫理學不僅為解決傳統倫理學困境,而且對構建一種新型生態倫理具有重要啟發。
一 伽達默爾解釋學的倫理學及其困境
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具有強烈的倫理學取向。受海德格爾生存哲學和亞里士多德實踐哲學影響,伽達默爾的思想從一開始就被烙上深深的實踐特征。然而,伽達默爾的興趣畢竟是解釋學,而且是沿著海德格爾的道路來闡述解釋學的普遍性。因此,他突破亞里士多德城邦倫理學,從解釋學普遍性角度建立一門人類共同體的倫理學。此外,伽達默爾受到柏拉圖和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特別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相互承認”推崇有加,認為“和解的奧妙是黑格爾辯證法的秘密”[1]33-34。故此,他提倡一種能在全球范圍內達成相互承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類共同體的對話倫理學。但著眼于現實,他的這一倫理學面臨著巨大挑戰和困境。
當下世界各國之間的交往方式對于伽達默爾提倡的對話無異于一記耳光。時至今日,國際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主要還是訴諸于經濟制裁和軍事行動。國與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和隔閡,使得人們的對話意愿很低,即使對話也不是建立在相互承認和尊重的前提之下,而是以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前提。這種對話實際上是在強權之下的扭曲交往,與伽達默爾追求的對話相沖突。
伽達默爾對話倫理學的困境,是由其解釋學的本質決定的。或者說,他的解釋學并沒有真正擺脫傳統形而上學的束縛,故其倫理學困境實際上是傳統倫理學困境的一個縮影。
伽達默爾解釋學雖表現出較強的實踐取向,但它同樣具有傳統哲學的整體主義與大全主義訴求。古希臘以來,哲學的抱負是找到一個最高原則作為世界的根據,以便將之統攝起來。然而,自現象學出現以來,哲學不再從實體出發,而是把世界理解為一種發生和顯現的過程。在現象學尤其是海德格爾現象學的影響下,伽達默爾把時間性、發生性的事件作為其解釋學的起點和歸宿。首先,他提出的效果歷史是以人是一種歷史性存在現象為前提,把人的存在還原到他的歷史,強調傳統對個體的決定性或個體向傳統的隸屬性。其次,他雖然認為理解作為視域融合的事件沒有終點,但他仍然假設這種融合是必然的,理解應該以此為目的,不斷達成一致,這實際上是預先為理解設定方向。
效果歷史和視域融合作為哲學解釋學的內核,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然而,當涉及到倫理問題時,它和傳統形而上學一樣表現為一種整體主義的一元論。在伽達默爾看來,理解者的理解活動是被規定的。向過去,受到理解者自身的歷史性的規定,向未來,受到一種不斷綜合、形成共識的要求規定。所以,在對話中一方面要對自己的歷史性所帶來的有限性保持意識,對對話伙伴保持謙恭,另一方面,要帶著善良意志與對話伙伴達成共同理解,這是伽達默爾解釋學蘊含的倫理原則。顯然,這種倫理原則是在對話者對自身狀況的認識基礎上形成起來的(效果歷史意識),而且是以某個事先假設的要求為前提提出來的(視域融合的要求)。盡管強調向對話伙伴保持敏感謙恭,但仍是一種理論態度,即從某個預設的前提出發提出某種應然的倫理要求。這種要求不是聆聽對方意愿的結果。就此而言,伽達默爾沒有徹底實現哲學的實踐性。實踐在他那里仍受某個超越存在的引導,不具第一性,故而帶有形而上學的理論態度,這是“他的對話共同體乃是一種語言烏托邦,顯得十分蒼白無力”[2]172的根本原因。
由于伽達默爾的倫理思想未跳出形而上學的理論態度,所以也表現出一種存在論的暴力。對此,或許有人會表示反對。誠然,伽達默爾強調對話雙方平等,相互尊重。他甚至吸收馬丁·布伯的“我-你”關系,對傳統形而上學和科學的“我-它”關系進行猛烈抨擊,指責“我-它”關系是按照我的原則抹殺、吞噬、同化一切其他存在者,具有強烈的暴力性。但是,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卻以另一種方式重新陷入這種暴力。在伽達默爾,自笛卡爾以來得到推崇的主體得到限制,然而卻出現了一個凌駕于主體間之上的施暴者。這個施暴者不是某個存在者,而是超越一切存在者的境遇或事件,在伽達默爾便是理解的事件。這一現象并非在伽達默爾才發生,而是西方自反思批判主體性哲學以來便開始出現,其代表性事件則是現象學。對此,列維納斯這樣評論:“哲學(傳統哲學)是一種自我之學,……現象學的中介化則采取另外一條道路,在這里,那構成真理之中項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從胡塞爾以來,整個現象學都是對境域觀念的提升,對于現象學來說,境域所擔任的角色與古典觀念論中的概念(主體)相當。”[3]16伽達默爾解釋學作為現象學的繼承與發展沒有擺脫這一窠臼。
為什么超越的境域是施暴者呢?它對倫理關系意味著什么?哲學作為一種理論思辨,其目的在于探尋存在者的本原,尋找其存在根據。然而,“對于每一個獨一的存在者來說,這樣一種沒有出口、不作回答、吞噬和毀滅一切存在者的中性的‘有’,乃是一種暴力”[4]12。這種暴力或許單從本體論層面并不太明顯,但從倫理學角度來看,便很明顯。倫理關系的基礎是獨立、具體,承擔責任的個體存在,其實質是讓自身之外的存在者將其懇求或命令教導給我。因此,每一個處于這種關系的個體拒絕被還原,否則他們即被剝奪表達的機會。然而,存在論把具體的存在者與存在關聯起來,“就在于把存在者中性化,以便統握它或掌握它”[3]17。
存在論對于倫理責任者、倫理關系以及倫理責任本身是一種抹殺。如果具體存在者依賴于某個超越者而存在,那么在面對自身之外的存在者時,首先呈現的不是他者本身,而是其存在的根據,相應地,首先做的不是聆聽他者,而是將其同化到那個以之去看待他者的根據中去。所以,存在論面對他者的首要態度是理論的,而非倫理的(實踐的),倫理問題的討論要在理論態度下展開。但問題是,這種以理論態度為基礎的倫理關系已經失去了倫理的實質,它不僅不能產生出對他者的倫理責任,而且形成對他者的暴力。
伽達默爾著眼于理解的歷史運動,將具體的個人作為歷史性存在同化到傳統之中,賦予歷史運動以綜合統一的特征,要求理解者本著相互尊重,努力達成一致,最終達成世界共同體。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存在論的理論化倫理觀,他的對話共同體的倫理學陷入一種語言烏托邦,實際上是形而上學理論態度下倫理學的共同命運。
二 列維納斯倫理學對伽達默爾倫理學困境的克服
倫理學,就其本質而言,不是理論的,而是實踐的。然而,倫理學的實踐性不同于伽達默爾所謂的實踐智慧。實踐智慧是在具體環境中選擇符合善或正當的能力,涉及到人的判斷力。倫理學應探尋的是促使人們選擇正當的動力,涉及到欲望。它比實踐智慧更加根本,因為前者不太考慮動因問題,或總以某個一般性動因為前提,如社會的和諧、公德的要求等。那么,倫理責任究竟動力何在呢?
法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大力提倡倫理學。他所謂的倫理學不再是存在論哲學之下的分支學科,相反它要逃離、打破存在論的一統天下。所以,他把倫理學作為第一哲學提出。他的倫理學對于今天的問題具有很大啟發意義。按前面的分析,傳統倫理學之所以不能產生個體的倫理責任,在于它是存在論的。倫理責任不能從存在論體系中推演出來,“面容的要求(倫理責任)不是意識構建出來的,而是遭遇到的”[5]XI。倫理關系是一種實踐關系,倫理責任只能在實踐中被喚起。實踐不是個體出于某個共同的、普遍的、一般的倫理要求(這些都是理論構建)而采取實際行動的過程,而是當個體與個體面對面時,與他者相遭遇的經驗。倫理責任只能從這樣的經驗中被喚起。
前面談到,凡是出于超越原則的倫理學都屬于理論態度,不能在個體中激起責任。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他者倫理學來分析其原因。如果倫理責任只有他者才能激起,那么,建立在某個超越原則基礎上的倫理學落于空洞,恰在它缺乏他者之維,它實際上只是某個原則從自己出發再回到自己的游戲。所謂的倫理關系是我與我理解的對象之間的關系,倫理責任是我出于我的原則認為應當承擔的責任。顯然,這種倫理學和存在論一樣是一種由原則到原則的演繹,它沒有落根于現實實踐,故而聽不見他者的聲音、也看不到他者的需要,也就無法從他者那里感受到迫切的責任感。
為什么缺乏他者維度呢?因為它總是以理論的態度面對一切。理論態度具有這樣的特征:持這種態度的人將所有他之外的事物根據某一原則進行理解和解釋,使之符合自己的規則,納入自己的體系。“理論意味著理解,就是說,一種如此通達被認識的存在者的方式,以至于這種存在者之相對于進行認識的存在者的他異性消失了。”[3]14因此,他者不可能出現在理論態度面前,倫理關系中的他者表現為對理論態度的質疑。“這種由他人的出場所造成的對我的自發性的質疑,稱為倫理。”[3]14由此可見兩種不同的責任:一種是我按自身原則,為了達成某個善的目的,向一個他所理解的“倫理客體”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另一種是由他者按照其自身的要求從我之外加給我的責任。前者是一般性倡議,具有普遍性、理論性;后者是具體性要求,具有個體性、實際性。而且,責任主體從“我們”轉換為“我”。“我們”作為一般性倫理要求的不在場主體,應當但不必然遵循它。但“我”作為遭遇到他者提出的倫理責任的承擔者,不得不履行責任。為什么“不得不”呢?這與另一個問題相關,即他者是怎樣把倫理責任加之于我的?
如前所述,他者通過破壞理論態度而出現,那么他者是否把我同化,然后將自己的要求強加于我呢?他者之為他者,在于其他異性和超越性。列維納斯用“無限”來描述這一特性。他者是無限意味著“他者超出在我之中的觀念,……他者每時每刻都溢出(我的)思想從(他者)的表達中引進的觀念”[3]23。他者不是我的競爭對手,他只是拒絕我的同一,保持他的外在性。因此,與作為“無限”的他者的關系是“從自我之能力所及之外的他人那里有所接受,這恰恰意味著擁有無限觀念”[3]23。而且這種關系是非對抗性的,“與他者的關聯是一種非排異反應的關聯,一種倫理的關聯”[3]23。所以,他者不是以強者的形象呈現,他者恰恰以弱者的形象激起對之的倫理責任,“他者的臨顯本身就在于用其在孤兒、寡婦、陌生人之面容中的赤貧來懇求我們”[3]54。這并不是把倫理責任訴諸于對弱者的同情。同情仍然是一種由我及他的同化行為。相反,他者以其赤裸、無辜的面容,以中止我的權能與控制,超越我預期的方式向我發出呼喚,“這個呼喚是作為一種憂慮和不安被經歷到的”[5]XIII。甚至激起一種羞愧,恰恰讓我感到我的同情是虛偽的。“在羞愧中,自由(自我)發現自身在其運作中是對他人的謀殺。”[3]60羞愧不能從我自身中反思出來,而只能由我之外的某物激起。他者超越我的同化,質疑我的權能,激起我羞愧,同時讓我對他者產生欲望。
為什么令我感到羞愧的東西還讓我對之產生欲望呢?薩特在討論他者問題時提到羞恥感。他認為他人通過注視激起我的羞恥感而出場,然而羞恥意味著我在他人的注視下被限制,被對象化,“沒于一個流向別人的世界、相對別人而言的自我”[6]328。因此在我的羞恥感中出場的他人,與我處于沖突關系,成為我要逃避的地獄①。列維納斯也主張他者是對我自由的限制,對我作為主體的理論姿態的否定。然而,他者以“臉”的方式向我表達②,即向我提出超越我理論同化之強權的要求和命令,讓我產生羞愧感。羞愧感是他者超越我理論同化之強權的結果。他者之“臉”在表達中激起的羞愧感,當然也有不悅的成分,但更多是意外和驚奇,甚至震驚。簡言之,他者激起的羞愧感不是對抗的結果,而是超越的結果,所以我不僅不會產生反感,反而會對帶給我震驚的對象產生欲望。因此,對他者的欲望不是企圖同化的強權意志,“不是作為對可欲望者的占有能滿足的欲望,而是作為對無限(他者)的欲望——善良”[3]23,這種欲望蘊含著一種必須回應的責任。
列維納斯最終回到了倫理學的基礎——善良,但他沒在傳統倫理學意義上理解它。善良是人與人、人與世界的原始關系,體現為我對他者的欲望。這種欲望不需通過占有,得到滿足,相反,它是一種在無限距離中的吸引關系。他者超越我的占有與我保持無限距離,因此,他者成為我欲望的對象,對我產生強大的吸引。這種超越需要(同化)的欲望是這樣一種責任關系:他者以其無限超越同化的陌異性向我發出的要求和命令,不但不令我反感,反倒“綁架”了我,“我是他者的人質”[7]125。我“不得不”向他承擔起責任,但不是出于強力的逼迫,而是我自發產生的迫切感。
伽達默爾也談論他者,主張應當對他者的他在性保持敏感,“歷史意識知道他物的他性”[8]509。他甚至強調他者在對話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必須重視與他者的相遇,因為總是有這樣的情況存在,即我們說錯了話以及后來證明我們說了錯話。通過與他者的相遇我們便超越了我們自己知識的狹隘。一個通向未知領域的新的視界打開了。這發生于每一真正的對話。”[9]21然而,伽達默爾仍是以我為出發點,以某個超越的存在為歸宿來談論他者。首先,為什么對他者保持敏感?因為我是有限的。在理解中,由于我的有限性,所以應當對他人的意見保持開放。其次,他者在對話中的意義在于補足我的理解。這意味著,他者只是手段,對他者保持敏感,不是因為他者本身,而是讓理解更加完善,更大程度達成一致。
盡管“伽達默爾開創的效果歷史意識已經為他者問題的討論爭得第一塊地盤。效果歷史意識與列維納斯的倫理學均有共同的思想旨趣,即實踐”[10]55,但是,由于他囿于追求綜合、統一的存在論訴求,仍從理論態度出發討論他者,致使其哲學的實踐性不徹底,從而無法真正聆聽他者的聲音。實踐是沒有任何預設的面對面。這種面對面是通過他者不斷打碎我的理論同化而得以呈現。從中,我被他者教會倫理責任。可見,只有將哲學的實踐性貫徹到底,不斷打破存在論的理論同化,才能為解決伽達默爾乃至傳統倫理學的困境帶來一線希望。
三 他者倫理學視域下的生態倫理建構
十八大以來,中國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然而,究竟何為生態文明?為什么要將它與“社會主義”放在一起?澄清這些問題,有助于闡發他者倫理學對于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發意義。
生態危機是工業文明發展的結果。反思批判工業文明,探索人類文明持續發展的道路,西方人走在前列。生態文明這一概念也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但是,由于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的內在關聯性,西方人一般把生態文明當作工業文明的一個補救措施,不認為生態文明是不同于工業文明的新文明。在國內,情況也較為復雜。由于國家大力提倡,生態文明成為熱門話題,但大家對該概念的理解并不清晰。大多數人把生態文明僅等同于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等具體措施。但中國提出生態文明建設或許還有更高的維度。習近平指出:“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11]顯然,習近平是站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把生態文明放置在人類文明形態的歷史發展中來理解的。它不是工業文明的補救,而是對工業文明的揚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共產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因此,工業文明作為資本主義的重要支撐必將為生態文明超越和取代。因為生態文明是共產主義和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之重要內涵,所以,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是社會主義的。
既然是一種文明形態,那么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在于意識形態的塑造和社會風尚的形成。只有在此基礎上,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等才具有內生動力。如果說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是以資本及其增值為目的,形成的是生產主義、消費主義和金錢主義的社會風氣,壓榨、破壞、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那么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社會就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宗旨,形成節制、簡樸和共享的社會風氣與尊重、保護、順應自然的意識形態。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生態倫理學研究者共同的愿望。學界歷來有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對峙。前者認為人是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主導者,人為其利益利用自然乃天經地義。同樣,人應當出于自身利益主動承擔解決生態問題的責任,“人對生態環境破壞負有道德責任,主要來源于對自身生存和社會發展以及子孫后代利益的關心”[12]146。相反,后者著眼于生態整體,主張人與其他自然存在地位平等。人沒有權利因為自己無限犧牲其他生態成員的利益,必須“從生態整體的角度限定人類的行為,為人類高速發展的經濟活動提供生態閾限”[12]63。
兩派主張截然相反,但背后的思維模式是一致的。它們都“以二元分裂的方式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們都不假思索地把人和自然首先確立為兩個互相獨立甚至對立的存在,然后在二者之間選擇一方為據點,由此推至另一方”[13]15,因此都是一種典型的理論態度。人類中心主義立足人類,把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原為人類自身的生存問題,得出一種在眼前利益與久遠利益之間取舍的功利主義生態倫理觀;生態中心主義立足自然生態體系,把人與自然關系還原為自然物與自然物之間的關系,無視人的社會性,得出一種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生態倫理觀。總之,兩者都沒有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實際出發,而是從某個理論預設推導出一種關系模式,導致其提出的倫理要求很難引發共鳴,喚起公民生態文明意識的自覺。可見,生態倫理的關鍵不是從理論上講清人與自然的利害關系,而是怎樣將這種利害關系從“知識”轉化為“責任感”。對此,列維納斯的他者倫理學可以提供一些啟發。
鑒于傳統生態倫理的困境,本文將從兩個方面闡述他者倫理學對生態倫理研究的啟發意義。
第一,生態倫理研究要實現實踐轉向。傳統生態倫理學的困境在于理論化,而倫理的本質是一種實踐關系,列維納斯把倫理作為一種我與他者的面對面關系,具有強烈的實踐特征。實踐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毋寧說它的終極動力要訴諸于感性和肉身,訴諸于當下的行動和情感的感發。因此,列維納斯倫理學與傳統倫理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任何規范倫理學或義務倫理學,不是對一些先行的倫理規范或義務或普遍命令的確定、尋求;而是關于倫理行動如何被感發、當場發生的倫理學”[4]161。列維納斯強調與他人面對面的關系,因為倫理行動只有在這種關系中才能感發出來。這意味著,生態倫理學應當致力于進入人與自然的實際性關系中(面對面),在經驗的基礎上生發出人對自然的倫理責任,而不是從假設的理論前提出發演繹一種倫理義務和道德責任。目前,生態倫理學并不缺乏理論分析,但人對自然應負的責任仍然很少落實。實現生態倫理學的實踐轉向,正是要把其中心從理論建構轉移到實踐動因形成上來,推動生態倫理學致力于激發責任感的探索。
第二,生態倫理的關鍵是作為他者的自然。他者之維是倫理關系之實踐特征的保障,沒有他者的倫理學難逃理論化窠臼。所以,生態倫理要實現實踐轉向的關鍵是作為他者的自然。這有兩層意思。第一,人類應當主動地、有意識地放下理論態度,把自然當作他者去傾聽其要求和命令,形成倫理責任。如果一味從理論態度出發把自然視為對象,那么生態倫理責任難以形成。即使人類有保護自然的意圖,也不能在作為對象的自然面前把保護行動堅持下去,因為人對自己設定的對象談不上責任。第二,自然作為他者主動打破我們的理論態度,讓我們形成倫理責任。如果人不主動轉變自己,那就只能等到自然以其絕對的陌異性,如以其破碎的面孔觸動、震撼我們,甚至以其震怒的面孔報復我們,把我們從理論的睡夢中驚醒,才能產生倫理責任。雖然此時我們會更加被動,但是除非人類早點醒悟,否則要產生倫理責任,別無他途。總之無論哪種情況,有一點是一致的,作為對象的自然無法向我們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要自然還只被視為滿足人類欲望的對象,那么尊重、保護、順應自然的責任感難以形成。倫理學在列維納斯不再是抽象的倫理原則,而是一種活生生的關系。這種關系的本質體現為超越占有和同化的欲望,體現為一種善。就此而言,生態倫理應當嘗試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一種超越占有的欲望關系。這種關系作為一種善的關系,不是由己及他,而是由他及己。生態倫理的重點應致力于引導人聽從并受教于自然,讓自然按其自身的要求教會我們應當負的責任。
自然是他者,并非要把自然神秘化、人格化。它對于生態倫理構建的意義,毋寧在于給人類的思維增添一個維度或成為一個提醒:即他者之“臉”提出的倫理命令“汝勿殺”。引申到生態倫理,即是“勿當自然為對象”。在近代西方思潮的語境中,“對象”是與“主體”相對而言的,對象是主體的構造之物。就此而言,“把自然對象化”是人類施暴自然的根本體現。所以,自然是他者,首先是一個思想的變革。即是說,如果將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他者倫理學來建構,那么它首先要革去理論態度下對自然的對象化理解,除去橫亙在人與自然之間的各種中介(原則、思想、理論),放棄對自然的同化。
資本主義把自然視為實現資本增值的對象,這一態度決定了它的意識形態是反生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生態的,在于它的意識形態是生態的。所以,建設生態文明不只是節制資本、升級產業,更是一種文明形態的塑造。形成一種對自然的倫理責任,是樹立生態文明觀的前提。因此,生態文明觀的塑造絕不是構建一個抽象理論體系那么簡單。文明是生活積淀的結晶,生態文明觀的形成需要整個社會形成自覺尊重、保護、順應自然的倫理責任和生活風尚。他者倫理學告訴我們,他者是產生倫理責任的基礎。所以,生態倫理應當引導人們放棄對自然的理論態度,在面對面中遭遇自然、傾聽自然,讓自然的他者之“臉”喚起我們的責任,形成一種人與自然的善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一種能喚起人們責任感的倫理學,必須是實踐的和他者的。實踐不是理論應用于實際的行為,不是做成符合善的行動,而是不斷放棄理論同化的暴力,進入與他者面對面的善的關系。只有在這樣的實踐中,他者才能作為獨立自主的存在者,按其自身的原則和要求,將一種倫理責任加于我們,這種責任是我們不得不回應的,因為它超越我們的理論同化,讓我們在愧疚感中被“綁架”,為我們履行倫理責任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注釋:
①薩特實際上是在一種顛倒過來的主客關系中討論他者的出場。他者的原始身份是主體,與我作為主體時將他人、他物設定為對象一樣,作為主體的他人在注視中將我設定為對象,把我從我的世界中剝離出來,讓我產生不愉悅的羞恥感。因此,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對他者的思考沒有擺脫傳統存在論的同化傾向。
②表達是一種語言行為。所以,列維納斯極其注重對話和語言,認為我與他者之關系的本質就是語言。然而,他所謂的語言不是伽達默爾所謂的達成共同理解的辯證語言,而是他者向我帶來啟示的語言,體現了他者之絕對陌異性帶來的意外、驚奇、創痛、愧疚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