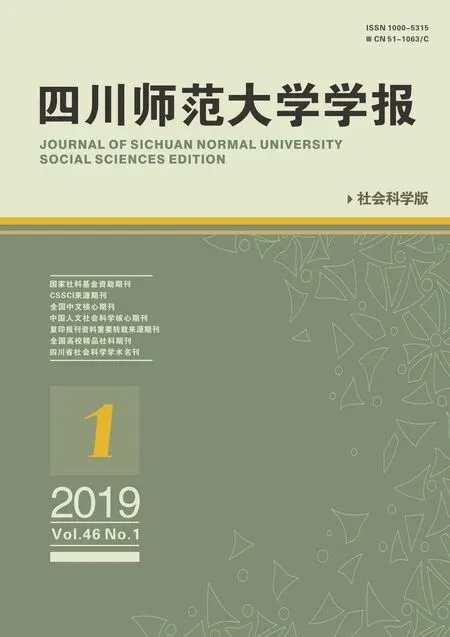地方性探索:1952年前的民族區域自治實施
——以川北行署平武藏區自治委員會成立為考察中心
(綿陽師范學院 民間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綿陽 62100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六章第五十一條明確了“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的原則,不過這一在當時起著憲法作用的綱領性文件并沒有也不宜對實行區域自治的條件、步驟以及自治區成立以后如何運作等具體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中央政府最早關于籌建民族自治區“實施細則”的文件是1952年8月9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就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成型而言,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8月9日這一時期構成了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制度)試驗階段,在民族區域自治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民族區域自治是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學界向來重視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既有研究對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8月9日之間的區域自治實施工作甚少措意,不僅闕如民族自治區創建的學術研究,也沒有充分意識到《共同綱領》后、《實施綱要》前的這段時間是民族區域自治實施史上的試驗探索階段,以致學界對在此期間成立的自治區的創建契機、過程、意義以及與其他地方工作的關系認識模糊。尤有甚者,作為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形成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其階段性特征、對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制度)定型的作用以及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工作經驗也沒得到系統的梳理。本文選擇“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這一西南大區范圍內最早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機構進行個案研究,嘗試就民族區域自治實施“試驗階段”在史實重建基礎上作深入探討,并以此重構這一時期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推行的階段性特征。
一 共和國初期川北行署民族工作的施政特點
《共同綱領》確立了“民族的區域自治”的法律定位,中央政府也在多種場合表明實行該政策的決心。不過,在《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頒布前的近三年時間里,政策實施及民族自治區的創建工作卻并未普遍開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重建社會秩序、培養民族干部需要時間外,另有三個因素不容忽視,即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還未得到明顯緩和、作為政策執行者的基層干部思想認識有待提高①、當時還未就如何實施政策形成統一與明確的認識。1950年8月9日,李維漢關于中央統戰部六、七月份工作向主席和書記處的報告就指出,當時“對區域自治的意義和實行步驟,了解極不一致,亟需研究處理”[1]68。
本文涉及的平武縣,建國之初隸屬劍閣專區,劍閣專區則是川北區人民行署管轄的四個專區之一②。川北區雖有回、羌、藏等民族分布,但其人口構成絕大多數為漢族,少數民族為數較少③。川北行署據此并未將民族工作納入“重點工作”之列。據1950年1月15日制定的《川北初期工作綱要》,工作主要包括:“甲、完成征借糧食任務,清理舊時財糧稅收,推行人民幣,交流城鄉物資,穩定市場,支援前線;乙、推行治安工作;丙、接管好城鄉。”[2]25-26
少數民族人口少,征糧、支前、接管任務繁重,行署未將民族工作列入“主要工作”,這一施政側重背后反映的是對民族情況的缺乏了解。川北行署在一段時間內不知轄區有“藏族”。據曾窮石研究,時任川北行署主任兼統戰部長的胡耀邦,是在平武土司到南充之后才知道平武有藏族,并且認為土司本人就是藏族④[3]117。據相關研究,川北不僅有藏族部落,土司王蜀屏也不是藏族,平武土司制度的特點之一就是漢人世襲土司,少數民族出身的“番官”協助漢人土司處理番人事務⑤。為掌握轄區少數民族情況、疏通改善雙方關系,在“平武藏區自治委員會”成立以后,1950年10月27日至1951年1月26日,川北行署組織“少數民族訪問團”訪問平武藏區⑥。“平武藏區自治委員會”成立前,行署既沒對少數民族情況進行過系統調查,也沒有對少數民族深入宣傳過新中國的民族政策。
建國之初,對少數民族缺乏了解是普遍現象,川北區并非特例。西南黨政最高領導人對少數民族的了解同樣不足,如劉伯承坦言“一知半解”,鄧小平自認“還是一個小學生”⑦等。劉、鄧的公開表述或有自謙的可能,但西南軍政委員會內部的往來公文亦透露出當時對少數民族“了解甚差”的情況⑧。新中國成立不久,解放區社會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大規模的民族訪問和調查還未進行。就西南大區而言,解放戰爭仍在繼續,在已控制地區也有國民黨潰軍與土匪作亂,少數民族多分布在深山僻野,因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彼此間均不夠了解,新中國的民族政策對絕大多數少數民族而言還聞所未聞。
對少數民族的了解,隨工作開展而有所改觀。1950年7月15日公布的《川北區當前施政方針》,改變了對民族問題不置一詞的作法。該文件在其“鞏固與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建立堅強的各級人民政權”部分規定:“對回藏等少數民族,應嚴格按照共同綱領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保護他們的權利,扶助他們的民族文化,并吸收他們中的代表,參加當地政權工作。”⑨
不過,該文件仍未將“民族政策”單列,而是置于“鞏固與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建立堅強的各級人民政權”條款之下,“回藏等少數民族”與“婦女”、“人民團體”一樣均屬“統戰對象”,雖提到了“吸收代表”以及“參加政權”,但這種建政方式與實行“區域自治”相距較遠。劉伯承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上宣布的《西南區的工作任務》中規定:“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各民族雜居地區之省、市、縣人民代表會議和政權機關內,各民族均應有其相當名額的代表和工作人員。”[4]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區域自治、在雜居地區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民族地區作了“聚居”“雜居”的嚴格區分,并規定了相應的建政方式。《施政方針》提到的“吸收代表”和“參加政權”,說明川北行署無意在轄區內實施區域自治,事實上也否定了平武藏區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性質。
據原川北區工作干部的回憶,最初的施政方針草案中甚至根本沒有涉及少數民族的政策表述,后來公布的《施政方針》第31條,則是在少數民族代表要求下添加上去的。具體內容如下:
在川北首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舉行大會發言,討論《川北區當前施政方針》草案時,川北少數民族代表、閬中回族民主人士馬騰九先生在全體大會上發言……施政方針總的精神條款我們都擁護,但其中就是沒有提到少數民族,這可能是大漢族主義留下的壞傳統的影響,希望大家看重少數民族。
耀邦當即向大會秘書長劉玉衡說,這個意見很好,草案中未單獨提到少數民族,這是一個很大的疏忽,一定要加上,一定要加上。……經過討論修改后,正式公布的《川北區當前施政方針》寫進了馬騰九先生的意見。[5]47
作為川北區施政總綱的“施政方針”,由胡耀邦親自主持制定,出現這種“很大的疏忽”,很難歸因為工作中的“粗心”,深層原因恐怕還是行署干部對民族問題的不重視、對少數民族上層的不信任。川北區各級干部心理上對少數民族不信任,缺乏與少數民族合作的意愿,這既可從收繳藏民槍支得到證明,也可從干部不愿與黨外人士合作得到印證。據《川北行署關于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情況的報告》披露:“各地在統戰中的關門主義仍很嚴重,干部作風非常生硬。”[6]25有些干部甚至對團結各界人士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都存在抵觸情緒。據記載:
怕犯錯誤。他們的說法是不開人代會,頂多說我統戰工作沒做好,但不至于在將來整我“左了”“右了”等等。……只怕壞人鉆進來……甚至有些怕到人代會上去作報告,因此形成這些縣內我們工作干部裸體跳舞。……認為川北真正的民主人士不多,有的倒是封建人士。[6]26
在長期接受階級教育的干部看來,欺壓、剝削人民的“封建人士”只是“統戰對象”,這導致階級意識抵消了統戰政策的部分效能。當地方干部面對“土司”、“番官”、“頭人”時,除階級壁壘之外,還需突破彼此之間的文化隔膜。《川北區當前施政方針》缺少民族政策這一“很大的疏忽”背后,除客觀上對少數民族不了解之外,還有主觀上的排拒心理作祟。基層干部不能準確理解、把握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執行起來難免打折扣。
是否具備實行條件,是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1950年制定的《對各少數民族施政方針草案》規定:在西南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遵照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規定,由各民族選舉代表組織各該地區的民族自治機關”;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成立“民族自治機關”,依據的是“共同綱領”;該文件附加的前提條件是“俟完全獲得解放和革命秩序建立以后”,符合“慎重穩進”方針⑩。平武和平解放雖為中共接管創造了條件,敵對勢力卻也因此未遭受沉重打擊,國民黨的潰匪、特務潛隱待機,人民政府權威遠未“下沉”至藏區基層。
共同綱領的原則性規定,不能替代具體的操作細則。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均缺乏具體實施的操作章程。就西南來說,專門負責民族事務的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于1950年2月著手籌建,其后還經歷了負責人的更換,當時正忙于自身的機構建設和干部配備,其業務工作還停留在對“舊有資料”的“編印”階段,根本未對民族區域自治問題進行過深入討論。川北區作為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直系下屬,缺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具體參照。
就西南區而言,川西有藏羌族聚居區,川南有彝族聚居區。相對而言,川北以及川東的少數民族數量最少。無論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交付的政治任務,還是川北行署的自我認知,民族工作均非其施政重點。對川北來說,當時對平武藏區的具體情況尚且茫然無知,更談不上與藏民有良好溝通和充分協商。川北區無論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準備,均缺乏在西南首先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礎。令人費解的是,在這種形勢下,“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宣布成立了。
二 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成立背景重構
平武藏區原系土司統治,為薛、王兩姓三個土司的世襲領地。民國一度改土歸流,改行鄉政,“一切捐稅,壯丁名額開始同漢區一樣負擔,廢除了土官領地內少數民族免納賦稅的歷史習慣”[7]65。不過,傳統的土司勢力并未遭到根本削弱,其對藏民的政治影響仍舊。平武和平解放后,于1950年1月5日成立人民政府[8]17-18。平武藏區的基層行政,基本沿襲民國舊制,另將黃羊、虎牙、陽地三個鄉劃歸水晶區領導,委任土司王蜀屏為代理區長,對其他有影響的人物也作適當安排。解放之初,中共的政治影響還未及深入基層,川北區又擔負著“支援前線”的繁重任務,與少數民族地方實力派合作,既符合“慎重穩進”方針,也切合平武藏區實際。
然而,平武干部對藏民的“繳槍”舉措,破壞了雙方合作的基礎,動搖了已趨穩定的社會秩序。《川北區黨委關于平武縣委對藏民政策發生錯誤問題的處理報告》,詳細地說明了基層干部的這次“盲動”行為:
北川發生暴動,該縣領導即慌亂盲動,在一次會議上用企圖暴動罪名,輕率決定扣捕七個地方勢力首領和收繳一切私槍。不顧黨的少數民族政策,令王蜀屏收繳藏民槍支一百一十枝。同時逼供和扣捕人犯中,彼等煽動,倘若失敗,即退至藏民區活動。該縣領導倘不加分析,懷疑王與他們有勾結,將王扣至縣府(按王系知識份子,在張秀熟同志影響之下比較進步,平時對藏族要求不重,有時給藏民代購貨物,因此與藏族關系較好)。藏民聽說因收槍扣起“王老爺”,愿繳出槍支要求釋放,并說如不釋放,他們就不在平武住了,縣府毫不介意,又收繳槍六十枝(兩次共繳一百七十枝)。王雖被釋放回區,但又遇我戰士打他的煙燈,自此情緒低落,藏族酋長也再不和我接頭。酋長澤子妹帶七、八人攜槍跑到松潘地區,因而藏民對我甚為疑懼。[9]44-45
地方干部的繳槍行為,明顯與民族工作“慎重穩進”的指導方針不符,與上級指示亦有抵牾。1950年1月制定的《川北初期工作綱要》,對槍支處置有明確要求,規定:對“國民黨潰散匪軍的槍支”應予以“收繳”,對“私槍”則“暫不提收繳,只作調查登記,準備放在下一步收繳”[2]25。藏民槍支,不屬于“國民黨潰散匪軍的槍支”,而且西南局認為在解放軍接近平武時,“藏民曾組織武裝配合我軍襲擊胡匪軍,維持平武縣治安,起了不少作用”[9]44。西南局的態度,不僅在于繳槍行為本身,更因由此引發的川北動蕩。田利軍教授研究指出,平武藏民經歷此事者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其依據的史料是土司族人王生沛及解放后曾在川北行署革命大學學習的王生桐回憶[10]:
把王蜀屏……關起,押起。嚯喲,白馬路曉得了。“客巴,我們要見客巴,我們要找客巴。”客巴就是老爺,客巴就是番人喊的老爺,見了來了一群,跑去縣政府去坐起,請愿嘞,曉得啵。[3]114
解放過后,那陣喊收槍。王蜀屏嘛,他的槍比較多……這下子王蜀屏就關起,關到監獄里頭。這下子哦,白馬路的人,來了一批人哦,坐到大堂里不走嘞。要把我們客巴放出來嘞,老爺嘞,喊的,要把我們客巴放出來,不放出來不行。[3]115-116
平武縣干部當時多為“南下干部”,對藏區政治結構、藏民思維模式知之甚少,無從體會藏民的心理——“‘王老爺’和‘薛老爺’的地位遠遠大過皇帝——有關他們的神話傳說中,權力的象征,都是‘老爺’沒有皇帝”[3]110。從中央到西南局三令五申民族工作必須“慎重”,但就平武干部來說,長期的革命經歷及老(漢)區工作經驗使其很難理解民族政策對“封建人士”的優待,面對擁有武裝并極具政治影響力的少數民族上層(平武土司由漢人世襲是例外情況),執行政策時難免出現偏差。
重新取信于藏民,卻并非易事。從平武藏民的角度來說,紅軍長征曾途徑包括平武在內的川西北地區。田教授研究指出,當時川西北土司(官)“一邊倒”地站在國民黨一邊,是中共過左的蘇維埃階級政策所致;他分析指出,就土司、番官而言,當時的“左傾”政策損害其特權,至于下層藏民,十數萬紅軍進入地瘠民窮的藏區,客觀上造成了藏民的生存危機,難免引發“誤解、嫌疑甚至仇視”[10]。鄧小平的講話同樣可以佐證這一點,他在談及民族政策雖“寬”,但川西北少數民族卻半信半疑時說:
這有歷史上的原因,紅軍北上,在那邊是把他們搞苦了,這點我們見面當然要向他們賠禮說明這個道理。……這在當時是為了保存紅軍,沒有辦法的,把他們的糧食吃光了,他們吃了很大的虧。
歷史記憶對民族工作產生影響,似乎不可避免。1950年1月19日,平武土司王蜀屏、番官楊汝在給松潘各部落的信中寫道:
共產黨已與二十四年(即民國24年——引者注)不同了,尤其是對我們藏胞,說依然是照我們的舊習土司番官制,信奉我們自己的教,不拉扶出款,所來的解放軍都很和藹,連我們平武的衙門都未駐扎,我們在這里已經守了二十幾天城了,現在正準備去打胡宗南的敗匪,繳得的槍支,說就交給我們,所以我們很喜歡,等到我們槍得到后,我們就回白馬路部落了,希望你們不要害怕,出來大家幫忙,說這些共產黨最為關顧我們,以這幾天看來,是確實的,特此布達。[11]118
這封信的本意,是贊揚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然而,其對“共產黨已與二十四年不同了”的特意強調,也反映了歷史積怨與繳槍事件造成的疑懼疊加給疏通藏漢關系帶來的障礙。番官楊汝雖因阻截國民黨潰軍受過表揚,但他對人民政府仍然“半信半疑”,川北區首屆人民代表會議邀其出席,他因“心有疑慮”而不敢赴會,川北行署各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再次邀請他參會,他還是不敢去[12]74。這種疑慮,在當時平武藏民中間頗具代表性,雖然最終有代表參加了會議,卻是在“地下黨和民主人士的動員”下勉強成行的。川北行署也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是“以恐懼心理來試探我們的政策”[9]44。
據川北行署總結,這次會議經“解釋”及“會議期間事實的證明”,消除了藏民的“疑懼心理”,知道了共產黨及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扶助是真誠的扶助”。行署的樂觀態度并非沒有根據。藏族代表出席各代會,緩和了關系;藏族代表除關心發還槍支外,還提出了“恢復部落制度”的政治要求,理由是平武藏區“歷為長官司、土通判、土知事、番官頭人制度”,在國民黨統治下,遭到“完全廢除,實行保甲統制,派任外籍漢人充任鄉保長以極盡壓迫剝削”[13]19。平武解放初期,地方政府似乎也對藏民有過類似的承諾,王蜀屏和楊汝聯署的《給松潘各部落的信》中,就曾提到共產黨說“依然是照我們的舊習土司番官制”。
藏民要求的“部落制度”,與后來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相去甚遠。就川北行署來說,當時并沒有具體的操作辦法可資參照,不可能對“民族區域自治”有后來那樣清晰完備的界定。川北行署的當務之急,是竭力彌合因繳槍事件而與藏民產生的裂痕,這不僅關系著與藏民的團結,更事關整個平武縣的安靖。就在川北區首屆人民代表會議召開期間,平武縣爆發了震動川北的“六·二六反革命叛亂”。這次叛亂,“持續二十天,影響方圓三百余里,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全縣四個區二十二個鄉、鎮,除第一(古城)、第二(水晶)兩個區外,其余……都同時發生了叛亂”[14]8,意味著除藏族聚居的水晶等個別區以外,整個平武縣均陷入了叛亂局勢。此時,穩定藏區局勢,對川北行署而言,已顯得十分急迫。于是,川北行署對藏民的要求迅速作出回應:
根據共同綱領第六章民族政策,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平武藏胞居住區可依原有慣例,恢復部落制度,免去一切負擔。[13]19
川北區首屆人民代表會議決定設立“平武縣藏族自治委員”。胡耀邦接見了王蜀屏,囑其“回縣去和藏區番官、頭人起來參加平武藏族自治區的籌建,成立平武藏族自治區”[7]66。同時,行署委派專人赴平武指導籌備工作。1950年7月19日,“奉縣府召示,以王蜀屏為主任委員,楊汝為副主任委員的九人‘平武縣藏族自治區委員會籌備會’成立,積極開展籌備工作”[13]19。從川北行署制定的《平武藏族工作計劃》來看,“廢除保甲制度、恢復部落”,構成了川北行署在平武藏區創建自治區的基本思路。這一思路,與川北行署在首屆人民代表會議上對藏民的承諾并無二致。
三 平武藏族區域自治的特點分析
經過十余天的準備,1950年7月31日,藏民各部落土司、各寨大小番官和頭人53人,黨政軍首長、各單位代表70余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大會推選王蜀屏為主任委員、楊汝為副主任委員,朱俊章、王金桂、澤子修、牟扭扭、薛衍、楊發安等人為委員[7]19-20。需注意的是,“平武縣藏族自治委員會”是由“平武縣藏族自治區委員會籌備會”直接轉化而來,其間沒有召開建政所必須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不僅擔負著與少數民族溝通協商的職能,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為新建地方政權提供合法化依據。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格平在中央民委第二次委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有個別地區建立自治區時,未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原封不動,只換了一個名義,這是不合于民族民主建政要求的。”平武藏區創建自治區的情況,顯然在此之列。
王蜀屏出任主任委員的原因,首先是其合作態度。平武解放前夕,他就在“張秀熟同志影響之下比較進步”,又參加過山防隊(平武最重要的地方武裝)起義,是“配合解放平武有功”之人[9]45-46。根本原因則是他在平武藏區的巨大政治影響力,“解放前在未改鄉保甲制之前,連白馬、黃羊以及木座鄉次一里等地是一個土司(群眾稱老爺)管轄,土長官司署設黃羊。土司是王實秋,王實秋死后,由其弟王蜀屏世襲”。王蜀屏對平武藏民的政治影響不僅在于世襲的土司身份,而且因“繳槍事件”導致的“威信空前提高”[3]118。同時,王蜀屏還握有武裝。據說:“鬧事過后……成立一個藏族自治區,搞籌備工作,就喊王蜀屏來承頭。王蜀屏他有錢,有槍嘜。”[3]115
出自薛、王兩姓土司家族的王金桂、王信夫、薛衍,擔任了自治區下屬三個鄉的負責人。這意味著自治區從區到鄉的各級政權負責人均為平武藏區的傳統勢力,擁有一定政治影響力,又與人民政府建立了合作關系。副主任委員楊汝似乎是一個例外。他不是出自世襲土司家族,而是出身下層藏人。不過,此人善于鉆營,解放前即已謀取了番官職位,履職后“懂得籠絡番民”,“掌握了番寨的實權”[12]73,同樣屬于平武藏區的實力派人物。
自治區的創建過程,沒有觸碰平武藏區傳統的權力結構。各級自治機構負責人員的組成,均為擁有實質影響力甚至武裝的地方實力派;他們在自治政府中的職務高低,亦取決于他們自身影響力的大小以及對人民政府的態度。這個群體通過與人民政府合作,獲取其世襲權力在新時代的合法性;人民政府借助地方實力派的政治影響,向藏區基層拓展了自身的政治權威。有學者認為,繳槍事件及其引發的藏民疑懼,使人民政府“意識在國家和人民之間,需要一些中間層面的代理人”及“土司的重要性,不能一下子打倒,還要利用他們對少數民族的感召力鞏固新建立的政權”[3]114-115。新生的人民政府是否意識到需要一個“中間層面的代理人”,尚需進一步討論,但就平武藏區的實際情況來看,土司不能“一下子打倒”則為必然。
鄉級自治機構的建政方式為“恢復”部落制。8月3日,平武縣人民政府以民字第1號文“劃日新(今虎牙、泗耳)、又新(今黃羊關、白馬)、新民(今木座、木皮)三鄉屬該委員會所轄”。8月26日,自治委員會呈報縣人民政府:“鈞府民字第九號通知‘你會所屬新民、又新、日新三鄉,現已通知移交,希你會接管。’本會已派土司王金桂會同番官牟扭扭前往新民鄉接管;派代理土司王信夫會同番官楊發安前往又新鄉接管;派土司薛衍會同番官曲雞木前往日新鄉接管。”所有鈐記沿用舊有土司番官印信,部落名稱仍然照舊日土司部落制度,即黃羊大部落(原又新鄉)、白熊大部落(原新民鄉)、虎牙大部落(原日新鄉),現三部落已經接收清楚,各就職視事[14]20。
恢復部落制度,是平武藏族自治的重要特征。中央政府當時對部落制度的態度,筆者未發現相關的正式表態。不過,鄧小平在談及西康省東部的民族區域自治時的報告中曾涉及到這個問題:
譬如在這區域自治里面,康東過去劃的有縣,縣也有一二十年的歷史了,保存不保存這個縣呢?在一定程度上說,縣當然是比部落進步,康東有一二十個部落,從發展前途看,保存縣是有好處的,而且已經是習慣了的,也有一二十年的歷史了,但他們贊成不贊成?有一個原則,他們不贊成就得取消,另外劃。
一方面,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意見,縣制存廢直接決意于其贊成與否;另一方面,隱含著對縣制和部落制的看法,即“縣是比部落進步”,“從發展前途看,保存縣是有好處的”。值得注意的是,若出現少數民族“不贊成”的情況,鄧小平給出的方案是“就得取消,另外劃”,而取消的對象比較明確,就是“過去劃的縣”。“另外劃”指的是什么?筆者認為,“另外劃”的不應該是“部落”,部落是自然形成的,不存在“另外劃”的需要;“另外劃”的只能是“縣”,如果藏民不同意現行縣的行政區劃,那就要進行區劃調整,而不是恢復設縣之前的部落制度。
該報告時間為1950年7月21日,在“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成立前,報告的主要聽眾是來西南調查少數民族情況的中央訪問團正副團長及全體團員以及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相關工作人員。川北區恢復平武藏區部落制度的舉措,與這次談話精神不符。按照常理,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第一,川北區決策層不知有此談話;第二,川北行署主觀上并不認為“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成立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區域自治”。
川北行署是否知情,雖無法判斷,但西南局及西南軍政委員會對平武藏區的情況則肯定有所了解。根據不僅在于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是川北區黨委、川北行署的直接上司,還在于1950年7月26日西南局曾就《川北區黨委關于平武縣委對藏民政策發生錯誤問題的處理報告》做出過批示[9]44-48。令人費解的是,川北區的“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成立在即,鄧小平在談及民族區域自治時卻說“沒有經驗”,隨即談到為取得“經驗”必須“開步走”的試驗地域也并非平武藏區,而是康東藏區。王維舟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上的發言指出:“必須在西南很快選擇一個適當地區首先試行起來,由一點做起,取得經驗,然后逐漸推廣。”[15]9這個講話就在“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成立當天。顯然,就西南軍政領導當時的理解而言,川北行署籌建的“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也不在“民族區域自治”之列。
既有研究對“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的性質語焉不詳,但有學者曾提及平武藏族自治區后來的“被承認”,依據的是李維漢把“平武藏族自治區”視為當時存在的民族自治區三種類型中的一類[13]21。李維漢獲取平武藏族自治區情況的渠道,來源于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報告。中央民委曾于1950年3月21日、4月17日兩次電令西南民委呈報“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區的有關資料”,后者遂于當年5月15日將“平武藏族自治區”名稱、區域及面積、民族成份、人口、行政區劃、政府組織系統、人事配備及領導關系等情況上報中央。李維漢時任中央民委主任委員,其報告視平武藏族自治區為“民族自治區”的一種類型,他還據此認為“平武藏族自治區”得到承認并無問題。事實上,在中央“承認”之前,西南將平武藏族自治區情況上報本身,至少標志著當時西南軍政委員會已經認定平武的藏族自治區屬于“民族區域自治”范疇。不過,這時的“承認”,與西南軍政委員會在其建立之初的“不認為”并不矛盾。
四 結論
有學者認為,平武藏族自治區的建立,對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行具有“樣板”意義。就這個西南最早的民族自治區的具體情況而言,其干部配備特點、基層政權形態等方面均與以后的民族自治區創建模式捍格不入。我們據此認為,“平武藏區自治委員會”不僅對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具備示范效應,而且其創建自身也源自人民共和國初期平武特殊的局勢。繳槍事件惡化藏人與人民政府關系在先,平武大規模武裝叛亂繼后,川北行署為“控攏”平武藏民各部落、穩定局面而在平武建立藏族自治區,是為其創建的內在邏輯。這個自治區成立之前,因為沒有召開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本身甚至缺失必要的法理基礎。這個自治區后來經過多次“修正”,終獲西南和中央的“承認”,但是就其創建而言,并不屬于對“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有意而為。
通過考察平武藏區自治委員會的成立過程,可以看出“試驗階段”籌建的民族自治區,其成立有一定偶然性。就平武藏區自治委員會來說,是川北行署因應行政危機的產物。地方政府雖援引了《共同綱領》的相關條款,其初衷卻是為恢復轄區的社會秩序。這一時期的民族自治區籌建,體現的是中央關于民族區域自治頂層設計尚未及完善之際,地方政府為處置地方事務而對“民族的區域自治”政策的隨機使用。地方政府的實踐探索,有助于中央政府總結經驗,完善政策及制度設計。地方政府實施區域自治政策工作中表現出來的諸多不足,反映了完善頂層設計之迫切,亦為中央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并制定“實施細則”提供了借鑒。
注釋:
①基層干部對少數民族雖抱有同情心理,但當面對民族隔閡時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1949年甘肅洮河事件可謂典型。洮河東西兩岸分別為漢回族聚居地,兩族矛盾十分尖銳。上級在部隊過河以前曾動員戰士要正確對待回族人民,尊重回族的風俗習慣,向回族宣傳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團結爭取回族人民支援解放戰爭。洮河東岸的漢族也同時向戰士做“復仇的動員”,漢族群眾的訴苦,不可避免地對干部產生了“一定的蠱惑作用”,民族隔閡與積怨也影響了部隊干部戰士對民族政策的執行,以致發生洮河群眾暴動事件(參見:《西北局對甘肅平涼海原等地群眾暴動事件的指示》,《西南工作》1950年第6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編印,第7-10頁)。洮河事件并非個例,梳理當時印發的黨政內刊資料,類似案例在滇、黔、川、康等民族省份多有發生。
②四川省當時被劃為4個行政公署,川北區行署管轄南充、遂寧、劍閣、達縣4個專區。參見:《西南行政區劃》,《西南政報》1950年第1期“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專輯”,西南軍政委員會辦公廳編印。
③川北行署的4個專區中,劍閣專區少數民族數量最多,平武屬于劍閣專區。據1952年統計,劍閣專區少數民族人口數量總計15066人,絕對數字雖不少,但對劍閣專區的總人口而言占比甚小。參見:《西南各省少數民族人口統計表(1950)》,四川省檔案館:建大11-1-94。
④在未經民族識別的情況下,平武白馬人被歸為“藏族”的原因,據解放初擔任要職的張秀熟回憶:川北行署成立后,“根據‘共同綱領’和黨的民族政策,對轄區少數民族須作正名工作。當時缺乏鉆研民族問題的專家學者,因平武和松潘緊鄰,松潘‘沿習’稱藏族聚居區,遂亦劃平武白馬、火溪兩鄉及涪江西岸虎牙鄉民族為藏族”。詳見:張秀熟《平武“藏區”問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平武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武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87年,第8頁。
⑤川北平武白馬人的族屬問題以及土司王蜀屏的個人情況,不僅川北行署當時不甚了解,即使在今天依然存在學術上的爭論。參見:蕭猷源《平武白馬藏族》,2001年;平武縣白馬人族屬研究會《白馬人族屬研究文集》,1987年;曾維益、曾窮石《龍州土司述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綿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綿陽文史叢書》(之七),1999年。
⑥在“平武藏族自治委員會”成立后,川北行署于1950年10月27日至1951年1月26日派出訪問團前往平武、青川、北川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或雜居地區,宣傳黨中央、西南局以及川北區黨委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參見:川北區民族訪問團《川北區九縣回、藏民族的一般情況》,《川北政報》1951年第2卷第5期;肖猷源《建國初平武縣民族工作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平武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武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2000年,第2頁。
⑧⑩《本會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施政方針的意見(1950.3.21)》,四川省檔案館:建大11-1-1。
⑨《川北區當前施政方針》,該文件于1950年6月18日由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制定,1950年6月28日川北區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西南軍政委員會批準實施,詳見《川北政報》1950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