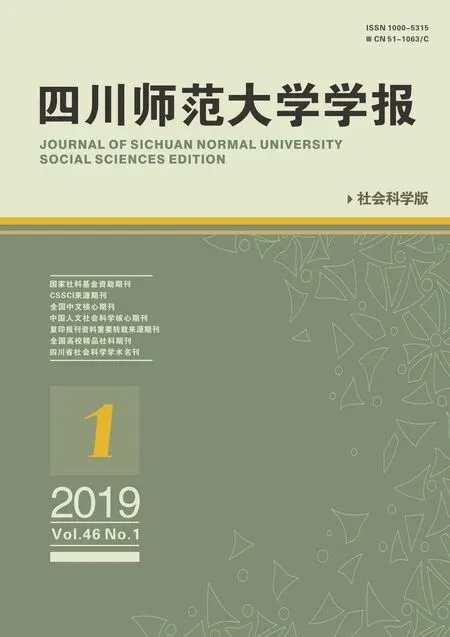十八大以來依規治黨成效論析
(電子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成都 610054)
古人云: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不以規矩則廢,黨不以規矩則亂。習近平指出,黨的規矩包括黨章、黨紀、國法以及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1]151。其中,黨內法規是中國共產黨立黨治國的重要規矩。黨的十八大以來,“講規矩”、“守紀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以規治黨”、“制度治黨”、“全面從嚴治黨”等理念折射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管黨治黨的決心和勇氣。研究黨的十八大以來依規治黨取得的成效,既是深刻了解黨內法規建設取得最新進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又是發掘全面從嚴治黨著力點的內在要求。
一 突破傳統立規理念
黨內法規是黨的生命線,依規治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獨特的政治基因。黨內法規概念由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之后,中共中央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在黨的文件中都使用過“黨內法規”或“黨規黨法”的表述,但由于歷史發展時期不同,各位領導人對黨內法規的概念、分類、功能、法理屬性、范圍的界定與認識并不完全一致,但依規治黨的理念是大體相通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內法規建設,黨內法規開創性建設、權威性認同達到新階段。對傳統立規理念的突破是新階段黨內法規建設最鮮明的標志之一,其核心要義在于將依規治黨作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將依規治黨作為與依法治國、制度治黨統籌推進的重要利器,為全面從嚴治黨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1.黨規定位:從軟性約束向剛性約束強化
黨內法規是不是法?黨內法規是硬法還是軟法?黨內法規是否符合法治的原則和要求?這些歷來是學界爭論的重要問題。就黨內法規與國法而言,二者分屬不同的規范體系,無論是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適用范圍、調整對象、規范效力、保障力量等方面都存在實質性不同,而基本范疇的差異,決定了國法與黨內法規硬法與軟法的分野、法治屬性與政策屬性的分野。但法規本身的屬性以及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特性決定了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分界并非涇渭分明,這就為法規法屬性的延伸提供了可能,為法規由軟性約束向剛性約束提供了可能。但可能轉化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或一定能轉化,因而需要進一步論證為什么黨內法規一定要從軟性約束向剛性約束轉化?如何實現轉化?以及轉化后如何處理黨內法規與國法之間的關系?
就為什么要轉化而言,可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證。一是黨內法規與國法在本質上具有共通性。依規治黨要求把黨組織活動和黨員個人行為納入黨內法規調整的制度軌道,依法治黨要求把政黨代表的公權力限制在憲法和法律所允許的框架內,二者都體現了法的規范性、約束性、強制性,當黨規與社會現象對立時可納入“法”范疇,與國法對立時,可納入政策范疇,黨規的雙重屬性要求其在運行實施中充分考量規范性和政治性的平衡。二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黨內法規建設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習近平在講話中反復強調嚴明黨紀、強化制度權威、嚴格執行黨規的重要性,并以“帶電的高壓線”與“橡皮泥”、“紙老虎”、“稻草人”對比來說明黨規的剛性約束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將黨內法規的定位從政黨內部的行為規范上升到國家法治的行為規范。
如何實現軟性到剛性的轉化,主要體現為黨內法規制定者將國法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植入黨內法規,提升黨內法規規范化程度。從一般意義上講,國法強調強制性,黨內法規強調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等規范功能,因而黨內法規建設要體現強制性、剛性、效力,必須借鑒國法鮮明的法治原則和法治意識,將國法中成熟的語言、格式、體例、規范結構等引入法規,以提升黨內法規的剛性約束力量,從而推動管黨治黨不斷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比如,《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將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在頒布后對王珉、楊魯豫、楊振超等一批喪失理想信念的黨員干部進行了嚴肅處理,這個典型案例體現了黨規釋放出來的剛性約束力。
在如何處理黨規與國法關系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秉持“國法高于黨規”、“黨規嚴于國法”的原則協調、銜接二者之間的關系。在立規方面,黨規制定者嚴格按照《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在黨規內容、黨規規定事項、黨規合法性、黨規實施、黨規評估等方面始終將國法的至上性作為最根本的考量因素。立規之嚴,體現為黨規較之法律在某些事項上更為具體、嚴格;在黨員與普通公民個人利益、公共利益沖突的處理上,對黨員更為嚴格;在黨員失職行為或瀆職行為的處理上,比國法更嚴格。二是黨中央雖主張強化黨規的剛性約束力,但始終堅持黨外事務由國法來調整,黨內事務由黨規來規范的標準,力求從內外兩個層面構筑規范權力運行的制度牢籠,鞏固政黨的執政根基。
2.問題導向:從“問題—回應”機制向“問題—防范”機制轉化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管黨治黨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強烈的問題意識是共產黨人制勝的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直面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問題,堅持把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切中黨內問題要害,對癥下藥,“四風”問題、腐敗問題、違紀違規問題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黨風、政風、民風日漸清朗。在同一系列具備歷史新特點的腐敗問題斗爭過程中,問題解決思路實現了從“問題—回應”機制向“問題—防范”機制的轉化。“問題—回應”機制,也可理解為“刺激—反應”機制,旨在解決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黨風黨紀問題,著眼于法規的立即效應,屬于“頭痛醫頭,腳痛治腳”的被動立規現象;而“問題—防范”機制遵循“發現問題—處理問題—防范問題”的思路,不僅致力于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更強調以“問題倒逼機制”,借力于問題的解決,來謀求更長遠的防范戰略,著眼于法規的長期效力和普遍適用性。
“問題—回應”機制與“問題—防范”機制最大的區別在于能否使管黨治黨問題適應于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能否對“問題怎么來、問題怎么去、問題怎么防范”作出科學的戰略分析與規劃,能否從根本上解決黨內存在的制度性、體制性障礙,在重點突破與全局統籌中維持黨組織的肌體健康。一個先進的政黨總是能找準時代問題,謀求長遠發展,這是對我黨先進性最鮮明的寫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黨勇立時代潮頭,不但解決了許多過去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且對如何治黨管黨問題有了更加科學性、系統性的認知。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執政環境、執政風險、執政考驗更為復雜,黨內突出性問題仍將長期存在,黨內新問題將會層出不窮,而且問題存在領域和存在形式會隨著全面從嚴治黨的推進而發生變化。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的嚴峻考驗,我黨以強烈的問題意識為導向,將反腐“永遠在路上”,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制度建設“永遠在路上”,趕考“永遠在路上”,作為堅定不移的治黨方針,并將“發現問題—處理問題—防范問題”的問題導向思路作為黨內立規的前提,不求法規大而全,但求法規務實、有效,借以通過制度性規范主動回應現實問題的需要,如黨內反腐法規體系中同時蘊含了預防腐敗、規制腐敗和懲治腐敗三大功能。簡言之,從“問題—回應”機制向“問題—防范”機制的轉化,使黨內法規更具針對性,有效解決了黨規與規范對象之間空對空或錯位問題,推進了黨內法規整體建設的科學性。
二 改進傳統制規技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器”之“利”是力度和質量的規定性,于制規而言,黨內法規之“利”指法規的含金量與規范性,而“利”既來自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指導,又來自黨內法規建設與時俱進的實踐探索。
1.法規制定:從“數量型立規”向“質量型立規轉變”
“數量型立規”側重制定,重數量輕質量;“質量型立規”強調立改廢并舉,重質量輕數量,但輕數量并非限制數量,而是要根據黨建要求制定法規。如:2016年,被媒體認為是黨內法規建設的關鍵之年、完善之年,黨內法規出臺不僅數量多而且分量重。2017年6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強調:“制定黨內法規制度必須牢牢抓住質量這個關鍵,方向要正確、內容要科學、程序要規范、保證每項黨內法規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2]而應該如何界定法規的質量呢?操申斌認為:“權力配置的科學性是判斷法規質量的標準。”[3]王建芹、農云貴認為:“規范效果與供給能力是判斷法規質量的標準。”[4]科學配置指優化權限、遵守法定程序、合理設置法規結構、規范黨內權力運行、實現黨內利益平衡、反映民意。而只有科學配置的黨內法規,才能起到管黨治黨的規范效果,也才會有強大的供給能力來回應現實問題的需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質量型立規的突破首先體現在集中清理新中國成立至2012年6月出臺的2.3萬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在黨中央《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關于廢止和宣布失效一批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決議》兩部黨規文件的明確指示下,經過修改、廢止、解釋、備案、清理、評估等集中處理,“廢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繼續有效的487件,其中42件需適時進行修改”[5]。此次大規模的黨規文件清理以質量為關鍵,有針對性地解決了制度體系內一批過時、老化、質量不高、功效不大的黨規,及時彌補了黨內規范的缺陷,促成了黨內法規體系的良性循環機制,為實現良規善治帶動黨內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黨內法規質量型立法的第二次突破,體現在黨內法規體系形成了從“點”上體系性建設到“線”上體系性建設到“面”上體系性建設的轉變,也就是當前黨內法規體系已經實現了從單一法規針對解決或規范某一問題或某種行為,到多項法規銜接而成的制度合力針對解決或規范不同問題或不同行為,再到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協調解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問題。法治系統是否體系化,是判斷法治系統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黨規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過程,也是不斷追求黨規體系化的過程。體系化建設要求按一定順序和邏輯建構不同性質的黨規、同一性質的黨規以及黨規與國法之間的配套實施,使制度之間環環相扣、層層發力,最大限度形成法規1+1>2的制度合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內部、黨內法規與國法之間越來越凸顯的協調性,折射了黨內法規質量的整體提升。
2.黨規聯結:從孤立零散向體系化轉變
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統的方式存在和處于系統之中的,只有要素與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才能產生系統的最大效應。黨內法規建設亦是一個全面的系統,只有各項法規之間協調、配套與銜接結合成一個內部和諧統一的網絡系統,才能發揮法規的聯動效力。王長江認為:“一個個具體的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并不是真正的制度,這些只能算作是形成制度的要素。制度是這些要素之間的有機聯結,形成的網絡系統。”[6]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內法規的體系化建設,2013年11月頒布的《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首次公開提出在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宏大目標[7];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強黨內法規建設”,“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8];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增強依法執政本領,加快形成覆蓋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方面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加快和改善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9]。可見,實現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化是黨內法規建設的重點。
李忠認為,“強化黨內法規的體系性,一是要求黨規體系內部的耦合與統一,即不同黨規部門之間、不同類型的黨規之間、不同位階的黨規之間,做到上下配套、左右聯動、前后銜接、系統集成”[10]。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框架可概括為“三個四”:確立了黨內法規四層權力位階——黨章、準則、條例以及規則、規定、辦法、細則;規定了黨內法規的四類制定主體——黨中央組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各部門和省(區、市)黨委;形成了黨內法規制度的四大板塊——黨的領導、黨的組織、黨的自身建設、黨的監督保障。此外,黨內法規內部制度體系建設實現了三種形式的配套:基于主干中央層級的黨內法規制度配套黨章,如2016年新頒布或實施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涵蓋了黨員個人行為、作風建設、組織建設、紀律規范的方方面面,形成以黨章為統領、以責任為導向的“制度群”;具體的黨內法規制度配套基礎主干的中央黨內法規制度,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配套《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密切協調;地方黨內制度配套中央黨內法規制度,如《甘肅省實施〈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辦法(試行)》配套《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工作機關條例(試行)》。黨內法規體系化是促進黨內法規科學化、規范化的要求,有利于集中發揮黨內法規在管黨治黨方面的制度功能,以整飭黨風、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三 狠抓執規效力
黨內法規的生命力在于落實,落實的關鍵在于制度的可操作性、實效性。習近平指出:“要增強制度執行力,制度執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11]黨內法規實施較之于國法最大的優勢在于黨規借以黨建的手段和方式進行,從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兩方面協調推進,真正讓法規發力、立威。
1.制度落實:從條文規范向行為規范轉化
黨內法規實施的過程就是將靜態條文規范轉向動態行為規范的過程,這需要抓關鍵少數,發揮領導干部以上率下的示范作用,制定黨內法規督查計劃,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健全問責機制,實現問責追責常態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建設在執規主體、制規權限、審批程序、權力運行和制約機制、監督機制、懲處機制、保障機制、評估機制等方面都實現了重大突破,真正使黨內法規實現了“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的效力。比如,《中國共產黨自律準則》頒布后,黨員的權力觀、地位觀、政績觀都得到了改善,之前普遍存在的“四風問題”、請客送禮、公款接待、“三公”經費、辦事托人等都從整體上取得了直觀成效,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不同于《中國共產黨自律準則》的正面倡導,《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規定黨員干部不能干的“負面清單”,把紀律和規矩立在前面,加強了廣大黨員干部明確的行為底線意識,使其心懷戒懼,行有所止。《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頒布后,釋放了有錯必究、失責必問的強烈信號,規范和強化了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統計,2015年,全國共有850多個單位黨組織和1.5萬余名黨員領導干部被問責[12];2016年,全國共有990個單位黨組織和1.7萬名黨員領導干部被問責,立案780件,給予紀律處分730人[13];2017年前5個月,某省“問責507起,問責黨組織45個,問責領導干部698人,超過上年全年問責人數”[14]。《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頒布后,黨內監督工作全面加強,以“零容忍”“無禁區”原則大排除、大檢修、大掃除黨員干部的作風之弊、行為之垢,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切實做到了執紀沒有例外。《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頒布后,各地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紛紛在制度建設、問責黨內問題、開展黨組織活動等方面下功夫,切實提高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斗性,鍛造了黨員干部的政治品格和理想信念。
2.執規方略:從全面向更全面轉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的執行體現了全面的特性,即執規內容無死角,囊括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建設各個領域;規范對象全覆蓋,上至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下至黨的最基層組織,都是黨內法規的輻射范圍,一律受到黨規的約束;制度建設全過程,黨內法規建設永遠在路上,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部署以來,黨中央更是將“全”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大老虎”還是“蒼蠅”,只要違反黨的紀律,就必定要受到相應處理,不允許有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存在,切實體現了紀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執規原則。
之所以說黨的十八大以來執規方略實現了從全面向更全面的轉化,是因為黨內法規打破了“法不責眾”“法不責微”的觀念,立下了“法亦責眾”“法亦責微”的決心。“法不責眾”“法不責微”的傳統觀念認為法律在“眾”與“微”前具有局限性與無力感,針對這個僥幸觀念,習近平明確提出“不以問題小而姑息,不以違者眾而放任”[15]90的觀點,只要違法違紀,不管人數眾多,還是問題細小,都不能姑息縱容,要堅持一查到底、有錯必究的原則。“法亦責眾”的典型案例體現為遼寧賄選案,經審理所有涉案人大代表全部被依法確認當選無效或依法辭職,被司法機關立案調查者多達50人,被紀委調查者多達431人。對此案件的處理,體現了黨中央治理腐敗的決心,堅定不移地同挑戰黨紀黨規黨法的黨員干部作斗爭的實踐努力。“法亦責微”體現為黨內法規既要抓大也不能放小,如果放縱“小便宜”“小方便”“小活動”“微腐敗”,遲早會釀成違法違紀的大錯。中央八項規定以及一系列準則、條例反復強調,抓黨的作風建設必須從小事抓起,必須防微杜漸,避免出現“沒查都是‘好干部’,一查就成‘階下囚’”的怪現象。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第八條對樹立良好家風作了明確規定,認為家風不僅是個人的小事,家庭的私事,直接關系著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好壞,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風正,才會有行為正。“法亦責眾”“法亦責微”是對全面從嚴治黨的生動注解。
3.黨規“溢出效應”:黨規的規范性范圍擴大
黨內法規的“溢出效應”指,“黨內法規的效力超出了對其所應調整的主體、事項、時間、空間等范圍,對非調整對象的黨組織、黨員,或是對非黨組、非黨員產生了影響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約束力”[16]25。對于黨內法規為什么會有“溢出效應”,學者觀點不一。少數學者認為是黨規自身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多數學者認為是黨規制定者的巧妙設計。
對于黨內法規的“溢出效應”目前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認為,黨規的“溢出效應”指黨規超出了規范的制定范圍,起到了普適性的作用[4]。黨內法規中的“溢出效應”最典型的體現為中央八項規定的頒布中央八項規定頒布的初衷在于規范中央政治局的全體成員,并未對除此之外的其他成員作出明確規定,但是中央八項規定一經出臺就在國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并由此催生了一個特有的名詞——“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而此精神的影響范圍遠遠超出了對特定規范對象的影響力,對全國所有的黨員干部以及社會人士都產生了連鎖效應。中央八項規定作為一種精神而言,是基于黨建思維抓黨的作風建設,同時通過中央政治局領導以上率下的行為弘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中央八項規定的“溢出效應”,促使黨員干部將他律與自律結合起來,將外在法規的剛性約束與內化于心的信念約束相結合,實現黨規的優化效應。另一種解釋認為,黨規的“溢出效應”指黨規介入了國法的規范范圍17]。如《關于黨員領導干部述職述廉的暫行規定》(中辦發)、《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中辦國辦聯合發文)、《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中辦國辦聯合發文)、《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中辦國辦聯合發文),這四部法規雖然都是黨內法規,但均是對現實中所暴露出來的一些社會問題所進行的規定,超出了黨規的規范范圍。而相應的法律條文并沒有作出相應規定。盡管黨規對這些社會問題的規定起到了規范效果,但問題本身的屬性決定需要國法的介入和調整,實現黨規與國法之間的互補與銜接。有一些學者認為,黨內法規的“溢出效應”會造成黨規與國法之間的界限混亂。但本文認為,黨規與國法雖有共通性,但二者畢竟屬于不同的規范體系,而這并不影響二者協調和銜接,從內外兩個層面構筑權力運行的牢籠,共同致力于治國理政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依規治黨在立規理念、制規技術、執政效力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構成了管黨治黨、從嚴治黨的黨內治理新格局。但必須明確的是,目前黨內法規建設成效還處在一個新的起步階段,黨內法規建設現狀與目標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存在很多問題,如黨員對黨內法規認識不足、黨員干部責任意識不強、黨員參與黨內法規建設動力不足、黨內法規體系還不健全、黨內法規質量還不夠高、黨內法規執行力還不夠、黨內法規人才隊伍建設相對滯后、黨內法規評估制度功能有待提升等一系列問題,因而必須將黨內法規建設作為學界研究的重點課題,加強黨內法規基礎理論研究,構建黨內法規理論體系,為黨內法規建設提供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