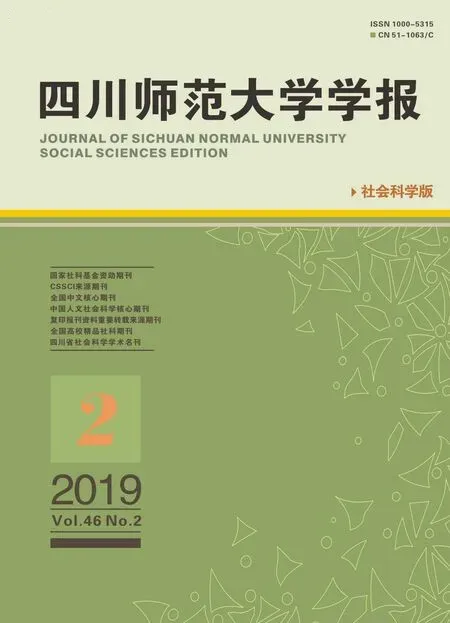人,詩意地棲居:“前臺-帷幕-后臺”模式下主客的凝視與對話
——評楊振之教授新書《東道主與游客:青藏高原旅游人類學》
(四川大學 旅游學院,成都 610041)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旅游人類學的研究熱點一直集中在民族旅游上,其投射焦點主要在于“旅游開發規劃”與“民族文化保護”之間的二元矛盾。自此,民族文化成為旅游人類學研究的進入視角和核心內容,并引發了許多有關旅游開發背景下文化商品化、文化舞臺化、文化真實性、文化變遷與傳承等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的研究為旅游人類學的中國本土化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也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將“文化”等同于“人本身”,以“文化研究”代替“人的研究”,導致旅游人類學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仍然不自覺地復制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范式,無法充分體現出“旅游”與人類學的關系及其意義,也使得國內旅游人類學研究難以突顯出自身應有的情景性與獨特性。
然而,眾所周知,旅游是一種由人所發起的文化實踐活動,文化也是一種被人創造出來的思想表達。因此,要想揭示旅游人類學的核心命題之一——旅游開發對東道主社會文化的影響,具體包括對傳統文化和社會變遷的影響,則需要關注創造文化的“人”——“東道主與游客”這一對旅游人類學中的經典二元關系。恰在此時,《東道主與游客:青藏高原旅游人類學研究》一書給予了我們“雨后逢甘露”的相贈,重新從“人”的視角出發,以其深厚的哲學人文知識與扎實的田野調查工作為基礎,批判性地對旅游人類學中的“主客關系”這一傳統命題進行了重新審視與思考,系統而深入地揭示出“旅游的符號化與符號化旅游”、“旅游真實性”、“凝視與對話”、“前臺-帷幕-后臺”、“旅游的本質”等幾個基本旅游研究問題之間的邏輯關聯,以及它們對東道主社會空間重塑與有效管理的意義和價值。這無論是對旅游人類學從“西學”走向“東漸”,還是對旅游基礎學從“實踐”走向“理論”,都是一次思想和實踐雙贏之成果。
本書選取了以藏族文化為主體、地處民族文化走廊的青藏高原旅游業發展為實地案例調查對象,全面有代表性地擷取了云南麗江古城、西藏山南手工藝、四川九寨溝歌舞表演、汶川地震前后羌族村落等幾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階段的旅游發展空間片段,借鑒性地運用了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論、卡西爾的符號創造論、戈夫曼的“前臺-后臺”等理論,由點到線到面,以歷時性與共時性的雙維視角勾勒出了青藏高原旅游業發展對民族傳統文化和地方區域社會的影響圖景,再次對旅游的社會文化影響這一傳統議題做出了創新性的研判與思考,其中一些概念、觀點和思想,無論是對旅游人類學的中國本土化發展,還是對提升民族旅游體驗質量及其目的地有效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一,東道主問題的研究。首先,關于“東道主”概念的重新定義。傳統意義上的東道主,通常指的是旅游目的地的原住民群體。而本書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發現旅游人類學中“主客關系”中的“主”這一角色,已不再僅限于原住民群體的討論,而是除了原住民之外,還有屬于非原住民的長期居住的旅游業的參與者,如云南麗江的“從陌生人到旅居者再到客棧經營者”,如九寨溝來自不同地區民族歌舞表演者的加入,如西藏手工藝品生產的本地化與外來者等等。這些成份各異的參與者和原住民群體共同組成了所謂的“原住民社區”,并扮演了“主客關系”中“主人”這一角色,甚至于其中的非原住民東道主比原住民還要更活躍。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在旅游供給越來越多樣化的大環境下,旅游目的地“東道主”這一概念內涵與外延的演變問題,這對當前旅游目的地空間管理與秩序重建提出了新的挑戰與更高的要求。其次,東道主的文化變遷問題。文化變遷,一直是以往旅游人類學討論頻次最高的問題之一。本書依然是從真實性角度出發,但不再拘泥于旅游目的地文化“是真是假”的傳統二元論爭辯,而是創新性地從事實的、認識的、信念的三個層面出發,在邏輯層面上理順并構建了一個“真實性”的體系,形成了旅游中的事實性真實性、相對性真實性到絕對性真實性的“真實性”體系,同時將以往學術界提出的舞臺化真實性、客觀性真實性、存在性真實性、自然生成的真實性等理論進行分層并納入這一體系,通過對大量旅游案例的研究,提出對事實性真實性和相對性真實性的討論,在本質上并無多大意義;而從存在主義角度出發的自我真實存在,卻可以使得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完成找回自我、回歸自我和實現自我的過程,以此突顯旅游的本質——“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一前所未有的新理念。再次,東道主的成長問題。作者有針對性地辨析了“旅游的符號化”與“符號化旅游”這兩類不同概念,指出當前大多數被批判的文化過度商業化、文化表演膚淺化、文化景觀舞臺化等問題,均屬于旅游的符號化這一概念范疇,并認為那些以虛假、拼湊、混亂的文化符號碎片來敷衍游客的做法,根源于東道主對自身文化不自信的事實。在此基礎上,又很有見地地提出了“前臺-帷幕-后臺”的保護與開發模式,通過“前臺”對“后臺”的經濟補償方式以及“后臺”為“前臺”提供原汁原味的食品、手工藝品等獲利方式,慢慢等待東道主社區一小部分文化先知先覺者傳承文化以及他們在文化上的自信和自我強大之后,方可構建起平等的主客關系。
第二,游客問題的研究。首先,游客的體驗問題。本書從存在主義角度出發,對傳統的游客體驗問題進行了拷問,以更高的哲學視野角度對旅游的本質問題進行了俯瞰式審視,新穎地提出了“人,詩意地棲居”這一有關旅游體驗本質的問題,認為“旅游雖然是人在形式上的空間移動行為,但本質上卻是走向遙遠生活的居住,是獲得自身顯現的詩意地居住”,“人,因此獲得存在的意義”。這一觀點可謂是對“旅游的本質是體驗”這一早已被公認言論的理論升華與醍醐灌頂。同時,也創新性地詮釋了“人為何旅游”這一常規性問題,有助于我們從旅游需求的角度來幫助優化旅游相關供給。其次,游客的參與問題。作者憑著對符號學理論的深刻理解與大量的旅游行為案例調查,提出了與旅游符號化相反的“符號化旅游”這一新概念,指出游客通過參與旅游地社區的文化創造而完成與原住民共同創新其原有文化價值的奇妙過程。在這里,作者第一次突破游客不僅僅是“看”的主體,不僅僅是一種被動的存在,也特地指出為東道主社會創造符號與生產符號的主體,是一類充滿了活力與熱血的客人,以自己的文化知識和文化理想與東道主進行不知覺的互動,在那么一個或幾個“閾限”的時刻里反“客”為“主”,為旅游目的地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與元素,也為東道主傳統文化賦予了鮮活的生命與意義,充分詮釋了“人”的主體性與互動性。再次,游客的成熟問題。符號化旅游要求旅游活動從只滿足于表演性的“前臺”體驗到一種深層的、對具有豐富涵義的文化內涵的“后臺”文化的追問和互動中去。本書不僅看到了東道主的成長問題,也闡釋了游客的成熟問題。在游客不成熟的前提下,游客對東道主社會文化的消費,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殖民心態,是一種毫無理由的優越感存在。然而,隨著游客消費心態的成熟,對于部分散客、文化旅游者來說,他們需要深入了解原生文化的內涵,希望可以長時間停留,或去“深入調查”。因此,對于“后臺”的規劃,就更加有必要和重要,只有讓游客以適當的方式走進“后臺”,才能真正實現與旅游地原生文化的互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旅游地社區居民對自身文化的覺醒與創造。因此,以“前臺-帷幕-后臺”的有效空間分隔管理來實現對游客行為的規范與引導,有助于實現主客的共同凝視。
第三,東道主與游客的關系。作者以深具人性化光輝的思想,對傳統的“旅游凝視”理論進行了反思及其批判,并以“對話理論”為起點,提出東道主與游客的關系,應該從“凝視”與“被凝視”,通過地域性資源的資本化策略、民族文化在旅游開發中的空間重構、符號化旅游的創造與激勵、前臺-帷幕-后臺不同空間管理策略等方式,最終走向東道主與游客之間的平等對話階段。特別地,以云南麗江古城文化調查為基礎,提出了對話應該包括“對話傳承文化”、“對話創新文化”,剖析了來自廣闊社會背景的游客,是如何在對話過程中完成了從陌生人到旅居者再至旅游地社區新主人的華麗轉身。同時,作者還深刻指出,對話,不僅僅限于傳統文化層面上,同時那些跨越時間、空間、方式的限制而進行主客情感平等的交流與表達,其實質可促成精神上的相遇,為展開新一段主客關系和社區旅游持續發展提供新的源泉動力。并且,旅游社區和他們日常生活之間明顯的界限也會逐漸消解甚至于完全消失,以至于旅游業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生活完全融于一體,游客的旅游空間與居民的生活空間并不總是那么涇渭分明,這充分體現了作者勇于打破固有的二元論僵化思維、嘗試以后現代主義理論視野來對旅游目的地新出現的主客關系給予理論經驗性總結與升華。在此基礎上,作者還提出旅游目的地新型的主客關系,應該是從“殖民”走向“尊重”,從“優越”走向“平等”,從“壟斷”走向“共享”。如何真正實現呢?作者并未空喊口號,而是以西藏手工藝生產調查、汶川羌族文化空間重構等為例,在借助旅游場域和資本、行動者、慣習等理論概念基礎上,通過分析其中的資本空間分布、利益分配體系、地域文化生產等場景,提出以調適機制來引導旅游場域中的主客關系,讓傳統的不平等主客關系逐漸擺脫權力和資本的威懾,以國家話語、知識資源、地域資本等新元素的滲入來幫助東道主社會的原住民群體實現其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自尊與自豪感。最終,讓東道主與游客在旅游場域中實現主客之間平等、友愛、共享、共創的生活空間構建,以體現出旅游目的地主客關系中“人”的情感性與精神性,方可實現傳統文化保護傳承與游客“詩意地棲居”體驗之雙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