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詩(shī)歌在西夏和契丹的傳播
(四川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成都 610066)
一
公元11世紀(jì)前后,中原詩(shī)歌在向塞外傳播的過(guò)程中曾受到遼王朝的重視,最著名的記載見(jiàn)于《契丹國(guó)志》卷七,其中說(shuō)到遼圣宗“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番臣等讀之”[注]劉曉東等點(diǎn)校《二十五別史》,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2000年,第57頁(yè)。。白居易《諷諫集》的傳世本題作“白氏諷諫”,也就是所謂“新樂(lè)府五十首”,這組作品的內(nèi)容切中時(shí)弊且文字淺顯易懂,故而得以在后世廣泛流傳,其中的《賣(mài)炭翁》在今日更是童叟皆知。然而,令人費(fèi)解的是,西夏與契丹同為中原北方近鄰,統(tǒng)治階層同為少數(shù)民族,可是中原的詩(shī)風(fēng)僅在契丹廣為流行,在西夏卻沒(méi)有產(chǎn)生人們預(yù)期的影響。[注]《夢(mèng)溪筆談》卷五所載沈括的《凱歌》已為人們所熟知。里面有“天威卷地過(guò)黃河,萬(wàn)里羌人盡漢歌”的句子,這應(yīng)該是在軍中用來(lái)鼓舞士氣的,未必是西夏真實(shí)情況的反映。見(jiàn):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mèng)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5頁(yè)。即便是在當(dāng)時(shí)傳播頗廣的《白氏諷諫》,我們至今也只見(jiàn)到零星的摘引:
《觀螙》戊舅技,《癝緳》氦遍禑,肂篟銅,莎篟銅,堅(jiān)竤聻硵前篟銅。
[《陰符》三百字,《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這幾句詩(shī)來(lái)自《白氏諷諫》里的《海漫漫》,只不過(guò)“《陰符》三百字,《道德》五千言”在存世本作“玄元圣祖五千言”。[注]白居易著、顧學(xué)頡校點(diǎn)《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9年,第57頁(yè)。且不論這是否意味著原著所據(jù)的版本有異,現(xiàn)在的問(wèn)題在于西夏人翻譯的這幾句詩(shī)并不是來(lái)自《白氏諷諫》原書(shū),而是來(lái)自一部中原佛教著作《隨緣集》的轉(zhuǎn)述。[注]索羅寧《西夏文〈隨緣集〉與西夏漢傳佛教流傳問(wèn)題》,胡雪峰主編《元代北京漢藏佛教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與此相應(yīng)的事實(shí)是,20世紀(jì)以來(lái)出土的大量西夏文獻(xiàn)中,不但沒(méi)有任何中原詩(shī)集的譯本,而且竟然連漢文的原本也未見(jiàn)到。這應(yīng)該不是偶然的現(xiàn)象,而是反映了中原詩(shī)歌在西夏和契丹的境遇不同。
此前的研究表明,西夏人對(duì)漢文原著的理解水平遠(yuǎn)遜于中原學(xué)者,他們?cè)诜g《詩(shī)經(jīng)》之類上古文學(xué)作品中相對(duì)艱深的語(yǔ)句時(shí)甚至不知道參考傳統(tǒng)注釋,從而導(dǎo)致訓(xùn)詁方面的謬誤頻出。[注]聶鴻音《西夏譯〈詩(shī)〉考》,《文學(xué)遺產(chǎn)》2003年第4期。相比之下,如果漢文原作的語(yǔ)言通俗,則西夏人的翻譯有時(shí)就基本能夠讓人接受。例如西夏譯本《類林》卷七和卷九各收入了一篇漢武帝《秋風(fēng)辭》的譯文[注]К.Б. 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224-225,519.,這兩篇譯文用字略有不同但表達(dá)的內(nèi)容一致。克平通過(guò)對(duì)詩(shī)歌的意象分析,認(rèn)為譯文符合“信達(dá)”的標(biāo)準(zhǔn),而且還體現(xiàn)出了一定的翻譯技巧。[注]K.B. Kepping, The Autumn Wind by Han Wu-di in the Mi-nia (Tangut) Translation, Б.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ост., Kсения Кепинг,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Омега, 2003.
卷七譯文
吻糣霹城緩竤超
荍砃連城綢蒼縹
乓砃挖城蚹鍵粔
眛冊(cè)返城蘞臀薵
況浦繰襲繼娟紂
澎碟疤城糬祊緢
芅蚗徑城繼罞哺
葒疤纁城糺絧癏
卷九譯文
吻糣霹城緩竤超
茋砃連篎綢蒼臲
乓砃蛙挖蚹鍵粔
眛冊(cè)返簄糾臀嘩[注]最后三個(gè)西夏字的意思是“不可忘”,不合于《類林》原文的“不可依”,反倒合于傳世本《秋風(fēng)辭》,這里面的原因尚不清楚,也許純屬偶然。參: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類林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9頁(yè)。
況浦繰碟繼娟膌
澎父紻晾糬祊紂
芅蚗徑城繼罞哺
葒疤纁城粙胎癏
漢文原作[注]西夏人據(jù)以翻譯的唐于立政《類林》原本已佚,這里的漢文來(lái)自金代王朋壽增補(bǔ)的《增廣分門(mén)類林雜說(shuō)》,與傳世《秋風(fēng)辭》略有不同。宋郭茂倩輯《樂(lè)府詩(shī)集》(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9年,第1180頁(yè))卷八四作:“秋風(fēng)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jì)汾河,橫中流兮揚(yáng)素波。簫鼓鳴兮發(fā)棹歌,歡樂(lè)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shí)兮奈老何!”
秋風(fēng)起兮白云飛,
草木黃兮雁南歸。
蘭有芳兮菊有菲,
思佳人兮不可依。
泛樓船兮濟(jì)汾河,
橫中流兮揚(yáng)素波。
簫鼓鳴兮發(fā)棹歌
歡樂(lè)盡兮哀情多
可以承認(rèn)這是兩篇比較成功的譯作,但是毋庸諱言,兩首西夏詩(shī)中都出現(xiàn)了一處對(duì)原文的理解錯(cuò)誤——第五句的“濟(jì)汾河”本來(lái)說(shuō)的是“渡過(guò)汾河”,而西夏文卻把“濟(jì)”音譯作“況”tsji,于是全句的意思就成了“樓船行駛在濟(jì)水和汾河里”。西北地區(qū)的多數(shù)人顯然并不知道濟(jì)水與汾河相距有數(shù)百公里之遙,一條船同時(shí)航行在這兩條河里自屬無(wú)稽。不過(guò)無(wú)論如何,譯者沒(méi)有把原文每句里的“兮”簡(jiǎn)單地對(duì)譯作西夏的語(yǔ)氣詞,而是分別處理成“城”(在…的時(shí)候)、“篎”(在…之后)、“襲”(在…之中),甚或處理成與前后語(yǔ)義搭配的實(shí)詞,這種靈活的翻譯手法還是值得稱道的。
中原詩(shī)歌在契丹的傳播以及遼代的文學(xué)水平已為學(xué)界所熟知。為了認(rèn)識(shí)中原詩(shī)歌對(duì)西夏的影響,我們首先應(yīng)該舉例分析一下西夏文獻(xiàn)里的譯詩(shī),并對(duì)其翻譯水平作出評(píng)價(jià),藉此可以對(duì)西夏人的文學(xué)語(yǔ)言理解能力形成初步的印象。
二
迄今見(jiàn)到的夏譯漢文詩(shī)歌全部來(lái)自中原著作的轉(zhuǎn)引,事實(shí)上都是西夏人在翻譯中原其他著作時(shí)連帶譯出的。不難認(rèn)識(shí)到,西夏譯者對(duì)詩(shī)歌的理解能力不及散文。例如《類林》卷七的“陳思王”條:
艱縦縑索蟟葇諜膿瞭,絧號(hào)疾晾,蹦禑妒:“舊蒤謀飼科寂息錄碽肒萯。蔲篟屬窾耳絹妹瞭十楚妒。”蟟葇艱縦殘槽寂碽屬,寂貢:“穩(wěn)瞮穩(wěn)菺葕,緪賒溺箌屬。鷗落蟬號(hào)膗,穩(wěn)魏蓙科穆。礌毋臷禿脜,商泉往絩緷?”縑索訂桅狼篟祤,疾絧兵。[注]《類林研究》,第156頁(yè)。
[長(zhǎng)兄文帝忌子建,心欲害之,故謂曰:“爾當(dāng)七步以內(nèi)成詩(shī)一首。詩(shī)不成則必定依法科之。”子建乃應(yīng)長(zhǎng)兄命為詩(shī),詩(shī)曰:“煮豆燃豆葉,釀醋取其味。枝者爐下燒,豆則釜中溶。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自沉默不言,害心止。]
《增廣分門(mén)類林雜說(shuō)》所引曹植那首著名的《七步詩(shī)》原文是: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注]《增廣分門(mén)類林雜說(shuō)》所引的這首詩(shī)與傳世本都不相同。《世說(shuō)新語(yǔ)》卷上首句作“煮豆持作羹”(劉義慶《世說(shuō)新語(y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頁(yè));《曹子建集》卷五無(wú)“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兩句(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第279頁(yè))。
對(duì)照兩個(gè)文本就能看出,西夏人把“豆在釜中泣”的“泣”譯成了“溶”,在這里等于說(shuō)“煮爛了”,意思不錯(cuò)但缺少了生動(dòng)。事實(shí)上現(xiàn)存的西夏詩(shī)歌極少用到“擬人”手法,看來(lái)黨項(xiàng)人對(duì)這種修辭格還不熟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漢文原作并不避諱用字的重復(fù)——“萁”“燃”“釜”“在”四個(gè)詞各用了兩次,“豆”用了三次,而西夏譯文除了“豆”(穩(wěn))之外都借助同義詞或者虛詞制造了用字的區(qū)別。看來(lái)譯者為避免重復(fù)用字還頗費(fèi)了一番心思,這雖然也屬一般的寫(xiě)作技巧,但效果并不理想。事實(shí)上,漢文原詩(shī)的重復(fù)用字可以理解為特意采用的藝術(shù)手法,西夏譯文反而讓人覺(jué)得多少有些喪失了原本的意味。尤其讓譯者感到為難的是“漉豉以為汁”一句——他明白“豉”是一種調(diào)味品,鑒于當(dāng)年河西地區(qū)的調(diào)味品只有醋而沒(méi)有豉[注]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番漢合時(shí)掌中珠》,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32頁(yè)。,他把“豉”譯成“醋”自然情有可原,可是這樣一來(lái)卻與詩(shī)的主題詞“豆”發(fā)生了矛盾——釀醋的原料主要是大米、高粱、小麥等,一般讀者恐怕很難理解豆子和釀醋有什么關(guān)系。
更有趣的是卷九“項(xiàng)羽”條征引的《垓下歌》:
兩嘻珊鍋祘融絳,瑪吵篟韌碈篟脭。碈篟脭窾莻耳粺,缽禛舊罏往肒底?[注]《類林研究》,第218頁(yè)。
[以力拔山氣蓋世,不逢吉時(shí)馬不近。馬不近則何所為,夫人爾今將做甚?]
《史記》卷七《項(xiàng)羽本紀(jì)》所引這首歌的原文是: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shí)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注]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3年,第333頁(yè)。
對(duì)讀一遍就可以感到西夏譯文簡(jiǎn)直荒唐——“逝”的意思是“往”,在這里竟被譯成了“近”(脭),全句也被理解成了“沒(méi)遇到好時(shí)節(jié),連馬都不親近我”,動(dòng)作的方向完全反了。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本來(lái)是項(xiàng)羽內(nèi)心思忖“我該拿虞姬怎么辦”,而西夏譯文卻是在問(wèn)虞姬“你現(xiàn)在想要干什么”,好像在說(shuō):夫人你打算自殺么?
縱觀存世全部中原文獻(xiàn)的西夏譯本,可以說(shuō)佛教經(jīng)典的翻譯水平最高,世俗著作明顯稍次,至于零星出現(xiàn)的中原詩(shī)歌,其翻譯水平就更是等而下之。黑水城出土的《類林》是西夏時(shí)代僅有的幾種官刻本之一,鑒于官刻本都是為政府服務(wù)的,因此可以相信擔(dān)任底本翻譯工作的一定是西夏最有學(xué)問(wèn)的文臣,而現(xiàn)在我們看到他們的漢文化知識(shí)尚不過(guò)如此,那么民間的狀況可想而知。例如唐代裴休為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寫(xiě)的敘言里三次征引《毛詩(shī)》,分別是《大雅·抑》的“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及《小雅·蓼莪》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和“顧我復(fù)我”,而相應(yīng)的西夏本僅簡(jiǎn)單翻譯了注疏,三處經(jīng)文竟然全被略去未譯[注]聶鴻音《西夏文〈禪源諸詮集都序〉譯證(上)》,《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顯然表明民間譯者對(duì)正確翻譯這幾句古詩(shī)缺乏信心。由此想來(lái),西夏不像契丹那樣有過(guò)中原整部詩(shī)集的譯本,這應(yīng)該是國(guó)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所導(dǎo)致的必然結(jié)果。
三
據(jù)遼金元三代的史料可以得知,作為統(tǒng)治階層的少數(shù)民族中間雖然有些人兼通漢語(yǔ),但總?cè)藬?shù)肯定遠(yuǎn)遠(yuǎn)少于不通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的漢人。由此估計(jì),中原詩(shī)歌對(duì)西夏境內(nèi)漢人的影響要大于黨項(xiàng)人,或許如宋人葉夢(mèng)得《避暑錄話》卷下所記:
余仕丹徒,嘗見(jiàn)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傳之廣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shuō)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8頁(yè)。
這話未免有些夸張的成分,但畢竟足以說(shuō)明柳永的詞作也受到了不少西夏人的歡迎。我們知道,北宋著名作家柳永的作品不專注典故的鋪陳,喜歡以平易的字句細(xì)致地描寫(xiě)市井風(fēng)物和文人志趣。可以想象,他那些長(zhǎng)篇的“慢詞”有利于在充斥著綺靡之風(fēng)的北宋都市傳播,不過(guò)在半農(nóng)半牧的西夏郊野卻未必能夠大行其道,若想把那些纖巧的詞句譯成西夏文更是難上加難。事實(shí)上,就像在中原一樣,柳詞在西夏的傳播范圍也應(yīng)該主要局限于附庸風(fēng)雅的漢族文人和歌伎之間。古來(lái)的下層知識(shí)分子大都有附庸風(fēng)雅的習(xí)慣——1991年在寧夏賀蘭縣的拜寺溝方塔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本殘損嚴(yán)重的漢文詩(shī)集[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溝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65-286頁(yè)。,其中存詩(shī)七十余首,全部詩(shī)作的用韻和平仄搭配基本符合格律要求,但遣詞和立意均未見(jiàn)高妙,作者只是套用了中原古人一些現(xiàn)成的意象和個(gè)別名句以敷衍成篇。例如其中一首佚題詩(shī):
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fēng),衡門(mén)反閉長(zhǎng)蒿蓬。被身□□□□碎,在□□□四壁空。歲稔兒童有餒色,日和妻女尚□□。□□貧意存心志,□恥孫晨臥草中。[注]湯君《西夏佚名詩(shī)集再探》,《西夏學(xué)》2016年第12輯,第160頁(yè)。
這首詩(shī)只有首聯(lián)保存完整。很明顯,第一句套用了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里的“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fēng)日”[注]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六,北京:中華書(shū)局,2010年,第175頁(yè)。,第二句套用了杜甫《秋雨嘆》里的“反鎖衡門(mén)守環(huán)堵”和“老夫不出長(zhǎng)蓬蒿”[注]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shī)詳注》卷三,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9年,第218頁(yè)。。對(duì)比一下原作的格調(diào),可以體會(huì)到,陶淵明是在無(wú)奈中渲染隱居的閑適,杜甫是在孤獨(dú)中抒發(fā)現(xiàn)實(shí)的憂思,而這位西夏作者卻只是在不住聲地哭窮,心靈境界未免太低。必須承認(rèn),這本惟一存世的西夏漢文詩(shī)集稱不上佳作,作者只是套著格律做些表面文章,描寫(xiě)景物時(shí)缺乏獨(dú)特的想象,抒發(fā)心境時(shí)缺乏細(xì)膩的情思,只不過(guò)多少受過(guò)一些近體詩(shī)的創(chuàng)作訓(xùn)練,也讀過(guò)一些前代的作品而已。詩(shī)集的作者大概是12世紀(jì)末賀蘭山下一個(gè)貧寒的鄉(xiāng)村文人[注]聶鴻音《拜寺溝方塔所出佚名詩(shī)集考》,《國(guó)家圖書(shū)館學(xué)刊》2002年“西夏研究專號(hào)”。,也許還有個(gè)別上層官吏參與應(yīng)和[注]湯君《拜寺溝方塔〈詩(shī)集〉作者行跡考》,《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第2期,第91-96頁(yè)。,他們模仿中原格律詩(shī)時(shí)總不免“形似而神不似”,或許這就是西夏境內(nèi)下層漢族文人的普遍水平。
至于黨項(xiàng)上層人士創(chuàng)作的漢文詩(shī)歌,可以說(shuō)目前幾乎沒(méi)有資料可尋,惟一的線索是銀川西夏王陵殘碑上保存的31個(gè)字:
……芝頌一首,其辭曰:
於皇……俟時(shí)効祉,擇地騰芳。金暈曄……德施率土,賚及多方。既啟有……[注]寧夏博物館(發(fā)掘整理)、李范文(編釋)《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圖版肆陸。
如果判斷最前面殘佚的字是“靈”,那么“靈芝頌”就可以對(duì)應(yīng)《宋史》四八六《夏國(guó)傳下》記載的夏崇宗乾順于1139年作《靈芝歌》一事:
[紹興]九年,夏人陷府州。靈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shū)相王仁宗和之。[注]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7年,第14023頁(yè)。
碑上那首殘?jiān)娎锏摹办痘省笔滓?jiàn)于《詩(shī)經(jīng)》,“多方”首見(jiàn)于《尚書(shū)》,這兩個(gè)詞早已退出了當(dāng)時(shí)人們的日常生活。假如那詩(shī)確是崇宗本人所作,則其對(duì)古漢語(yǔ)的熟悉程度是值得夸贊的,不過(guò)史籍里沒(méi)有關(guān)于崇宗文化水平的具體記述。
此外我們?cè)贈(zèng)]有見(jiàn)到西夏君王撰寫(xiě)的詩(shī)歌,值得注意的只有黑水城遺址所出的一部手抄本詩(shī)集[注]梁松濤《西夏文〈宮廷詩(shī)集〉整理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這部詩(shī)集收錄了西夏大臣的作品三十首左右,全部為無(wú)韻的雜言體,表現(xiàn)出了與中原格律詩(shī)迥異的黨項(xiàng)傳統(tǒng)風(fēng)格[注]聶鴻音《從格言到詩(shī)歌:黨項(xiàng)民族文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寧夏社會(huì)科學(xué)》2018年第4期。。前人大約是考慮到詩(shī)的內(nèi)容都是歌頌黨項(xiàng)民族的光榮歷史和西夏當(dāng)朝的政治清明,所以將其擬題為“西夏宮廷詩(shī)”[注]З.И. Горбачева, Е.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54.。作為西夏當(dāng)朝大臣的應(yīng)制之作,這些詩(shī)歌并沒(méi)有采用中原的格律,想必是投君王所好。這給了我們一個(gè)印象,即中原詩(shī)歌在西夏君臣心目中的地位不及黨項(xiàng)傳統(tǒng)詩(shī)歌。
附帶說(shuō),黑水城遺址還出土過(guò)西夏國(guó)師鮮卑寶源詩(shī)文集的幾個(gè)刻本[注]孫伯君《西夏俗文學(xué)“辯”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第4期。,那里面的詩(shī)雖然用西夏文寫(xiě)成,但是似乎表現(xiàn)出了對(duì)漢文詩(shī)歌或俗曲的模仿痕跡。這些詩(shī)一反黨項(xiàng)傳統(tǒng)的無(wú)韻雜言體,轉(zhuǎn)作每句固定為五言或七言,而且在句末用韻。不過(guò),這似乎不足以佐證中原文學(xué)對(duì)西夏的影響,因?yàn)樽髡啧r卑寶源是個(gè)和尚,他所接受的歌曲形式和主題更可能來(lái)自佛家講經(jīng)時(shí)的“證道歌”。
四
中原詩(shī)歌在西夏傳播不廣,原因之一當(dāng)然是西夏缺乏遼代那樣相對(duì)深厚的群眾文化基礎(chǔ),然而更重要的是西夏統(tǒng)治者對(duì)中原詩(shī)歌乃至中原文化的態(tài)度與契丹統(tǒng)治者迥異。《遼史》卷七二《義宗倍傳》:
時(shí)太祖問(wèn)侍臣曰:“受命之君,當(dāng)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duì)。太祖曰:“佛非中國(guó)教。”倍曰:“孔子大圣,萬(wàn)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注]脫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1209頁(yè)。
以孔子為標(biāo)志的中原漢文化受到了太祖阿保機(jī)的推崇[注]《宋史·夏國(guó)傳下》記載夏仁宗曾經(jīng)在1145年“重建大漢太學(xué)”,次年尊孔子為“文宣帝”。由于史籍中再未見(jiàn)尊孔的具體記述,所以孔子在西夏似乎僅僅被用為大漢太學(xué)的符號(hào),跟阿保機(jī)推崇孔子不是一個(gè)性質(zhì)。。到了道宗時(shí)代,契丹已經(jīng)在極大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其傳統(tǒng)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洪皓《松漠紀(jì)聞》卷上載: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yǔ)》至“北辰居所而眾星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guó),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wú)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注]《宋元筆記小說(shuō)大觀》,第2794頁(yè)。
值得注意的是遼朝皇帝使用的“中國(guó)”一詞,那是在契丹人心目中代表先進(jìn)文明的中原地區(qū)。西夏人也崇敬“中國(guó)”(碟繕),但西夏文獻(xiàn)里的這個(gè)詞指的卻是作為佛教圣地的吐蕃[注]例如俄羅斯科學(xué)院東方文獻(xiàn)研究所藏本《仁王護(hù)國(guó)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后序愿文》(инв. № 683)記載一個(gè)藏族喇嘛的頭銜為“碟繕菞蓕例身繕祇”[中國(guó)大乘玄密?chē)?guó)師]。,稱北宋王朝則只用“漢”(錫),并且持有明顯的蔑視態(tài)度[注]有趣的是,西夏這個(gè)“漢”的字形是由“小”和“蟲(chóng)”拼合而成的。。例如西夏宮廷詩(shī)《夏圣根贊歌》這樣諷刺北宋君王:
錫聻紗,堅(jiān)堅(jiān)藶滾藶沏砿,唉唉對(duì)倘對(duì)篟脤。[注]Е.И. Кычанов, Гимн священным предкам тангутов,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96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0.
[漢天子,日日博弈博則負(fù),夜夜馳逐馳不贏。]
西夏人和契丹人對(duì)中原的不同態(tài)度是歷史上形成的。這里面的關(guān)鍵在于,契丹人當(dāng)初從漠北南下,與中原王朝的關(guān)系是“鄰國(guó)”,而西夏人當(dāng)初是從北宋統(tǒng)治下分裂出去的,與中原王朝的關(guān)系是“敵國(guó)”。為了給“裂土分國(guó)”制造理由,西夏統(tǒng)治者從一開(kāi)始就不斷強(qiáng)調(diào)黨項(xiàng)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不同,甚至連發(fā)型這樣的細(xì)節(jié)也不放過(guò)。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月:
元昊初制禿發(fā)令,先自禿發(fā),及令國(guó)人皆禿發(fā),三日不從令,許眾殺之。[注]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北京:中華書(shū)局,2016年,第6262頁(yè)。
在典章制度方面,新獨(dú)立的西夏政權(quán)雖然不會(huì)完全擺脫中原模式,但仍然希望盡量在表面上制造些區(qū)別。例如據(jù)《宋史》卷四八五《夏國(guó)傳上》所載,開(kāi)國(guó)君主元昊在給北宋朝廷送去的表章中說(shuō)到: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lè)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注]以上二句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卷一二三寶元二年正月辛亥補(bǔ)。見(jiàn):《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第6677頁(yè)。。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lè)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愿一垓之土地,建為萬(wàn)乘之邦家。[注]《宋史》,第13995-13996頁(yè)。
元昊的以上改革項(xiàng)目不涉及政府組織。早年的黨項(xiàng)部落并沒(méi)有中原那樣嚴(yán)密的組織制度,那么,西夏建國(guó)后的政府機(jī)構(gòu)設(shè)置全盤(pán)照搬中原,自然也可以理解為與北宋分庭抗禮的首要措施。至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由于黨項(xiàng)人預(yù)先有自己本民族的傳統(tǒng)存在,則與中原風(fēng)格之間的取舍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尤其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的倡導(dǎo)。進(jìn)一步說(shuō),相對(duì)缺乏詩(shī)歌傳統(tǒng)的契丹人而言,西夏統(tǒng)治者在詩(shī)歌體裁方面多了一個(gè)選擇,而他們之所以大力推崇黨項(xiàng)傳統(tǒng)詩(shī)歌而不宣傳中原作品,顯然是和西夏建國(guó)之初的“改大漢衣冠”相適應(yīng)的。
《遼史》卷十《圣宗本紀(jì)一》說(shuō)遼圣宗“十歲能詩(shī)”,最終有“御制曲五百余首”。從傳世的《傳國(guó)璽詩(shī)》類推[注]宋孔平仲《孔氏雜說(shuō)》(民國(guó)景明寶顏堂秘笈本)載這首詩(shī)的全文是:“一時(shí)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yè)當(dāng)永昌。”,可以相信所有這些詩(shī)歌都是漢文作品。據(jù)夏仁宗朝某位大臣寫(xiě)下的西夏文《新修太學(xué)歌》記載,仁宗似乎也寫(xiě)過(guò)詩(shī),而且被用作了太學(xué)的教材,由此向全體百姓(黑頭赤面)推廣:
紒竭睎,綃蚦綃禑蒾息皢,遍緵梆唐緳祇腞;羴磀羴鉤剛寂仕,礝暴缸諜篔箌臀。[注]西田龍雄《西夏語(yǔ)『月々樂(lè)詩(shī)』の研究》,《京都大學(xué)文學(xué)部研究紀(jì)要》1986年第25卷,第23頁(yè)。
[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語(yǔ)文,千黑頭處為德師;聽(tīng)作御策御詩(shī)詞,萬(wàn)赤面處取法則。]
可以相信,太學(xué)里“番君子”學(xué)習(xí)的“御詩(shī)詞”必是仁宗用西夏文寫(xiě)下的黨項(xiàng)傳統(tǒng)體裁作品,只可惜這些詩(shī)詞一篇也沒(méi)有保存到今天。然而無(wú)論如何我們可以理解,存世文獻(xiàn)中西夏臣子寫(xiě)的詩(shī)都是黨項(xiàng)風(fēng)格,契丹臣子寫(xiě)的詩(shī)都是中原風(fēng)格,這都和皇帝的喜好密切相關(guān)。事實(shí)上,契丹皇帝和西夏皇帝喜歡讀的書(shū)也有很大不同:遼圣宗讀的是《貞觀政要》[注]《契丹國(guó)志》卷七,劉曉東等點(diǎn)校《二十五別史》,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2000年,第57頁(yè)。,希望吸收唐朝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yàn);而夏景宗喜歡讀的是《野戰(zhàn)歌》和《太乙金鑒訣》[注]《宋史·夏國(guó)傳上》卷四,第13993頁(yè)。,一心要與北宋爭(zhēng)斗。對(duì)中原文化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加上兩個(gè)民族不同的文化水平,最終導(dǎo)致了中原詩(shī)歌傳入西夏與傳入契丹之后的境遇迥異,這與少數(shù)民族是否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無(wú)關(guā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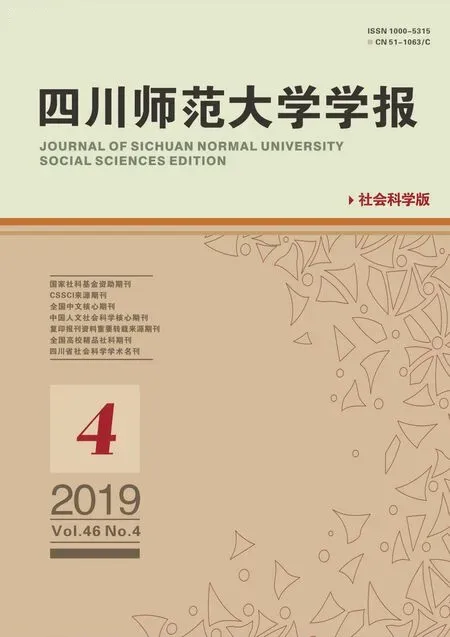 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4期
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4期
- 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被忽略的中國(guó):30年來(lái)英國(guó)歷史教科書(shū)中的中日戰(zhàn)爭(zhēng)敘事
- 我國(guó)西部貧困地區(qū)中學(xué)生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的類型及特點(diǎn)
——基于“學(xué)習(xí)努力目標(biāo)”的調(diào)查研究 - 農(nóng)村中小學(xué)教師工作價(jià)值觀與工作投入的關(guān)系:社會(huì)支持的中介作用
- 校園欺凌防治與中學(xué)生核心素養(yǎng)關(guān)系實(shí)證研究
- 可持續(xù)生計(jì)分析框架下的返鄉(xiāng)農(nóng)民工創(chuàng)業(yè)業(yè)態(tài)選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