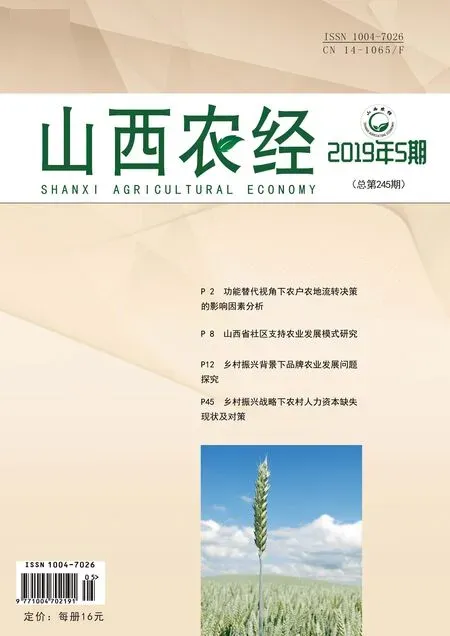山西省社區支持農業發展模式研究
(山西財經大學 山西 太原 030006)
近年來公共食品安全問題頻發,越來越多消費者開始重視食品安全問題并反思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發展受限于其本身特征,為了規避風險追求收入增長,農戶自發產生了對新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制度的渴求。
在此背景下,致力于保證健康安全食品,強調生產者與消費者“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新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社區支持農業(簡稱CSA)逐漸成為一種新選擇。CSA以保護耕地為理念,通過預付資金的方式促進城鄉互動,可以有效調動需求方和供給方的積極性,實現加強城鄉互動、保障食品安全、促進農業生產和保護生態環境等目標。
1 文獻綜述
CSA理念起源于瑞士,在日本得到初步發展,2008年以后開始逐步進入中國。CSA中“社區”一詞,不單指傳統意義上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行政區域概念,更非小區、居民住宅等地理區域范圍。“社區”可以看作一群具有相似偏好的人,有著共同的價值理念及認知基礎,再加上地理區域相互臨近,往往會以集體方式進行某項行動。
美國社會學家喬治·希勒里(George Hillery)指出,社區是一群互動的有機體[1],共同分享同一個居住環境。程存旺繼續發展喬治·希勒里的觀點,指出CSA是生活在同一地理區域內、具有共同意識和共同利益的社會群體[2]。石嫣是創辦中國CSA農場的第一人,她認為CSA中的“社區”是一種社會學概念上的社區,是由一群愿意支持CSA理念和價值觀念的中產階級群體構成的[3]。
CSA是一種新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致力于保障食品健康安全、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互信互助。羅賓·范·恩(Robyn Van En)將CSA概括為“食物生產者+食物消費者+每年的相互承諾=CSA和無數的可能性”[4]。劉飛指出CSA模式是將脫嵌的食品市場重新嵌入到社會網絡之中,這種嵌入性降低了食品生產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使得消費者的食品購買更加安心[5]。
部分研究學者指出了CSA可能存在缺陷。伏洪勇認為CSA社區中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實質上是在一定的合約約束下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二者很可能陷入有限理性下的囚徒困境,需要完善制度設計來解決社區內的信任博弈[6]。
2 CSA發展經驗研究
2.1 國外發展現狀
2.1.1 日本 CSA 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復蘇,大力發展工業導致了環境破壞和各種公害病,引起了人們對食品安全的恐慌,CSA應運而生。縱觀CSA在日本的多年發展,可借鑒經驗主要有如下幾點。
(1)創新傳統銷售模式。消費者可以根據喜好自愿加入耕地,親近自然并體驗種植的快樂,實現參與式的體驗。
(2)重視綠色農業園區的建設與布局。CSA以保護綠地和耕地為原則,尋求與自然和諧友好的共處方式,注重節約能源及保護生態環境。
(3)拓展農產品的多元營銷渠道。CSA除運用傳統營銷渠道外,還創立了與多平臺進行銷售對接的新型營銷渠道。
2.1.2 美國 CSA 經驗
1985年,美國首個CSA農場成立。“風險共擔,收益共享”是美國CSA秉承的發展理念。大部分CSA農場消費者只需提供資金支持,不需要貢獻勞動力,享有管理權、監督權。消費者與農民同為CSA農場股東,關系緊密。美國CSA的發展經驗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政府重視干預農業發展。美國國家農業支持保護政策(以政策補貼為主)隨著農業發展逐步調整演進,以CSA為主體,各組織提供政策支持的農業發展體系逐漸形成。
(2)開展農業合作,降低投資風險。農民與消費者同為股東,共擔風險。美國CSA農場通過與其他農場進行戰略合作以應對風險。
(3)注重農業的積極社會效應。社區通過農場反哺社會,形成了一種雙向互惠合作發展的良好循環,推動CSA健康多元化發展。
2.2 國內發展現狀
與國外相比,中國CSA發展起步較晚,且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小毛驢市民農園”是中國第一個CSA農場。通過消費者在種植之初預付生產者全年生產費用,給農民提供了資金來源保障。農民進行高投入有機生產和采用生態方式種植,以保證食物健康、安全。
綜合國內、外CSA發展經驗來看,經濟發展促使CSA行為受到消費者青睞。目前,我國CSA發展較為成熟的地方集中在較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CSA仍處于探索發展初期。
3 蒲韓鄉村CSA發展之路
山西省永濟蒲韓鄉村社區是第六屆國際CSA暨第七屆中國社會農業大會重點推廣的典范之一。永濟市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從1998年創辦寨子科技中心21年來,自成綜合服務體系[7]。
種植出售時令水果、棉花、小麥等農作物是蒲韓鄉村社區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這對資金鏈維系及銷售渠道通暢提出了較高要求[8]。社區在充分了解農戶收入瓶頸后,結合當地農作物種植特點,積極開展城鄉互動業務,為農戶開辟農產品銷售渠道。
通過內部消耗和外部合作方式,將產品銷往永濟市等地。社區輔導員定期走訪調查,充分了解掌握農戶生情況及農產品銷售新動態。針對服務農戶計劃做出適宜適當調整,提供符合蒲韓CSA特色的差異化本土公共服務[9]。
4 蒲韓鄉村CSA的SWOT分析
4.1 優勢(Strengths)分析
4.1.1 風險共擔保障農戶利益
蒲韓鄉村重視整個食品體系中出現的問題,與消費者共同承擔損失。消費者提前預付生產費用,即便在具體生產虧損,農戶利益和生活也不會受過大影響。
4.1.2 有機生產保障食品衛生安全
蒲韓社區在農作物種植上注重生態種養殖理念,不濫用農藥化肥,采用有機生產方式播種生產,保護當地農耕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形成良性循環。
4.1.3 距消費地近,物流便利
蒲韓社區主要消費區域集中于運城市內,利于縮減運輸成本,在同級產品中形成價格競爭優勢。
4.2 劣勢(Weaknesses)分析
4.2.1 高成本、高價格,銷路難開
消費方多為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及部分零散個體消費者。由于從事有機生產,蒲韓社區農產品銷售價格約高于市場價30%。居民出高價消費健康的意愿不高,使CSA規模難以擴大。
4.2.2 新型農業業態發展不充分
第三產業處于孤立發展境地,缺乏產業有機融合。缺乏融入當前“互聯網+現代農業”的時代潮流與趨勢,導致產銷信息不對稱、產品資源浪費、規模效益難以實現等問題。
4.2.3 剩余農產品積壓問題難以解決
由于信息交流不暢通、市場導向意識薄弱等原因,農戶無法及時有效獲取可靠信息。沒有構建起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整體循環經營模式,導致剩余農產品積壓時質優賤賣,違背有機產品的銷售理念。
4.3 機遇(Opportunities)分析
CSA是一種新型農業合作組織形式,在國家重視食品安全及有機農業發展的大環境下,必將得到更多的關注與認同[10]。
我國CSA大約于2003開始播種,2006年以后才真正生根發芽。其所包含“綠色農業”“服務三農”等契合時代趨勢的思想,一經發展就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4.4 威脅(Threats)分析
即使在多方刺激與補貼下,居民對健康消費的認知也不能有效激勵其去消費價格明顯高于普通農產品的CSA農產品。
信任問題也極大地制約著CSA的發展,預付款方式降低了消費者參與熱情。消費者流動性較大,CSA銷售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
5 山西省CSA發展困境
5.1 信任體系搭建不完善
CSA生產模式的成功施行,需要生產者和消費者相互信任、共擔風險。但實際情況是雙方信任關系緊張,尤其在農藥化肥使用方面。其主要原因是CSA在農業生產過程、環境質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無法進行透明監督。監督體系不健全,使以上3種監督無法有效保障。
5.2 地域特色品牌影響力不足
品牌是重要的無形資產,農產品品牌化是農業市場化與產業化的必經之路。山西省CSA在構建農產品品牌化發展過程中,存在整合協調力不夠、缺乏創新性思維以及綜合性合作經濟組織管理困境等問題,未能真正實現品牌效益。
5.3 “劉易斯陷阱”制約農業發展
隨著城鎮化水平提高,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以及高收入、高報酬的利益誘惑驅使農業勞動力不斷向二、三產業轉移,造成農業生產人才流失。“劉易斯陷阱”正進一步制約著農業包括CSA的發展。
6 對策與建議
6.1 完善農業監督體系建設
加快建設農產品認證和食品安全追溯體系。以社會力量倒逼CSA生產的規劃性、可持續性與綠色有機,借以擴大CSA品牌的知名度。
建立健全守信獎勵和失信懲戒制度。從制度層面激勵CSA農戶誠信生產、誠信經營,給消費者一個真正綠色、安全、放心的CSA農產品交易市場。
6.2 品質、品味雙提高,實現農業多功能發展
品質是打造品牌的基礎。推進“三品一標”認證,制訂CSA有機農產品的產品標準、生產標準、保鮮加工標準、存儲運輸標準等,嚴格把控“品質關”。
山西省CSA發展應立足實際,結合“一村一品”政策,挖掘本地農產品特色,實現多元銷售方式并存,拓展農業多功能發展。結合休閑農業模式讓消費者回歸田園、回歸自然,可以有效降低運輸成本,提高CSA經濟效益。
6.3 “內培外引”,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建立健全現代農業人才培訓機制,支撐CSA需要。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使生產效率更優、產品質量更高、創新能力更強。
各地政府要積極制定人才引進政策。重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縮小城鄉“硬件”差距。提高人才入駐福利,吸引人才流入。大力發揚各地優勢文化特色,以文化吸引人才入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