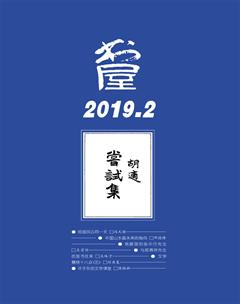瞻對始景從
陳輝
芝加哥的冬天來得早,11月已是漫天大雪,第二年的4月還會雪花飄飄。芝加哥大學置身于芝加哥南郊的密歇根湖畔,冬天則更加寒冷,這也使得芝大學者心無旁騖地專心治學、閱讀與討論,在眾多領域開創了芝加哥學派。芝大所有專業的本科生皆需修滿至少十五個學分博雅教育的核心課程,其思想來源于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時至今日,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無疑是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韋伯之問”在于:為什么資本主義沒有在古代印度、在古代中國予以有效展開?為什么科學的、藝術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發展沒有在印度、在中國走上西方現今所特有的理性化道路?他給出的答案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那里的資本主義缺乏一種整體性“獨特的精神氣質”。這種貫穿于社會理性化的獨特精神氣質,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基于勞作的天職觀。人須恒常不懈地踐行艱苦的體力與智力勞動,完成個人在現實中所擔負的責任和義務,將勞動本身作為人生目的,視勞動為天職,并且是獲得最終恩寵的唯一手段,唯有勞作而非悠閑享樂方可增益上帝的榮耀,把勞動視為一種天職成為現代工人的基本特征。韋伯認為失去信仰的科層制組織則會淪為“奴役的鐵籠”,如此,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呈現為:“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事實上,天職觀構成了西方文化特別是責任倫理的根基,由此產生了分工、專業、創新、效率、可計算化等近代社會的基本元素。
其次,基于禁欲的平安觀。新教世俗禁欲主義的本質特征在于潔身自好,嚴肅莊重的律法精神所形成的價值理性,律法具有凌駕于世俗權力之上的權威性與獨立性,視戒律和秩序為核心,隨時幫助人們做出有節制的注重實用的決策,從而具備明達事理、有條不紊的性格,其核心價值在于認為“禁欲得平安”(asceticism leads to peace)。
其三,基于信任的社會觀。在韋伯看來,清教徒對教友的信任,由于受宗教的制約,這種信任具有“無條件的、不可動搖的正當性”。儒家所適應的塵世過于注意優雅的姿態,“儒家君子只顧慮表面的‘自制,對別人普遍不信任,這種不信任阻礙了一切信貸和商業活動的發展”。信任是商業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基本機制,以信任合作為特質的社會資本是提升民主質量的關鍵。
韋伯作為影響深遠的社會科學家,其研究價值在于從文化權力的視角,透過比較研究解讀社會發展的不同路徑,深入分析現代性成因的內在機理。就文化與社會的相互關系而言,其后較有影響的學者是雷蒙·威廉斯與柯利福德·格爾茨。雷蒙·威廉斯認為十九世紀以來文化主要有四種含義:心靈的普遍狀態或者習慣;整個社會智性發展的普遍狀態;藝術的整體狀況;包括物質、智性、精神等各個層面的整體生活方式。文化的當下內涵“則包括了整個生活方式”。因此,借助文化可以對歷史的本質進行深入探索。人類學家柯利福德·格爾茨將社會的形態視為文化的實體,認為文化是“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對文化的分析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即“分析解釋表面上神秘莫測的社會表達”。由此,借助心靈狀態與社會精神有助于理解社會變遷為何如此,將會如何,以及應該如何。
毋庸諱言,文化權力研究肇始于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韋伯認為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從權力轉變為權威有三種基本的形態,即傳統型、魅力型與合法型。其中技術上最完善的治理形式為合法型權威,即“建立在相信統治者的章程所規定的制度和指令權力的合法性之上,他們是合法授命進行統治的”。合法型統治的基礎則在于文化,他比較分析了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勾連,探討了資本主義何以首先產生在西方。這其中新教倫理(the protestant ethic)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清教徒的精神氣質在于“合乎理性地組織資本與勞動”。理性化幫助人們做出有節制的、注重實用的決定,增強了資本主義對生產標準化的興趣。清教徒的精神從荷蘭到英國再到北美,一以貫之。他認為,在一項世俗的職業中要殫精竭慮,持之不懈,有條不紊地勞動,這樣一種宗教觀念作為禁欲主義的最高手段,同時也作為重生與真誠信念的最可靠、最顯著的證明,對于我們在此稱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活態度傳播發揮了巨大無比的杠桿作用。
金耀基認為,若欲充分地理解在中國發展現代型國家的問題,仍需回到韋伯那里。韋伯對于中國資料的使用雖多為二手文獻,仍具備歷史的穿透力。
十九世紀中、日兩國皆為自身輝煌的歷史而自豪,但在面對外來的西方文明之時兩國卻有著不同的反應。羅茲·墨菲認為中、日兩國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不會拒絕接受任何有用的外國理念,日本人長期以來從中國引進文化的經驗以及他們對新理念的開放胸懷,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資產得以全面引進西方的技術和思想,進行較為徹底的自我改造;清政府皇室和絕大多數民眾從內心深處是排外的,甚至反對洋務派官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革措施,而是主張在保持中國文化主體不變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技術,因此當中國傳統文化瓦解的時候,中國就不可避免地沉淪下去。最后的結果是中國在虛弱和恥辱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而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卻開始大踏步地前進。由此可見,中、日兩國居于主導地位的文化理念不同,支配了相異的社會變遷,形成了不同的政府治理機制,日本構建了近代化的中央政府(modern central government);清政府仍然延續了傳統的中央帝國,在此背景下,清政府的內憂外患則不斷加深。著名學者郭廷以認為任何民族的命運皆取決于其對時代環境的適應力,即“決之于文化”,“文化為人群謀求生存與生活需要的產物”。
二十世紀兩位重要學者道格拉斯·諾思與塞繆爾·亨廷頓仍然延續了文化權力與制度建構的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思認為,十七世紀的英國與西班牙都曾面臨著財政危機,兩國卻走上了不同的發展之路,這反映了兩國不同社會的深層性制度特征。在此基礎之上,美國與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之所以不同,在于兩地所傳承的不同文化結構。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延續的是聯邦政體、分權制衡、私有財權的制度結構,拉丁美洲是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殖民地,延續的是中央集權、官僚傳統的政治文化。
塞繆爾·亨廷頓則以韓國與加納為案例,分析了這兩個國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處在同等發展水平,經濟數據亦大致相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亦相似,初級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所占比例彼此相近,絕大部分的出口皆為初級產品,接受外援的水平相似。但是三十年后,韓國成為工業巨人世界一流經濟強國,擁有大量創業公司與創新產品,出口商品包括汽車、電子器材以及尖端技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西方發達國家水平,并且邁上了穩固的民主制度化進程。而在加納,這些變化卻無一出現,加納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于韓國的十五分之一。究其原因在于韓國人重視節儉、投資、勤奮、教育、組織和紀律,而加納的價值觀卻與之不同。總之,文化對于制度建構起著潛移默化的導引功效,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于無聲處聽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