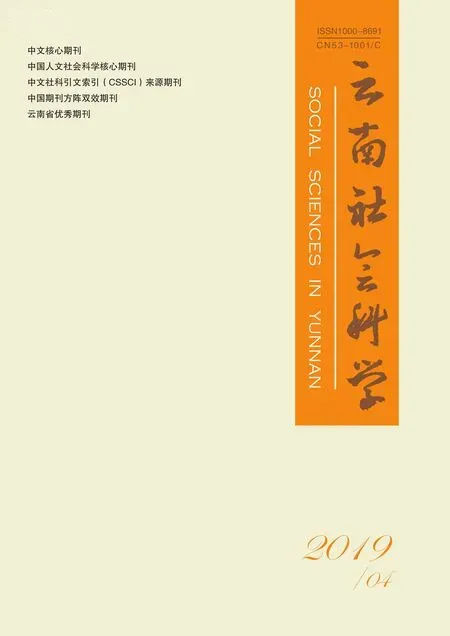網絡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的當代繼承與發展
高艷芳
互聯網技術的推廣和日益普及對21世紀的人類生活影響極其深遠,它引領人們步入了一個嶄新的數字化時代。網絡空間成為產生新民俗、新民間文學的重要場域,以該技術為基礎的網絡民俗文化生態隨之形成。便捷的操作,多元的發布平臺,實時、廣域的傳播使得網絡民間文學風生水起,迅速凝聚了規模龐大的用戶群體。網絡民間文學是當下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著一個時代潛在的社會欲望與發展動力,對民眾的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有著巨大的影響,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本文主要就網絡民間文學的形成、特征及其價值意義展開探討,以期能為當下的網絡民間文學研究提供些許借鑒和參考。
一、網絡民間文學的形成與界定
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其相應的文化生態,任何時代的發展及其技術的進步都意味著新的文化生態及其新的價值判斷標準的產生。誠如傳媒大師麥克·盧漢所指出的:“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①[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3頁。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和逐步普及,引發了全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思維方式的出現,與之相應的網絡民俗文化生態由此形成,網絡民間文學也隨之產生,并不斷發展。
(一)“網絡民俗文化生態”的形成
不同文化生態對應著不同的民俗文化事象和民間文學現象,文化生態對民俗的形成與演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黃永林在《民俗文化發展理論與生態規律闡釋及其實踐運用》中提出了“民俗文化生態”的概念,認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及自然環境等因素是民俗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因素的變化決定了民俗的發展與變化。①黃永林:《民俗文化發展理論與生態規律闡釋及其實踐運用》,《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互聯網技術的持續、深入發展已全面介入民眾生活和民眾傳統。網絡與民眾生活須臾不可分離,其影響已波及至民眾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與之相應的文化生態逐漸形成。這里借用黃先生的概念,將之稱作“網絡民俗文化生態”。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民間文學的實踐主體及其民眾生活方式等較之傳統民俗文化生態發生了轉變。
首先,就實踐主體而言。伴隨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入網人數逐年攀增,民間文學實踐活動由“線下”逐漸轉移至“線上”。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已沖過8億大關,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了57.7%。中國手機網民數量已達到了7.88億,其中手機入網的比例高達98%以上,人均周上網時長為27.7個小時。②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9年8月。可以看出,多數民眾已經發生了“網絡化”的轉向,“網民”已成為了民眾的大多數,“線上”狀態已成為民眾生活的主流。
其次,就民眾的生活方式而言。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廣大民眾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網絡化”的轉向。就民眾的政治生活來看,網絡拓展了廣大民眾參政、議政的途徑。其一,通過網絡民眾可以隨時隨地了解和跟進政治動態,增強了民眾與政治的聯系。其二,網絡的虛擬性、匿名性特征使得民眾敢于真實地表達自我觀點,發表政治見解,賦予了民眾參與政治的勇氣。就民眾的經濟生活來看,網絡解構了傳統的消費模式,“線下”的實體店購物逐漸被“線上”的網絡購物替代。人們的支付方式也由“線下”支付逐漸轉變為“線上”支付。就民眾的日常生活來看,一是,網絡已發展成為民眾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重要途徑,使得知識和信息的獲取極為便捷。二是,網絡成為民眾進行社交活動的主要平臺,這打破了以往社交的時空限制,擴大了民眾的社交范圍。三是,網絡改變了民眾的娛樂休閑方式,網絡成為民眾娛樂休閑的主要平臺。
不難看出,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民間文學的實踐主體及其民眾的生活方式等較之傳統民俗文化生態已經發生了較大轉變,與之相應的網絡民間文學也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民間文學的特征,在此情形下,需要對之進行重新的認知和界定。
(二)“網絡民間文學”的界定
美國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在《誰是民俗之“民”》中闡明道:“技術是民俗學家的朋友,而非敵人。技術并不會消滅民俗;相反,它會成為民俗得以傳播的重要因素,而且還會為新民俗的產生提供激動人心的靈感源泉。”③[美]阿蘭·鄧迪斯:《誰是民俗之“民”》,見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附錄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頁。人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技術發展會造成民俗的消亡,但事實并不總是這樣,很多時候,技術發展不僅不會造成民俗的消亡,反而還能提升民俗的傳播效率,推動民俗的廣域傳播,甚至技術本身也可以發展成為民俗的內容。互聯網技術在改變民間文學傳播方式的同時,也成為了網絡民間文學的內容。遺憾的是,在互聯網技術已對民間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情形下,學界至今仍未達成對網絡民間文學的統一界定。
總體看來,目前學界對于網絡民間文學主要有以下幾種界定:其一,將網絡文學創作立場、基本特征與傳統民間文學進行比照,在比照結果相同或者相近的情況下,得出網絡文學即為網絡民間文學的論斷。其二,從網絡作品與紙質文學的親疏關系出發,將網絡文學作品分為“文人化”和“民間化”兩種不同的傾向。前者多存在各大文學網站中,屬作家文學范疇;后者多活躍于微博、微信等私人空間,是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民間文學。其三,從生成與傳播媒介角度出發,將通過網絡生成、傳播的網絡文學稱為網絡民間文學。④高艷芳:《網絡民間文學的審視》,《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可以看出,界定標準的不統一及其對網絡民俗文化生態的忽略,導致了現有界定內涵和外延的模糊性。
宏觀上看,網絡民間文學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當下“生活革命”和“技術革命”合力作用的結果,是傳統民間文學在當下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的繼承與發展,需將之放置在宏觀的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進行綜合考察。微觀上看,網絡民間文學與當下的互聯網技術關聯緊密,是傳統民間文學與互聯網技術結合的結果。質而言之,網絡民間文學是民間文學的組成部分,是在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對民間文學的當代繼承與發展,它以傳統民間文學為根基,以鮮活的民眾生活為取向,以網絡為創作生成平臺和傳播傳承媒介,滿足了廣大民眾的日常文化審美需求,也使得民間文學通過網絡繼續活躍于當下的民眾生活。網絡民間文學在具有傳統民間文學屬性的基礎上,還具有鮮明的網絡屬性。
二、網絡民間文學的繼承與創新
民俗的傳承性決定了民俗文化的發展須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創新,民俗的活態性則決定了民俗文化發展與創新的必然性。①黃永林:《民俗文化發展理論與生態規律闡釋及其實踐運用》,《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以此觀照網絡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可見其對傳統民間文學特征的繼承與創新。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繼承并非紋絲不動的繼承,而是一種發展性的繼承;創新則是在民間文學與互聯網技術結合基礎上的創新,與網絡民間文學的網絡性特征相互關聯。
(一)發展性的繼承
民間文學的“四性”特征,即集體性、口頭性、變異性、傳承性是關于民間文學特征的經典論述。傳統民間文學意味著“歷史”的存在,網絡民間文學意味的“當下”的存在。網絡民間文學作為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的民間文學,既有對傳統的繼承,也有對之的發展和超越。
1.集體性方面。民間文學的集體性主要指民間文學具有集體創作、流傳、加工、保存,以及為集體服務的特點。網絡媒介空前的傳播速度和廣度拓展了民間文學的實踐空間,網絡空間的自由開放性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到民間文學的實踐中來,網絡民間文學因此具有了明顯的集體性特征。然,通過對比可見,兩者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差異。
首先,從集體性的指向上來看,傳統民間文學以傳統農業社會文化生態為背景,其集體性指向了傳統社會的大多數——農民,多與身居社會底層、文化水平低下者相關聯。網絡民間文學則以網絡民俗文化生態為背景,與工業社會、城鎮化、信息化等緊密關聯,其集體性指向的是活躍于網絡空間的網民,以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市民居多,具有市民化的傾向。其次,從匿名性特征來看,傳統民間文學主要通過口耳相傳的模式進行傳播傳承,反復的講述、轉述使得最初的創作主體、時間、地點等已無從考證,民間文學隨之處于了一種匿名的狀態,這是一種被動的、無意識的匿名。網絡民間文學的匿名往往是主動選擇的結果,是一種主動的、有意識的匿名,通常具有可逆性的特征。
2.口頭性方面。農業社會文化生態背景下形成的傳統民間文學,其形成與發展往往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民間文學實踐往往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得以實現,“面對面”成為民眾交流的前提,口耳相承成為民間文學實踐活動的主要途徑,“口頭性”成為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之一。這里的“口頭性”更多地指向了民間文學的傳播傳承方式,指向了“面對面”的交流。網絡民間文學則不同,網絡民間文學為保持“說話”和“在聊”的效果,②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7頁。采用的是“口頭性”的語言,具有口語化特征,是一種語言風格。在網絡民間文學實踐中,鍵盤代替了“口頭”,網絡傳播代替了“口耳相傳”。網絡民間文學的“口頭性”更多地指向了網絡民間文學的語言風格,而非傳播傳承方式。傳統民間文學的“口頭性”在網絡民間文學中發生了“網絡化”的轉向,“網絡化”的存在打破了傳統民間文學稍縱即逝的存在,使其成為一種可以保存的言說方式。③唐璐璐:《網絡時代民間文學的堅守與更新》,《中國藝術報》2011年2月16日。
3.變異性方面。民間文學的變異性是指同一民間文學作品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被不同的講述者、甚或同一講述者的講述過程中,發生變異的現象。口耳相傳的傳播傳承模式造就了傳統民間文學的變異性特征。這種變異性多與講述者自身的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地域文化等相關聯,多數情況下是一種“不自覺”的變異。網絡民間文學生成、流傳于網絡空間,以網絡為媒介進行傳播傳承。便捷的操作使得作品易保存、轉發、增減、刪改。網絡民間文學中的變異是一種“自覺”的變異,往往是在“流傳”過程中,個別人為了凸顯個性或為了達到某種效果而進行的“自覺”的變異。
4.傳承性方面。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將人類的文化傳遞模式劃分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前象征文化”三種基本類型,指出在第一種文化模式中,他文化的延續主要依靠“老一代”的知識經驗傳授,此時,“老一代”即是文化的權威。第二種文化模式則是同輩人之間的相互學習,通過相互學習的模式實現文化的傳遞。與后象征文化相反,在前象征文化模式中,“由于年輕人對依然未知的將來具有前象征性的理解,因而他們有了新的權威”。①[美]瑪格麗特·米德:《代溝》,曾胡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第67-92頁。傳統民間文學通過口耳相傳、代際相承的模式得以延續,年長者因此成為傳承的骨干,文化的權威,屬“后象征文化”模式。在網絡民間文學實踐中,年輕群體成為活動的中堅,他們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擁有廣闊的生活空間,尤其是具有熟稔的網絡技術,完全可以拋開年長者的經驗,通過網絡獲取各方面的知識與信息。網絡民間文學實踐中,年輕群體擁有自由獨立的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引導年長者的義務,屬“前象征式文化”模式。
(二)革命性的創新
“民間文化的活態性決定了民俗文化創新與發展的必然性”②黃永林:《民俗文化發展理論與生態規律闡釋及其實踐運用》,《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網絡民間文學是民間文學的當代承繼與發展,以網絡為媒介的特質注定了其革命性的創新,這在網絡民間文學的廣域性和即時性方面體現尤為明顯。
1.廣域性特征。這里的廣域性主要是相較傳統民間文學的地域性而言的。傳統民間文學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所謂地域性,一方面指民間文學內容的地域性;另一方面指流傳范圍及其語言的地域性。網絡民間文學實踐活動打破了時空的局限,不同地域的人,可以同時或不同時處于同一網絡空間,進行實時或延時的交流,打破了地域性的限制,具有了廣域性的特征,這主要體現在網絡民間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傳播范圍方面。
從作品內容和實踐主體來看,受傳統思想觀念及交通條件等因素的制約,傳統民間文學通常是一定地域內的民眾,依據該地域民眾的生產生活進行的創作,實踐主體和創作內容往往局限在一定地域之內,具有地域性的特征。網絡民間文學實踐則打破了時空局限,具有了“廣域性”的特征,全國范圍內、乃至全球范圍內的網民可以處于同一空間,進行交流。另外,網絡民間文學的內容,往往與全國、甚至全球范圍的社會熱點、社會興奮點相關聯,充分展現了作品內容的廣域性特征。
從流傳范圍及其語言看,傳統民間文學的傳播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鑒于傳統社會的封閉性特征,其傳播速度及其傳播范圍都十分有限,通常局限在一定的地域內流傳。網絡民間文學以網絡為媒介進行傳播,以網絡語言進行創作和流傳,打破了地域性的語言限制,網絡媒介以“比特”為速度單位進行傳播,極大地縮短了傳播的時間,拓展了傳播的范圍,實現了廣域性的傳播。
2.即時性性特征。網絡民間文學的生成、流傳依托于網絡媒介,創作更為便捷,流傳更為迅速,使得網絡民間文學具有了“即時性”的特征。所謂即時性,一方面指作品生成過程的即時性;另一方面指傳播、更新速度的即時性。
從生成過程看,網絡民間文學多與社會熱點和興奮點緊密相關。網絡信息的共享性及其便捷性,使不少突發事件能夠迅速被廣大民眾知曉,在極短時間內引起整個社會的關注。民眾發表自我觀點、見解的作品會隨之猛增,一時間內形成大量相關作品。如,2008年三鹿集團的“三聚氰胺”事件被曝之后,迅速引起了廣大民眾的關注。短時間內,涌現出大量與之相關的網絡民間文學作品。從傳播、更新速度看,傳統民間文學的傳播和更新以“人”為載體,以人的活動為傳播的先決條件。相較于傳統民間文學的傳播,網絡傳播具有快捷、迅速的特點,其傳播不受人的活動、印刷、運輸等因素的制約,打破了時空的限制,天涯咫尺成為現實,實現了短時間內的即時性傳播。新信息的產生往往會促成與之相關的網絡民間文學作品的產生。網絡信息的更新迅速引起了與之相伴的網絡民間文學的更新,實現了即時性的更新。網絡民間文學的這種即時性特征,一方面有利于人的偶發靈感的呈現;另一方面也注定了許多作品只是“快餐式”的存在,難以形成經典。
網絡民間文學是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的當代民間文學,網絡民間文學的衍生性決定了其對傳統民間文學的繼承及其對傳統民間文學基本特征的堅守;網絡民間文學的技術性決定了網絡民間文學的網絡性特征,這就注定了網絡民間文學對民間文學的繼承絕非一成不變的繼承,而是一種發展性的繼承。同時,網絡民間文學的網絡性特征也注定了網絡民間文學的革命性創新,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創新正是推動民間文學當代發展的關鍵。
三、網絡民間文學的“當代性”重申和表達
民俗是歷史的,更是當下的,活躍于當下民眾的生活當中。網絡民間文學是傳統和現代的鏈接,賦予了民間文學“當代性”的表達內容和傳達手段;更是對民俗學、民間文學“當代性”的重申,展現了學科本有的“當代性”關注。
(一)“當代性”的重申
民俗是一種活態文化,民俗文化生態的改變帶來了民俗、民間文學的變化。部分民俗、民間文學可能因不被當下民眾需要而遭遇淘汰,部分則可能發生變異而延續于民眾生活當中,當然也會產生新的民俗和民間文學。質而言之,民俗學、民間文學是關于傳統的學問,更是關于當下的學問。
民俗學、民間文學的“當代性”問題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美國民俗學者鮑曼曾指出,如果民俗學一味沉浸于一定歷史階段或文化中的遺留物研究,那么,伴隨時代的發展、傳統的消亡,學科的存在必然會受到威脅。①[美]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楊利慧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1-53頁。與之類似,中國知名民俗學專家鐘敬文也曾多次強調民俗學的當代性特征,指出初期的民俗學研究范圍相對狹窄,但伴隨學科的持續發展,其研究范圍會不斷拓展,直至涵蓋社會生活與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②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附錄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頁。戶曉輝則更進一步指出,民俗包含過去,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流行下來的經驗和見證,但“民俗的本質在當下和現在,即它永遠在活生生的當下實現和構造的過程中讓過去和未來同時,讓過去在現在被激活,讓未來在現在被披露出新的可能”③戶曉輝:《返回愛與自由的生活世界——純粹民間文學關鍵詞的哲學闡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9-370頁。。高丙中則指出了民俗學忽視其“當代性”引發的不良后果:“如果民俗學家的視野里只有文化而沒有生活,那么他必然只會注意到民俗的歷史性,因為文化的就意味著傳統的、由歷史積累的、已經完成的;如果民俗學家著眼于生活,那么他必然要關心民俗的現實性,因為生活的就意味著此時的、正在發生的。”④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09-110頁。對于民俗學的“當代性”特征學界有著較為清晰的認知,但實踐的發展卻是令人遺憾的,較長時間以來,民俗學始終將歷史遺留物視為學科的關注對象,而將現實生活中不斷涌現出的新生民俗事象和民間文學現象排除在外。
民俗學、民間文學的歷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但決不能因此忽略涌現于當下的諸種民俗事象和民間文學現象。民俗研究需結合當下的網絡民俗文化生態,貼近民眾生活,動態把握民俗的發展與演變。現實生活的變化注定了既有民俗的調整和演變,也決定了與之相應的民俗和民間文學的產生和發展。網絡民間文學作為民間文學的繼承與發展,是傳統民間文學的當代延續,更是當下民眾鮮活生活的真實展現。網絡民間文學無論是在表現內容,還是表現形式等方面都突出地展現了民間文學本有的“當代性”特征,凸顯了學科本有的“當代性”特征,是對學科“當代性”的重申和強調。
(二)表達內容的“當代性”
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曾說:“人不可能過著他的生活而不表達他的生活,這種不同的表達形式構成了一個新的領域。”⑤[美]卡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283頁。網絡民間文學作為當下民眾生活的表達,在表達內容方面充分展現了其“當代性”的特征,其內容的“當代性”一方面有對傳統民間文學主題的繼承,另一方面也有對之的開拓和發展。
傳統民間文學主題的延續。網絡民間文學以當下的生活現象為內容來表達傳統的民間文化主題,為傳統民間文學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傳統民間文學所褒獎的愛國主義,所憎惡的衙內現象等在網絡民間文學作品中都有充分表達。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表達是以民眾當下鮮活的社會生活為基礎,用當代人的意識,當代的表達手法,對上述民間文學主題進行了新的建構。
新的民間文學主題的開創。網絡民間文學中的多數作品以當代社會問題為內容來反映當下社會現象和民眾情感,充分展現了民間文學與時俱進的品格。伴隨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社會問題也隨之浮現。其中那些與民眾生活關聯緊密的,諸如環境問題、房價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及食品安全問題等迅速成為了網絡民間文學的表達主題。如各地流傳的關于霧霾的網絡段子、網絡小故事等即是民眾關注環境問題的表現。再如,瘋傳于網絡空間的關于房價的各種網絡民間文學作品,或詼諧幽默,或冷嘲熱諷,無論哪種都充分展現了民眾對居高不下的房價的無奈。此外,以就業、變性、整容、交通堵塞等為主題的網絡民間文學作品也是層出不窮,屢見不鮮。這些作品是當下社會問題的直接展示,也是民眾態度和理想訴求的表達。
(三)傳達方式的“當代性”
網絡民間文學通過網絡平臺生成、流傳,在傳達方式上體現了充分的“當代性”特征,這在視覺化轉向及其電子化傳達方面體現尤為明顯。
視覺化轉向。美國傳播學者米爾佐夫指出視覺文化“絕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日常生活本身”①[美]尼古拉斯·米爾佐夫:《視覺文化導論》,倪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這是一個視覺狂歡的時代,“看”已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圖像式文化填滿了人們的生活日常。網絡作為一種綜合性媒介,集文字、圖像、音頻、視頻于一體,伴隨網絡媒介的持續、深入發展,視覺文化不只是“看”的文化,而是以“看”為主導,集聽覺、觸覺等為一體的視聽盛宴。網絡民間文學的出現迎合了視覺文化的需要,充分發揮了網絡媒介的綜合性優勢,各種類型的網絡民間文學作品層出不窮:電子文本型、圖文并茂型、音頻型、視頻型,不勝枚舉,極大地豐富了民間文學的表達方式,打破了以往以聲音為主導的傳播模式。網絡民間文學的綜合性表達使得民間文學的表達更加形象、生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言、象、意”之間的矛盾,增加了民間文學被“看”的機會,也即增加了被民眾了解、認知和接納的機會。
電子化傳播。網絡民間文學主要活躍于網絡空間,以電子化的形式進行傳播。電子化的傳播極大地提升了網絡民間文學的傳播效率,推動了網絡民間文學實踐的展開。同時,電子化的傳播還推動了作品的保存和保護。傳統民間文學通過口耳相傳的模式進行傳播傳承,較少形成固定的文本,不易保存,易于遺忘。以電子化形式傳達的網絡民間文學作品可以進行隨時隨地的保存,任何異文、任何版本都可以得到有效保存。這不僅方便了民間文學的保存,也提高了民間文學保存的精確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民間文學的保護和傳播傳承,避免了傳統民間文學遭遇的“人亡技滅”的尷尬局面。
網絡民間文學以當代的民眾生活為表現內容,使得當下的民眾生活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以互聯網發展為技術支撐,賦予了民間文學網絡化的傳達手段。網絡民間文學不論是在表達內容,還是傳達方式方面都凸顯了“當代性”的特征,是對民俗學、民間文學“當代性”的重申。
結 語
民間文學源自民眾生活,服務于民眾生活,生生不息。社會的急速發展及科技的突飛猛進使得以刀耕火種為時代背景的傳統民間文學終究成為“歷史”,而以網絡民俗文化生態為生成背景的網絡民間文學則成為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民間文學是時代、科技、文化等諸種因素合力推動的結果,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網絡民間文學是網絡民俗文化生態下,民間文學的回歸與激活。一方面有著對傳統民間文學的繼承和對傳統民間文學基本特征的堅守,另一方面也有著革命性的新變和創新性的發展。網絡民間文學充分強調了民俗學、民間文學本有的“當代性”特征,為民間文學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和表達手段,賦予了民間文學新的傳播方式,使得民間文學能夠繼續活躍于民眾生活當中。
不能否認,現下的網絡民間文學作品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不時有暴力、色情等不和諧因素充斥其間,這有悖于民間文學發展的應有之意,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對之,需以開放的心態,理性地審視。對于網絡民間文學,唯有展開深入研究,把握其發展、運行規律,因勢利導,才能使之獲得更好的傳承與發展,才能使之更好地服務于民眾生活及當下的中華文明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