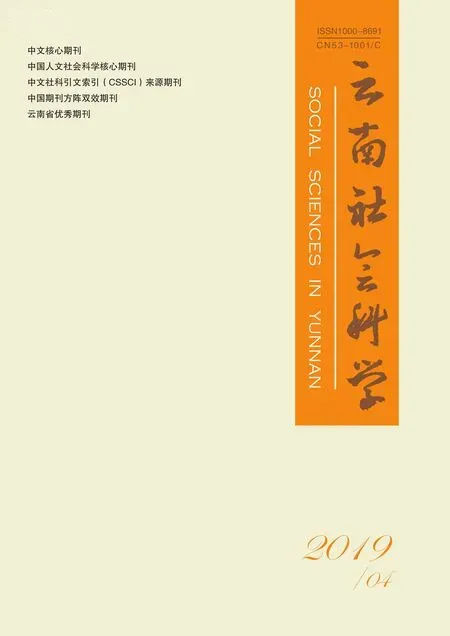從“亞文化”到“后亞文化”:青年亞文化研究范式的嬗變與轉換
閆翠娟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隨著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后現(xiàn)代理論話語的盛行和網(wǎng)絡新媒體技術的普遍應用,青年亞文化顯現(xiàn)出復雜、多變等諸多新的文化癥候,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的解釋力不斷受到質疑。2002年,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遭到校方解散,作為一種學術機構的伯明翰學派不復存在,作為一種學術流派的伯明翰學派也搖搖欲傾。在英國,多中心的文化研究格局開始形成。在世界范圍內(nèi),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迅速崛起,文化研究的國際化特征日益顯現(xiàn)。亞文化研究進入“后”伯明翰時期或后亞文化研究時期。
從某種意義上說,后亞文化研究是以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對立面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后亞文化研究者們普遍認為,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理論和模式已經(jīng)不能解釋新時代背景下的亞文化現(xiàn)象和亞文化現(xiàn)象中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困境。他們通過對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多重批判,試圖重新構建青年亞文化的概念工具、理論體系、闡釋模式。以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為代表的后亞文化研究學者,對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提出了四方面的批評和質疑:第一,將青年各種各樣的消費主義表現(xiàn)等同于工人階級的抵抗觀念,從未認真考慮過娛樂與青年亞文化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第二,忽視了青年亞文化的區(qū)域性、流動性和變異性,沒有考慮到青年對于音樂和時尚的響應會出現(xiàn)一些本地化的變種。第三,沒有認識到媒體在亞文化建構中的創(chuàng)造作用,而是將媒體視為對青年亞文化進行收編的重要幫兇。第四,只把青年看作一個16-21歲的年齡范疇,認識不到可以把青年轉變?yōu)橐庾R形態(tài)范疇、精神狀態(tài)而不是生活特定階段的其他流行文化資源①[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文化譯介小組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8-13頁。。基于此種認識,后亞文化研究強調(diào)青年文化的流動性、多變性和混雜性,高揚媒介在青年亞文化形成發(fā)展中的正向功用,注重從消費邏輯中探尋青年亞文化所包含的娛樂性和自我身份認同,出現(xiàn)了一些有重要影響力的后亞文化研究學者和著作,如:薩拉·桑頓的《俱樂部文化:音樂、媒介和亞文化資本》、戴維·馬格爾頓的《后亞文化主義者》、戴維·馬格爾頓和魯伯特·魏策勒主編的《后亞文化讀本》、安迪·班尼特和基思·哈恩-哈里斯主編的《亞文化之后》、保羅·霍德金森和迪克的《青年文化:場景·亞文化·部落》等。
一、碎片化的身份認同:亞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后亞文化”一詞,可以追溯到錢伯斯(Chambers)1987 年的著作《大都市圖繪:通往現(xiàn)在的可能性》①I.Chambers,Maps for the Metropolis: A Possible Guide to the Present,Cultural Studies, 1987(1):pp.1-21.,后經(jīng)波爾希默斯(Polhemus)在《時尚的演化:第三個新千年我們穿什么》(1996)中使用,馬格爾頓在《后亞文化主義者》(1997)中正式提出,得到班尼特、雷德黑德、邁爾斯等諸多研究者的認同和支持,開始廣為人知。2001年5月,“后亞文化研究:大眾文化及其影響下新后亞文化的形成”研討會在維爾納召開,后亞文化作為文化研究的專門術語得到學界和官方的認可,標志著后亞文化研究理論范式的形成和后亞文化時代的到來。
后亞文化研究的理論范式以皮埃爾·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讓·鮑德里亞的媒介理論、米歇爾·馬菲索里的后現(xiàn)代思想為理論資源,以后現(xiàn)代主義和文化經(jīng)濟全球一體化語境下的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為研究對象,認為青年亞文化在風格表征、實踐邏輯上,已與伯明翰學派所關切的二戰(zhàn)后英國社會的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相去甚遠,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短暫性、流動性、異質性、虛擬性等后現(xiàn)代特征。因此,新的亞文化研究應該關注年輕人碎片化、個人主義的“后現(xiàn)代經(jīng)驗”及其在年輕人建構自身文化身份中的意義價值②S.Redhead,Subcultures to Club cultures,Oxford: Blackwell Press,1997,p.95.。“后亞文化”概念作為“后現(xiàn)代社會”概念在亞文化領域的派生③陳一:《新媒體、媒介鏡像與“后亞文化”——美國學界近年來媒介與青年亞文化的述評與思考》,《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4期。,有助于闡釋亞文化群體在復雜多變的全球化網(wǎng)絡時代虛擬社群身份的凸顯和文化符號消費時代亞文化抵抗意識的消解等諸多身份困惑問題④[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6頁。。在波爾希默斯看來,當代青年亞文化“存在于一種街頭時尚主題公園(streetstyle themepark)當中”,人們對青年亞文化風格的選擇就像是從大超市中選購商品一樣,相異甚至完全對立的亞文化風格被相鄰地陳列在貨架上供人們選擇。此外,在后亞文化研究者的視野里,亞文化不再是抵制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而僅僅是一種帶有自我身份確認的消費選擇過程;媒體也不再只是對青年亞文化進行圍剿、收編的幫兇,而是充當了亞文化風格建構的資源庫和亞文化風格傳播的搬運工,促進了文化的融合,塑造了身份的完整性,鞏固了亞文化的地盤,并為亞文化組織的包容性、政治性提供了更大可能⑤馬中紅:《從亞文化到后亞文化——西方青年亞文化研究理論范式的流變》,《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1月16日,第13版。。同時,亞文化也不再是受地域局限的本土化建構,而是可以汲取全球商品消費中任何可用資源的全球化建構。正如馬格爾頓和魏策爾在《究竟什么是后亞文化研究》中所言:后亞文化研究關注的是新千年以來在社會變遷變革中產(chǎn)生的各種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致力于揭示青年亞文化如何在全球文化與各式各樣本土文化錯綜復雜的重構連接中,產(chǎn)生種種新的混交文化星座⑥Rubert Weinzierl and David Muggleton,“What is‘Post-Subcultural Studies’Anyway” in David Muggleton and RubertWeinzierl eds.,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Oxford: Berg Publishers,2003,p.3.。
二、新部族、場景、生活方式、亞文化資本:亞文化研究的新語匯
面對新媒體和全球化背景下青年文化現(xiàn)象的諸多變化,后亞文化研究者們認為伯明翰時期的“亞文化”概念已經(jīng)無法描述和概括這種變化,以幫助人們理解當代文化生活方式的復雜性,如班尼特、大衛(wèi)·錢尼所言:“作為一種抽象理論模式的亞文化概念的傳統(tǒng)的社會學意義,同它在日常的、本地語境中的應用之間出現(xiàn)了日益明顯的相互背離”①[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文化譯介小組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200頁。,“晚現(xiàn)代(late-modern)文化的諸多新發(fā)展已使得亞文化概念顯得多余了”②[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44頁。,它作為文化研究術語的解釋策略正在失去意義③[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68頁。。在這種情形下,“新部族”“場景”“生活方式”“亞文化資本”等一系列新范疇被提出,成為后亞文化研究的關鍵詞。
“新部族”(neo-tribe)一詞由米歇爾·馬弗索利提出,意指“個體通過獨特的儀式及消費習慣來表達集體認同的方式”,即它們的形成“不是依據(jù)階級、性別、宗教等‘傳統(tǒng)的’結構性因素,而是依據(jù)各種各樣的、變動的、轉瞬即逝的消費方式”④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41頁。。班尼特將這一概念引入后亞文化研究當中,并指出“新部族”比“亞文化”能夠更好地捕捉到“年輕人的音樂和風格偏好不斷變換的性質,以及青年文化群體的本質流動性”⑤[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69頁。。馬格爾頓也吸收了馬弗索利的新部族思想,指出后亞文化是“不再與周圍的階層結構、性別、種族鉸鏈”的個人選擇式狂歡,是多樣的、流動的、通過消費建構的。借用新部族這一概念,后亞文化研究者考察了俱樂部、音樂、舞蹈等亞文化現(xiàn)象,展示了新時代背景下亞文化群體邊界的開放性、流動性、交叉性,否認了清晰的、獨特的亞文化邊界的存在,并以此消解了伯明翰學派對具有清晰邊界的諸多亞文化群體的線性研究及其所構建的階級闡釋模式。
“場景”(scene)原本指稱戲劇、電影中的場面,后被引入亞文化研究領域來表征某種具有地域性和“亞文化”特征的空間。與新部族相類似,“場景”表征了一種個體能夠自由進出的開放性物理空間,人們是否進入一個場景主要受個人偏好的驅動,而受階級、性別、宗教等結構性因素影響較小。在威爾·斯特勞(Will Straw)看來,“場景”“真實地描繪了各類人群和社會團體之間的一種特定關系狀態(tài),融合了各種特定的音樂風格聯(lián)盟”,是一種可以依據(jù)在大街、夜總會或其他市區(qū)地帶的各種風格化、音樂化的聯(lián)盟來調(diào)整方位的文化空間⑥[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序言,第18頁。。杰夫·斯塔爾認為場景是一種特定的城市文化背景和空間編碼實踐……可以暗指那些即興的、暫時的、策略性的聯(lián)想和因其有限而廣泛滲透的社交性而產(chǎn)生的文化空間,蘊含著變遷和流動(flux and flow)、移動(movement)和易變性(mutability)⑦[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63頁。。“場景”是一個比“亞文化”更具理論說服力的概念,它能夠推動對于一個城市的文化空間、各種產(chǎn)業(yè)、體制和媒體之間相互關聯(lián)性的分析……可以促成對轉換性角色(shifting roles)的思考……也能為音樂場景和其他場景(電影、戲劇、文學、藝術等)共有的關系提供一種比較豐富的圖示方法(cartography)⑧[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64頁。。基思·哈恩-哈里斯使用“場景”這一術語,通過對全球極端金屬樂場景的分析,揭示了日常生活與引入矚目的壯觀場景之間的復雜關系。但是,與威爾·斯特勞、杰夫·斯塔爾認為場景是一個自由出入的空間不同,他認為極端金屬樂場景并非是一個自由出入的空間,場景演出成員的身份也不是高度流動的,而是與極端金屬樂場景有著穩(wěn)定而深刻的聯(lián)系,并把它當成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現(xiàn)身之所。
“生活方式”(lifestyle)最早由馬克斯·韋伯(1978/1919)提出,后經(jīng)麥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和大衛(wèi)·錢尼使用,直至雷默(1995)和邁爾斯(2000)明確提出用它來代替“亞文化”,并以此作為一種更精確的理論模式來闡述和解釋正在改變的身份政治和當代青年的各種風格聯(lián)盟。生活方式這一概念主要關注消費者的創(chuàng)造力,認為商品作為文化資源,其發(fā)揮作用的方式是從日常生活層面,通過對集體意義的銘刻產(chǎn)生的。⑨[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序言,第17頁。也即是說,在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既有的商品資源、青年個體的生活體驗、青年所處生活區(qū)域的風俗與傳統(tǒng)都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是青年綜合運用上述諸要素的現(xiàn)實結果和青年消費偏好的顯現(xiàn)。具有相同或相近生活方式的青年會相互吸引并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可見,與伯明翰學派對階級背景的強調(diào)不同,生活方式的提倡者更看重消費偏好。
“亞文化資本”(subcultural capital)這一概念由薩拉·桑頓提出,她在《俱樂部文化:音樂、媒介和亞文化資本》一文中,對英國俱樂部文化和銳舞文化的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tài)等進行了分析,指出俱樂部文化是一種多維的社會空間,是一種亞文化的集合,不同亞文化分支保持著自己的服裝代碼、音樂風格、舞蹈風格和一切被認可或不認可的儀式。在俱樂部中,人們選擇與自己趣味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并建立進一步的親密關系。在薩拉·桑頓看來,“伯明翰的傳統(tǒng)既過于將年輕人的休閑政治化,也同時忽視了在其中發(fā)揮作用的權力之間的微妙聯(lián)系”。①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第358頁。因此,俱樂部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包含著競爭關系的微觀權力結構,亞文化資本是判斷個體在這種微觀權力結構中地位高低的重要依據(jù),它構成了俱樂部運行的社會邏輯。亞文化資本以“酷樣”(hipness)為表現(xiàn)形式,是年輕人謀求社會權力、獲得社會地位、認識自我價值的途徑和標志,也是年輕人為了建立另外一種結構而擾亂主導結構的一種手段,以及面對時代和社會結構的問題而產(chǎn)生的一種矛盾的文化反映。在亞文化資本中,發(fā)揮作用的不是階級、收入和職業(yè),而是年齡、性別和種族。薩拉·桑頓借助“亞文化資本”這一概念,分析了長期以來被不同程度忽視的亞文化群體內(nèi)部的權力關系議題,一方面她繼承了伯明翰學派將青年亞文化視為是青年面對社會結構問題的文化反映這一基本觀點,另一方面,她又試圖矯正伯明翰學派所使用的階級分析模式,從對階級關系的過度強調(diào)轉向對年齡、性別、種族與青年亞文化內(nèi)在聯(lián)系性的關注。
三、 碎片混交、娛樂表達、媒介共謀:亞文化研究的新文化觀
(一)從邊界穩(wěn)定的風格文化到變動不居的碎片文化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無論當時的現(xiàn)實文化圖景如何,伯明翰學派都將青年亞文化描述為有著明確邊界和引人注目的外觀、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繼承性、延續(xù)性、反叛性的文化類別,而把青年亞文化群體界定為具有較高同質性和忠誠度,并且分享著相同的社會文化屬性和基本觀念的一群人。從泰迪族到光頭仔再到朋克,他們只關心有適度穩(wěn)固的邊界、突出的形態(tài)并在特定的行動或場所中緊密結合的亞文化②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第380頁。。這種判斷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受到了后亞文化學者的強烈批判和質疑。他們批判伯明翰學派夸大戰(zhàn)后亞文化群體的統(tǒng)一性和內(nèi)聚力,忽視青年亞文化內(nèi)部的多樣性和變動性,認為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無法解釋個體在各種不同的亞文化團體之間的流動行為;他們質疑伯明翰學派將青年亞文化區(qū)分為一個個彼此獨立的封閉類別的分類方法和試圖通過對每一個青年亞文化類別的個案解析以獲取青年亞文化全貌的研究路徑。例如,杰夫·斯達爾指責伯明翰學派將亞文化變成了一種奇觀,提供了一種無效的描述工具,模糊了當代文化實踐的復雜性③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第386頁。。薩拉·桑頓明確宣稱伯明翰學派靜態(tài)的、有界限的“亞文化”觀念“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④[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79頁。。格里·布魯斯蒂恩基于對媒體粉絲文化的討論,指出大多數(shù)被稱做“亞文化群體”的團體并不是界限明晰的、同質的、自發(fā)的、依據(jù)階級甚至年齡劃分出來的群體⑤[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78頁。。杰夫·斯塔爾在對蒙特利爾場景音樂研究的基礎上,倡導不能把亞文化研究簡化為一種關于風格姿態(tài)(stylistic gestures)和矯飾風格(mannerrisms)的分類學,提倡將風格重新置于一系列更復雜的、轉瞬即逝的和變化的實踐當中⑥[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63-64頁。。泰德·波爾希默斯也指出,隨著媒介飽和世界的到來,當代“亞文化主義者”不再對某些特定風格執(zhí)著信奉,而是反諷性地引用多種資源,在“風格超市”里不斷地自由變換自己的外觀①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第341頁。。
在批判的基礎上,后亞文化研究者指出當代亞文化已不再是摩登族、光頭黨等分門別類的概括,其風格、形式、實踐呈現(xiàn)出更加鮮明的多元化趨勢,正在演變?yōu)橐环N更多“混交”性質的新興亞文化形態(tài)②陸揚:《從亞文化到后亞文化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青年亞文化已由鐵板一塊的同一化風格演變成支離破碎的片段化風格,個體對青年亞文化的信奉也由忠貞不一的堅守演變成模糊不定的游移。各種“亞文化”群體和風格已經(jīng)不再能夠顯示出與過去一度宣稱的那種內(nèi)聚力和團結程度等同的東西了③[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95頁。。正如大衛(wèi)·馬格爾頓、鮑曼、布賴恩·特納所言:界限清晰的亞文化風格已經(jīng)在后亞文化時代消融了——一種獨立的、反復無常的“時尚旅行者”在一個“不真實、無關意識形態(tài),只是在玩一種風格的游戲”的服裝世界里,在“快速而自由地從一種風格向另一種風格移動”的過程中狂歡④[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00頁。。在后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的朝圣者(pilgrim)——真理、真實性、忠誠和穩(wěn)定性的探求者——已經(jīng)讓位于一些日益流行的隱喻形象(metaphorical figures)——如漫步者(stroller)、游民(vagabond)、游客(tourist)和玩家(player)。人們現(xiàn)在居住在“機場候機室”般的隱喻空間當中,在這個淺薄而短暫的環(huán)境中,幾乎沒有人展現(xiàn)出忠誠感或眷戀感,每個人都是“匆匆而過”⑤[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09頁。。
(二)從階級視域下的風格抵抗到消費視域下的娛樂表達
自菲爾·科恩將青年亞文化詮釋為是對父輩文化中懸而未決的矛盾沖突的象征性解決開始,伯明翰的學者始終從階級視域出發(fā),將青年亞文化視為是工人階級、黑人、女性等邊緣、弱勢群體對支配階級霸權的一種抵抗方式,是邊緣、弱勢群體對社會結構中諸種矛盾的一種“象征性解決”方案。
然而,在諸多后亞文化研究者看來,伯明翰學派這種將階級關系作為青年亞文化原動力的立場,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然站不穩(wěn)腳跟。他們不贊同階級地位與亞文化群體風格之間存在清晰的同源對應關系,也不認同青年亞文化僅僅是對階級困境和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回應。他們堅持認為在后現(xiàn)代社會中,個體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已替代階級、性別、宗教等傳統(tǒng)結構因素,成為區(qū)分和識別群體的首要因素,當代青年文化的建構和區(qū)分也主要基于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的差異,而非階級地位、性別和宗教信仰的差異。不論是馬格爾頓指出的亞文化是“不再與周圍的階層結構、性別、種族鉸鏈”的個人選擇式狂歡,它“沒有規(guī)則,沒有本真性,也沒有意識形態(tài)信奉,只是在玩一場風格游戲”⑥[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00頁。,還是伊夫拉特·茨隆將亞文化、后現(xiàn)代時尚描繪為一種“沒有意義附著的符號狂歡”⑦[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99頁。,抑或是約翰·西布魯克提出的“無階層文化”(Nobrow),都證明了在青年亞文化研究中階級視域的衰落和消費視域的崛起,以及對青年亞文化抵抗性的強調(diào)逐漸被對青年亞文化娛樂性、身份認同性的強調(diào)所取代。
伯明翰學派注重“以代碼的形式銘刻在風格的虛飾外表下的隱藏信息”,例如,他們會把光頭仔的背帶褲、工靴解讀為工人階級男性氣質的回歸,把朋克佩戴納粹徽章解讀為憤怒、震驚、種族主義等。這些風格背后的隱藏信息往往以主導意識形態(tài)為指向,表達著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背離與反叛,這構成了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的基本分析邏輯,而這一分析邏輯的前提則是伯明翰學派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附屬意識形態(tài)的二元劃分。然而,作為伯明翰學派風格抵抗理論分析前提的二元劃分觀念在后亞文化階段卻受到了質疑和批判。后亞文化主義者一般都持有以下這種假設——后現(xiàn)代的社會群體已經(jīng)打破了諸如“主導的”和“從屬的”這樣的二元差異,把整個亞文化觀念都描述成多余的東西⑧[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79頁。。如大衛(wèi)·錢尼指出,在一個主流文化已被分解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偏好的世界里,曾經(jīng) “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區(qū)別,已經(jīng)不再適用了①[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57頁。。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也指出,試圖在“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畫出涇渭分明的界線,這總是會產(chǎn)生一個“不真實的、僵化的世界……”②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第345頁。。因此,伯明翰學派所探討的那些因弱勢身份聚結在一起的亞文化群體,在消費文化時代,已經(jīng)失去了所依附的社會現(xiàn)實基礎,也失去了進行“儀式抵抗”的“英雄精神”。亞文化社群活躍于各種亦真亦幻的俱樂部亞文化或亞文化場景當中,已經(jīng)演變?yōu)榛祀s性、短暫性、碎片化的“無關政治”的“流動身份”③David Muggleton and Rupert Weinzierl,eds.,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Oxford & New York:Berg Publishers,2003,p.52.。在后亞文化的文化觀念里,銳舞派對、俱樂部文化等,主要表達了青年群體對快感的追尋和對自我身份的確認,顯示出那些基于階級的抵抗形式的瓦解④[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79頁。,標志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對抗性的”青年風格的死亡。在后現(xiàn)代背景下,亞文化不再是革命的、政治的,而是混搭的、去政治化的,變成了一種不違背主流意識形態(tài)、隔靴搔癢似的游戲和無關政治的、基于消費的自戀式表演。
(三)青年亞文化與媒介的關系從對立到共謀
受斯坦利·科恩“道德恐慌”思想的影響,以霍爾為代表的伯明翰學者普遍認為對亞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收編始于媒體的“威權共識”。媒體通過定義、放大、預測和象征化等手段在引發(fā)道德恐慌的過程中發(fā)揮著核心作用,在對青年亞文化進行意識形態(tài)收編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伯明翰學者始終把媒體置于青年亞文化的對立面,賦予其青年亞文化風格扼殺者的頭銜。正因如此,被收編并最終歸于平庸就成為青年亞文化難逃的宿命結局。這是伯明翰學派在媒體與青年亞文化關系議題上的基本觀點。
然而,這一基本觀點卻遭到了后亞文化學者的批評,他們批評伯明翰學派把媒體與青年亞文化截然對立起來,把青年亞文化風格的建構過程視為是與媒介完全絕緣的封閉過程。薩拉·桑頓在《俱樂部文化:音樂與亞文化資本》中曾批評道:“將亞文化看作混沌世界中的一個透明的小天地,仿佛亞文化生活在言說一種繞過傳媒的真理”⑤Sarah Thornton,Club Culture: Music and Subcultural Capital,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5,p.119.。而事實上,無論是青年亞文化風格的建構還是傳播,都離不開媒介的助力,因此,也就并不存在完全不受媒介影響的純原創(chuàng)性的青年亞文化。在后亞文化研究者看來,青年亞文化從一開始就汲取了大量的媒介資源,并將其轉化為自身風格的一部分。正如史蒂文·康納所言:在20世紀晚期,青年風格中“創(chuàng)新”與“收編”的循環(huán)已經(jīng)加速,真實的“原創(chuàng)性”與商業(yè)的“剝削”已難以區(qū)分⑥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第343頁。。薩拉·桑頓也指出,“亞文化”并不是從一粒種子當中生出來,靠自身的能量成長為參天大樹,然后才被媒體理解的神秘“運動”。相反,媒體及其他文化工業(yè)在亞文化產(chǎn)生之初就發(fā)揮著重要作用⑦[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序言,第13頁。。因此,并不存在純“原生態(tài)”的青年亞文化,青年亞文化從一開始就是“青年與大眾傳媒結成的動態(tài)的、高度自反性的關系的產(chǎn)物”。
尤其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廣泛而深刻地介入人們?nèi)粘I畹慕裉欤环矫妫浇楸旧硪呀?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轉變和分化,他們并非只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應聲蟲”,而是獲得了更多的獨立話語權。另一方面,媒介與青年亞文化之間的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緊密和撲朔迷離,以網(wǎng)絡為代表的現(xiàn)代媒介在青年亞文化的建構、傳播過程中,發(fā)揮著前所未有的重大影響,對青年亞文化創(chuàng)制者、傳播者的媒介意識和媒介素養(yǎng)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概括而言,以網(wǎng)絡為代表的現(xiàn)代媒介在青年亞文化的建構、傳播過程中發(fā)揮的影響體現(xiàn)在4個方面:一是為青年亞文化風格的建構提供豐富的原材料;二是為青年亞文化的傳播提供廣闊的空間;三是幫助青年亞文化由最初分散零落的亞文化片段聚合為風格明晰的亞文化形態(tài);四是傳播青年亞文化的風格特征,擴散其輻射范圍,延長其生存周期。在互聯(lián)網(wǎng)等現(xiàn)代媒介的助力下,年輕人從日常生活中的經(jīng)濟、文化束縛中解放出來,以青年文化話語為基礎,自由自在地結成跨地域、可交流的新聯(lián)盟①[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亞文化之后:對于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第195頁。,并通過積極的“符號創(chuàng)造”實踐,讓“風格的意義”不完全存在于亞文化突擊隊(subcultural shock troop)這個小圈子的“符號游擊戰(zhàn)”中,同時也存在于通過日常“基礎性美學”參與到認同建構的快樂的普通青年當中②陶東風、胡疆鋒:《亞文化讀本》,第343頁。。在媒介力量的深度參與下,后亞文化時期的青年亞文化已經(jīng)發(fā)展為一種虛擬性與現(xiàn)實性交相輝映,不斷突破地域局限、年齡界限、階層壁壘的全球性文化景觀。
結 語
總體而言,后亞文化學者們雖然都認識到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理論在闡釋青年亞文化實踐新發(fā)展方面具有局限性,需要構建新的亞文化理論體系,探索新的亞文化解釋框架,但他們在是否保留亞文化概念,以及如何構建新體系、新框架方面卻未達成明確一致的意見,也未形成相對統(tǒng)一且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在后亞文化學者中,既有主張放棄亞文化概念的激進主義者,也有主張試圖保留和修正亞文化概念的改良主義者;既有對伯明翰學派理論范式和研究范式的批判、背離,亦有對伯明翰學派理論范式和研究范式的回歸。
作為伯明翰學派對立面出現(xiàn)的后亞文化理論,在對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進行批判的同時,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幾乎同樣多的質疑。如以布萊克曼③Blackman,Youth Subcultural Theory: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Concept,Its Origins and Politics,From the Chicago School to Postmodernism,Journal of Youth Studies,2005(8),pp.1- 20.、黑斯孟哈④Hesmondhalgh,Subcultures,Scenes or Tribes:None of The Above,Journalof Youth Studies,2005(8),pp.21- 40.為代表的學者對后亞文化理論無視政治力量的質疑,如以特利沙·希特利克、羅伯特·麥克唐納⑤Tracy Shildrick and Robert MacDonald,In Defence of Subculture:Young People,Leisure and Social Division,Journal of Youth Studies,2006(9),pp.125-140.為代表的學者對后亞文化理論低估了階級和其他的社會不平等對當代青年文化的潛在義的質疑。再如以納亞克、波士、荷蘭斯為代表的學者對后亞文化理論過于強調(diào)亞文化是青年個體化、流動化的消費選擇的質疑,指出青年文化認同將繼續(xù)“與家庭歷史、性別、職位、階級、地域緊密聯(lián)系”⑥A.Nayak,“Ivory Live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Making of Whiteness in A Postindustrial Community,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3(6),p.320.,“種族、階級、社會隔離、權力關系等核心概念,仍是理解青年生活方式和文化選擇的中心”⑦M.Bose,“Race and Clas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in David Muggleton and RubertWeinzierl eds.,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Oxford: Berg Publishers,2003,p.178.,文化認同依然“視結構背景和物質因素而定”,“根植于‘真正社會世界’的社會結構”⑧S.Ball,M.Maguire and S.Macrae,Choice,Pathwaysand Transitions Post-16:New Youth,New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City,London :Routledge/Falmer ,2000,p.55.等。因此,無論是來自后亞文化理論內(nèi)部的分歧,還是來自后亞文化理論外部的質疑,都表明后亞文化理論的發(fā)展依然任重道遠,構建一個能精準描述和解釋后現(xiàn)代青年亞文化圖景的理論框架仍是迫切之需。而從伯明翰亞文化理論與后亞文化理二元對立的牢籠中跳脫出來,兼收并蓄地引入更多的理論解釋工具未嘗不是后亞文化理論發(fā)展完善的合適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