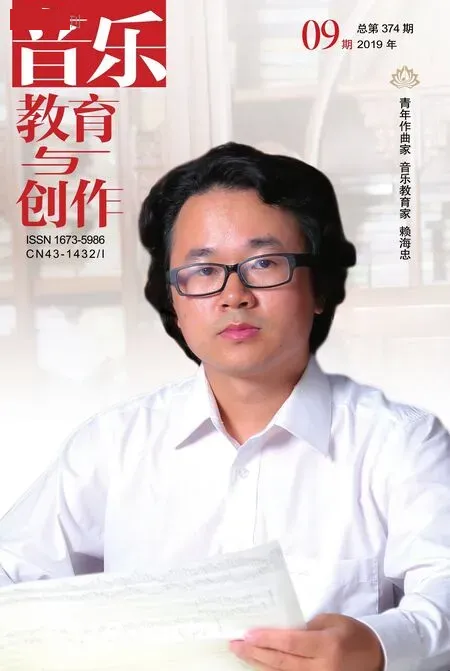原生態音樂德育功能彰顯的路徑研究
□ 楊明剛 付 仿
為了創造尋根的“天人合一”的德育生態與文化環境,原生態音樂德育功能的彰顯崇尚道法自然,以敬畏之心認識世界,以慈悲憐憫、和善純良之心面對他人,以清凈之道沉潛覺悟道德境界,以原生型音樂質料浸潤道德生命個體,以“無為”實施德育,以“不言”教化他者,在人、社會與自然的均衡和諧發展的生態共同體中尋找與感受生命的本真與價值,筆者認為原生態音樂德育功能的彰顯可以通過以下路徑:
一、道法自然,推行不言之教
原生態音樂德育功能發揮需要德育主客體順應自然,致虛守靜,充分發掘德育主客體自組織的內部系統功能,行不言之教,回歸德育的生態場域。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的開放與系統,其內平衡主要是靠生命與環境系統的耗散、超循環以及協同等來維系,德育主體與自然、社會系統之間是一個平衡——不平衡、有序——無序狀態的相互轉換與耗散的過程,通過協調、合作、互補,“一個非平衡的開放系統,不僅可以通過突變從無序走向有序,而且也可以通過突變從有序再進入混沌狀態。”(鄒甲申,鄧浩:論馬克思主義自然哲學[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15.)。
在真實性、整體性與奠基性的原生態音樂德育的場域中,德性從個體的內心滋長,具有存在依附性與內傾性的特點,德育主客體通過回歸自然的方式,挖掘德性于自然中的內在依附性,道法自然、回歸自然,多樣與多元的自然不至于遮蔽人的個性。尊重自然規律,充分調動整體系統的內調節力量,是作為德育主體面的人在面對人、社會與自然的混沌體時應有的態度和方式。
針對當下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說服式德育方式,德育的過程漠視對自組織系統功能的發揮,借外力干預強力灌輸,其結果必然導致德育主體的自組織的調節功能的喪失,內生性的學習欲望亦消失殆盡。實施原生態音樂德育的主體需要秉持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復歸于樸的生活態度與方式來面對德育的內容,而且應該采取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貴柔守雌,挖掘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誠如Bergson 所言:“一個由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社會要求命令的秩序體系,和由代表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的人們向我們每一個人所作的一組呼吁。” (Bergson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p.68.)。
由此,我們可以從人、社會與自然的整體維度充分發掘其德育意蘊與內涵,倡導不言之教。其一,發掘榜樣的力量,通過宣揚榜樣的先進事跡來引導德育內生性的形成,如城步的盤歌、排歌和古言中就以岳飛、花木蘭以及本民族信奉的神作為榜樣;其二,積極挖掘內生性力量,在大自然中體悟真善美,致虛守靜,仰望天空,通達宇宙與生命的意義,促成德育的自我生成。德育的有效性需要人的沉潛修煉、致虛守靜、復歸于樸,充分發掘德育主客體自組織的內部系統功能。
二、天人合一,重視聆聽與交流
天人合一的原生態音樂的德育觀認為,德育主客體是一種平等交互的主體間性關系,亦是一種主客維度消弭的非主體關系,強調主客體間的平等與自由,這種主客關系的融合有利于交流與互動,德性在平等的身體場域中,“大德”與“玄德”的標準得以澄明,教化內化于心,主體性在自由精神的彰顯中得到釋放,在“天人合一”與“身心合一”的包容宇宙萬物的場域中,“天人合道”與“天人合德”的審美之境得以生成。
傳統德育課堂將德育內容視為嚴肅的規訓性內容,認為師生是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教師是主導,學生是服從者與聆聽者,不平等的師生關系必然導致學生學習主動性與創造力的逃離。
欲構建平等的原生態音樂場域中的德育師生關系,其一,要構建符合原生態音樂德育功能有效性發揮的環境,即以歌聲為媒介,以天地為教室,宇宙萬物為施教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言一行,一曲一詞皆為為教材,這里只有組織者,沒有灌輸者;只需引導者,無需領導者。其二,教師需去聆聽學生發自內心的、富有天性的、自然淳樸的、感性生動的原生態音樂彰顯的道德見解。要讓學生不再是被動的受眾,而應成為主動的道德探尋者。
再者,師生應是充滿對話與交流的互動,因為“沒有了對話,就沒有了交流;沒有了交流,也就沒有真正的教育。” ([巴西]保羅·弗萊雷:被壓迫者教育學[M],顧建新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師生在“和而不同”的氛圍里,相互啟發,自由言說,從而使獨立思想得以自由表達,創新思維得以繽紛綻放,精神視界得以多邊融合。“在生態論視域下,課堂始終充滿著未確定性和未完成性,蘊含著轉變和創造的種種玄機。”(周慶元,黃耀紅:走向課堂的生態和諧[J],高等教育研究,2008(3):76.)。“未確定性”和“種種玄機”正是激發學生德育創造力、好奇心與興趣的內在動力。
由此可見,欲使道德教化內化于心,就需要使交互的師生融入到天地宇宙之間,到原生態音樂的環境之中,吸吮天地之精華,領略傳統音樂文化之精要,虛其心,篤其行,切己體察,方可真正成為孔德之人。
三、環境陶冶,倡導自覺自悟
原生態音樂的德育環境具有潛移默化的特質,它是一種原生意義上的本真傳承,是自然對自由生命體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浸淫,是非概念性、非功利性的人與自然的互動與交往,多樣性與差異性的生命個體具有與自然交往的內在動力,“生命的千姿百態為人們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擴大和加深了人們本來已有的與大自然的交往。”(雅斯貝爾斯:生命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知新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1:116.)。
原生性的傳統音樂文化在陶冶性情、修心養性以及德行建構之中,呈現出超越物質性界定的詩化的道德精神感化力量,陶冶是一種生活世界的教育,“陶冶作為某一時代世界和宗教的歷史現實性之語言是充滿生命力的,同時陶冶又是交流、喚醒和自我實現的中介。”(雅斯貝爾斯:生命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知新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1:103.)。作為真實、可感、具體、感性及在場的德育方式,陶冶亦是一種現實的倫理的生活表征,是遠離抽象“道德律令”的人性化感動與創生性本真精神的生成,面對創造性的、能動的、能生長的德育對象,在“天然給定性”中世界接近,直面事物的本身。“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性,陶冶則意味著,在鑄造和展開人的這一天然給定性過程中,通過人自身的活動、意識和他特有世界的形式與一般的形式接近。”(雅斯貝爾斯:生命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知新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1:104.)。
德育實踐中亦需要主客體具備生命關懷理念,當踐行德育成為生命自覺,德育內涵必然會在德育對象心靈深處產生強烈的震撼,德育主體自然成為杜維明先生所言的“為人楷模的德育導師”,“在儒家傳統中最崇高的理想人格是圣王。在這個理想背后的信念是人必須自我修身,以成為一個為人楷模的道德導師”。(杜維明:一陽來復[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144.)。馬克思也認為“自覺的活動”是“人的類特性”,“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6.)。這就說明,德育的主體首先是自由的具有自我意識的個體,德育的對象應該是“自由自覺”的人。
在原生態音樂的德育過程中欲充分利用環境陶冶的功能,發揮德育主客體自覺自悟的能動性,彌補傳統德育在此方面的不足,我們可以: 第一,倡導學生深入自然與生活世界,深入少數民族地區的田間地頭,在原生態的音樂環境中感受倫理道德精神,因為陶冶就是現實的德育知識,“陶冶活動本身就是已獲得教養的表述和繼續教育的途徑” (雅斯貝爾斯:生命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知新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991:103-104.)。第二,可以美化校園環境,將優秀的原生態音樂文化融入其中,賦校園環境以魅;第三,營造寬松活躍的課堂氛圍,構建人性化的考核內容體系,體現真善美的道德追求,確立知識、信仰與行動合一的目標;第四,引導德育主體重視生命自覺與自悟,沉潛、冥想、徹悟德育的文本理論,從生命意義的本真和靈魂、心靈的敞亮的高度將德育的內容融入生命主體,并化于天地之間,踐行于切實將“覺”與“悟”作為德育過程的重要一環;最后,將包括原生態音樂文化融入德育范疇,充分利用原生態音樂文化的親近感和認同感,找到文化自信,在自信的基礎上通過自覺與自悟達成文化自覺,通過本民族的文化張力提升民族文化影響力進而彰顯生命意義,因為“接地氣”的文化積淀更加容易吸引、催生生命自覺與自悟的呈現。
四、審美世界:激發原生性審美體驗
馬克思認為審美是人與自然的對象性活動,人具有審美的需求,用藝術的方式和用經濟的方式掌握世界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社會的人的感覺不同于非社會的人的感覺。只是由于人的本質的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如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總之,那些能成為人的感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才一部分發展起來,一部分產生出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6.)。審美活動是德育主客體的創造性活動,是一種異于道德說教的生命本真的審美呈現,是作為社會的人的本質力量的一種特殊的展現。同時,審美主客體是交互的雙向生成的辯證統一的關系,存在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大自然的美以“道”的形式呈現,而“道”具有無形性,主體依附性和內傾性的特點,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李耳:老子[M],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2003:2.)。自然美依附于主體的審美感受,內生于主體的生命頓悟,只可默會,不可言傳,渾渾噩噩,不即不離,若即若離,需繞開語言的表述,作自然之子,身臨其境,因為“從語言過渡到生活的整個問題,只存在于哲學幻想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28.)。需用心參悟,通過深刻體驗直達宇宙與生命之道,體驗神奇的非理性的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提高審美意識與修為,在混沌境界中整體的感悟自然無形的美。
盡管如此,但是,現如今的我國大學德育基本是停留在教師的道德說教與照本宣科的書本教材當中,殊不知枯燥乏味的說教會使生的心靈逃離德育的本真,主客體的靈肉交往才能產生精神的提升與靈魂的陶冶,既不主動親近大自然,還忽視自然之美的交互作用。
針對此種情況,首先,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要認同并踐行德育教材的構成元素就是一場“旅行’的觀點。筆者認為費孝通老先生于1990 年的80 華誕的聚會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社會和諧觀點,對解決目前的德育困境具有積極的意義。其一,各美其美,就是要認識到自然美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與獨具個性的五彩繽紛的自然界交互可以給德育的主客體帶來創造性的體驗,皮亞特認為:“知識在本源上既不是從客體發生的,也不是從主體發生的,而是從主體和各個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初便是糾纏得不可分——中發生的。”(常俊玲:原生態藝術傳承與兒童審美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9.)。德育的有效性就是在這種“糾纏得不可分”的“天人合一”的整體的混沌狀態中得到提升的。其二,美人之美,尊重各個民族的原生態文化,大自然是以“游戲”方式存在的,“游戲”不是一種實體性的活動或某種對象物,而是藝術作品中那種具有吸引游戲者(藝術創作和欣賞者) 的魅力并使游戲者“卷入”到游戲中的東西。([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 [M].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137.) 因此,給德育主客體以充分的自由,心懷淳樸本真的游戲精神,釋放主體的精神動能,毫無保留的懷抱大自然。
綜上所述,原生態德育應在無為的混沌狀態之中,在真實自然不矯揉造作的行動中,在看似閑散閑暇的交往中,秉持尊重多樣性、差異性、主體性的原生態德育理念,遠離說教,重視人的欲望喜好,順應人的本性,釋放人的生命。利用主體心靈的存在依附性、內傾性與內生性功能,使原生態德育意蘊內化于心,充分調動德育對象的自組織的內部系統功能。心懷敬畏與謙卑,知天命,順天理,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堅持“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張永祥:國語譯注[M],上海三聯書店,2014:413.) 的原則,參贊化育,構建廣延性、無限性與自主性的德育課堂,以新的原生態視角著力提高德育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