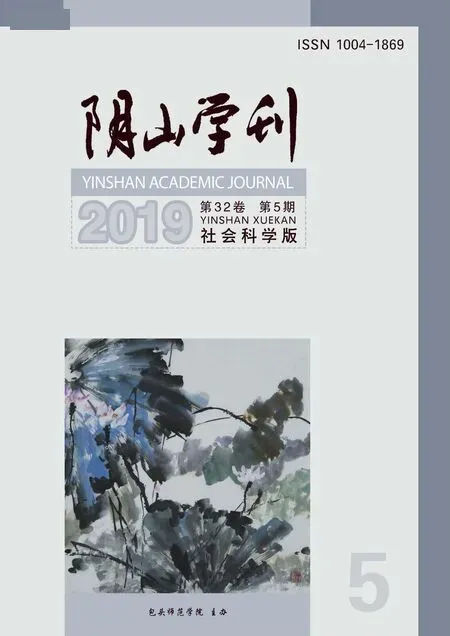“一帶一路”倡議下南海的新“航行自由”觀
——反駁美國“過度海洋主張” *
呂 禎 禎
(海南大學 法學院,海南 海口 570100)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推進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國維護周邊環境安全的戰略舉措。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離不開海上自由通行問題的解決,甚至可以說“航行自由”在“一帶一路”的建設和合作中起到相當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對中國而言,中國南海溝通了印度洋與太平洋,其優越地理位置不僅體現在航海便利上,同時也體現在此海域上空的政治與經濟效益匹配上。另一方面,南海通道對我國能源安全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在南海的國際法立場上,中國主張的“航行自由”是在不損害國際法以及沿海國主權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海洋航行和貿易的權利。這一主張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平利用海洋”以及“不得對各國進行武力威脅”的規定,有利于保持與南海周邊國家的穩定關系,也有利于妥善處理我國與東盟、與美國的關系。在國際法的框架之下,中美兩國通過各自主張的“航行自由”理論進行博弈也是合理穩妥地應對南海爭議問題的一種重要途徑。但美國的“過度海洋主張”缺乏《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支撐,甚至是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錯誤解讀,明顯違反了其中“和平利用海洋”的原則。
一、“一帶一路”倡議豐富了“航行自由”理論的內涵
(一)“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合作原則
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的聯合公報中,中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五項合作原則,包括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和諧包容、市場運作、平衡和可持續。其中,平等協商原則強調對他國領土完整的尊重以及對他國行使主權采取不干預的方式,這充分體現了五項合作原則建立在《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的基礎之上。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之上開展相應合作項目的協商和規劃。在與東盟國家的交往中,中國本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體現的國際法精神,提出保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和航行自由及安全。這種提法更有益于南海沿海各國在共同恪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基礎之上進行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議,從而避免采取極端行動使爭議擴大化、復雜化。國際法首要的基本原則就是主權獨立平等,而“一帶一路”倡議中提出的五項合作原則首先要求沿線各國相互尊重他國的主權,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不得以任何形式對他國國家獨立和內政以違反國際法基本精神的任何方式進行侵犯與干預。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互利共贏、和諧包容就是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延伸以及演繹。同時,這為中國在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框架之下主張“航行自由”提供了支撐。
(二)“航行自由”理論的源流
“航行自由”源自海洋自由原則,是海洋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在海洋大國早期殖民擴張以及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和對外交流中產生了重要影響。15世紀時,葡萄牙和西班牙意圖通過宣稱對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主權、禁止他國的貿易和航行來瓜分世界。英格蘭提出反對,認為海洋可被所有人利用,不得為任何人據為己有。直到17世紀,荷蘭國際法學家格勞秀斯從自然法的角度撰寫了《論海洋自由》,認為海洋不屬于任何國家,所有人都有進行海上航行和貿易的自由。[1]并且格勞秀斯認為海洋與內海和海灣是不同的,后者可以被沿海國家完全控制。而沿海國即使擁有對某一海域的主權,也不應阻礙其他國家的航行自由。后來這種觀念逐漸普及開來。按照當時的國際習慣,普通商船和軍事船舶并未明確區分,因此軍事船舶的自由航行未受限制。此后,航行自由成為廣泛承認的海洋治理原則之一。第一部關于海上捕獲和封鎖的國際公約《巴黎會議關于海上若干原則的宣言》在1956年誕生。該宣言并未出現“航行自由”一詞,但對航行自由和貿易自由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來又確立了海洋中立、普通商業航行不受軍事干擾等國際海戰規則,奠定了航行自由的法律基礎。1958年的《公海公約》規定了“公海自由”原則,并將海洋劃分為“領海”和“公海”。航行自由主要是在公海,自此“航行自由”原則由習慣法轉化為成文法。而后來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明確規定海洋作出五部分的構成。其中領海是一國享有完全主權的領域,在此區域,此國可以獨立自主行使完全性排他性主權。可見,航行自由則適用于除領海和毗連區以外的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和公海。但航行自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和平目的利用海洋”的宗旨。因此,締約國要以和平的目的進行海洋活動,自由航行不得以損害沿海國家的合法利益為代價,包括主權性權利和執行管轄權。此外,領海的無害通過制、群島海道通行制和海峽水域的過境通行制都是對航行自由的限制。同時,公海中的航行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公海航行懸掛旗幟等。此外,航行自由還要求維護安全和保護自然生物資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系統龐大、內容繁雜,其中的航行自由是通過不完全列舉進行規定的,其受限的范圍和程度并未明確規定。因此其模糊性為一些國家根據自身利益進行解讀提供了空間,從而導致航行自由問題產生復雜化、類型化的趨向。另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未明確規定沿海國的領海是否允許他國軍用船舶無害通過,使得各國就航行自由問題產生許多沖突。另一方面,海洋爭端既是爭海洋中蘊藏的豐富自由,也是爭航道方便國際貿易,由此推動了航行自由的理論和實踐的不斷發展。
二、美國的“過度海洋主張”理論及實踐
二戰后,美國的海洋大國地位受到挑戰。為維護其海洋航行自由,美國對沿海國家提出“過度海洋主張”。美國的航行自由政策源于1945年的《杜魯門公告》。《杜魯門公告》認定大陸架的水域屬于公海,公海自由和無礙航行的權利不受任何影響。于是,美國政府于1979年制定了“航行自由計劃”,其目的是保障其軍事力量在全球范圍內暢通無阻。
(一)美國“航行自由計劃”的內容
“航行自由計劃”是針對沿海國一種“過度海洋主張”。總體來說,其由以下部分內容構成。首先,美國對他國歷史性海灣水域采取了否定的立場。即使這個國家能用事實以及文獻等方式來論證這個海灣水域是具有其本國自身的歷史性特征,但美國依然不承認歷史性海灣水域在國際法上應有的合法地位。其次,美國主張劃定領海基線可以不以國際習慣法作為依據,即使這種國際習慣法來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提倡的內容以及基本精神的要求。再者,如果一國的領海在寬度上小于12海里,那么此時此國領海可以被視為覆蓋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可以不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體現的國際習慣法,在此海域不再實行嚴格的“過境通過”。因此所有通過此海域的船只,即使這些船只是海軍輔助艦船和軍艦性質的也同時享有無害通過權。只要這些船只在通過此區域之前對沿岸國采取了事先通知方式或得到沿岸國批準即可“無害通過”。可見,美國這種主張擴大了“無害通過”的主體種類。在其看來,承認了“無害通過”船只可以自由選擇載有何種貨物種類、甚至能夠容許載有武器裝備進行通過。這些“無害通過”理論的要求完全顛覆了國際法的邏輯。并且,如果一國主張其領海寬度超過了12海里,那么此國可以作出聲明對12海里以外的海域擁有被國際法所默認的管轄權,例如可以在此區域設置諸如所謂的安全警戒區域;甚至對所謂安全區域進行等級劃分。但國際習慣法不容許美國設置拒絕群島海道通過等障礙。可見,“航行自由計劃”作為美國的“過度海洋主張理論”,旨在維護美國片面主張的“海洋自由原則”。它強調的是在政治與軍事領域進一步對沿海國家的“海洋主張”進行圍堵以及限制主權國家在國際法范圍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從而保證美國軍事力量的全球機動暢通。同質而言,美國的“過度海洋主張理論”理論是新時期美國海洋霸權的體現,挑戰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美國政府在此理論的幌子之下進一步制定了緊密的外交活動,以“軍事宣示”的方式來對抗其他沿海國家的“海洋主張”。
(二)美國利用航行自由理論在中國南海制造的海上摩擦
美國并非南海問題的當事國,但其一直關注并干涉南海及其他海域的航行自由,甚至美國政府通過發表國際聲明的方式來宣稱其對中國南海的權利。例如“關于南沙群島和南中國海的政策聲明”以及“關于南海問題的聲明”。甚至還炮制出所謂的《海洋界限: 中國在南海的海洋主張》等政府官方文件。美國極力對外聲稱,南海的航行自由屬于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范疇。美國的這種對外政策直接體現在中國南海的航行自由摩擦事件上。中美在中國南海的對立沖突圍繞在領海內軍艦是否享有無害通過以及他國軍事活動能否發生在另一個國專屬經濟區內等方面。近年來,美國軍艦無視中國的南海權利和安全,以“航行自由”為借口進行行動,引發中美兩國的摩擦和矛盾。2018年1月17日,美國以闖入的方式直接以將其驅逐艦“霍珀”號部署在中國黃巖島的海域。中國海軍對此作出強烈的警告,并且通過軍事方式作出回應美國的這種違反國際法的做法,即“黃山”號導彈護衛艦對驅逐艦“霍珀”號進行了驅逐。類似事件還曾數次出現。例如在2017年8月10日在中國南海的美濟礁12 海里內發現了美國的驅逐艦“麥凱恩”。同樣,中國政府在符合國際法范圍內派出中國海軍對美國的驅逐艦“麥凱恩”查證識別并作出了必要的警告和驅逐。美國在2017年7月2日還命令導彈驅逐艦“斯坦塞姆”號在未經中國政府允許的情況下,擅入西沙群島中建島12 海里,中國海軍派戰斗機和軍艦對其進行警告驅離。2016年12月15日,中國海軍在南海附近海域打撈上一艘美國水下無人潛航器,次日美國聲稱該船是美國“鮑迪奇”號海洋測量船,呼吁中方立刻歸還,此事件再次表明美國在其航行自由理論之下無視國際法秩序。
(三)美國“航行自由行動”的缺陷
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由來已久,其戰略意圖有三:第一,對抗沿海國的有關“過度海洋主張”。第二,借以進行軍事行動,進行外交抗議。第三,試探外國并進行磋商。由此可見,美國采取“航行自由行動”是其海洋戰略的重要部署,旨在鞏固其傳統海洋強國的地位,延續其海洋策略和政策,并且對國際法產生影響。美國從外交、軍事、國際法等各個方面對目標國展開行動,外交部和國防部聯合指揮,國防部以該行動顯示其某種主張,外交部借其抗議并挑戰他國的“過度海洋主張”,以咨詢和協商的形式規范海洋秩序。因此該行動又稱“羽毛和錘子行動”。美國為實現自身海洋利益,利用公約對航行自由的模糊規定,憑借堅實的海軍力量來達到其軍事、政治、經濟上的目的。同時,美國將“航行自由行動”程序化、規則化,以避免與對抗國的軍事沖突,以此表現其重視國際法而避免使用武力。然而,仍有相當一部分沿海國家對美國這些挑釁性行動表示不滿和反對。《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國際法和國際秩序都是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包容性”以及構建新型國際關系。[2]因此,美國戰略性的航行自由行動危害十分明顯,其實質是利用傳統的海洋自由原則,以軍事和外交部署為手段實現美國自身的利益。盡管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得到精心安排和論證,在國際社會構建新的海洋秩序之時,美國利用自身軍事力量表達訴求的行動屬于肆意破壞和扭曲一般國際法的單邊行為,是國際法中的霸權主義。即使一般國際法或國際法的一般法律原則并沒有完全精準的定義,但一般法律原則作為國際法的淵源,也是各國國內法體系的共有原則。[3]美國為實現自身海洋利益而利用1958年在日內瓦達成的四個海洋法公約所形成的對其有利的條款,固守海洋法秩序的“二元論”,單邊創立了“國際水域”并任意構建“過度海洋主張”,并肆意解讀國際法的一般法律原則。然而,我們根據《海洋法公約》的序言和正文,可以推出公約的根本精神在于各國應以互相合作和諒解的方式解決海洋問題;并且各個海域的問題密切相關,應從整體上進行考慮。公約序言中要求各締約國在公約框架下遵循總原則。而對于非締約國,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非締約國不受條約約束。但若《海洋法公約》的非締約國以國際習慣法等方式接受某種權益,則要同時履行相關的國際法或公約規定的義務。
三、中國新的“航行自由”觀對美國“過度海洋主張”的反駁
從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海外貿易格局來看,有超過80%的貨物是需要通過中國南海航線運輸。一旦中國南海自由航行遇到障礙則必然導致南海航行受阻,中國是最大受損國。但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緊密相關,南海航行受阻也必然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作用。毫無疑問,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更關心中國南海的航行自由問題。中國提出新的自由航行觀,旨在使中國南海航行更加自由同時也更加安全和便利。《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規定的“和平目的利用海洋”的原則適用于所有的海域,也涵蓋了中國南海附近的水域。由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航行自由的模糊性規定,在一些具有主權爭端強烈的海域,某些國家懷有干涉他國主權的意圖而有對航行自由原則作出了違反國際法的任意解讀,從而對他國海洋活動進行了粗暴的擾亂。事實上,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通過遵循公約的宗旨,參考相關國際法的規則并且使用相關公約解釋或者適用的協定,也可以解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因此,一些國家以此為由,通過國內立法來優化航行自由原則,減少公約的模糊性。如果其他國家的航行威脅到沿海國家的“主權性”權利,例如影響海洋環境和漁業利用,妨礙修建人工島嶼等設施,那么沿海國有權限制其航行自由。[4]2002年,“威望號”游輪漏油事故印證了這一點。中國新的自由航行觀形成和發展除了與中國自身政治經濟發展相關外,還有很大部分因素是中美不同的航行自由主張所帶來的海上摩擦。
(一)中國傳統的“航行自由”觀
中國傳統的自由航行觀認為在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內,外國軍事船舶和飛機進行的軍事測量和偵察活動違背了國際法的和平原則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這種觀點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原則和規定為基礎,結合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主張,著眼于近海防御為主的海洋安全觀。但隨著我國逐步走向海洋強國,越來越多的海外利益是需要通過海上航行途徑來實現。傳統的國家安全觀以保障國家領土安全為目標,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尤其著眼于軍事防范。但隨著冷戰結束、國際局勢的變化,國家安全觀也隨之改變。除了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國家安全還衍生出包括安全利益、安全發展和安全威脅等方面。[5]現代的國家安全觀包括領土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環境安全、信息安全和能源安全。[6]因此,對航行自由制度也應該開始從法律角度進行重新審視,并且還需要著眼于總體國家安全觀以及綜合考量各種安全因素。其次,中國海軍的發展也令國家安全觀被賦予新的內涵。以前的中國海軍由于缺乏遠洋作戰能力,近海防御為主的海洋安全觀催生過去所主張傳統的自由航行觀。但是隨著世界貿易一體化的進程加快,以及國際政治多邊合作日益頻繁,這些都要求對之前處于保守態度傳統的自由航行觀進行新的完善甚至改變。再者,中國海軍經歷了由黃水海軍過渡到藍水海軍的變化,海上力量擴展到遠洋及深海地區,已經形成了具備遠征作戰能力的新海軍型態。中國傳統的自由航行觀已經無法適應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對 “航行自由”的認識已從傳統的公海自由的單一形式逐漸擴展為適應不同海域的多種通行制度體系。
(二)中國新的“航行自由”觀對海洋航行權的充分行使持肯定立場
之前國內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大部分學者都對航行自由保持過于謹慎的態度與保守的立場。后來,中國主張的航行自由原則的內容也發生了明顯的新變化,例如中國在國際場合多次主張遵守國際法和尊重沿海國合法權利是實行航行自由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中國官方在國際場合對海洋航行權的充分行使進行了肯定。中方提出的南海 “航行自由”突出其內涵指向,不僅涵蓋國際法所規范并保護的各國船舶有權在南海無障礙通行基本含義,還包括相關的飛越自由、航道安全、海上反恐、海上安全等多層內涵。中國政府的官方行為可以被解讀為:中國新的“自由航行”原則是對海洋航行權的充分行使持肯定立場。1992年中國頒布《領海與毗連區法》,要求外國軍事船舶須經中國政府批準后才能進入中國領海。一些國家打著所謂的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別國海域進行軍事活動,對沿海國的主權造成了實質性的安全威脅,從而催生了新的航行自由觀。此外,中國提出新的“航行自由”觀旨在補充說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關于航行自由中涉及的軍事活動問題所產生的漏洞。同質而言,沿海國對他國軍事船舶在其領水中的航行自由進行一定的限制,是為了維護自身的主權性權利和自然資源以及海洋安全,但這并未違背國際法原則。雖然中國主張在南海的主權及相關權利權益也可能會受到其他國家對航行自由的質疑。但是中國政府通過多次發表聲明,中國積極參與建設南海航行安全,致力于以友好協商談判的方式解決與鄰國的爭議,維護南海的航行自由,不因南海爭議而使航行自由受到實際影響。
(三)中國提出新“航行自由”觀的原因分析
1.從“歷史性權利”的角度看待新“航行自由”的合理性
美國利用《公約》規定的模糊性,提出“過度海洋主張”,錯誤解讀“航行自由”原則,將領海的“無害通過權”當然適用于外國軍用船舶;且認為公約并未明確禁止外國船舶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軍事活動,根據“法無禁止即自由”的一般法律原則,美國當然有權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軍事活動。因此,美國忽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毗連區法》和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多次派軍艦駛入中國南海主權島嶼附近水域并從事軍事測量等活動,侵犯了中國主權領土安全和歷史性權利。
中美兩國在中國南海上摩擦頻發,除了政治原因,還在于兩國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航行自由原則和中國在南海“斷續線”內的“歷史性權利”的解讀是不一樣的。兩者在對中國在南海“斷續線”內的“歷史性權利”理解依然還存在主要層面上的根本對立的分歧。在美國看來,中國所闡述的中國在南海的“斷續線”以及“歷史性權利”解釋可以讓中國站在符合國際法基礎之上合法合理地在南海建設島礁。而在美國看來中國在南海建設島礁是一種嚴重侵害美國在國際社會上一直主張的“航行自由原則”。美國認為美國軍艦在中國南海奉行航行自由原則是在“國際水域”內進行航行活動,并且認為美國軍航所航行的中國南海水域并非是中國行使國家主權的、具有管轄權的水域。因此中國干預美國軍航在中國南海航行是一種不符合國際法的行動。而中國則不認同美國這種論證過程,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中的“航行自由”原則與美國的解讀不同。在中國看來,“航行自由”原則是指在不損害國際法和沿海國主權的前提下進行海洋航行和貿易。中國與南海的關系可以從“歷史性權利”的角度論證論證其邏輯正確性。國際法的“添附”規定給中國在南海建設島礁提供了十分充分的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明確規定了主權國家對島礁的各項權利。主權國家可以在以島礁為中心而產生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甚至包括毗連區以及大陸架方向內行使權利。中美在此問題上再次出現分歧,其原因主要在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航行自由”原則的規定存在模糊性和漏洞。另一方面,“歷史性權利”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缺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從1982年制定以來被稱為世界性質范圍之內的“海洋憲章”,在維護海洋秩序方面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在國際社會上主張本國的海洋合法權益的法律依據和來源。該公約在總體上體現了當時的國際社會對海洋問題的共識,但它仍然模糊甚至缺失了部分條款。《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航行自由權進行了不同情況的規定,而這些情況都建立在不同海域不同的法律地位之上。這些詳細的區分規定盡管可以避免一些漏洞出現,但是仍然潛伏了諸多模糊地帶,最為明顯的就是無害通過權存在較大的漏洞。外國軍艦是否被認為是無害通過權中所認可的船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未作明文說明,這導致了不同的國家以自己立場和利益需求作出了任意解讀。例如美國認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沒有明確規定軍事船舶和飛機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航行活動,而是允許其享受公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未禁止軍事船舶和飛機在公海航行中的測量和偵察活動。因此,沿海國對他國在其專屬經濟區進行軍事測量和偵察的阻止不符合國際法。這種觀點建立的基礎是航行自由原則的發展過程、航行自由原則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里的結構位置以及各國對領海“無害通過權”的法律限制的對比。雖然在客觀上解釋公約的字面含義,但其忽略了沿海國家有權對自身國防軍事安全的進行正當合法的關切。而對于“歷史性權利”,《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未使用“歷史性權利”這一概念,只是在第10條、15條及298條提到“歷史性海灣”和“歷史性所有權”,并未規定或說明其定義、性質、構成要件等。因此,各國根據需求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不同解讀和適用,并不意味著各國可以隨意解釋乃至歪曲這些概念,美國提出的未禁止軍事船舶和飛機在公海航行中的測量和偵察活動缺乏國際法的法律支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國際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假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身的規定存在模糊以及爭議,那么解讀這些模糊不清的規定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據作為支撐。一般國際法原則在法律上提供了最有力、最有效的解讀《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法律依據。其次,解決模糊性規定和爭議的另外一種途徑就是,憑借《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身對于自身規定存在的模糊地帶的解讀方式作出了相應的解讀。《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其序言中就明確規定,一般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可以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模糊不清的條文解讀依據。并且《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正文部分中第 293 條也規定可以適用不與公約相抵觸的國際法規則。另一方面,在國際法體系中也可以找到邏輯上的依據,例如《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本身就確立了現代國際法條約應該如何解釋的諸多規則。從這一角度來看,各國解釋和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于“航行自由”原則以及“歷史性權利”等概念的厘清,完全可以從以上所論述的途徑中找到解釋方法和適用框架。因此,根據一般國際法原則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以及和平利用海洋的宗旨,可以正確解讀“航行自由”原則,也可以解釋美國對“航行自由”原則的過度主張以及中國基于自身合法權益要求一定程度限制“航行自由”原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應對南海局勢變化的必然要求
近年來,南海 “航行自由”問題逐漸成為中美在亞太地區進行博弈的重要議題,美國以南海 “航行自由”為切入口介入南海問題,同時部分周邊國家以南海“航行自由”為借口使南海問題“國際化”。美國艦機巡航、黃巖島、中建南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致使南海地區安全局勢迅速升溫。為控制美國利用南海“航行自由”問題引發的負面影響,穩定南海局勢,中方提出了對南海 “航行自由”認知態度。
(四)中國新的“航行自由”觀在實踐中的應用
美國以“航行自由計劃”為借口,對沿海國實行航行自由行動,在此實踐過程中常與中國產生沖突。1986年,中國提出外國軍用船舶須經事先允許才能在我國領海無害通過,隨后美國軍艦未經中國事先允許就進入中國領海,實踐其“航行自由行動”,以挑戰中國的主張。中國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了自己的主張,例如中國將“外國軍用船舶須經中國批準才能進入中國領海”這一主張寫入法律。1992年2月中國頒布了《領海及毗連區法》就是中國在航行自由問題上的一種立法實踐反映。美國對中國以國內立法方式將“外國軍用船舶須經中國批準才能進入中國領海”寫入《領海及毗連區法》提出了外交抗議。美國認為該法案體現了中國的“過度海洋主張”,并通過多次“航行自由行動”進行抗議。但中方的立法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基本原則規定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中美兩國對“航行自由”原則的不同解讀導致雙方在專屬經濟區內的軍艦活動、軍事測量等方面產生了一系列的海空摩擦。[7]對于中國進行的南海島礁建設,美國以“航行自由”原則為其在南海的軍艦航行和軍事活動提供所謂的合法依據,否定南海島礁的合法地位,否定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8]美國在南海頻繁實踐“航行自由行動”違反“和平利用海洋”原則。因為“和平利用海洋”要求締約國在行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的基本權利時候不得以武力或違背國際法原則的任何方式威脅他國的領土主權和安全。[9]《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締約國有法律約束力,而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和長期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因此美國即使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也必須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作為有國際習慣法中的有關規定。特別是在“航行自由行動”問題的爭議方面,美國對“過度海洋主張”的定義顯然是按照公約的標準進行的。而在訂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各國因限于當時的海洋軍事設備和技術,未能預料到海上軍事測量對沿海國主權和安全以及對“和平利用海洋”宗旨的重大影響,因此未能詳細規定,但是從后來的其他法律法規中也可窺一斑。例如《南極條約》中規定的“和平目的”排除了軍事性質的措施,禁止軍事演習、武器實驗、建立軍事基地或要塞。[10]“和平利用海洋”是手段和目的兩者的和平,是對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尊重。沿海國為維護自身的主權和領土安全,要求他國的軍用船舶在進入其領海前事先取得沿海國的同意或批準,這也符合國際法的要求。美國以自身對《海洋法公約》的解讀為依據,未經事先允許和同意就進入中國南海海域,不僅曲解了航行自由原則,并且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安全以及侵犯了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在南海的斷續線內,最早進行考察記錄的就是中國。在元代時期,中國天文學家郭守敬在南海進行了天文觀測;1883年,德國擅自在該水域進行測量調查,受到中國的抗議后停止。近代以來,中國一直保持對南海海域的科學研究,對其享有優先權。2016年12月15日,美國水下無人潛航器闖入中國南海海域,中國對此作出相應的處理措施。這事件這也體現了中國為維護本國在南海地區的主權和歷史性權利,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國軍用船只在南海海域的航行。
四、結 論
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航行自由”在中國南海問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多年來,中國南海地區形成了國際習慣航道,各國享有過境通行的權利,但不意味著可以進行軍事活動,而應以和平為目的且尊重沿海國的主權和安全。“過度海洋”主張是以戰略主張為目的的外交辭令,必須認清實質,以理辯之,堅決維護我國在南海的合法權益。中國或可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方式對待“航行自由”問題。雖然難以否定或無視“航行自由”在國際上的歷史內涵,但可以豐富其國際法上的基本內涵,增添航道安全、飛越自由、海上遇險救援、海上反恐、打擊海上跨國犯罪等實際內容,與南海沿岸各國共同提出維護南海 “航行自由”的倡議,促進南海的海上航行自由與安全保障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