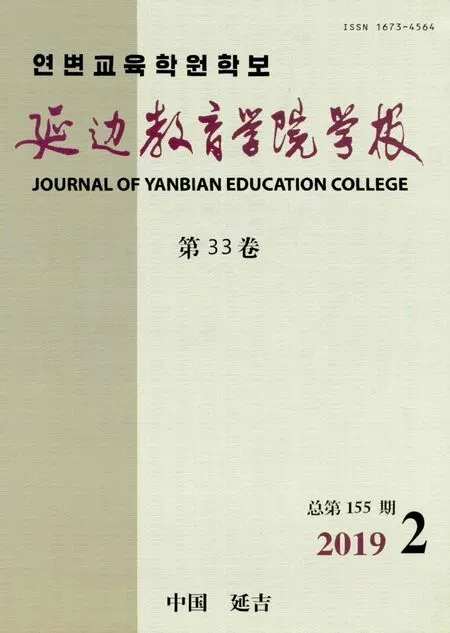“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學分析
王雪琪
“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學分析
王雪琪
(鄭州成功財經學院,河南 鞏義 451200)
“五四”白話文運動起源于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化,摒棄舊文學,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對語言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本文對“五四”白話文運動中對文言文的誤解進行分析,并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學考辨進行探討。
“五四”;白話文運動;語言學
“五四”白話文運動提倡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用白話文作各類文章,將白話文作為通用書面語。“五四”白話文運動對我國語言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推動著我國語言學的變革。
一、“五四”白話文運動對文言文的誤解
1.言文一致
“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認為文言文十分落后,主張對其進行變革。他們認為文言文會對人們的啟蒙教育形成阻礙,所以中國才會有大量的文盲。“五四”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傳播新文化,但文盲太多會對新文化的傳播形成很大的阻礙。言文一致說是建立在語言中心論基礎之上的,這種觀點認為文字附屬于口語,應保持文字與口語的一致性。比如,在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中,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會比中國發展得更好,是因為其文字與語言具有一致性,在語言方面占有明顯的優勢。但是,黃遵憲所談及的文字并不是中國表意的漢字,而是西方表音的文字,將其與漢字進行比較本身就是不科學的。我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這些文字的出現與口語并沒有多大關系,只是當時人們為方便“結繩記事”而發明的。白話文最開始出現在唐代,其與文言文處于平衡互補的狀態,文言文最顯著的特點是精簡,而白話文則比較生活化,富有時代性。文言文與口語之間的不一致,是從西方語言特點來看的,并不適用于漢語改革。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以后,白話文也沒有真正的口語化,而是形成一種語言混合體。
2.文言死文字
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中,許多運動發起人全盤否定文言文,他們認為文言文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書寫系統,應該隨著舊時代的遠去而被拋棄。比如,胡適曾在自己的《文學改良芻議》中認為,文言文很“死”,白話文則很“活”,用前者不如用后者。但實際上,文言文是一脈相承的,是在我國本土中發展起來的文字,其與語體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拉丁文、希臘文等,則屬于全死的文字,我國的文言文與這些國家的文字是有區別的。每個國家的語言文字都有自己的特征,也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所以,吸收其他國家語言文字中的精華,摒棄本國語言文字中的糟粕,本身是一種非常正確的行為。但是,通過一味否定文言文去推崇白話文也不可取。
二、“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學考辨
1.關于語言的中心主義
有語言學家認為文字只有兩種體系,一種是表意體系,一種是表音體系,漢字就是表意體系中最典范的例子。
(1)西方語言中的聲音中心主義
西方語言學家在對語言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基本沒有涉及到漢字,主要對表音體系進行研究,且所研究的表音體系是以希臘字母為原始型的體系。比如,黑格爾認為,語言發展規律與歷史發展規律是相同的,都是從低到高。德語、拼音文字等的出現,都是為了對聲音進行記錄,所以在黑格爾眼中,語言就是一種比較好的文字形式。漢字屬于表意體系,為非拼音式語言,其不具備較為適當的“正音發展之手段”,所以不能像西方文字那樣將個人的聲音表現出來,不能將口頭語言直接呈現出來,只能通過相關的符號將觀念本身再現。因此,黑格爾認為漢語發育不全,能呈現書面表達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從本質上看,無論是西方的思想、哲學,還是西方的文學和藝術等,其語言基礎都是以聲音為核心的,即都體現著聲音中心主義。
(2)漢語中的文字中心主義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漢語都在一個十分封閉的環境中發展,并沒有經歷過外來先進文明的挑戰,所以在漢語發展過程中也未曾進行自我審視。“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接受過西方教育,當西方文明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時,由于漢語所承載的思想和文明都比較落后,所以即使漢語中的優點也被視為缺點,認為漢語不具有可取之處。于是,漢語便自我消融到西方語言中。但是,有的西方語言學家雖然對漢語持輕視態度,也將表意體系作為兩大文字體系之一,而表意體系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漢字。比如,有些西方學者對漢字、西方文字進行對比分析,認為兩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漢字并不受“聲音中心主義”的支配。漢語也并非黑格爾所說的發育不全,其有著自身的優點。如果將西方語言看做是以聲音為中心的,那么漢語則是以文字為中心的。即西方語言可能有兩種本位,一是言本位,二是音本位;而漢語也有兩種本位,一是文本位,二是字本位。“五四”白話文運動就是從文字中心主義到聲音中心主義的轉變。
2.語言的不同屬性
(1)工具性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研究者認為語言只具有工具性。“五四”白話文運動也認為白話文只具有工具性特點,認為文言文不是適用的工具,而認為白話文十分合用,所以要將文言文這一不適用的工具棄掉,只使用合用的白話工具。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廢止文言文,因為文言文在代表思想的時候不是那么方便。同時,提倡使用國語,因為國語在代表思想的時候則十分方便。所以,從本質上來看,“工具論”認為思想與語言之間存在二元對立關系,思想先于用語言,有的思想可以脫離語言而存在,有的語言也可以脫離思想而存在。思想有具體的內容,而語言是一種形式,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對思想進行革命,能夠實現“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文字則是傳達新思想的重要工具。認為語言只具有工具性特點,那必然會形成語言與思想脫離、與文化脫離、與民族和歷史脫離的結果,因為語言具有思想本體性。
(2)思想本體性
之所以會出現“工具論”,是因為在“五四”白話文運動期間,無論是西方哲學還是中國哲學,在語言認識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實施過程中,就有人開始意識到語言不只具有工具性。比如,從陳獨秀的觀點來看,文言文承載不了新的事物和道理,文言文中還存在著許多腐毒思想。周作人也認為,其之所以會反對文言文,是因為在文言文中存在許多荒謬的思想,會危害讀者。陳獨秀和周作人認為文言文比白話文落后,不僅體現在其作為工具方面的落后,還體現在文言文所承載的思想太過于腐朽,這就說明語言具有思想本體性特征。
3.不同類型的語言
文言文帶有明顯的局限性,本身顯得十分老朽,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五四”白話文運動期間,有許多新的思想和見解涌現出來,這些新的思想、見解急需要得到表達,這就為白話文創造了很重要的發展平臺,將文言文逼向沒落的深淵,白話文因此而取得勝利,并出現不同類型的語言。
(1)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
語言學家認為語言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世俗語言,一種是詩歌語言,前者包括口頭語言和除后者以外的語言。世俗語言即日常語言,其主要功能是工具,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溝通。在對日常語言進行使用的過程中,要遵守相應的規則,會被語法所限制。書面語言被周作人稱為“文章語”,他認為一個國家只能有一種國語,但可以有口語和文章語兩種語體。口語是在普通說話的時候使用,文章語則是在寫文章的時候才使用,但文章語要以口語為基礎,在用字方面會比口語更加豐富,在組織方面也會更加精密,主要用于對比較復雜的思想感情進行表達,口語不具有這些方面的能力。比如,口語與書面語在語體方面就不同,所以在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會不同。說話為口語,即使將其記錄下來也不代表其就是書面語,書面語無論是在用字上,還是在組織上,要求都會更高。但“五四”白話文運動中的胡適卻沒有對兩者加以區別,認為“話怎么說,就怎么寫”,這會降低書面文章的質量。
(2)詩歌語
詩歌語與口語和書面語都不同,不需要絕對的服從外在結構和法則,更注重對精神能量的體現。比如,語言學家認為,在語言最開始形成的時候,所有事物的生命都被認為是神關注的,所以語言具有神性。而在對每一種事物進行命名時,更需要豐富的想象能力,相比之下對推理能力的要求就不那么高,這時候的語言又具有詩性。但是,在對語言進行使用的過程中,神性逐漸被疏離,賦予其更多的邏輯性,使得語言成為人們日常交際中用的工具,詩性也逐漸被隱藏。怎樣才能使消失的詩性再次出現呢,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認為,采用文學中的“陌生化”原則,能夠使語言的詩性呈現出來。也就是說,要賦予日常語言藝術性,增加語言形式的復雜度,這樣就能達到增加感覺難度和時間長度的目的。因此,詩歌語言是一種讓人比較難懂的語言,又是一種比較晦澀的語言,在這類語言中還會充滿障礙。然而,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中,詩歌的魅力卻蕩然無存,成為與日常語言并沒有多大區別的語言。
綜上所述,“五四”白話文運動中對文言文存在一些誤解,聲音中心主義與文字中心主義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而白話文運動就是后者向前者的轉變,并開始體現出語言的不同屬性,不同的語言類型在白話文運動中也受到曲解,使得語言學的發展在當時有些混亂。
[1]于小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語言源流[J].中國文化研究,2013(1):202-207.
[2]羅建華.試論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興起緣由[J].中共合肥市委黨校學報,2017(3):60-64.
[3]高玉.論清末民初報紙白話文運動及其歷史意義[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49-57.
[4]湛瑩瑩.晚清白話文運動與五四文學革命的聯系與區別[J].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7(6):85.
[5]張丹蘋.中國現代語言變革與文學的失語性發展——以五四白話文運動為中心[J].劍南文學(經典閱讀),2013(1):168.
[6]段懷清.通往近代白話文之路:富善在第一次上海傳教士大會上的報告之考察評價[J].山東社會科學,2015(7):87-93.
2019—02—01
王雪琪(1985—),女,河南鹿邑人,鄭州成功財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H0-09
A
1673-4564(2019)02-00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