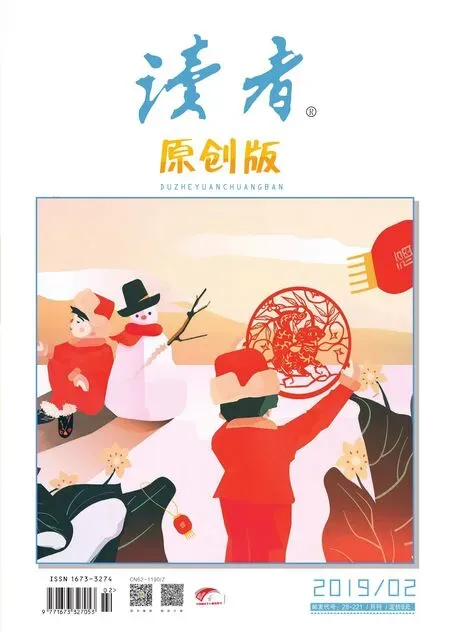菜 園
文|南在南方
程顥有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心地如常,從來不易。萬物若手足,信手寫來,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閑時喜歡看知堂老人的文字,有天晚上臥看他在《瓜豆集》自序里說瓜豆:“我這瓜豆就只是老老實實的瓜豆,如冬瓜、長豇豆之類是也。或者再自大一點稱曰‘杜園瓜豆’,即杜園菜。吾鄉茹三樵著《越言釋》卷上有‘杜園’一條云:‘杜園者兔園也,兔亦作菟,而菟故為徒音,又訛而為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蓏之屬,出自園丁,不經市兒之手,則其價較增,謂之杜園菜,以其土膏露氣真味尚存也……’”
“土膏露氣真味尚存也”,這句平淡的話忽然惹得我不安起來,像是一只貓想要捉住自己的尾巴,分明是自己的,卻捉不住—“杜園菜”也有,只是隔得太遠。這樣想時,不免又嘆氣,是以前有,現在也沒有了,菜園還在,荒在老家。
農家菜園,鮮有常換地方的,比如我家里,那塊菜園一直在那兒,離屋不遠,能接近肥水,至于雞,扎下籬笆就好了。
祖父喜歡興菜園,一年四季都有綠色。就算大雪封山,雪來之前,他用苞谷稈蓋在芫荽上,蓋在菠菜上,菜依然鮮綠。就算不蓋,豌豆苗頂著雪,那一抹嬌滴滴的綠,也是惹眼。
菜園里的祖父是個園藝家,籬笆上一半爬豆角秧,一半是黃瓜秧,南瓜一定是種在地頭,其余的,無非是茄子一行,辣子一行,給小青菜留地方,給蒜留地方。每一樣菜蔬,他讓它在哪兒就在哪兒,看上去疏朗清爽。祖父80多歲時還要去菜園,站不了,他坐在小板凳上;從前的鋤頭也拿不起了,打了一把小號的鋤,像個玩具,他坐在菜園里鋤草,可愛極了。
祖母在灶前灶后忙,偶爾喚我一聲,去菜園摘個黃瓜,去掐點兒蔥……像是一眨眼,我就辦好回來了。那時祖父總要說一句:“可別摘瓜種啊。”瓜種是他選好的,一般都是藤上的頭一個瓜,就像皇上的頭一個娃兒,那是要當太子的。
《笑林》里說:“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踏菜園!’”后來人喜歡用“羊踏菜園”形容生活清苦。不過,那時沒多少葷腥,有個菜園,有些菜蔬可吃,也是極大安慰。
很多年過去了,祖父祖母不在了。時間于我像拱豬,不知不覺把我拱在高處拱到遠處,夠不著一棵菜園里的白菜。
偶爾在書里看見菜園,總要失神。
南朝周颙在山里修佛,衛將軍王儉問他吃啥,他說:“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他何菜好吃,他說:“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這答的,好聽,好看,好吃。早韭、晚菘都在菜園里頭。杜甫念念不忘“夜雨剪春韭”,想來這春韭也是種在菜園里的,不然,那么細的葉子,又下雨,去哪兒剪呢?
種菜用不著快刀斬亂麻,緩緩地,甚至笨笨地,都是趣事。子貢南游湖北,準備回山西,經過陜西漢中,看見一個老頭抱著甕,給菜園澆水,一會兒一趟。可是甕里的水,澆不了多少菜。他好奇啊,問老頭為啥不用桔槔汲水澆呢,現成的啊。老頭說,我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喜歡這樣澆園咧。
這個古老的鄉黨老頭是我喜歡的,這樣的老頭在老家至今還有。
雖然有鐵牛犁地,快過耕牛,他不用,因為鐵牛犁地不曉得深淺,而耕牛拉著唐時流傳至今的曲轅犁,一步一步走過去,翻過的都是熟土;他不肯用除草劑,那些草啊,從古至今都長著,從古至今都是鋤頭在鋤它,可是劈頭蓋臉給它灑農藥,叫它服毒,這是辱沒草咧。
每次聽聞,都想要鋪天蓋地地贊美他,似乎也沒有特別的意義,就是一份古意在。陶淵明寫:“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他回家了,我還在城里掙扎。
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
知堂先生說:“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確說,但我覺得這是頗有意義的,第一可以食貧,第二可以習苦,而實在卻也有清淡的滋味。”
我在陽臺上弄了一個菜園,說是菜園,其實是個直徑不到一米的大塑料盆,里頭填滿了土,放在支架上,工具只有一把孩子玩沙子的鏟子。我在里頭種過苦菊、小蔥、紫蘇,有一年栽了四株朝天椒,最后摘了一籃子紅辣椒,收獲感油然而生。
這不是我想要的菜園,總想著哪一天回老家,如同黃梅戲里唱的“你挑水來我澆園”。菜地在,鋤頭在,水井在,人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