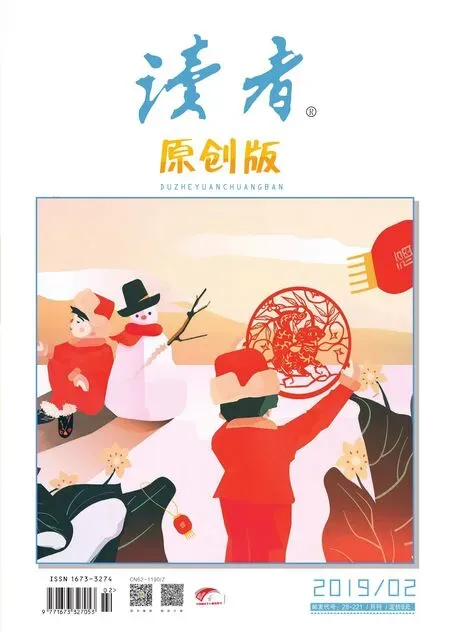向北而行
文|鄭曉蔚
2004年,我從南京某大學畢業,入職當地一家都市報社,擔任體育新聞版面責任編輯。
一
那時候,中國足球還在蠶食2002年韓日世界杯的剩余紅利,“三千足記(足球記者)”是這個行業依然紅火的“人證”。以龔曉躍、張曉舟等人為代表的知名球評人盡情玩弄著漢字拆組游戲,編織出閃亮迷人的金球式長句。
龔曉躍優雅地說:“我們傳播,我們思索。我們無法忍受失真,我們絕不原諒無恥。仰望無益,俯視無情。所謂俯仰無愧天地的基礎,乃是平等地交流、平靜地觀察、平和地論證。”
張曉舟詩意地說:“假如說馬拉多納是大地與河流的私生子,那么梅西就是一個足球工業的試管嬰兒。馬拉多納屬于天外邊,而梅西則把天空變成他的玻璃房子。”
還有“足記”辛辣地說:“沒有血性、沒有觀點還叫評論嗎?從文體而言,那不應該叫‘議論文’,而應該叫‘說明文’。”
我多么想跟他們一樣—說出蕩氣回腸的金句,寫出令人拍案叫好的文本。
二
在南京報館,我每天都妄圖抖摟“一身才華”,在那些嗷嗷待哺的體育版面上盡顯風流。用一位作家的話說就是,“我只是寫”。
當年的報紙行情可不像如今。在智能手機尚未問世的報業暴利期,紙質報刊是公眾接觸一手信息的重要介質。為了便于市民就著早報吃早點,我們編輯成了夜間工作者。
我們是看不見日出的職業群體。在無數個黑夜,我編發了很多“靠譜”的體育新聞,制作了很多“不靠譜”的體育版面,在紙面上盡情揮灑著我的精與血。
每月發餉,我的銀行卡里都會增加6000塊。這對一個出身于小鎮工薪階層的孩子而言,宛若巨款。
工作有了,收入穩定,生活品質隨之發生了改善,我也矯正了將“班尼路”和“真維斯”當名牌的認識。似乎一切都算是落定了。
父母開始為我張羅買房。我仍記得,同事2005年在南京市區購房的均價是4000塊一平方米。
別問我怎么知道的,我閑錢多的時候,曾借錢給同事買房。
三
我安逸地躺在金陵的溫柔鄉里。
直到2006年7月,《新京報》體育部主編、我的好友阿丁跟我說:“如果你有更大的野心,你應該來北京,來這里見世面。”
這一下戳中了我的心事。我渴望去北京“實現夢想”,也渴望去新京報社。畢竟,那是一個“一出生便風華正茂”的新聞夢工廠 。那里,還有我所敬重的報人。
我雖有此念,但又有所踟躕。畢竟對我這個踏入社會僅兩年的年輕人而言,由南京至北京是一次勇敢而折騰的遷徙。作為江蘇人,南京讓我感到踏實,因為跟在老家泰州的父母離得很近。而一旦投奔“皇城根兒”,不僅三個月的試用期意味著前途未卜,未必能夠留下,我和父母之間也很難彼此照應。
一半是舒適區的溫暾,一半是夢想的沸騰,我一時左右為難。
躊躇了兩個多月,直到讀到了杰克·凱魯亞克《在路上》中的金句“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我便不再猶豫。
那一年,我二十有四,我把自己投進了一節開往北京的夜奔綠皮車廂。
我承認,如果那時候高曉松創作出“生活不只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的歌詞,那么我的決定會做得更容易一些。
四
北漂后,阿丁成了我的領導,也成了我的貴人。
他是性情中人,為“誘騙”我來京,經常在電話里向我描繪下夜班后大家消夜拼酒的溫馨場景,結果為我接風當天,他就被我“放倒”了。他對部門兄弟們極盡關照,搭伙吃飯總是搶著埋單,單憑一腔子豪情義氣,把部門各路人馬攏在一塊兒。
耳濡目染,我如今也成了一個熱衷張羅飯局、偷摸去前臺埋單的人。曾有人說,人過了30歲之后,朋友圈就會逐步固化,不再會有擴充。我如今越發品咂出這句話的深味,也就越發珍視純粹的友情,對純粹的飯局格外上心。
熱愛寫小說的阿丁就有一幫固定的飯局搭子—有他的至交、伯樂、前同事、現同事、前領導……而每次組局總會捎上我。
飯局中的諸位都是文化人。一入局中,便似被一個個精神糧倉包圍。

這是一群可以催促你上緊發條不斷進步的良師益友兼酒肉朋友。阿丁在酒桌上熱衷于把話題往文學方向拐帶,大家談論的永遠是卡夫卡、博爾赫斯、余華和王小波,這就逼你必須把這些大部頭全部看完,才能夠在酒桌上奪取話語權。于是,我只得買來《卡夫卡精選集》《博爾赫斯全集》《余華作品集》以及王小波的書,像偷看武功秘籍一般秉燭參詳。阿丁和他的朋友們撒歡說一路,我尾隨買一路。
當我對外界感知的越多,便自知懂得的太少。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從一個生性自負的人,變成了一個懂得自重的人;從一個“始終保持謙卑”的人,變成了一個以“高調做事,低調做人”為信條的人。
感謝貴人的提攜,感謝北京的厚重,感謝飯局的滋養,感謝自己的決定。
阿丁和體育部的兄弟們都“包藏”著出書的野心。他領銜的“橫貫線寫作四人組”最終都成了事兒,陸續有作品集在書店出售。其他部門同事常戲言,《新京報》最有文化的部門是體育部。
我也通過阿丁結識了一眾朋友。但我從未想過,他們會在日后成為我新一輪的命中貴人。
五
落腳“皇城根兒”下三年,歷經新聞制作工序的摔打,我的編輯素養和駕馭文字的功力均大為精進。若非阿丁的舉薦提攜,我的閱世情懷與精神修為恐怕都很難再上一個臺階。
我曾和阿丁發生過一次嚴重的“業務摩擦”。2007年西甲完結,我考慮用“貝克漢姆作別皇馬”收尾,阿丁認為落點走偏,主張專注于“當場最佳球員”。我試著說服領導:“單就本場而言 ,你說得沒錯;但打量整個賽季,大腕貝克漢姆告別足球主流舞臺絕對是最具新聞發酵力的賽末點,這應是共識。”
阿丁一時語塞,轉身走了。而我之所以膽敢當面沖撞領導,是因為深知阿丁是一個好人,一個不屑給下屬穿小鞋的忠厚兄長。
過了幾日,阿丁在飯局上跟我說:“你說得在理。”
受阿丁的熏陶,我不再迷信權威,逐步擁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培育了理性質疑的精神。運用這些工具,我在洞悉真相的過程中獲益頗深,而這是過往20年的正統教育所無法給予我的。
而北京的生活,讓我變得謙卑、自信,內心強大。
六
當時間這把殺豬刀將我劈成“三張”,當我對這里高企的房價感到彷徨,當急切來京看望我的母親說“一來北京腳就皸裂”,當我讀到王朔《致女兒書》中直達內心的一句話,“既然不能永遠在一起,那還不天天在一起嗎”,我便決定—卷鋪蓋回家。
所以說,讀書和交友一樣,都是令人受益匪淺的事情,都可以為你的生活指引方向。
2009年,也就是北漂的第三年,我買了一張回程車票。
臨別前,阿丁張羅了五輪酒局為我餞行,次次含淚稱“真不送了”。然后,阿丁會和朋友們交流近期所看書目。
返遷南京時,我支付了不菲的書籍托運費。
七
我回到了此前的報社。
闊別南京千日,房價不復當年—當年我所中意的市區樓盤已被炒高至均價每平方米兩萬元。有人打趣說我這一趟出去虧了,北京的收入終究沒能跑贏南京的房價。
我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并未覺得后悔。是的,在物質層面,我蝕本了;但于精神世界,我賺翻了。我彌合了思考中的邏輯斷鏈,彌補了教育中的歷史欠賬,讓自己變成了一個精神世界更為豐富、強健的人。
而時任領導由于沒能出去見過世面,精神世界的構建與格局均受局限,自然不能像前領導阿丁一樣,包容異質思維與不同意見。
跟初入社會面對職場不公心生不忿不同,我對眼前所發生的一切有了更為強大的辨析能力,更容易洞悉人心的叵測與人性的幽暗,也更容易做到不以為意與自我消化。
在我看來,報社現實窘境促成了這一切。即便收入銳減,我依然不屑于投機與鉆營。我必須像北京老話兒說的那樣硬氣活著:局氣,有理有面兒—否則對不起北京三年豪義飯局的滋養。
八
昔年酒桌談笑的那幫兄弟之中,有好幾個站上紅利風口,轉行從事了公眾號內容生產。
承蒙幾個老兄弟看得起,我便有了一些打零工賺稿費的去處。是的,我依然“只是寫”,這讓我穿上了保有生活尊嚴的鎧甲。
我想,如果不是因為在北漂中結識了這幫古道熱腸的兄弟,我可能就會枯坐辦公室為稻粱發愁。
北京朋友們的好意還不止于此。其中一位,捧著我的一摞作品進行了前期推薦;而我又捧著我的另一摞作品,順利通過面試,進入一家薪資頗豐的體育傳媒公司。
我發自內心地感恩在北京的那段工作經歷,它始終在滋養我。
或許,生活就是一張定期存折:多年前為實現理想所付出的心血、落下的虧空,多年以后都會找補回來,加息奉還。
每當有實習生就是否北漂來征求我的意見,我都會立即為他推開一扇窗,鼓勵他向北而行。因為,窗外是你的天空,身后便是你的江湖。
現在不明白不打緊,因為遲早有一天,你會如我一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