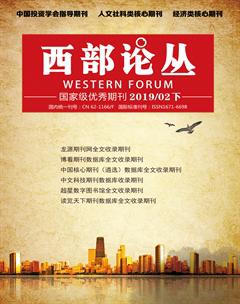藏傳佛教寺院周邊的社區研究
摘 要:本文以拉卜楞寺周邊社區“塔瓦”村為例,以分析“塔瓦”一詞的詞義考究,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一個詞的產生、發展和演變,通過對“塔瓦”一詞的研究,不僅能了解其歷史形態,可以整體把握藏區的村落形式,最終得出假設性結論:藏區寺院與周邊社區互惠互利的關系這一要點,運用到藏區新牧村建設中。
關鍵詞:拉卜楞 社區 塔瓦
“塔瓦”一詞是音譯詞,據《漢藏大辭典》對其解釋,釋為“邊際、界限、盡頭”,“塔瓦”也屬于名詞,一指邊地居民;另一指寺院附近的居民。辭典對“塔瓦”這個詞的解釋落腳點在“人”,對于“人”所處的地理位置的描述,前一種為“邊地”,比較模糊,而后一種解釋比較明確,即寺廟附近。
一、塔瓦作為一類人稱代詞
(一)“塔瓦”被釋義為寺院周圍的赤貧戶或流浪人。解放前,藏族社會的社會階層分為貴族階層、貧民階層、賤民階層,而塔瓦則屬于賤民階層。“藏族的賤民階層有‘約倉(奴戶)、‘過約(終生奴隸)、‘塔瓦(住在寺院周圍的賤民)等。賤民階層的共同特點是,缺少或沒有生產資料,生活貧困,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國民族問題資料檔案集成》中載:“塔瓦指依附在寺院周圍居住的赤貧戶。他們基本上沒有人身自由,是被視為最貧苦、最下等的人。”“赤貧戶無生計者,或出于受懲罰,或出于無奈來到頭人賬房周圍或寺院周圍做苦役,頭人周圍者稱之為‘烏拉赫,寺院周圍的稱之為‘塔瓦。”
(二)諸多文獻中明確解釋“塔瓦”即“奴隸”,且特指寺屬奴隸。《黃南藏族自治州概況》一書中載:“塔瓦是奴隸。”《黃南藏族自治州概況》一書中明確指出:“塔瓦是奴隸。”《同德縣志》記:“塔瓦是寺院周圍的人,實際上是寺院的奴隸。”《河南縣志》記:“每個寺院都有自己的實屬寺院奴隸的寺院‘塔瓦,寺院‘塔瓦及大部分僧眾只有為寺院勞動的義務,沒有享受勞動收獲的權利,一切勞動收獲,只有宗教上層有權處置。”以上資料記載中的“塔瓦”的解釋均偏向于“人”。
(三)在有些文獻中,塔瓦并不屬于純粹的奴隸之意,其境遇和地位并不似奴隸般悲慘,相較于奴隸尚有一定的特權,暫且解釋為“半奴隸”。此處,塔瓦對所依附的寺院履行繁重義務的同時享有一定的權利。“塔爾寺的屬民即一般所說的寺院的寺戶,甘青藏區稱之為塔瓦。這部分農民在清朝時代不給政府納糧支差,僅給塔爾寺交租糧。”
二、塔瓦作為一種地名代稱
其一,有些文獻中記載,塔瓦是一種部落形式,或稱作塔瓦部落,或稱作寺院部落。此類部落一般圍繞在寺院附近,并且供寺院服役。《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指出,“塔瓦,義譯有族、小族、小部落,赤有寺院部落,音譯通常作塔瓦或塔哇。”在陳慶英主編的《中國藏族部落》中,塔瓦被解釋為藏族部落的一種組織形式。書中列出石藏寺塔瓦部落、拉加寺塔瓦部落、剛察寺塔瓦部落等各種情況。以石藏寺塔瓦為例,在“清末明初,當時社會十分動蕩,有一些小部落和牧民為了躲避戰亂和沉重的差稅而就近投奔了當地的石藏寺,以尋求寺院和藏班智達的庇護,藏班智達的藏拉德也由此迅速擴大。由于大量的人口前來投奔,石藏寺的藏拉德和塔瓦部落成為人戶眾多的部落。”[1]
其二,藏族村落或社區往往是在部落的基礎上發展衍變而來。寺院周圍的塔瓦戶聚居,逐漸形成村莊的規模,人們把他們所居住的村莊稱為“塔瓦”。“塔瓦”作為村莊或社區的含義穩定傳承下來,并特指圍繞寺院而形成的村莊。例如,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瓜什則鄉駐地被稱之為塔瓦,其因以村民居住在寺院周圍而得名。以及拉卜楞寺院的上塔瓦村和下塔瓦村都是指居住在寺院周圍的村莊。如今,塔瓦村莊和近鄰寺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寺院政教合一制度被徹底推翻后,“塔瓦”百姓不再在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受寺院的控制,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塔瓦依然受傳統影響,認為自己和寺院有著特殊的關系,尤其在保護寺院和為寺院出勞務之力的時候。特別是在各種宗教活動時期,塔瓦村的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其三,在藏族坊間說“去塔瓦”有“去街上”之意,塔瓦即代表市集。《青海百科大辭典》中記:“塔瓦,青海東部農業區操漢語的藏族群眾方言,是藏族人對商戶在藏區駐地的稱呼。”[2]筆者認為,塔瓦指代集市的含義,是在寺院經濟興起之后。隨著寺院經濟的發展,塔瓦因所處地理位置的優勢,成為貨物流通和經商的場所,吸引了大量的回、漢、蒙人在此定居,長此以往,塔瓦成為集市的代稱。
三、其他解釋
有些文學作品中將塔瓦通俗地解釋為“討口子住的地方”,并且塔瓦隸屬于當地的大寺院。“塔瓦的討口子每月初一、十五能在寺院里領大布施。”[3]塔瓦在此是寺院周圍貧困人聚居的地方,并強調塔瓦百姓能在寺院領到布施。據《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載:拉卜楞曾統轄三十五莊,十八牧族,七千帳篷,人口約兩萬。在拉卜楞附近有十三莊,拉卜楞市集主題是一個寺院大集團及其附屬的上下兩塔瓦。塔瓦意為清道夫住所。[4]此處“清道夫”道出了塔瓦與寺院的密切關系,塔瓦的政治立場是依附于寺院的。
綜合大量文獻記載,塔瓦一詞內涵豐富,且為歷史產物,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時期藏族社會的一種發展情況。 塔瓦或指完全依附于寺院,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資產額奴仆;或指與寺院關系密切,對寺院履行一定的義務并享受一定的權利的屬民;或指自行成為一個小團體,小部落,并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寺院管理體系中的一部分;或指不清凈之地;或指清道夫住所;或指貧苦人、流浪人聚居的地方.
四、塔瓦與寺院的共生關系
民主改革前,拉卜楞寺實行政教合一制度,拉卜楞寺在政治和經濟上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拉卜楞寺在物質方面占有大量資源,塔瓦居民所住的房屋、所耕的農田、所用的交通工具等都是租用寺院的,連他們勞動所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居民的衣食都是寺院間接提供的。所以,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塔瓦居民的發展離不開寺院。然而,正是因為塔瓦居民租用或租種寺院的房屋、農田、牲畜、從而也推動了寺院的經濟發展。
隨著拉卜楞寺名聲遠揚,上、下塔瓦村的住戶逐漸增多,并出現了作為交易市場的“從啦(市場)”清末民初,拉卜楞寺開始開放塔瓦,允許各族商人居住經商,于是內地回、漢商人逐漸入駐拉卜楞寺周邊,頁成為了塔瓦的一份子,塔瓦的規模由此開始擴張。塔瓦從最初的寺屬居民和村莊變為周圍農牧民交易其商品的初級市場。到形成以塔瓦為中心的市場,再到塔瓦的繁榮、規模的不斷擴大,形成以 其為中心的城鎮,到現在的極其繁華,都收到了拉卜楞寺的極大影響。拉卜楞寺的影響,不僅確定了它本身的地位,而且極大地促進了其塔瓦的繁榮和發展。在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被徹底推翻后,它仍然吸引著大量的各族人來此生活。
呂大吉《宗教學通論》中提到的“宗教四要素說”。宗教是一種社會化的客觀存在,它具有宗教觀念、宗教行為、宗教組織制度四個基本要素,這四要素呈現出一定的次序,宗教觀念是核心,宗教情感次之,宗教行為再次之,宗教組織和制度則屬于最外層。[5]從這四個層面來剖析世俗信眾與宗教之間的關系便得到了理論的解答。塔瓦之于寺院,寺院之于塔瓦的重要性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來不來信眾的宗教觀念的形成,宗教情感之深厚,宗教行為之虔誠,拉卜楞寺宗教制度之完備,使得寺院與信眾密不可分。從客觀環境和心理上,宗教滿足了人們內心的孤獨感、恐懼感和無助感,在宗教中尋找到了心靈的港灣。人們的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在共同的宗教觀念和價值觀得到重新整合。[6]盡管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下,宗教活動依然是拉卜楞信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信眾對佛教信崇已然內化于心。
五、塔瓦文化對藏區村落建設的啟示
藏區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一方面,在廣袤的土地上,水草豐富,大部分人以游牧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青藏高原自然條件高寒嚴酷,生產生活環境較為惡劣,游牧的移動性規避了自然風險。另一方面,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河谷和山麓地帶形成農耕區和農牧交錯區,在這些地方,人口集聚,人們從事相對穩定的農業生產活動,并逐漸形成村莊或城鎮。在某種程度上,“定居”、“村莊”、“城鎮”燈飾農業文明的產物。而游牧文明的特點是居無定所,本無村莊可言。但是現在很多游牧區域也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村落,我們發現,這些村落多圍繞寺院而建,人們仍然以游牧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游牧地點相對比較固定,在定居點上人們安居樂業,不再定期舉辦搬遷。牧民在保障了生產勞動的同時,有了固定的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不僅滿足了他們的生產生活需要,更滿足了他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這對于世世代代信仰藏傳佛教的人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寺院或者宗教活動場所是他們日常生活中離不開的地方。這是人們寄托靈魂的地方,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所以,寺院在人們從游牧到定居的生活方式轉變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典型的如拉卜楞塔瓦,對于游牧民定居于村落的建設有著積極的啟示意義。
注釋
[1] 青海社會科學藏學研究所.藏族部落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28
[2] 嚴正德等.青海百科大辭典[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533
[3] 白翼.共波父子[J].紅巖,1957:7
[4] 甘肅省圖書館書目參考部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肅分冊)[M]蘭州:甘肅省圖書館,1984年574
[5] 呂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編[M],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76
[6] 丁莉霞.藏族不同社區僧俗藏傳佛教信仰狀況的特點考察[D].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6.05
參考文獻:
[1] 嚴正德等.青海百科大辭典[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
[2] 白翼.共波父子[J].紅巖,1957
[3] 甘肅省圖書館書目參考部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肅分冊)[M]蘭州:甘肅省圖書館,1984年
[4] 呂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編[M],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
[5] 丁莉霞.藏族不同社區僧俗藏傳佛教信仰狀況的特點考察[D].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6.05
作者簡介:姓名:尕藏卓瑪 ,性別:女(1983-9),籍貫:四川成都,學歷: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學,單位:四川省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