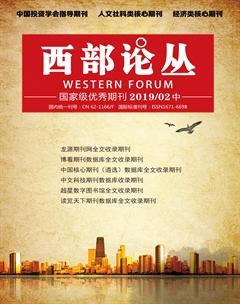改革開放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邢娟紅 康芳民
摘 要:全要素生產率是地區或者是國家技術進步、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標志。而分區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為理解地區差距提供了重要途徑,同時可將各經濟體經濟成長總體情況直接反映出來。本文主要致力于探究改革開放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結合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模型,分析其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情況和原因,并最終指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在未來的增長趨勢。
關鍵詞:政策建議 全要素生產率 改革開放
全要素生產率(TFP)是經濟增長研究領域中的重要概念,又被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主要反映投入要素的綜合產出效率,包含資本、勞動力等。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經濟增長潛力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衡量經濟效率的指標。如果全要素生產率對國家貢獻大,則說明主要憑借技術進步獲得國家整體經濟增長;而如果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小,則說明主要憑借要素投入獲得國家經濟增長的提升[1]。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才會獲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不斷提升要素使用效率;而單純憑借要素投入,則經濟會陷入停滯,邊際要素報酬會遞減。在我國之前的經濟發展中,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有多大,有何種因素會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或者未來會呈現出怎樣的變化趨勢,為了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趨勢進一步分析和探究,上述問題均是需要進行認真而深入的研究。
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模型
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為TFP)主要是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對于資源(人力、物力、財力)開發利用的效率,是總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經濟增長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又被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主要反映投入要素的綜合產出效率,包括有形的生產力要素,比如資本、勞動力、土地等,以及無形的生產力要素,比如技術和管理。
TFP最早是在上世紀50年代,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M·索洛提出的,一個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特性的總量生產函數和增長方程,也稱為索洛殘差,以此形成了現在通常所說的全要素生產率,并習慣性地把它歸結為是由技術進步而帶來的生產率。因其簡單易操作性和科學普遍性,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廣泛采納和應用。
在2015年3月5日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做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第一次提出了“增加研發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是全要素生產率首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2015年12月7日,為制定“十三五”規劃,召開的規劃編制工作國內外專家座談會上,也出現了“企業要通過提高生產率提升效益,中國經濟也要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李克強總理在發改委主持召開的座談上說,“‘十三五規劃編制要推動深入實施創新驅動,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可見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現階段需要我們密切關注的新名詞。
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經濟增長潛力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衡量生產效率的指標。
全要素生產率無法直接從總產量中計算出來,因此只能采取間接的方法。
GY=GA+aGL+bGK
其中:GY是指經濟增長率;GA是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又稱索洛余值,技術進步率);GL是指勞動增加率;GK是指資本增長率;a是指勞動份額;b是指資本份額。
舉例來說,假設在生產中投入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總計100萬元,共生產出來150萬元的總產量。這150萬元的總產量就是由兩個方面的貢獻構成的,其中100萬元是因為一共投入了100萬元的生產要素所帶來的,剩余的50萬元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所做出的貢獻。如果本年度的產量比上年度增長15%,其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長為10%,那么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為5%。
二、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于改革開放之后的增長和原因
(一)全國平均TFP增長率
顯著的階段性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基本表現,在各階段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不盡相同。按照我國30年經濟發展歷程特點,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0年,在這一階段主要是解決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階段,是從1991年到2000年,在這一階段,基本實現了總體小康;第三階段,是從2001年以后,進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為了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長進行更清楚的分析,需對三階段各要素做出的貢獻進行解析。
首先,整體考察改革開放30年來平均TFP增長率。自改革開放到1984年期間穩中有升,而1985-1990年期間表現較差,TFP增長率在1992年達到最高點,之后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增長率再次下降。國營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在改革開放初期均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勞動者的積極性。但是1985-1990年間的增長基本為負,原因是政府實行了緊縮的經濟政策,用于解決經濟過熱的問題,但是由于宏觀調控政策不夠完善,造成市場疲軟,出現通貨緊縮,使得整個經濟增長出現衰退,加之不穩定的國際政治局勢,因此導致1989和1990年的TFP增長為負。我國的TFP增長率在進入到90年代之后表現良好,而最高點是在1992年時,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國在1992年,由于改革開放的領域和范圍逐步擴大,全國人民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經濟聯系加強,對我國TFP的提高非常關鍵[2]。在降低通貨膨脹的同時,宏觀調控也取得顯著成效。我國TFP增長率于1995年后,長時間在較低水平上波動。其主要原因是隨著宏觀經濟發展逐步降溫,1998年出現的通貨緊縮,資本的過度深化加劇勞動力低水平利用,出現經濟生產能力過剩的情形,長期低水平的科學研究和公共教育支出,甚至更加劇了一些社會矛盾,且實質性改革的停滯不前,經濟改革的效益遞減,都影響到TFP增長率的提升。
針對早年間我國TFP增長率的變化情況,將從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改進兩方面進一步分析。我國的TFP增長率在1978-2007年間是0.28%,生產效率的改進是主要來源,累積的TFP增長率為96.9%,技術進步率為40.3%,1978-2007年間生產效率進步率是50.4%。劃分為1978-1990和1990-2007這兩個時間段進行觀察,按照生產率變化的階段性特點,發現兩者的貢獻在不同階段存在主次之分。自改革開放到1990年期間,生產效率的改進非常顯著,全國TFP增長為年均0.1%,平均增長率是4.26%。因我國進行了很多制度層面的改革,生產效率獲得提升,也因此說明之前的要素配置結構,已經不適應技術進步的需要[3]。
但是技術要素占據主導地位主要在1990年后,且高達9.43%的是在1992年,盡管期間表現出一定降低,但是因技術進步的作用,平均技術進步率達到1.12%,使得TFP增長率在1990-2007年達到0.42%。因當時處于改革攻堅階段,效率釋放低于改革初期,改革效益遞減。但是在此期間,由于加快了技術引進的步伐,得益于開放進程、外商直接投資的加速和國際貿易快速發展,促使技術水平大幅提升,更加便利于我國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4],使得技術進步率也有所增長。
(二)分析和比較東、中、西部平均TFP增長率
改革開放以來增長率變化趨勢基本相同。總體上來說,我國東部年平均TFP增長率最高是0.825%;從累積的角度來看,相較于西部的96.3%和中部的69.1%,我國東部110.2%顯著較高;從主要增長TFP的來源看,生產效率改進是最主要原因,其中東部增長0.978%,中部為1.652%,西部是1.56%。盡管三個地區年均技術進步率都是負值,但是技術進步存在很大差異。東部較其他二部存在顯著技術優勢,從累積角度看也如此。主要原因是東部的FDI(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和國際貿易均促進其技術模仿和引進,是較早開放且程度較高的地區,因此技術進步相對較快,且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和人員的投入均較大,促使其技術水平較高,自主創新能力較強[5]。而中西部地區處于內陸,自主創新能力較弱,技術進步率較低,使得在TFP增長中,生產效率的改善成為主要推動因子。
在不同時間段,東、中、西部TFP增長率表現不同變化特點。1978-1990年間西部最高,可達到1.311%,而東部當時是負值,中部較低,因高低差異化的TFP增長率,逐漸縮小了三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差距,中西部地區追趕效應很好體現,國家層次在1978-1990年間經濟總體差異造成這種追趕效應的逐漸縮小[6]。具體分析TFP增長組成部分,發現生產效率的改進為主要原因,但是程度各不相同。其中相較于東部的2.734%和中部的4.698%,西部的5.787%這一年均效率較高。但是在1990-2007年間情形發生轉變,其中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的是中部和西部,但是下降最快的是西部,東部最高是2.074%。TFP增長率的區域差距,促使區域發展差距的擴大,同時造成三區域間水平差距拉大。
四、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在未來的增長趨勢
市場的快速進步,鼓勵對廠房等進行大規模投資以擴大生產。然而,當結束工業第一階段,實物資本偏向的技術進步減少,且生產出較高的TFP增長。高技能工人要求受到更好的教育,且進行更多的R&D;投資[7]。從早期工業化階段之后,這樣的趨勢便可看出。盡管勞動節約和資本緊密型仍然是技術進步的表現 ,但是相對于有形資本,實物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減少,而技術進步偏向無形資本使用。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轉變發展方式,不能夠再像之前一樣繼續憑借廉價的資本和勞動力,應加強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一步提升TFP。
1、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程度
在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層面,我國的對外開放還做的不夠,盡管已經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未來積極地吸引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以及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仍然是對我國經濟效率進行提升的重要途徑[8]。
2、人力資本的積累
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到達經濟發展較高階段會增加。提升人力資本是關鍵一步。我國勞動力數量的增長,在未來會明顯降低,因此增加有效勞動力,并強化教育是非常關鍵的,在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上政府需積極加大力度。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到人力資本積累階段后會更加重要,但是低收入家庭對教育的投資,會受到資本市場不完善的影響,所以通過對低收入家庭教育水平的貼補,可促進經濟更好發展,同時能夠減少差距。
3、科技水平的提高
對于經濟增長來說,科技進步平均每年會貢獻0.3個百分點,不管是在自主創新或者是引進吸收上,均和國外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存在很大的科技進步的空間。我國的經濟在未來的快速增長,會激勵技術的進步和創新,可保證R&D;投入的增加,反過來會促進經濟增長,長此以往形成良性循環[9]。
4、政府工作效率提升,行政體制完善
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政府始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需要致力于提升行政效率,并恰當地履行公共職能,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效率。對于全要素生產率來說,政府消費性支出有很強負面作用,我國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上升,會造成很大浪費。假設我國可在政府行政管理層面可獲得較大改善,則能夠顯著提升生產效率。
5、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建設可促進經濟增長,并使得生產效率提升顯著。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基礎設施的改善在1999-2007年間平均每年是2.5個百分點。我國的基礎設施仍然有很大改善空間,盡管漸趨完善[10]。
6、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將資本從低效率產業轉移到高效率產業;加快促使勞動力轉向非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從而大幅提升勞動生產率。我國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在2009年的時候比重占據38.1%,假設大概為經濟增長貢獻0.5個百分點,則今后每年會降低1個百分點。在我國的制造業資源配置上存在很大扭曲,假設其內部勞動和資本重新優化配置,則我國的TFP水平能夠提升30%-50%,邊際產出達到美國的水平。假設未來能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20%,那么每年TFP平均能夠增加0.9個百分點。
7、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深化
我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經濟體制改革也進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體制當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特別是滯后的要素市場改革,造成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一些新的體制問題在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不斷積累,特別是一些和政府部門關系密切的利益集團由此而形成,在面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上,可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會出現假借權力阻礙市場競爭的現象。經濟中的壟斷權力,是阻礙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我國仍需進一步加強[11]。
結 語
本文以中國省區為研究對象,主要從總量分析角度出發,僅僅從經濟增長的要素上,對中國省區經濟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及對于地區收入差距,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作用。盡管一些可能會產生影響的因素也有所考慮,但是仍然不夠,特別此次研究沒有將把空間、地理、產業因素的影響納入。所以在進一步研究此文的時候,可從上述提到的方面展開進一步且深入化的研究和探討,關于其對我國生產率和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除此之外,要分類出人力資本的教育程度,對不同教育層次的勞動者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研究,也是本文需進一步研究的地方。
參考文獻
[1] 張延群,張瀝元.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潛力分析 ——從歷史和改革的視角[J].中國科技論壇,2017,(11):45-50.
[2] 魏夏韻.商業銀行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與對比——基于三階段DEA-Malmquist指數法[D].西南財經大學,2016.
[3] 張自然,陸明濤.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地區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J].金融評論,2013,5(1):7-31.
[4] 姚瑤.環境規制對中國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D].湖南大學,2014.
[5] 胡曉琳.中國省際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收斂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江西財經大學,2016.
[6] 杜汜敏.全要素生產率視角下我國區域中心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研究[D].河南大學,2013.
[7] 季云翔.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上市銀行效率影響研究——基于企業異質性模型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D].東華大學,2014.
[8] 趙雪陽.基礎設施對浙江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基于浙江縣域數據的分析[D].浙江理工大學,2016.
[9] 萬婷.江蘇漁業全要素生產率評價:基于DEa-Malmquist指數方法的測度與分解[D].南京農業大學,2013.
[10] 許亞杰.進口貿易技術外溢與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D].揚州大學,2012.
[11] 張麗娟.江蘇省外貿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研究——基于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的視角[D].上海師范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