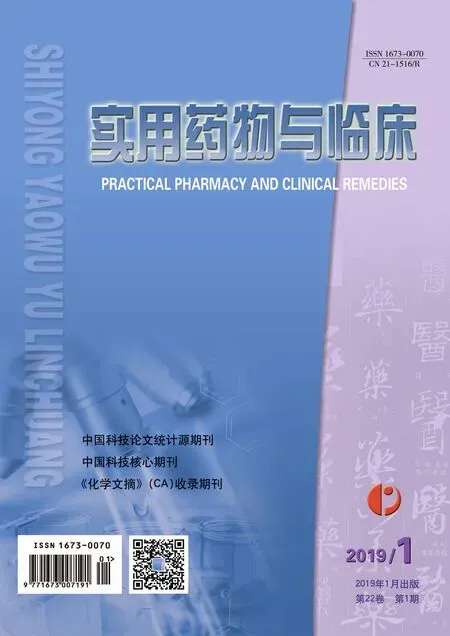某院2017年門急診藥房不合理用藥處方帕累托圖分析
阮毅銘
0 引言
帕累托圖又稱主次分析圖,它能從大量數據中找出主要因素、次要因素并以圖形的方法直觀地表達出來[1]。筆者通過帕累托圖分析法對某院2017年門急診處方進行回顧性分析,確定不合理處方存在的主要因素、次要因素、一般因素,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旨在進一步規范醫院處方用藥,提高處方質量,避免不合理用藥,保障醫療安全。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某院2017年的門急診電子處方。
1.2 處方提取和分析方法 通過醫院管理信息系統(HIS)提取數據,時間為“2017年1-12月”,每月樣本量設置為“1 600”,隨機抽取門急診1 600張,連續抽取12個月,處方總數為19 200張。依據《處方管理辦法》、《新編藥物學》、2010版《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試行)》、藥品說明書及相關疾病的診療指南等資料對抽查的處方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其中不合理用藥處方693張,占抽查處方總數的3.6%,將不合理用藥的類型分為9大類,并按降序排列,計算各不合理用藥類型的構成比和累計構成比,比較影響處方合格率的主要因素、次要因素和一般因素。根據上面的統計數據進行帕累托圖分析。
1.3 帕累托圖繪制方法 采用Excel 2003軟件,以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為橫坐標、不合理用藥處方數為縱坐標做直方圖,以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為橫坐標、不合理用藥處方數累計構成比為縱坐標做折線圖;再以相同的橫坐標作為基準,將直方圖和折線圖拼在一起,繪制成帕累托圖。
2 結果
2.1 不合理用藥處方因素分類 某院2017年不合理用藥處方因素分類見表1,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帕累托圖見圖1。由表1和圖1可知,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A、B、C、D項累計構成比在0%~80%區間,為主要因素;E、F項累計構成比在80%~90%區間,為次要因素;G、F、I項累計構成比在90%~100%區間,為一般因素。

表1 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及因素類型

圖1 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的帕累托圖
注:A.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B藥物選擇不合理;C.用法用量不合理;D.聯合用藥不合理;E.重復用藥;F.中成藥適應證與證型不符;G.無正當理由超說明書用藥;H.處方用藥量超“急3慢7”規定;I.配伍禁忌
2.2 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分析[2]。
2.2.1 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 包括以下3種情況:第一,不合理聯合應用抗菌藥物。例如:闌尾炎處方開具了克林霉素棕櫚酸酯分散片和甲硝唑片。闌尾炎的致病菌多為腸道的G-桿菌和厭氧菌,克林霉素的抗菌譜主要針對G+球菌和厭氧菌,對G-菌無抗菌活性,由于克林霉素與甲硝唑的抗菌譜均覆蓋厭氧菌,故兩者無明顯的聯用指征。
第二,無指征使用抗菌藥物。例如:急性皰疹性咽峽炎處方開具了頭孢呋辛酯片。現病史提示患者咽痛、頭痛1 d,無發熱,其就醫當天也未行任何檢驗和影像學檢查。考慮皰疹性咽峽炎由柯薩奇病毒A組病毒引起,故在無合并細菌感染的前提下,無使用抗菌藥物的指征。
第三,抗菌藥物品種選擇不合理。例如:上感處方開具了頭孢克肟膠囊。約70%~80%的上呼吸道感染由病毒引起。細菌感染可繼發于病毒感染,以溶血性鏈球菌多見,其次為流感嗜血桿菌、肺炎鏈球菌和葡萄球菌等。第2代頭孢類抗生素的抗菌譜足以覆蓋上述細菌,可優先考慮選擇使用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鉀。不推薦使用第3代頭孢作為上感的首選用藥。
2.2.2 藥物選擇不合理 例如:甲狀腺機能減退處方開具了甲巰咪唑片(進口)10 mg po bid。說明書提示,本品為硫脲類抗甲狀腺藥物,用于治療甲狀腺功能亢進癥。抗甲狀腺藥物是導致甲減的主要病因之一,甲減患者使用硫脲類抗甲狀腺藥物會加重患者甲狀腺功能減退,出現代謝降低的相應癥狀,通過反饋效應,可以激活腺垂體,隨后可出現甲狀腺腫的生長。故不建議醫生在明確患者甲減的條件下選擇硫脲類抗甲狀腺藥物。又如:上感處方開具了牛黃清感膠囊。說明書提示,本品功能主治為疏風解表,清熱解毒,用于外感風熱所致的感冒發熱,咳嗽,咽痛。且注意事項明確指出,風寒感冒者不適用本品,其表現為惡寒重,發熱,無汗,頭痛,鼻塞,流清涕,喉癢咳嗽。但該患者證型為風寒,寒則熱之,治法理應祛風散寒。故與本品適應證顯著不符。
2.2.3 用法用量不合理 例如:全身多處皮膚軟組織挫擦傷;處方開具了克林霉素棕櫚酸酯分散片(75 mg)×40片,用法:150 mg po qd。克林霉素屬于時間依賴性抗菌藥物,按照說明書用法,必須每天q12h~q6h才可達到T>MIC。1次/d的用法難以達到有效的血藥濃度,建議醫生參照藥物說明書調整用法用量。
2.2.4 聯合用藥不合理 例如:某診斷為腦出血、高血壓、糖尿病的處方開具了瑞格列奈片(1 mg po tid)和格列吡嗪緩釋片(5 mg po bid)。《中國成人2型糖尿病胰島素促泌劑應用的專家共識(2012年版)》指出,磺脲類促泌劑與格列奈類促泌劑雖然在分子結構和作用靶位上存在不同,但兩者合用的臨床證據尚不充分,一般不推薦兩者聯用。同樣,《磺脲類藥物臨床應用專家共識(2016年版)》也明確指出磺脲類不宜和列奈類藥物聯合使用(A級推薦)。因此,建議醫生調整口服降糖藥的方案。又如:高血壓、腦梗死處方開具了氨氯地平膠囊5 mg po qd;硝苯地平緩釋片(Ⅰ)10 mg po qn。根據《高血壓合理用藥指南(2015版)》,現行高血壓防治指南主張,聯合用藥應避免使用同一類藥物。我國臨床主要推薦以CCB為基礎的優化聯合治療方案,包括:①二氫吡啶類CCB+ARB;②二氫吡啶類CCB+ACEI;③二氫吡啶類CCB+噻嗪類利尿劑;④二氫吡啶類CCB+β受體阻滯劑。氨氯地平膠囊和硝苯地平緩釋片均為長效的鈣通道阻滯劑,沒有足夠的臨床證據證明兩種CCB聯用有協同作用。
2.2.5 重復用藥 例如:胃炎處方開具了枸櫞酸鉍雷尼替丁片和復方鋁酸鉍顆粒。枸櫞酸鉍雷尼替丁片中的枸櫞酸鉍和復方鋁酸鉍顆粒中的鋁酸鉍均能起到胃黏膜保護劑的作用,沒必要同時使用。
2.2.6 中成藥適應證與證型不符 例如:診斷為肺炎患者,證型為肺熱,治療應以清肺熱為主,該患者開具百令膠囊,根據說明書該藥補肺腎,益精氣,用于肺腎兩虛引起的咳嗽、氣喘、咯血、腰背酸痛,慢性支氣管炎、慢性腎功能不全的輔助治療,與該患者證型不符。
2.2.7 無正當理由超說明書用藥 例如:蛔蟲病處方開具了阿苯達唑片(合資)。根據該藥品說明書,本藥禁用于孕婦、哺乳期婦女及2歲以下小兒禁用。而該患者僅為1歲5個月,顯然在禁忌證范圍內。
2.2.8 處方用藥量超“急3慢7”規定 無特殊情況下,門診處方超過7 d用量,急診處方超過3 d用量,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況下需要適當延長處方用量未注明理由。例如:糖尿病、高血壓患者當天拆解2張處方共開具了腦蛋白水解物片×168片(用法:1片 po tid)。根據《處方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十九條規定,處方一般不得超過7 d用量;急診處方一般不得超過3 d用量;對于某些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況,處方用量可適當延長,但醫師應當注明理由。而當天開具的腦蛋白水解物片按照其用法用量處方量長達56 d,嚴重超出我院及社保用藥規定。
2.2.9 配伍禁忌 例如:多張發熱處方中使用了頭孢呋辛鈉針(進口)與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混合靜脈滴注。根據《400種中西藥注射劑臨床配伍禁忌應用檢索表》(沈建平、宗希乙主編,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注明上述兩藥存在配伍禁忌。建議將上述兩藥分開滴注。
3 討論
帕累托圖是按照事件發生頻率大小順序繪制的直方圖,圖形有目標指向明確、突出重點、簡單、直觀的特點,可以較為便捷地找出影響處方合格率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本調查結果顯示,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38.82%)、藥物選擇不合理(14.14%)、用法用量不合理(12.84%)、聯合用藥不合理(10.97%)是造成不合理用藥的主要因素,這4項累計占不合理用藥處方總數的76.77%,其中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在所有不合理用藥處方中占比例最高,達到38.82%,值得重點關注,顯示醫院仍需加大力度進行抗菌藥物的專項治理。藥物選擇不合理、聯合用藥不合理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主要表現在醫生對藥物治療學及抗高血壓藥、抗糖尿病藥等聯合應用的知識掌握得不夠扎實。重復用藥(6.49%)、中成藥適應證與證型不符(4.90%)是造成不合理用藥的次要因素,主要和次要因素累計共占不合理用藥處方總數的88.46%。某院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與其他醫療機構結果有明顯差異[3]。例如,用法用量不合理占不合理用藥處方的12.84%,排在第3位。這與我們在調劑過程中的體驗不同,我們在調劑中發現醫生用法用量錯誤發生的幾率很高,原因是本調查是回顧性分析,用法用量不合理等比較明顯的錯誤大部分都由藥師告知醫生進行更正。可見,處方調劑前審核、干預對保證用藥安全意義重大。
在實際調劑工作中,雖然藥師對醫師處方按規定進行了調配前審核,并對不合理用藥處方進行了干預(對不合理用藥處方,醫師必須修改正確后才能調配發藥),但從醫院2017年門急診處方不合理用藥情況及典型案例回顧性分析和臨床藥學室在每月的處方點評分析中發現,一些處方常存在較突出的不合理用藥問題,藥師調配核對時沒有發現,藥師的處方調配前審核工作有待加強。
處方調劑前審核和干預是保障臨床用藥安全有效的最后環節,體現了藥師在合理用藥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調劑前干預要求藥師在審方過程中能迅速發現問題處方,還要進行仔細的分析,將處方的不合理情況反饋給醫生,在三甲醫院巨大的門診量和處方量工作下,藥師對處方審核時間短,同時缺乏患者相關檢查信息、病歷等資料,醫院也缺乏對調劑藥師在臨床藥學方面審方能力的培養,可能導致部分問題處方出現“漏審”現象。理想狀態下,調配前干預可防患于未然,理論上可保障每一張經過調劑的處方合格,確保每一位患者應用的藥品安全合理有效。目前,大部分醫院根據《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試行)》(2010年)對不合理處方采取每月抽樣點評1次的方式進行事后干預,使醫生和藥師認識到已發生的不合理用藥情況,防止再犯相同的錯誤,對于不合理用藥的監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事后處方點評的結果存在滯后性,對已經取藥甚至用藥的患者來說沒有意義,不能對門急診全部處方進行全面、實時監控。因此,為保證合理用藥,保障醫療安全,采取調配前處方干預逐漸成為醫院門急診開展藥學服務的必然趨勢[4]。
然而,這種模式需要另外安排專職臨床藥師進行處方全審核,單憑未經資格培訓的調劑藥師完成這樣的任務會比較牽強,而且,藥師要做出正確的判斷,通常還需要查閱資料和患者相關檢查信息,導致患者候藥時間較長,在門診量和處方量龐大的醫療機構,較難提高工作效率,可操作性不強,但由于技術的進步和互聯網的發展,開發針對實際情況、有個性化解決方案的不合理處方智能審核系統成為可能,此智能審核系統在醫生開方的過程中即可以及時有效攔截并提示出現的不合理用藥,保證正確合理的處方才能下傳核價和調配,無需再等待藥房的審核反饋,可提高工作效率,減少患者等候的時間,避免藥師因自身臨床用藥知識水平與經驗積累的不足導致的處方把關不嚴[5]。智能審核系統并不能完全代替藥師人工審核,因為智能審核系統的各項處方審核功能需要藥師對不合理用藥的經驗總結進行帕累托圖分析,然后進行人工設定;需要在工作實踐中針對實際情況不斷更新、增加新的功能和增加新的內涵;智能審核系統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藥師的人工審核不可缺少,最后必須由藥師來把關,但智能審核系統可有效減輕藥師的工作負擔和壓力,在調劑和核發藥物環節也能更加專注和準確。當然,不合理用藥處方存在的問題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干預措施的實行等因素而發生變化[6],藥師應定期利用帕累托圖,及時了解不合理用藥情況的變化趨勢。綜上所述,有針對性地加強處方的調配前審核和干預,可及時有效地提高醫院合理用藥水平,保障臨床用藥安全,藥學服務也會更上一個層次。